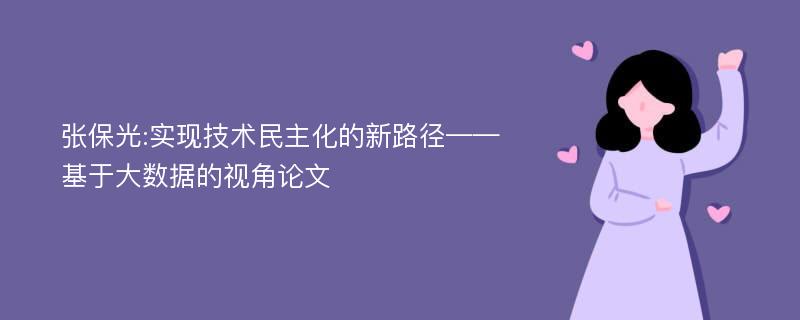
摘要:芬伯格的技术民主化就是要充分肯定公众参与政治的民主意愿,并进一步实现自身利益,但他从局部政治运动出发来实现民主变革这条道路难以满足民主的内在要求。大数据技术的出现为构建一条新的技术民主化道路提供了现实基础。大数据以其大容量、大价值、多样化等特性扩展了技术参与者的利益范围,把技术设计的话语权从单一的中心分离出来以赋权于民,将宏观社会运动和微政治学整合在一起确保了参与者的利益,从而使技术的民主化得以可能。
关键词:大数据,技术民主化,利益,去中心化,微政治学
技术哲学家安德鲁·芬伯格的工具化理论近年来风头正盛,但在此基础上芬伯格对技术民主变革的论证并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事实上,芬伯格带有批判性的工具化理论之最终旨趣就在于实现技术的民主化,进而通过技术变革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民主。芬伯格提出的技术民主化就是要扩大社会成员的个人自由,让他们积极且富有成效地参与到技术设计与技术决策之中,尤其是使弱势群体和社会下层等“外行行动者”也参与其中,以确保其利益诉求得以实现。芬伯格构想了实现技术民主的方案,即用局部政治行动来影响技术设计。但这一渐进式方案不具备可行性,局部政治活动无论是从组织性、影响性、时效性还是成效方面,都无法达到技术民主化这一目标。实际上,芬伯格只是在理论上提出了一种使技术民主化的方向,也就是说,芬伯格关于技术民主化的构想在现实中没有找到可行的方案,因而有必要探寻一种更为合理、可行的路径。
芬伯格认为现代技术本身往往蕴含内在的民主潜能,“这些潜能也许能通过一种更高水平的生产力来实现[1]”。近代以来,技术创新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深刻影响和改变着各种社会关系,立基于我们当前的社会,技术俨然已经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那么,技术的不断发展为技术民主化的实现创造了条件。民主化过程中,我们应尽可能地将现代技术整合为民主的内在要素,使其最大限度地推动民主的发展。目前,大数据技术对当代的技术决策以及设计过程的影响尤其巨大,它“继人力、资本之后成为一种新的非物质生产要素,其作为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支撑科学研究和各类应用服务”[2]。
关于大数据的概念,目前学界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定义。Gartner公司将大数据定义为:“大数据是高容量、高速和多样性的信息资源,这需要成本效益、创新的信息处理形式以增强洞察力和决策能力。[3]”另外,美国国家情报局办公室和IBM、麦肯锡、网易科技等都对大数据做了近似的定性描述。虽然上述对于大数据进行定义的方式、角度以及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其对大数据的内在认识大同小异,即大数据归根结底是一种集信息的收集、保存、维护、共享的数据集。最重要的一点是,大数据的价值并非数据及其规模本身,而是由大数据所反映的“大决策”“大知识”“大问题”等。以此为基础,大数据作为一种高效的资源和工具,将有助于缓解民主理想和民主现实之间的张力,强化技术民主化的趋向。
本文针对机动目标跟踪,基于降维CKF,线性简化CKF [9],采用时变Markov转移概率IMM算法,设计了交互式多模型降维容积卡尔曼滤波算法( IMM-RDCKF),提高了算法的鲁棒性和估计精度。仿真表明,计算量约为IMM-CKF的一半,仅比IMM-EKF增加约30%,目标跟踪精度提升,便于工程应用。尤其是匀速运动速度估计精度提升约27%。这对于预警探测、火力控制、指挥控制等军事应用领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大数据与参与性民主扩大化
芬伯格认为,技术作为知识、设备和资源的文化统一体,其发展轨迹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是人类选择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技术是由人类的选择塑造的,反过来,技术也影响了人类的选择,因此,“人”是技术实践的参与者。所谓“技术变革的民主化”,意味着“赋予那些缺乏财政、文化和政治资本的人们接近技术设计过程的权力”[4],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参与者利益。就此而言,技术民主必然是一种参与性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这种参与分为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两种形式,直接参与指的是在技术的研究实践中亲自进行技术设计,间接参与是指通过公众运动对技术设计或者科技决策施加影响。在大多数情况下,公众对技术的参与不是直接的技术性参与,而是非正式的、间接的价值、意识、意义的参与。
进而,芬伯格指出,民主的前提是公众在参与技术设计的过程中渴求获得更多的责任和权力,但是“今天工业社会中的公民似乎更加盼望‘逃避自由’,而不是扩大自由的范围”[5]。芬伯格认为这是因为公众缺乏参与意识,即“技术使用者/参与者不能识别或维护技术中‘正确的’的利益和变化”[6]。缺乏参与意识正是技术民主化的最大障碍,只有公众在技术生活中恢复其原有的主动性,技术的民主化才能够真正实现。
北塔采用H形结构,全塔包括上塔柱、中塔柱、下塔柱、上中塔柱连接段、中下塔柱连接段上横梁、中横梁、下横梁及塔座。北索塔总高242.308m。塔顶高程255.308m,塔底高程(塔座顶高程)+13.000m。
显然,要使公众主动参与技术设计与技术决策,这需要开启民智。这里的民智指公众能对技术产品、技术知识以及技术专家、科技政策等有一个基本的、清晰的认识,能理性、独立地思考技术问题,同时开放地接受或批判现有的技术观点。公众的主动性参与必须建立在一个对与自身息息相关的技术有正确理解的前提下,每个人要真正意识到技术产品为他们带来的各种有益或有害的影响。如何开启民智,让“人”认识到其在技术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受到时代和技术发展的限制。在技术没有获得长足发展的情况下,芬伯格对此并没有提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法。现代社会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技术的出现及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参与技术发展的主动性。首先,大数据以其海量存储和即时性、多样化、互动性等特点为信息分享提供了便利条件。在这样的情境下,大量的技术信息以及相关的知识可以共有、共享,公众能在海量数据中找到自己需要的技术资源,并且有能力从知识维度和社会维度两个层面理解这些技术的内涵。此外,公众可通过互联网、移动设备等接触到大量新思维,这克服了数据不流通时代获取新信息的局限性,改变着人们的文化认知,扩大了公众的视野。其次,从技术存在的意义而言,大数据使复杂的技术“简单化”。单纯从技术角度看,有些科学技术知识高深晦涩,颇具复杂性,这势必使大众参与和支配技术的能力降低,从而影响到他们的参与热情。但是技术专家的互动式在线答疑为公众开启了一个能够深入了解技术知识的途径,技术专家利用大数据收集并分析公众所提出的问题,随后将这些问题整理成不同的类别,根据不用的用户需求,做出不同程度的解答。这种技术设计专家、决策者、管理者和公众间有效的信息交流机制,使公众不需要深入理解复杂、高深的技术知识,但是能够了解技术存在的意义和作用,这无疑从宏观上拓展了了民众的参与程度。最后,大数据时代“设计工具”的广泛应用增强了公众参与技术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公众借助这种工具对技术设计过程有一个完整的体验。例如,AI(人工智能)使用户通过输入数据的方式设计产品。有了开放的工具与开源的平台,人们可以轻松了解技术设计过程,并在体验的过程中获取灵感,根据自身潜能衍生出更多的创新模式。总之,纵观人类发展史,信息获取的难易程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识。类似于印刷术,大数据极大优化和促进了当代知识和信息的获取和传播,以至于催生了公众对参与技术发展的内在需求。可以说,大数据标志着人类在认识世界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
芬伯格参与并见证了法国五月风暴这场社会革命运动,他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种宏观政治学(关注阶级斗争、社会运动、人类解放等宏观事件的政治学)已不适合当代社会的发展。此外,后现代主义思潮理论家利奥塔、德里达等所主张的微观研究给芬伯格以启迪并促使他对社会现状进行反思。在这过程中,芬伯格发现个人的力量及其所发挥的作用在技术生活中开始凸显。这是因为, “在技术社会,边缘性潜在的是每一个人生存条件的状况。……我们日常生活的技术环境不再像我们在60年代所想象的那样似乎是野蛮的压迫者,而是一种‘软机器’,一种把我们包括在内的松散地组织起来并极其脆弱的结构”[18]。面对社会环境的变迁和人的自主性的恢复,芬伯格逐渐扬弃原有宏观的、大规模的技术暴动而转向微政治学。在芬伯格的视野中,技术微政治学是一种建立在局部知识和行动基础之上的小规模干预的政治学,也是公众抵抗技术霸权的形式,这种“抗议旨在通过用户、顾客或受害者的压力来改变特定的技术或技术系统。这样的鼓动缺乏许多传统意义上的政治运动的机制,它也许没有集中的协调,只有在想要达到的方向上有一种含糊的共识,但它能够超越被实证主义对进步的信仰的霸权所妨碍的技术政治学的早期形式”[19]。这一点已被许多典型例证证明,女权运动、同性恋组织运动、反种族歧视运动等都是成功的局部和微观层次上的政治运动。
如图4所示。将源特征图中p’附近的内容放大,则p’点正好落在了点(x1,y1),(x1+1,y1),(x1+1,y1+1),(x1,y1+1)4个相邻点中间。双线性插值算法就是利用源特征图中(x1,y1),(x1+1,y1),(x1+1,y1+1),(x1,y1+1)这几个整数点的像素值来计算目标特征图中p点的像素值。对应计算公式为公式(1),(2),(3),(4),(5)。
或许,我们应该看看人文主义学者对外行行动者参与科技研究的探讨。值得一提的是,学者海尔格·诺沃特尼(Helga Nowotny)、彼得·斯科特(Peter Scott)和迈克尔·吉本斯(Michael Gibbons)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他们曾提出“集市”(agora)概念来说明科技人员和社会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所谓“‘集市’是一个以开放和民主的形式进行推理和决策的公共空间”[9],在这个空间中,“科学、技术、经济或公共利益之间相互交流和协商”[10],并且参与主体之间的辩论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向。当然,这期间充斥着利益对立和冲突。斯科特等人的“集市”理论确有独到之处,“集市”为行动者提供了更民主的参与方式。但他们的这种理论抽象而晦涩,很难在现实条件下实现。我们只能沿着他们所开辟的思路去探索。对于民众来说,当前的大数据技术为其提供了上述意义上的公共场所,而大数据作为一种工具,是具有可操作性的。民众在这个“集市”中可以畅所欲言,使其利益诉求具体化。
当前,世界格局加快演变,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推动 “一带一路”建设,各国要秉承 “共商、共建、共享”,牢牢抓住发展这个 “最大公约数”,在国际上, “中国欢迎各方搭乘中国发展的 ‘快车’、 ‘便车’,欢迎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参与到合作中来”[1];在国内,各省市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建设,审时度势、抢抓机遇、顺势而为。湖南作为红色资源大省,充分发挥红色文化中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和历史价值,是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客观要求,也是湖南省开放崛起和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的必然需求。
其次,技术设计始终要服务于人,大数据以用户为中心反向追溯,从庞杂的数据背后挖掘、分析用户的行为习惯和爱好,从中发现更符合用户品味的产品和服务,同时结合用户需求有针对性地调整和优化技术设计。在这一过程中,技术设计者及决策者自觉关注了公众的利益。而且,这种虚拟环境实际上模糊了不同人种、阶级、种族或性别之间的区别。大数据作为一个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开放和参与的公共领域减弱了不同群体之间利益的对立与冲突,显然,这种情境下,弱势群体或处于不利境地的人们的利益得以体现。然而,仅仅“激发公众对技术的参与热情并保证其利益的实现并不是技术民主变革的结束,而是社会行动者与技术设计者、决策者之间争取平等权利(或权力)的社会斗争的开始”[11]。技术民主是不同群体之间保持权力平衡或者彼此之间相互制衡的结果。不言而喻,“各种重要的技术决定今天是由政府和商界的少数精英在没有大量公众参与的情况下做出的”[12]。要想实现技术的民主化,这需要变革传统的权力制衡体系。
二、大数据对技术权威的解构
芬伯格的技术微政治学对实现技术民主具有支持作用,这种超越宏观革命的技术微政治学确实激发了下层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积极性。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使技术的民主转化具有了可能性。但芬伯格提出的微政治学也仅仅是作为技术民主化的理论依托,至于如何在具体程序上争取更多的人参与技术设计和民主运动,他没有在理论维度和实践维度上对此进行详细分析。而且,微政治学有其理论上的困境。事实上,小规模的斗争虽然取得成功,但这些行动者仍被社会视为边缘性群体,以至于他们的利益难以为社会所认同。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调动全社会民众的主动性、热情和资源以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最为重要的是,芬伯格忽视了现实的严峻性。在全球市场经济的浪潮中,现代社会虽然在不断调和统治者与普通大众的矛盾,但由于财产权、管理权的不平等分配导致两者之间实质性的不平等依然存在,利益分歧难以化解。更有学者指出,“即使是在微观层面(例如在单个研究项目中),只要研究中政治和经济条件没有得到反映,外行行动者看似平等的参与终将是徒劳的”[20]。由此可见,全球政治、经济框架下局部领域的民主化发展对于整个社会的民主进步微不足道。所以,应以开放的、反思的方式对待芬伯格的微政治学。
首先,大数据提供了更加自由、平等和多样化的平台,这是一个让公众表达意见的公共空间,也是了解民情的重要渠道。民众可以通过文本、音频、视频、传感信号以及点击流等形式自由地表达各自的价值诉求,间接塑造或选择技术产品。特别是社交媒体上的转发、评论、点赞行为是公民表达意见的最直观的方式,只需要一次点击便能透露出自己的意见与态度。这种自发的行为彰显出强大的群体意见,甚至能够成为众意的风向标。更重要的是,这些激进的参与模式超越了传统的地域和政治边界,将全世界受技术影响的人们连结起来,他们可以在同一时空、不同地域对技术问题采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向进行讨论、辩论。在虚拟的世界中,社会联系发生的唯一基础就是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关切。那么,在辩论的过程中,民众的利益诉求会更为清晰。事实上,他们这种行为本身已经形成了一种自发的民主化思潮。
芬伯格对技术民主化的设想具体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微观层面,指的是技术设计上的民主化,即技术自身的民主变革。另一个是宏观层面,指的是以技术为中介的制度的民主化,即在技术行为中外行和专家之间权力分配上的民主化,以此为基础来实现技术机构运作过程的民主化。芬伯格将这种民主化称之为“深层民主化”。“深层民主化”的本质是权力自上而下的转移,在芬伯格的观点中,这种权力是对技术中决定性议程的控制。芬伯格称这种控制为“操作自主性”,他具体解释道,“操作自主性”是指技术“所有者及其代表在关于如何经营业务的自主决策上很自由,不必顾及弱势群体以及周边团体的利益和看法”[15]。“深层民主化”的提出是为了削弱操作自主性,确保公众参与技术设计的权力从而实现其自身利益。
如何实现权力的重新分配呢?芬伯格强调激进的弱势群体中个人对技术的干预能力,他认为这种干预能力的逐渐加强会影响更多的公众参与到技术设计中,以此“促进各种被抑制的知识与计划者和执行者的官方技术知识之间的交流”[16]。虽然公众通过这种局部参与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民意,但并不具有普遍的价值,民意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质疑与挑战。大数据技术这一新兴的舆论工具打破了精英们垄断权力的倾向,破除了旧有的话语垄断机制。
首先,大数据使技术权力“去中心化”。技术专家和普通公众,谁来主导技术设计话语权(表达的权力)的问题一直是技术民主化的核心问题。在信息技术不发达的时代,信息来源、获取信息的方式单一,这直接导致大众获取的信息不全面,掌握信息的程度参差不齐,使他们对于许多领域的专业技术知之甚少,从而不得不依赖或盲从各类专家,这也是技术专家治国论(technocracy)兴起的社会历史根源。大众没有更多选择余地,这在某种隐形层面上天然地弱化了民众行为(发言或参与)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参与热情,这种情况势必造成技术权力的中心化。当前信息数据集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增长,大众接收信息的方式不再单纯依靠大型媒体,不再单一接收主流媒体发出的声音,每个人都可以是信息产生的源头与扩散渠道。这打破了过去依靠技术官僚、权力关系等垄断技术资源的绝对中心话语权格局,实际上这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过程。“去中心化”主要是技术对普通用户的赋权,释放每一个人的潜能,使每个人都有选择发表或听取建议的权利。“去中心化”的理念是“协同共享”,共享的内容不再由权威机构或精英人士提供,个体化的内容逐渐成为主流,技术专家不再是权力的中心。技术知识和信息的共享使技术本身走向平权化,这无疑有助于提升技术的民主化程度,从而推动新型公共领域的建构。
其次,大数据有助于提升民主政府的透明度,这使政府机构信息和个人信息形成对称,继而打破政府与人民之间权力不平衡的局面。很多人认为谷歌和亚马逊等网站是大数据的先驱者,事实上,政府机构才是大规模信息的原始采集者和使用者。政府利用自己的权力优势收集和积累了大量数据,这当中“大部分数据的价值都是潜在的,需要通过创新性的分析来释放。但是,由于政府机构在获取数据中所处的特殊地位,他们在数据使用上往往效率很低”[17]。那么,政府机构所掌握的信息对于民众来说是不透明的。这导致民众所知晓的信息和政府的信息完全不对称。在这种情境下,政府部门可以独自决定技术问题能否在他们的议程上,甚至有些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被搁置,没有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内。毋庸置疑,信息不透明、不对称影响了技术的民主进程。2012年3月,美国政府提出“大数据研究和发展倡议”,发起全球开放政府数据运动,并投资2亿美元促进大数据核心技术研究和应用。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加入这股热潮中。支持者呼吁政府提供大量的无害数据,使这些信息为公众所掌握以利用这些数据进行创新。政府信息网络公开使公民的知情权能以最低成本快速实现。另一方面,数据透明化有利于公众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有效防范行政权力的主观性与随意性,使之客观、公平、公正地对技术及其影响进行判断。政府数据的公开亦使去权化趋势愈加明显,这从反面体现了政府机构权力的弱化,为权力向民众下移提供了切入点。
三、大数据对微政治学的批判
芬伯格受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强调参与者利益是技术民主化进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另一方面,芬伯格对技术权威的解构使民众获得参与权以确保参与者利益的最大化。但以上两个方面只是解决了技术民主转化的必要性问题。但更重要的问题是:技术向民主转化是如何实现的?
正如芬伯格所强调的,推进技术民主的关键因素在于公众对技术设计的参与,但这种参与性民主的实质在于参与者的利益。芬伯格认为,“人一旦卷入到技术网络中,就具有了一些特殊的利益……现存的技术规划常常服务于这些利益”[7]。参与者的利益驱动人们重新构造技术体系。芬伯格提出的所谓“参与者利益”指的并不仅仅是狭隘的经济利益,更多的是指向人们对自身价值、意义、自由等潜能的明确而具体的自我确认。需要说明的是,参与者的利益并不是真正独立的因素,而是要在道德、法律的物质框架下体现在技术设计和技术结构中。
芬伯格将“利益”作为其分析的起点,那么,如何扩大参与者的利益是技术的民主变革亟待解决的问题。芬伯格尝试以“责任文化”为基础寻找推进技术民主的良方。芬伯格“赋予文化强大的向导功能和人们崇高的自我觉悟,他尝试在文化环境中以责任自觉调和霸权意志、公众参与者及技术专家之间的关系,将不同主体的利益糅合于技术代码之中转化为技术设计,确认技术的民主化走向”[8]。但在利益驱动下人性面临严峻考验,责任文化很难对人们从道德上形成强有力的约束力。若想通过这种方式实现技术民主化乃至人的自由与解放,仍面临重重困难。芬伯格要想走出责任文化的乌托邦,需要另辟蹊径。
工业革命以来,技术的专业化随着社会分工加速发展,在这一进程中个人的力量开始逐渐强化。学者萨义德(Edward·W·Said)在《知识分子论》里指出,越专业化,就越受限于狭隘的知识领域。专业化最大的流弊,就是专业化的追求者无可避免地流向权威主义,他们或者被权力所雇佣,或者无条件的接受权威所拥有的特权。技术本质主义者在这种观点上走的更远,他们认为“技术的发展服从自主的和价值中立的逻辑,在这当中以科学知识为基础的技术精英(工程师、城市规划者、物理学家、建筑师等)通过对效率规则以及知识的垄断认识到更多有效、可靠的办法来完成现代社会的目标”[13]。这种技术精英论“把我们禁锢在由专家所营造的世界中,这些专家主张用专业知识将受其影响的外行群体的利益和话语权排除在技术设计范围之外”[14]。芬伯格基于对技术本质主义的批判提出的技术民主化思想是对技术精英、技术权威的解构,以此表明每个人都有权成为技术设计的参与者。
(1)样品采集。通过现场考察评估,在底泥过滤车间采集了4个具有代表性的底泥样品。编号为DN-1~DN-4,每个样品由3~5个子样品混合而成。
综上所述,溶血对多项生化项目检测准确性均带来不良影响,所以医护人员在临床检验过程中应严格执行相关操作予以采血,并做好样本运送和分离工作,减少或避免样本溶血现象发生,进而保证检测结果准确。
用SAS 9.2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定量数据的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或Wilcoxon秩和检验,并描述其例数、均值、标准差等。定性数据的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Fisher精确概率法;若考虑到中心或其他因素的影响,采用CHMχ2检验。时序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组间整体比较检验水准为0.05。
如何打破当前的这种困境从而扩大局部运动的影响呢?芬伯格对此没有做进一步的思考。如今,一个无限生产、分享和应用数据的时代已然开启,大数据以其大容量、大价值、多样化等特性正在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思维和行为方式,它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加快了技术民主化进程。
第一,大数据改变了人类的行为方式,这种改变将传统的宏观政治学和芬伯格所倡导的微政治学融合在一起,从而扩大了局部运动的影响。各种智能工具的推广降低了人们获取和发布信息的门槛,人们可以愈来愈便利、轻松地参与技术活动。将公众的意见、建议等予以量化,以数据的形式呈现出来,公众可以以这些数据为基础一目了然地看到技术及其影响,技术设计与发展总是处于公众的视野之内。技术行为者共同关心的问题驱动他们组成社会性群体,他们为得到社会认可公开在网上进行游行、示威等,甚至这些行动者可以自觉地围绕在少数几个意见领袖周围形成力量、利益的割据。网络数据其实就是社会的缩影,网络上的社会运动实际上是以往斗争形式的延伸。无论何种形式的社会运动在本质意义上殊途同归:为共同利益而斗争。由于大数据分布在全球多个服务器上,以往政治和社会运动的深度和广度远远不能和网上运动相媲美。例如,在大多数境遇下,人们可以透过某事件的影响,将人道主义价值观沉淀于其中,这将促使大部分人以利益相关的姿态来支持行动者的斗争,局部运动的范围和影响迅速扩大。这就说明了宏观的社会斗争不能全然被否定,对于今天的社会变革来说,社会集体、团体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仍然很大,作为社会基础的技术的变革需要宏观社会运动和局部运动的融合。正是这种融合,使以设计主体和价值多元化为主要内容的技术民主化成为可能。
第二,大数据为技术的民主变革打开了普通民主程序的大门,使民主变革的途径趋于多样化。芬伯格指出,政治理论家通常会把民主概念限制到完全应用于国家,但技术网络创造了新的政治主体,例如寻求得到实验药物或临床实验的病人。与传统政治理论相反,“这样的主体公然藐视传统的地域或政治边界”[21],以至于芬伯格认为通过投票等正常程序使民主扩大到技术领域是极其困难的,技术民主化不可能通过投票等方式实现。然而,大数据在技术民主化和普通的民主程序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大数据将不同地域的民众聚集在一起,他们可以通过网上投票支持或反对某项技术设计或决策,政府部门亦可针对关系民生的具体问题,在网络上举行听证会,通过利益主体的诉求与辩论,收集民众的意见。大数据使民众和政府之间有了一个良性的互动。此外,网络参政与问政,立法草案的网络公布和讨论等都有效克服了民主僵化的现状,使公众的意见更容易表达。
四、结语
对技术民主化而言,大数据在推动技术民主化进程的同时,也存在一些无法忽略的症结。
第一,大数据带来的信息纷繁多样,优劣掺杂,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成为民主化发展的障碍。尽管丰富的信息资源使可供大众选择的内容多了,但是选择的成本也随之提高。在这种混杂的拟态环境中,公众难以从直观上进行价值判断和信息取舍,这就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以及物质成本“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当时间成本、物质成本等超出公众所能接受的限度的时候,公众自然会对信息源的权威性和可信度进行考量,这恰恰与技术民主“去中心化”的愿望背道而驰,从而囿于技术民主化的目标。
第二,大数据有可能打破已形成的均衡利益,使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再度陷入困境。尽管大数据让民众可以自由地的表达其观点、态度和倾向,也让民众与政府、机构、专家的互动更为及时和便捷,但大数据不单单赋权于民,也赋权给了政府和技术决策者。实现民主的根本条件是社会各阶层、各群体之间利益和力量的均衡,始终保持彼此之间的制衡和妥协。从实际情况来看,政府及决策者手中有着比普通人更有利的条件,一旦大数据为政府及决策者所垄断,就有可能重新加剧国家政府与人民之间权力的不对称,他们会更加有针对性地操纵民众。那么,此种情况下,民众的利益难以实现,这有悖于芬伯格技术民主化的初衷。
模糊控制、专家控制、神经网络控制、PID控制、自适应控制等是工业机器人运动控制系统的主要方法,为了达到更好的动态性能,最终实现控制要求,一些新的控制方法就出现了。在控制算法方面既要保证一定的鲁棒性,又要满足参数实时变化的要求。
第三,大数据的核心价值便是其预测能力,但基于预测得出结论使人的自由意志成为一个伪命题。技术民主化的目的就是让民众有权对技术方案、技术产品按照自己的愿望做出选择。大数据通过对人类行为的分析做出预测本身“不仅违背自由意志的原则,同时也否认了人们会突然改变选择的可能性(无论可能性有多小)”[22]。技术的民主化必须要为民众保留足够的参与空间。如果人们过度依赖大数据的预测能力,势必会“扭曲人类最本质的东西:理性的思维和自由选择”[23]。
此外,虽然技术民主化在大数据的视域内其内在潜能得以体现,但大数据技术并不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充分条件,技术民主还建基于人文传统和制度约束等种种因素之上。
首先,大数据客观上推动了技术的民主化,但是技术本身不可能直接带来民主,归根结底民主的实现需要运用这些技术并且向往民主的人来完成。倘若技术专家或决策者能自觉地允许受众群体参与设计过程,或者受众群体在欣赏或者使用技术产品的过程中达到一种自洽的氛围,必然能顺利抵达民主的意图。这就需要技术社会积累足够的人文底蕴为技术的民主设计和转化创造良好的氛围。人们自身应努力在当前的技术生活中创造这样的人文环境并保有人文情怀。
其次,技术民主化需要制度和政策的支持。任何技术的发展都不可能一蹴而就,都伴随着好坏两方面的可能性。数据和其他领域的新技术一样,带来了短期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断对我们管理世界的方法提出挑战。这需要政府出台一系列制度和政策以支持和促进技术上的良性发展,防止技术的滥用使民众的利益受到损害。
参考文献:
[1] [4] [5] [7] 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M]. 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5, 8,19,22.
[2] 马帅,李建欣,胡春明.大数据科学与工程的挑战与思考[J].中国计算机学会通讯,2012,9(8):22-30.
[3] Isaac R. Porche, Bradley Wilson, Erin-Elizabeth,Data Flood:Helping the Navy Address the Rising Tide of Sensor Information[M].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2014:2.
[6] [13] [14] [21] Gerald Doppelt. What Sort of Ethics Does Technology Require? [J /OL] The Journal of Ethics 5:155-175, 2001:169,156,156.168.
[8] 刘同舫.技术可选择还是现代性可选择?[J].哲学研究, 2016(7) :110.
[9] [10] [11] [20] Martin Lengwiler. Participatory Approach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istorical Origins and Current Practices in Critical Perspective [J /OL]. Science, Technology&Human Values,2008,33(2): 194,195,196,197.
[12] [16] [18] [19] 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M]. 陆俊,严耕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序言12,序言12,46,43.
[15] Andrew Feenberg. DemocratizingTechnology:Interests,Codes, Rights[ J/OL].The Journal of Ethics 2001(5):186.
[17]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大数据时代[M].盛杨燕,周涛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149.
[22] [23] Kenneth Cukier,Viktor Mayer-Schoenberger. The Rise of Big Data:How It's Changing the Way We Think About the World [J /OL]. Foreign Affairs, 2013,92(3): 38, 38.
AnewwaytorealizethedemocratizationofTechnology——Basedontheperspectiveoflargedata
ZHANG Bao-guang
(CollegeofPhilosophy,NankaiUniversity,Tianjin,China300350)
Abstract: Feeberg's democratization of technology is to fully affirm the democratic will of the public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s and further to realize their own interests. But it is difficult for Feeberg to meet the inherent demands of democracy by local political movements to achieve democratic change. The emergence of big data technology provides a realistic basis for building a new road of technology democratization. Large data, with its large capacity, great value and diversification, expanded the interests of the technical participants, separated the discourse right of technical design from a single center to empower the people, and integrated the macro social movement with the micropolitics to ensure the interests of the participants, thus making the democratization of the technology possible.
Keywords: big data, democratization of technology, interests, decentralization, micro-politics
收稿日期:2018-07-26
基金项目: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当代科学哲学的自然主义进路研究”。
作者简介:张保光(1983-),女,河北省保定市人,南开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科学技术哲学。
中图分类号:F4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2815(2019)01-0020-07
标签:技术论文; 数据论文; 伯格论文; 民主论文; 利益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其他政治理论问题论文; 人权论文; 民权论文; 《科学经济社会》2019年第1期论文;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当代科学哲学的自然主义进路研究”论文; 南开大学哲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