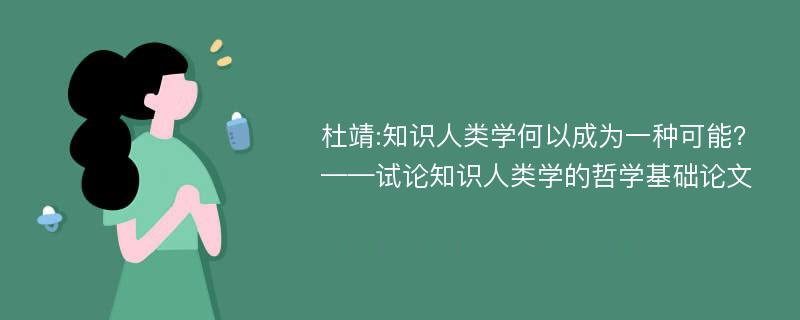
摘 要:探寻知识是怎样被生产或制造出来,是知识人类学的一个重要观察点。目前流行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模式实际上不是关于对象的研究,而是一种在象的研究。在这类研究中,知识主体通过意识、价值等介入或貌似客观地以选择概念和理论参考的形式参与到在象制作之中。本文试图给知识人类学提供一份哲学基础,而在过往的后现代实验民族志反思中和写文化人类学研究表述中总是对哲学的启发遮遮掩掩。其实,后现代人类学基本上是在田野中澄明后现代哲学的想法。
关键词:界隔;在象研究;哲学基础;知识人类学
一、引言
知识人类学习惯于从文化的立场去看待知识运动问题。它大约要处理三个层面的东西。第一个层面是探寻人们如何遵循文化模式去认知世界。即如何知之识之,在此“知识”是个动词。第二个层面是探寻知识是怎样被生产或制造出来。第三个层面是探寻知识如何制造了人这个主体,也制造了这个世界。需要说明,知识人类学虽与思想史有关但不是思想史研究,就像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知识考古学中所声明的那样。[1]本文所关心的是第二个问题,即知识怎样被生产或制造出来,并试图以中国人类学的实践来支持本文的理解。
迄今为止,西方学术界对知识人类学已有相当的推进,特别是在追问“知识是怎样被生产或制造出来”方面。从集体记忆角度讲,承载任何知识的文本,不过是特定人群的集体记忆[2-5],由此探索集体表象对知识生产的价值;就权力(power)支配而论,米歇尔·福柯采用知识考掘学方法研究知识和权力的关系[6-7],而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Said)试图考察东方学背后的西方意识形态谋略[8],二者都是追问不对等的权力如何塑造了知识面貌;受文学解释理论影响,海登·怀特窥探到了知识编纂背后的修辞学问题。[9]到了1980年代,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和乔治·马尔库斯 (George E.Marcus)领军的写文化(Writing Culture)学派出现,开始综合以往视角,试图通过探寻民族志书写背后所隐藏的诗学和政治学来思索不同人群文化图像的呈现问题[10-11],实际上是关于民族志知识的生产问题。
以上是针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思考,而面对自然科学知识生产领域则出现了科学人类学。1962年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讨论了伴随范式转换带来的观察方式的转变与革命等问题。[12]但这项研究只是按照自然科学发展的内在脉络来思考问题,严重忽略了科学之外的社会意志和科学家的个体意志对科学知识生产的影响,因而产生了对科学知识生产的参与性观察之研究。1979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拉图尔(B.Latour)和沃尔佳(S.Woolgar)进入了加利福尼亚一个神经-内分泌实验室里,观察“科学家们的日常生活如何导致了科学‘事实’的建构”,以此思考自然科学研究是否真的像自然科学家们所标榜的那样“理性与客观”。或者说,科学家们所研究的“事实”是否真的就是“客观事实”,还是一种人为及社会建构或选择的“事实”。[13]笔者在研究百年中国体质人类学史时,也试图对此有所追问。[14-16]
然而,上述都是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对知识生产所作的思考,本文则试图看哲学家如何思考这个问题。也就是说,给出知识人类学的一个哲学基础乃是本文的任务。
本文认为,目前流行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实际上是一种在象的研究,因为我们往往通过明确的精神介入或貌似客观地以选择概念及所寄托的词语的形式参与到在象的制作之中。诚如美国作家与哲学家亨利·戴维·梭罗(Henry?David Thoreau)说的:“其实,无论什么书都是第一人称在发言,我们常常把这点忘掉了。”[17]因而,本文定位于分析何谓在象研究,并指出在象研究的广泛存在性。
二、知识主体的意识、价值等进入到在象里面
我们习惯上把研究目标称作“对象”,其实,这一提法是自然主义或科学主义侵入人文社会科学的证据之一。因为科学主义习惯上把研究者和被研究的物象拉开一定距离进行观察和审视,所以便有了“对象”这一说法。在关于对象的研究中,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各自保持着独立和距离:一个要观察,一个被观察,二者相对而存在。或者说,被观察者在我们对面而存在。这种观念主要来自笛卡尔(René Descartes),他的理性主义是近代科学建立的哲学基础。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也指出了当时西方知识界对知识所达成的共识:“一般说来,知识就是客观化,客观化就是把自己以外的必须知道的东西作为一处外在的东西而加以具体化。”[18]
那么,何谓概念呢?李凯尔特把概念(Begriff)定义成“从现实中归纳起来以便用以把握现实的那一切东西的总和”。[32]难道概念所揭示的世界真的能够完全再现吗?答案是:我们不可能把现实如实地纳入概念之中,概念的获得只是一个统计学思路。概念建构研究目标的过程也就是撇弃事物所拥有的、而概念不能容纳某些内涵的过程,它遮蔽了许许多多的异质性。
综上所述,胃镜检查术是消化内科医生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之一,但有一定的风险。在教学过程中,带教老师需全程监管,从“手把手”教学到“放手不放眼”,全面提升教学质量及教学安全,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人文与临床相结合,全面提升研究生的综合能力。当然,在内镜教学过程中还会有新的问题出现,需要不断摸索与总结,积累经验,使内镜教学体系更加完善,培养优秀的内镜医师,推进内镜技术的传承与发展。
从知识人类学角度讲,关于对象的研究,在认识论上犯了二元论错误。认识的主体被悬置在客体之外,却不知认识的主体已经在客体之中了。诚如克罗齐所言:“在我们所已描绘的哲学中,真实界被确认为精神,这种精神不是高悬在世界之上的,也不是徘徊在世界之中的,而是与世界一体的;自然已被表明是这种精神本身的一个阶段和一件产物,因而二元论被它替换了,一切超验论,不论其起源是唯物主义的或神学的,也已被替换了。”[19]克罗齐明确说:“精神之外不存在外在事物。”[20]
事实上,认识一个事物是从我们意识到它的那一刻起开始的,当我们试图捕捉它的时候,人的意识已经参与了那物的创造了。它不会在我们的意识之外而存在。任何拉开认识主体和客体距离的尝试和努力都是徒劳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与其说是研究外在的客观事物,不如说是在研究我们自身,因为认识主体把自身投射进了那物之中。那物就像光学里所讲的虚像,但又不同于物理学里讲的虚像,因为虚像是从视觉出发而获得的,这里说的那物是心意的发明和建构,我们的心是造成这虚像的凸透镜或凹透镜。
这真是出乎我的所料,这么有教育意义的课文,竟然有人不喜欢?我的心里泛起嘀咕,全班热烈的气氛也一下子冷了下来,我看看有点胆怯的几个孩子,决定还是给他们自由发表的空间,鼓励他们说出自己的想法。
沿着这个思路,可以找到前辈人留给我们的许多智慧(以历史知识的生产为例):
德罗伊森(J.G.Droysen)说,我们所获得的并非是自在发生的映像,而是我们观念与我们精神建构的映像,是一个自在的代替品。[21]
克罗齐(Bendetto Croce)也曾多次表达了这一看法。他主张:“没有一件事实在被做出的时候是不通过那永远在行动中萌芽的意识而被知道的。”[22]他又说,历史是人类意志和心智的产物。[23]
H.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强调从现实的全体性角度思考问题,即从作为物体的实在和心灵实在的总和中,把现实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或“一元论的”整体。[24]尽管李凯尔特还把关于文化的研究称作“文化科学”,但却从根本上将二者区分开来。他说:“自然产物是自然而然地由土地里生长出来的东西。文化产物是人们播种之后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根据这一点,自然是那些从自身中成长起来的,‘诞生出来的’和任其自生自长的东西的总和。与自然相对立,文化或者是人们按照预计目的直接生产出来的,或者是虽然已经是现成的,但至少是由于它所固有的价值而为人们特意地保存着的。”[25]李凯尔特主张从价值(wert)的角度考察文化。那么,什么是价值呢?他解释说:“关于价值,我们不能说它们实际上存在着或不存在,而只能说它们是有意义的,还是无意义的。”[26]
而历史哲学家凯斯·詹京斯(Keith Jenkins)在论及历史知识生产时说得更明白:“所有的历史都是历史学家思想的历史。”[27]
科学主义或自然主义的研究从研究的在象中驱逐了作为研究者的个人,抽空了在象中的个人,从而使得在象变成了对象,由此对象变得异常抽象。这是科学认识的暴政所在。
人文社会知识学科所研究“目的物”根本不是纯粹的自然物或自在物,因为我们所研究的是我们的意识所捕捉到的东西,是我们基于特定观念所呈现在意识里的东西。这样一个“目的物”,实际上是我们的观念与传统学术操作中所讨论的 “对象”或自在物相互构建的产物。也可以说是二者互摄或互统的产物。因而,这种合成“目标物”实际上里面既包含着对象也包含着“我”,即研究者自身。我们称之为“在象”。意思是,我们在里边的“对象”。
小说中,基姆多次自问自己是谁——他渴望自由自在,从小便习惯了的生活,但是他所受的教育,以及与人相处时候收到的优厚待遇,又使他常常提醒自己是个“洋大人”。但是,吉卜林在《基姆》中想要传达的并不是反映在自己身上的两种文明的尖锐冲突,而是明确地表达了融合的愿望。小说第八章的篇首诗即为明证:
①九麦2号、②中麦895、③小偃22(CK)、④秦农578、⑤西农223、⑥陕农33、⑦武农6号、⑧凳峰168。
知识的主体由两种方式进入在象:像刚才这一部分所讲的知识的主体有明确的意识介入是第一种;第二种是知识的主体貌似客观,但通过选择概念并推动概念运动以把自己介入到在象里面。下面所讨论的是第二种情形。
三、通过选择概念与词语而进入在象
上述讨论的是认识主体的“意淫”,这一部分讨论知识是概念或参考理论的“意淫”。
我们认识的事物往往不是事物本身,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头脑中事先已有的某个词汇所指示的概念意义。我们在认识事物时首先把它预判为 “某物”。这种预判是一种归类或定位。我们头脑中必定事先储存了一个概念,当外界的事物与这个概念“遭遇”的瞬间,我们便拿了头脑中事先存在的概念来套,看其是否合乎那个概念。如果合乎,我们就说某某某是某某某;如果不合乎头脑中的图景,我们就用另外的事先储存的概念来称谓。
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和现象是与其他事物和现象完全等同,而只是与其他的事物和现象或多或少相类似;而且在每个事物和现象的内部,每个很小的部分又是与任何一个不论在空间和时间方面离得多么远的部分不同的。每个现实之物都表现出一种特殊的、特有的、个别的特征。至少任何人都不能够说,他在现实中曾经看到某种绝对同质的东西。一切都是互不相同的。李凯尔特称这一条为“异质性原理”。[31]
需要说明:目标不是目的,从构词上讲,目标是从视觉出发所捕捉到的物象,而目的则是从心意出发的所指;目标指涉的是表象,目的是为了心的满足。但本文有时也把后者称作“目的物”。
但李凯尔特也犯了错误,他不主张在“概念”和“通过概念作出的阐述”之间划一条原则性界线。一般人认为,这对后世影响极为不好,因为不对“概念”与“通过概念作出的阐述”作出区别,在逻辑学上则违反了“同意反复或语义循环原则”。所以,在学术研究中,当我们选择一些概念以及一些理论,我们通常称作理论参考工具,进行研究时,我们只是照着这些概念和理论规定的方向和范围进行考察,并选择事实。选择的过程是一个建构的过程。正如克罗齐所言:“先收聚事实,然后按照因果关系把它们联系起来。”[33]那么,这样考察出来的结果,不是同意反复或语义循环,又是什么呢?这样的事实还是自然而然的事实吗?但是,这里我们暂不管这种研究好不好,反正我们知道它很流行,我们的目的是要从知识论上研究这类研究,违反不违反同意反复逻辑原则在此不构成一个问题。
有杕之杜,其叶菁菁。 独行睘睘。 岂无他人?不如我同姓。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无兄弟,胡不佽焉?(睘,孤独。)[3]111-112
这样,我们就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认识到:在象的研究根本不是研究显现在我们眼前的事物,而是研究我们所选中的那个概念以及指示这一概念的词语。用头脑中的词语替代了被研究的对象。研究的是概念的制造物。
近几十年来,许多从事少数民族研究的学者往往从“问题”出发去思考边地人群。当我们把“民族”一律当成问题来对待时,民族不出问题、边疆不出问题才怪呢。这种情况同样见之于社会学界。许多从事应用社会学研究的人也往往假设中国社会出问题了,故需要矫正。其实,换个角度看,未必就成为社会问题。媒体同样也会参与社会问题的制造。我的意思是说,许多“问题”也许原本就不是问题,恰恰是我们把它们当成了问题,它最后就真得被夸大成了问题,或问题越来越多。是我们头脑中的概念和意向投射的结果。在象的研究是一种预判式的研究,这种预判制造了真正的社会问题。所以,对在象的研究进行研究,就是要弄清知识界何以要发明问题、怎样发明问题,以及有关的发明的问题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
四、投身对在象研究的研究
首先,完善传统民居的植物文化演化发展体系。对其民居植物在当地的社会发展史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作耦合文化研究,使民居植物的配置有理有据,归纳形成一套较全面的植物文化演化体系,为未来民居的植物设计提供可靠依据。
考虑在水力压裂产生的裂缝中存在N个位置随机的传感器节点{xi∈R2:1≤i≤N},同时存在K个位置已知的锚节点{ai∈R2:1≤k≤K}。令传感器节点i与其邻居节点NHi之间距离为
最近几年来中国大陆有几位重要文化人类学家讨论了对民族志的看法。
当然,也许我们会有途径突破。即,把我们还原到出生状态。但试想:我们刚生下来不就是一个白痴吗?白痴能思考问题吗?因而,胡塞尔现象学是虚伪的,是很难做到的。他就像鲁迅所刻画的那类形象:“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现象学的人类学,听起来是个很好听的名字,似乎仅此而已。 不过,我们还是要感谢现象学,因为它指出了语言概念参与了学术制作的过程。这一点为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所接受并发扬。
海德格尔认为,传统哲学的错误在于:在没有了解存在物究竟怎样在以前就肯定了它们的在(sein,or,being,指存在物的显现和在场。),把在当作是自明的,从不追问在是怎么样在起来或在出来的。他认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把怎样“在起来”这个问题转换成了 “在的本质是什么”,把在和在者(seiende,显示出其存在的现实以及仅仅是观念中的事物、现象)混为一谈,于是哲学进入了一个“在的遗忘时代”。笛卡尔虽然提出了“我思故我在”,可他并没有说明“我在”究竟怎样在。即“我”如何在场、如何到场问题。假如不先阐明我在,也就无法谈到“我思”,因为“我思”以“我在”为前提。与胡塞尔相同,海德格尔认为本质并没有隐藏在现象背后,现象本身就是“本质”。他的现象学方法的目标不是解决主客观关系,获得对于客体的正确认识,获得客观真理,而是把人直接体验到自己的在的种种状态展现出来、揭示出来。真理不是知识,而是人的在本身的展现和澄明,或者说是在的“无遮蔽状态”。发现真理就是展现、澄明“在”。存在先于本质。只有当此在(dasein,即人,追问在者的在的独特的在者,作为在的意义的发问者和追究者的人的存在)存在着时,牛顿定理、矛盾原理以及其他任何真理才是真的。在有此在之前没有真理;在不再有此在之后也不会有真理。此在的思与在者的在是同一的。在在思维中形成语言。语言是在的家。语言就是思中的在,即把思中之在说出来。语言并不象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所坚持的那样是表达知识的工具,也不是逻辑和语法结构,而是现实在的意义的结构。传统哲学的主要错误在于不把思维和语言当作在的直接呈现。[36]
刚才为了行文的方便,我使用了“同一对象”这一词语。其实,这样说是不妥当的。因为当立场和视角变换了的时候,实际上它们所面对的是不同的事物。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说:“处理与以前一样的同一堆资料,但通过给它们一个不同的框架,使它们处于一个新的相互关系系统中了。”[40]这种变换,将使研究者工作于一个不同的世界中。[41]语言人类学家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说,1890年以来,西方科学领域内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尤其是物理学领域。变革的主要原因与其说是发现了新的事实,不如说是发现了新的思考事实的方式。[42]这种现象,可以进一步借用沃尔夫的“语言相对论原则 (linguistic relativity principle)”来说明。即,使用明显不同语法的人,会因其使用的语法不同而有不同的观察行为,对相似的外在观察行为会有不同的评价。因此,作为观察者的他们是不对等的,也势必会产生在某种程度上不同的世界观。[43]
1.2.4.6 含量测定。取不同产地的咖啡生豆和焙炒豆,按“1.2.2”方法制成供试品溶液,按照“1.2.3”色谱条件测定咖啡中绿原酸、葫芦巴碱、D-(-)-奎宁酸、咖啡酸的含量。
其实,我们只是走进了我们预设的意境之中,我们并没有走进历史的现场或者回到历史的田野之中。这不是说,作为一个现代人无法沿着时间隧道倒逆,根本上说,我们走进了一个刚刚拿起来的词语之中了,悬浮在历史之外。因为历史既是理解的前提,又是理解的产物。正如伽达默尔说:“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37]这也类似于伽达默尔说的“视域”一词。“视域其实就是我们活动于其中并且与我们一起活动的东西。视域对于活动的人来说总是变化的。”[38]不是我们掌握语言,而是语言掌握着我们:我们在语言之中成其为人。“相对于某个语言共同体的个体成员来说,语言保持着某种独立的生命。随着这个个人在这种语言中成长起来,语言就把他引入某种特定的世界关系之中”,“世界之所以是世界,只是因为它进入了语言。也只有当世界在语言中获得表达,语言才具有实在的存在”。[39]
通讯服务器的数据流主要从变压器终端流向通讯服务器,相比于手机服务器的协议内容较少。因此本文以手机服务器为例,更好地描述该模块。
五、流动的文化图像
如果不同的研究者怀揣不同的主体意识、价值立场,包括选择了不同的概念和理论参考框架,那么,即便对“同一对象”进行观察,也会呈现不同的图像。这种视角和立场的变换,最终导致人类学家所呈现的文化图像具有一种流动性。
康德提出现象与物自体。他认为,我们永远也无法认识物自体,真正的物自体是不可知的,我们只能迂回地接近。
那么,我们一贯的流行研究何以是一种在象的研究呢?或者说,怎么就流行这一研究或知识的认知模式呢?可以用康德(Immanuel Kant)的合目的性理论来解释。他在《判断力批判》中说“有关一个客体的概念就其同时包含有该客体的现实性的根据而言,就叫作目的。而一物与诸物的那种只有按照目的才有可能的性状的协和一致,就叫作该物的形式的合目的性。”[28]在他看来,正是由于某种意图的实现而产生愉悦,而意图的实现则是把单纯经验规律的多样性归结为原理的统一性。康德说:“一切意图的达成都与快乐的情绪相联结;这意图的达成有一先验表象为其条件,像在这里对于所有反思着的判断力有一个原理一样,快乐的情绪也是被一个先验和对每个人都有效的根据所规定:并且也仅仅是由客体联系到认识机能。”[29]而西方另一美学家鲍桑葵(Bernard Basanque)也指出:“在鉴赏判断中所包含的关系方面,美是一个对象的合目性的形式,只要这个对象能在没有目的观念的情况下知觉到。”[30]从感觉上言,充满意图的学术研究工作也会在内心里产生快乐的体验,因为我们找到了自己,或者说直观到了自己和自己的力量,尽管我们很少人承认并且似乎连想也未曾想过这回事。我们在象的研究旅程,就是自己跟自己见面。它是一种艺术工作,也是一场学术自恋的幽会。具体而言,即我们在做研究时,往往先设定一个工作概念或分析框架,然后从这个概念和分析框架出发去做一番考察,最后在结论部分又加以回拢,这个循环的知识之旅让人在感觉上非常舒服。我们期望了一个目的物,最后就获得了这个目的物。我们还瞒哄自己:这逻辑推理很严密。
实际上,海德格尔关注的是人如何参与了“存在”的制作。这就把笛卡尔理性主义所坚持的“自在物”荡除出研究视野之外,转向了一个语言学的方向,去观察语言如何制造了人和世界(包括知识世界)。后期的海德格尔把语言作为存在主义的承载主体。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继承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观点,并用解释学的观点进一步发展了存在主义。
胡塞尔(Edmund?Husserl)面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还原法”或“加括号法”以摈除概念或词语对研究的影响,从而醉心于“现象”,并认为,现象本身就是本质。[33]但实际上,我们真得能够彻底摆脱概念的影响吗?即使我们在执行研究时不使用任何概念、不参考任何理论分析框架,难道我们就能摈除自小成长过程中接受的一套观察世界的方式吗?能摆脱我们赖以栖身的社会集体意识或集体表象的影响吗?列维-布留尔(Lucien?Lévy-Bruhl)已经广泛地论证了人类认知如何受到集体表象的制约。[34]在他看来,不同的社会拥有不同的文化,因而不同文化中的人们会拥有不同的集体表象,从而有不同的知识模式。
选取2015年1月~2016年12月在泗洪县人民医院住院行冠脉造影患者461例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冠脉造影结果将其分为非冠心病组(对照组)和冠心病组(研究组)。详细记录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244例,女217例,年龄37~88岁,平均年龄(63.57±10.13)岁,有吸烟史176例,并发高血压者252例,合并糖尿病者88例。
朱炳祥自2011年至2015年在 《民族研究》上先后发表了四篇关于民族志问题的讨论,第一篇提出了“主体民族志”这一概念。他认为,民族志客体都是被主体建构出来的,科学民族志只是一个虚假概念,故而所有的民族志都只能是“主体民族志”形式,而以往的民族志存在的重大缺陷是对主体表述的缺失,并提出了“互经验民族志”。[44]第二篇提出了本体论意义上的科学民族志范式和认识论 (知识论)意义上的后现代民族志范式两个先后相续的类型。前者追问的问题是“异文化是什么”,后者追问的是“异文化是怎样被认识的”,两者以1970年代为分界线。[45]在第三篇里,朱炳祥试图通过表述者的“自律性”和“裸呈”等表述技巧,希望走出表述危机。[46]在第四篇里,朱炳祥与刘海涛联合尝试了一次“主体民族志”学术实验。第一主体“即田野对象关于宗教信仰问题讲述的直接呈现”,第二主体“即民族志者解读过程的曲折显示”,第三主体“即评审者审读意见的公开展出”,提出了“三重叙事”的新的民族志文本方式,以回应后现代实验民族志“对话性文本”所面临的“两种危险”和“一种批评”困境。[47]实际上这是一个多方合作,即由被研究者、研究者与评审者共同完成的文本,并完整地呈现于读者面前。
在朱炳祥阐述他的观点期间,蔡华却借助批评格尔茨的“主体”、“主观性”概念的机会,再次倡导科学民族志方法论,认为完全可以客观地呈现研究对象的文化图像。[48]这显然与朱炳祥的主体民族志提法存在了张力。
张小军认为,过去对“民族志”中文译法存在学理上的不足,鉴于在方法论上“文化”缺失(对文化信息的本质理解)以及面对后现代理论挑战的乏力与失语,主张启用“文化志”以取代之。他建议从文化的真实与歧义性,互主体性与“文化的经验”三个方面入手开展“文化志”研究,强调了文化认知的基础上的互为经验之上的“文化的真实”。[49]
从朱炳祥的讨论中,显然可以看见他受到了王铭铭早年所译著的两本书的影响。一本是乔治·E马尔库斯和米开尔·M.J.费切尔所著的《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世代》[50],另一本是《文化格局与人的表述——当代西方人类学思潮的评价》[51]。这两本书对马林诺夫斯基以来所建立的科学民族志发起了批评,其基本精神认为,客观地呈现被研究对象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了呼应朱炳祥的研究,王铭铭着重梳理了20世纪以来民族志的实践形态,即本体论与知识论的交互问题。但在梳理中他其实又不完全支持朱炳祥的见解,即认为,民族志形态史是由两种并存面向之间关系结构的先后两次“反转”构成的。[52]另外,王铭铭又另外撰文主张,民族志最好被理解为一种关乎人文关系的研究。[53]其实,他的研究观念是很实在的。
最后,刘海涛试图给以上各种观点以收官之作:主体民族志重在揭示他者(“被书写者”)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寻求民族志者与他者之间的视界融合及其所依赖的共同概念基础,比照西方人类学学术史语境中的“民族志新本体论回归”而言,具有局部体现和路径补充的重要学术价值。在“后现代实验民族志之后民族志如何前行”这个关乎民族志未来发展方向的核心问题场域中,由主体民族志所集中体现出的包容民族志者、他者以及读者等各种主体诉求在内的“人志”走向,是民族志前行的一种代表性发展方向。[54]虽然他对主体民族志心有倾向,但也未敢轻易否定科学民族志和文化志的实践与表述。
通过以上简要梳理可以看出,诸位作者间并未达成共识,相反,各有主张。这就不免给读者留下一个思索,即究竟什么是民族志?若是把大陆人类学从业人员的观点都发表出来,该不知有多少关于民族志的定义。其实,他们都是囿于自己多年的民族志实践经验以及面对的问题,主观上先设定了一个概念,并由此出发来谈论民族志问题。尽管朱炳祥的互为主体民族志强调被调查者和读者的声音,但这样一个民族志做法仍是他所事先设计的一套思路,一个心念济起的结果。
进一步从人类学思想史来讲,我认为,在本质上言,朱炳祥所提的“主体民族志”概念并没有超出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涉及的“参与性对象化”(participant objectivation)理论范围。“参与性对象化”将认识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55]只不过,朱氏是在布迪厄思想指引下去做一件具体的活儿,但可惜他的诸篇著述皆不曾提及布迪厄这一思想。
在第四篇文章中,朱炳祥强调三者的主体性,但是从他的理论预设出发,恰恰没有实现一个完整的关乎三者的主体性呈现,即他说的“裸呈”。被访谈对象段超生的陈述,仍然被看做一个客体而被作者和审稿人看待,而且是有距离的被审视。其实,段超生的陈述是被研究者朱炳祥的问题意识即提问给型塑出来的,未必就是本来的回答和面目,但作者朱炳祥和刘海涛并没有裸呈段超生当时在回答问题时的内心所想以及主观上的判断与选择,他们只是展示了自己写这篇文章的真实想法与思索过程,因而在执行自己研究信念时不够全面和彻底。既然强调主体性,那么,最终的民族志文本就是三方互动的结果,为什么只有田野调查人和审稿人才署名,而被研究者段超生没有署名?署名者当时是怎么想的?要不要把这个署名权衡过程中展示出来?既然被调查者失去了署名权,为何又可以称为三方“互为主体性民族志”?又,作者朱炳祥所呈现的材料是经过他剪裁、选择的结果,继而进行了第二次再型塑。
电极越多,可以增加分辨率,提高成像质量。由于受空间限制,过多的电极导致又导致电极尺寸的减小,导致两电极间采集的信号微弱,减低了信号的敏感性,同时,过多电极也会大大降低采用速率,导致成像速度慢。因此,本文设计的微流控芯片传感器选用圆形横截面16电极传感器。
另外,上述学者似乎都忘了一个问题,即为谁书写的问题。究竟是为作者自己去写,还是为国家、社会还是其他机构、群体来书写?看上去,朱炳祥的主体民族志考虑到了读者的意见,但那并不是最终的读者,他心目中的“读者”(即评审者)其实仍不过是文本撰述人之一,且这个“读者”是民族志工作者预先设计进来的。过去作者发表作品也会吸收评审者的意见,只是大部分作者并未详细指出评审者的贡献,尤其未展现在正文中。而老实的作者往往在注释或文末对提意见者表达谢意。这其实,已在某种程度上揭明了民族志的互为主体性问题。朱炳祥先生提出了一个主体民族志概念,那么,今后学界就要对他的民族志作品拭目以待,即看他是否都兑现了诺言?又,他的主体民族志观念所生产的民族志,究竟是否为广大读者所接受?显然这也是学界未来所拭目以待的。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民族志作者应该尊重读者,而不是膨胀自己的书写权力。没有形形色色读者的供养,民族志作家将会失业。既然如此,民族志作者得为各类读者服务。
同样的争论也见诸对云南喜洲“民家”或白族的理解之中。最近,青年人类学者马丹丹梳理了自许烺光以来至王铭铭、梁永佳等数十位学者几十年间对这一对象的民族志关照。从她的学术史回顾中,我们似乎看到这样一幅图像,即每一位学者都力图把民家或白族“煮成一锅清汤”,结果到头来合在一起却是“一锅粥”。马丹丹认为,这是由研究者的前提意识与视角主义之间的关系塑造的结果。[56]笔者和杜抱朴最近考察了古人类学和古代居民人种学领域里的研究,发现也存在同样问题,由此造成了东亚现代智人起源的化石人类学与分子人类学之争,和安阳殷墟人骨是多种系学说和单一种系包含几个亚类型学说之间的纷争。[57]
评价结果需要按照隶属度最大原则来判定,由于Vague值是一个区间数,可采用Liu和Wang提出的相对计分函数来作为Vague集隶属度的排序规则,公式如下:考虑弃权部分的影响,式8表示对弃权部分按照的比例进行无限次的细分,直到未知信息不影响对评价对象关于评价等级隶属度的判断。
沃尔夫说,持特定世界观的人对自己说话和思考方式的独特性习焉不察,以为是逻辑的必然,但是对一个圈外人、每一个熟知多种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的人、甚至在一位后来者,一位使用基本类型相同但多少有些差异的语言的科学家看来,却不一定是这样。在这些人看来,被普遍正式接受的理由也许只是些非常独特的“说话方式”。[58]这句话也完全适应于上述诸学者。
就学理而言,主体民族志探索者的探索是值得肯定的,无非是想展示民族志知识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但他们仍然因陷于“民族志”这个框架而纠结。其实,探索到这一步,不如干脆甩开“民族志”这个陷阱,去掉这个称谓,大踏步地迈入知识人类学的探索。
六、结论与讨论
在象,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此在在知识生产过程去呈现自己,而最终生产出的知识产品这个“象”中便分有了此在。而在象研究,就是此在投射、呈现自己的研究。
以上的振动注塑成型技术均只是在注塑成型的局部过程中引入振动力场,华南理工大学瞿金平院士及其团队通过对振动力场引入聚合物加工过程的深入研究,提出全过程脉振注塑成型工艺,即将振动力场引入塑料熔融、塑化、注射和保压全过程[18-21]。瞿金平院士及其团队研制了电磁动态注塑成型装置,如图3所示。该装置利用电磁力产生振动力场,通过特定的机械结构将振动力场叠加到注塑螺杆上,使螺杆在注塑成型过程中获得一个轴向的脉冲作用,从而实现将振动力场引入注塑成型的全过程。
列维-布留尔曾经认为,只有在原始思维那里才有“互渗”现象。比如,他说:“原逻辑思维的集体表象所保证的彼此互渗的实体之间的联系又是多么密切啊!互渗的实质恰恰在于任何两重性都被抹煞,在于主体违反着矛盾律,既是他自己,同时又是与他互渗的那个存在物。”[59]其实,在现代知识学人的思维中同样存在这种现象。
那么,知识人类学的研究,就是研究在象研究,观察此在(认识主体、研究主体、知识主体)如何在知识生产过程或研究过程去呈现自己、投射自己,把自己或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编织进最终知识成果中。
本文讨论了两种何以到达在象的途径。一种是此在把自己的意识、价值等投射进对象中而衍生出了在象,一种是此在借助概念、语词或参考理论框架等进入对象而产生出在象。当然,已有的知识社会学已经很好地讨论了社会集体对知识生产的作用。
此文的目的不是要反对客观的研究,客观研究只是我们的一种审视对象。但本文的信念认为,客观的研究很难做到,所以才提出在象的研究这一说法。因为我们意识到,所谓客观也是一种立场,一种视角,由我们主观所选择,且主观选择在前。我们一向觉得,只有那样才能做到客观,否则就是不客观。这里面显然存了一份主观预设,在我们开启研究或知识生产流程之前,我们的认知先已“在象”了。如果我们能意识到在象问题的存在,然后极力摒除学者的自我投射,也许这篇短文才有些微意义。但这是可能的吗?或者说,当我们发现根本无法摈除自我投射时,那么就老老实实地告诉读者,我们的认知是有选择和立场的,剩下的问题交给读者去判断好了。那时读者也许会听从我们的意见,也许会更换一个视角去观察和思考。我们应该相信读者的智商。但作为读者,也许应该理解上文提及的伽达默尔的智慧,应该不断反问自己所感受的是否是作者所要传达的东西?
另外,在中国本土的现代学术脉络里,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的“层累说”虽主观上是怀疑以往的文献典籍的真实性,但实际上为后世开启了一个智慧,即思考历史知识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问题。[60]而人类学家李安宅在早年的祖尼人研究中也发现了,不同文明背景的人类学家在解释祖尼社会与文化时也会不自觉地附加上自己所身处社会里的一套象征解释体系[61];在他开始“进藏”之前,他同样发现汉地知识分子对藏人存在同样的认知现象。[62]这样的本土智慧同样也应该成为今后我们探索知识人类学的思想营养,尽管它们不在哲学层面上提问题。
最后毫无遮掩地指出,知识人类学这样追问问题的方式本身也是一种在象思考。即庄子感叹的“我何尝不是这样”。知识人类学是一门既拿着枪指着他人,也拿着枪指着自己的学问。它不仅破除他者,也破除自我。即,破除我执。认知是一个图像建立与拆除的双重过程。我们亲手建了它,又亲手拆了它。知识人类学贵在享受其中的乐趣。
参考文献:
[1][6]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马月,译.顾嘉琛,校.北京:生活·读书·知识三联书店,2003:148~173.1~235.
[2]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127.
[3]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313.
[4]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分有限公司,1997:50~51.
[5]杜靖.历史人类学视野中的档案与文献[J].青海民族研究,2010,(1).
[7]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莫为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1~506.
[8]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0:1~454.
[9]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M].陈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1~594.
[10]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E.Marcus.Writing Culture: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M].Berkel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1-266.
[11][50]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M].王铭铭,蓝达居,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1~229.
[12][41]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版)[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1~176.94~113.
[13]B.Latour,S.Woolgar.Laboratory Life: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M].London:Sage,1979:240.
[14]杜靖.中国体质人类学史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1~334.
[15]杜靖.实践的科学人类学: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的新路径——以中国体质人类学史研究为例[J].青海民族研究,2014,(1).
[16]杜靖.体质、文化与历史——中国现代体质人类学研究中的观念问题[A]//席焕久,刘武,陈昭主编.21世纪中国人类学的发展[C].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251~266.
[17]亨利·戴维·梭罗.瓦尔登湖[M].徐迟,译.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
[18][35][59]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M].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450.1~452.450.
[19][20][22][23][33]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M].道格拉斯·安斯利,英译.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50.9.37.71.47.
[21]贝内德托·克罗齐.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M].田时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222.
[24][25][26][31][32]H.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M].涂纪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4.20.21.31.35.
[27]凯斯·詹京斯.历史的再思考[M].贾士衡,译.台北:麦田出版社,159.
[28]康德.判断力批判[M].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5.
[29]刘彦顺.论后现代美学对现代美学的“身体”拓展——从康德美学的身体缺失谈起[J].文艺争鸣,2008,(5).
[30]鲍桑葵.美学史[M].张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343.
[34]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M].舒曼,编.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73~186.
[36]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M].陈嘉映,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3~265.
[37][38]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册)[M].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384~385.390.
[39]Hans-Georg Gadamer.Truth and Method(Second,Revised Edition[M].Translation revised by Joel Weinsheimer and Donald G.Marshall).London.New York: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Press,2004:401.
[40]Herbert Butterfield.The Origins of Moderns Science,1300-1800[M].Lodon:?G.Bell Google Scholar,1949:107.
[42][43][58]杰杰明·李·沃尔夫.论语言、思维和现实——沃尔夫文集[M].高一虹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234.235~236.236.
[44]朱炳祥.反思与重构:论“主体民族志”[J].民族研究,2011,(3).
[45]朱炳祥.再论“主体民族志”:民族范式的转换及其“自明性基础”的探求[M].民族研究,2013,(3).
[46]朱炳祥.三论“主体民族志”:走出“表述的危机”[J].民族研究,2014,(2).
[47]朱炳祥,刘海涛.“三重叙事”的“主体民族志”微型实验——一个白族人宗教信仰的“裸呈”及其解读和反思[M].民族研究,2015,(1).
[48]蔡华.当代民族志方法论:对J·克利福德质疑民族志可行性的质疑[J].民族研究,2014,(3).
[49]张小军,木哈塔尔·阿皮孜.走向“文化志”的人类学:传统“民族志”概念反思[J].民族研究,2014,(4).
[51]王铭铭.文化格局与人的表述[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130~164.
[52]王铭铭.当代民族志形态的形成:从知识论的转向到新本体论的回归[J].民族研究,2015,(3).
[53]王铭铭.民族志:一种广义人文关系学的研究[J].学术研究,2015,(3).
[54]刘海涛.主体民族志与当代民族志走向[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4).
[55]皮埃尔·布迪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引导[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99.283..
[56]马丹丹.模棱两可与理解差异——喜洲的文本及回访文本阐释[M].青海民族研究,2018,(3).
[57]杜靖,杜抱朴.作为元认知世系学观念在体质人类学研究中的呈现:一项知识人类学洞察[M].思想战线,2018,(6).
[60]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A]//顾颉刚.古史辨自序(上册)[C].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2.
[61][62]陈波.李安宅与华西学派人类学[M].成都:巴蜀出版社,2010:32~59.149~185.
How Knowledge Anthropology Become a Possibility?
DU Jing
Abstract:Exploring that knowledge is how to be produced or made,is an important observe point of knowledge anthropology.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mod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the present is not really a kind of objective research,but a study on dasein into object.In the study,with a certain consciousness and value standpoint,or seemingly objectively selecting some concept and theoretical references,Cognitive subject project themselves into the making of"dasein into object".There is the study on"dasein into object"in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in our country.The paper try to provide the theory base of philosophical theory for knowledge anthropology,but postmodern experimental ethnography and Writing Culture school always Don't want to mention it.In fact,the postmodern anthropology basically being the postmodern philosophy in the field work.
Key words:The Study on Dasein into Object; The Base of Philosophical Theory;Knowledge Anthropology.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9)01-0098-07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冷门绝学)《百年中国体质人类学史》(批准号:2018VJX056)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8-11-09
作者简介:杜 靖(1966-),男,山东临沂人,青岛大学法学院教授 文化人类学博士 体质人类学(古人类学)博士后,青岛大学中国法律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汉人社会、科学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和中国人类学史研究。
[责任编辑 骆桂花]
[责任校对 胡成霞]
标签:民族论文; 人类学论文; 知识论文; 主体论文; 概念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青海民族研究》2019年第1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冷门绝学)《百年中国体质人类学史》(2018VJX056)论文; 青岛大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