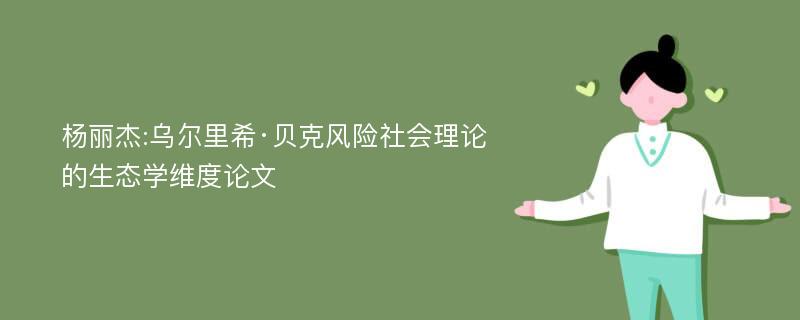
摘 要:风险社会理论的形成有其存在的历史沃土与现实土壤。工业社会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以阶级和社会问题为主的第一阶段与以生态和环境问题为重点的第二阶段这两个不同阶段,表明贝克风险社会形成的生态风险渊源。森林消失、人口膨胀、温室效应、臭氧层损耗、核辐射、核反应堆和化学灾难事故、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导致风险分配逻辑取代财富分配逻辑,共性的需求为共性的焦虑所取代,而对于共同面对的问题,形成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即任何事情都没有任何一个个体或机构对其负责等表明风险社会蕴含生态风险危害。反思性现代化理论和世界主义构想等风险社会解决方案的生态学维度对于化解严峻风险挑战虽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仍具有深度借鉴价值。
关键词: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生态风险;风险分配逻辑;反思性现代化;世界主义构想
风险社会的突出时代特征之一,是表现为生态风险。为此,本文旨在探讨贝克风险社会形成的生态风险渊源,风险社会蕴含的生态风险危害,风险社会解决的生态方案等,认为贝克风险社会理论虽具有一定局限性,但是对当代社会发展仍具有深度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风险社会形成的生态风险渊源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1944—2015)1986 年提出“风险社会”(Risk society)概念和理论。任何一种思想和理论的产生都有其存在发生的现实土壤,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的形成也不例外。而风险社会理论的形成植根于中世纪德国沃土,又因全球化趋势而发展起来,在明确历史脉络里可以审视到现实主义力量,在这段历史时期里,工业社会的发展演变经历以阶级和社会问题为主的第一阶段和以生态问题为重点的第二阶段这两个不同的阶段[1]30。根据贝克对于19世纪人们生产活动生态环境的描述:“掉到泰晤士河里的水手并不是溺水而死,而是因吸进这条伦敦的下水道上恶臭和有毒的水汽窒息而死的。”[2]18贝克提出,至少是工业社会产生的时期,地球上所有物质都有意识到死亡危险的能力,“人类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各种社会形态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是一种风险社会。”[3]26其生态渊源主要包括全球化、科学技术滥用和工业现代性深层次制度危机等相关层面。
从图2可看出,谷索的就位对吊索索力影响很小;脊索就位对不同索的索力影响不同;膜的安装将提高吊索的索力。
(一)全球化时代带来的生态风险
贝克认为,风险社会包括生态危机、全球经济危机和“9·11”事件后跨国恐怖主义网络风险。这三个层面分别遵从导致风险冲突的不同逻辑,拥有各自专属风险范围[4]72。虽说并不是所有人在二战结束后都感到饥饿,但是污染总是民主的,例如核辐射对待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态度,即使是总裁的自来水龙头中的自来水也含有地下水中的硝酸盐成分。“让我们把事情简化为一个未经提炼的公认的公式:饥饿是阶级的。即使在二战刚结束时,也不是每个人都挨饿。但在核污染面前是人人平等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是‘民主’的。”[1]81全球风险社区由全球威胁发展演变而来,并且它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历史产物[1]52。在19世纪与20世纪上半叶时期,与工业生产相联系的职业风险比较而言,对动植物和人类生命难以抗拒的现代性风险,已然超越民族国家的界线,并整体呈现全球化的趋势[2]7。在全球风险社会语境下,直接受到风险影响的团体机构开始抵制来自诸如化工厂、核电站以及废料垃圾焚化场和生物技术研究所和某些技术工厂的恶劣破坏[5]37。贝克将生态剥夺与现代化风险的认知勾连了起来。
风险不仅具有全球性,也具有潜在性,原先的潜在风险正在日趋凸显,人们越来越切身感受到风险对人类自身的冲击和危害,从感官上体验到这些刺激因素。贝克列举江河湖海污染、森林资源流失、酸雨对于建筑物和文物古迹遗址的腐蚀,特别是核反应堆事故、化学物质灾难,加之现代传媒业发达,食品安全等现代风险问题严重影响着人们生产生活,有毒食物的清单上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我们所熟悉的名称[2]64。
(二)科学技术的滥用带来的生态风险
科技的发展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其消极影响是由于科技滥用,会给整个人类造成灾难[6]。当代“科技全球性的世界已然形成全球风险世界”[7]。科技滥用成为风险社会产生的主要成因。因为我们面临的风险与科技应用有着密切联系,人类社会面临的诸多危机和困境绝大部分根源于现代技术。科学成果应用于实际生产生活当中,科技因素被卷入风险状况的起源和深化过程[2]200。人类的活动已经不可避免地污染了生态环境,破坏了大自然的生态平衡。贝克声称:“‘最安全的’东西最终成为不可测量的;核弹与核能以及其所有威胁超越了所有的概念和想象力。”[2]219-220
(2) 小数乘法的意义是在整数乘法的意义、小数的意义、分数的初步认识(包括求一个数几分之几的应用题)的基础上进行教学的.小数乘法的意义比整数乘法的意义有了进一步的扩展.小数乘以整数包含两种情况:第一种理解与整数乘法的意义相同,第二种表示为求一个数的十分之几,百分之几……是整数乘法意义上的扩展.小数乘以小数,则直接表示为表示为求一个数的十分之几、百分之几……小数乘法的计算法则和整数乘法的计算法则相似,不同的是要在最终的结果里确定小数点的位置.应注意,运用乘法运算律释义小数乘法的意义及小数乘法的计算法则,有助于学生对知识点的深入理解.
贝克认为,在世界风险社会语境下,科技不当使用带来不良后果,即科学化风险,将其归因于之前的科学体系存在的技术缺陷和发展程度的不完善[2]195-196。 也就是说,风险微积分学被生态大灾难,如核能危害、化学危险及转基因技术威胁等逐渐蚕食消减了。其一,人类对全球性风险问题的关注度逐渐增长,而这种风险则是无法挽救的和不受限制的;其二,不论是规避风险还是事后减轻风险造成的危害,如果生态大灾难的毁坏程度过于严重的话,也就不存在事先规避和事后减轻的状况了,并且有些状况的结果检测是根本无法进行的;其三,由于风险是不分民族国家的界线的,超越了时空的局限,所以说它的影响是深远的[1]72。全球化具有极度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是其对当今世界重要影响之一。在当今时代,现代风险表现出一种全球化趋势,世界面临风险迅速波及到其他国家乃至整个世界,贝克称此为中世纪穷人的传染病,世界富裕社区也难以幸免[2]49。如当今比较热点的食品安全问题,特别是转基因食品问题,逐渐成为全球性的事务,成为公众比较关注的关乎自身健康的事情,人们对于转基因食品概念知之甚少,这种未知领域更让公众感到害怕和恐慌[1]139。再如既具有物理性又具有社会易爆炸性的核能危机与生化危机随时对人类生存产生威胁,因为它们具有潜在性。在使用核能之前,管理组织都会向公众发出安全声明,但实际上他们无法真正为自己的安全承诺负责到底,他们通常在灾难发生后,很难作出为公众所信服的解释。他们无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无法承担之前所承诺的事项和责任,更无颜面对公众的质疑和责难。有两点需要强调:一是这些管理机构迫于长期压力,通过采取行动,使得原本较为安全的事务更加安全;二是另一种导致无效安全声明情形是人们对于风险结果的大量关注,导致对于风险事故过分担心和怀疑,人们也就不会在意任何人和任何机构作出的安全声明,而这种安全声明也就失去意义了[1]76。贝克认为,人们感性情愫难以从心里接受哪怕微小的来自核辐射、转基因食品和化学废料污染所造成的危险,因为这些威胁完全在人的知识能力可控范围之外,未知的力量是最可怕的,也最容易引起恐慌,关键这些风险是威胁人类生命的,使得人们的生活变得不安全[1]74。
不仅现代化具有反思性,科技不当使用也具有反思性。贝克认为:“科学文明进入了一个它不再只是去科学地认识自然、人和社会,而是去认识它自己、它的产物、影响和错误的阶段。科学不再与从预先存在的依赖中‘解放’相联系,而是与它们自己产生的错误和风险的界定和分配相联系。”[2]194-195贝克指出:“一便士大小的铅砷微粒飘落在城镇,氟化物蒸汽把树叶熏焦,蚀刻玻璃,致使砖块瓦解为碎片。居民们遭受皮肤起疹、呕吐和头痛的痛苦。所有这一切从哪里来的是明摆着的。白色烟尘明显是从那个工厂的烟囱冒出来的。”[1]73贝克认识到有毒废料来源于化学工业,而对于有毒废料应如何处理?一般解决方法是倾倒废料,致使有毒化学废料演变成一个地下水污染问题,然后化学工业又可通过制造净化饮用水制剂来获得更多利益和财富,这里包含一个多米诺骨牌效应,接着如若人们喝了含有化学净化剂的水,因为某些化学物质的存在会影响大众身体健康,还需要医用药品登场,去解救或者延缓源头所带来的“潜在的副作用”[2]221。 这种潜在负面影响具有全球性,生态环境破坏、食品不安全、含毒消费品等屡见不鲜的消息接踵而至,或更有甚者核能、有毒化学品、反应堆事故等。现代化风险的生产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地球越来越不适合人类居住。
贝克指出:“系统而言,从社会演化史的角度来看,或早或晚,在现代化的连续进程中,‘财富—分配’社会的社会问题和冲突会开始和‘风险—分配’社会的相应因素结合起来。”[2]17风险社会中存在不平等因素可以加深阶级社会不平等,而阶级社会不平等现象加速风险社会不平等因素的产生演变,为风险生产提供坚固的防护墙和正当理由的是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2]50。财富是人们可以通过感官切实感受到的实体存在,而风险有时是潜在的,它具有一定的非现实性。从某种意义上,风险既具有现实性也具有非现实性。一是许多已发生危险和破坏已经摆在人们的眼前,如温室效应、臭氧层损耗、核辐射、核反应堆和化学灾难事故等;二是风险具有潜在性,有些风险不会马上出现,但它们已然在母体里孕育并伺机待发,这也是风险的可怕之处。如此看来,某些风险一旦爆发就会难以收场,不但事先是无法规避的,事后造成损失也是无法挽回的,无法采取任何措施去处理和解决的,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毁灭是巨大的,对人类生命安全的威胁是难以估量的[2]35。 “因而,风险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区别不仅与财富生产和风险生产的生产和分配‘逻辑’间的区别相一致,而且源于以下事实:首要的关系被颠倒了。工业社会的概念假定了‘财富逻辑’的主宰地位,并且断言了风险分配同它的相容性,而风险社会的概念则断言了风险分配和财富分配的不相容性以及二者的‘逻辑’冲突。”[2]188贝克认为,“风险生产和分配的‘逻辑’比照着财富分配的‘逻辑’而发展起来”[2]7,现代化风险的威胁具有超国家性,不再局限于具体个别民族国家,突破传统界线并具有全球化发展演变的趋势。现代化风险并不懂得国界,不带有阶级烙印,是不具有识别富裕和贫穷能力的、非阶级化的全球性危险。
在当前风险全球化时代,科技已卷入风险起源和深化过程,由于科学在认识和实践两个层面上的不确定性,可能给人们带来风险[8]。危险已将科学逻辑引入无所适从境地中,如对于核、化学和遗传试验而言,科学正盲目徘徊在威胁边界。人类不能等待安全问题出现后才对安全加以声明,而在问题出现前就有肯定把握,就可作出有力安全承诺,正是由于安全承诺失效,工程师们才不断增加作出承诺次数,但是这些承诺一次次被现实打破,工程师们的权威也随着承诺次数增加而呈现递减状态。而“公众对专家的信任直接影响公众对风险治理的评价和风险决策。”[9]
(三)生态问题是现代性深层次制度危机
“工业社会的社会制度已经遭遇了由有关这个星球所有生命的决策制定导致的史无前例的破坏的可能性。”[1]71风险社会是现代性变异产物,风险概念与反思性现代化概念相联系,特别在政治上二者是反思性的[2]19。风险社会作为社会理论和文化诊断类型的现代性的一段时期[5]10,伴随着全球性危机,生态风险逐渐在工业化社会道路上占据主导地位,随着环境问题尖锐化,生态在总体上呈现恶化趋势,表现为温室效应明显、土地退化加剧、林草植被破坏严重,生物多样性锐减以及自然灾害频仍等。森林消失是经过数个世纪演变的,将森林毁坏后改种农田,为了生产生活滥砍滥伐,将森林破坏殆尽,导致气候不良变化。森林逐渐消失了,且森林消失具有全球性,生动诠释工业化带给自然的负面影响。贝克以森林覆盖率很高的挪威和瑞典为例,提出即使这两个国家本身没有重工业,但它们也难以逃脱工业化带来污染的影响[2]18。“反思的现代化”意味着要直面在工业社会的制度中不能得到纠正和解决风险社会的后果[1]97-98。
工业社会中风险也与贫穷有一定相关性,高度发达工业化国家为既享受工业化带来的利益和财富,又拥有良好生活环境,便自私地将其污染严重的工业产业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不发达的偏远角落’里的车站最受欢迎。”[2]45比起因为化学物质而中毒死亡威胁,因饥饿死亡的威胁更引人注目,更令人可怕,更会引起公众恐慌,饥饿死亡论据说服化学物质中毒死亡论据从而占上风。因为人们要吃饭要解决基本生存问题,认为只有广泛使用化学物质,消灭虫害和腐烂,提高土地产量,才能获得所需基本口粮。那些低收入的国家,也可以通过使用化学肥料来提高粮食产量,拥有充足粮食储备,才能在国际政治经济上获得相应独立性,才能少受制于其他发达国家[2]46。公众对于风险压力的反应是模糊的,风险意识淡漠或有时迫于生活需要而无法选择,比如当下热议的转基因食品等,特别是在工业生产中心附近居住的低收入群体,他们直接并长期接触生活环境中各种污染源,由于迫于生存压力,他们只能选择忍受这种糟糕的空气和生活环境[2]37。在贝克看来,高度工业化带来的全球生态危机源于工业生产产生的负面影响,生态危机不仅流于环境问题表层,它在本质上是在工业社会中一个深刻制度性危机[5]12。风险社会是现代社会的其中一个发展阶段,它的出现是工业社会逐渐遭到淘汰的另一面[5]9。发达国家高度工业化给全球带来生态威胁的影响最为深远,其影响还包括对于后果不确定性和无法预测性,生态危机给全球制造较为严峻生存困境,贝克认为“工业生产的无法预测的结果转变为全球生态困境根本不是一个围绕我们的这个世界的问题——不是一个所谓的‘环境问题’——而是工业社会本身的一种意义深远的制度性危机。”[1]102环境运动宗旨逐渐变成对于工业化状况的反抗,而不仅禁锢于对个别状况保护,如建立环境保护区和保护个别植被和动物物种等,它已超越对于个别可见威胁的情形,因为风险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且风险也具有潜在性,有些风险现象是可见的,但也有不可见的许多风险现象正在潜在威胁人们伺机待发,也许这些威胁不会马上爆发,但它们会在某个地区、某个时间、在某个个体或团体身上发作出来[2]199。
二、风险社会蕴含的生态风险危害
在风险社会语境下,风险社会的社会风险类型多种多样,其中生态风险是风险社会众多类型的重头戏,在贝克的风险社会基本思想和基本理论中蕴含着极其鲜明的生态特征,渗透着极为凸显的生态因素。为此,我们从生态学维度自觉审视,风险社会蕴含的生态风险危害主要表现为生态风险是风险社会的重要风险类型,还表现为风险分配逻辑取代财富分配逻辑,更表现为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等三个重要层面。
如果数据获取功能模块成功监听并获取到Bmob后端云数据库的数据更新,则该代码会将获取的数据通过Toast消息提示的方式显示在昆虫生境移动监测软件上。其次,使用Postman插件向Bmob后端云数据库上传一条昆虫生境数据后,进入Bmob后端云控制台查看数据更新状态,数据已经成功上传到Bmob后端云数据库。需要注意的是,在数据上传期间软件要在运行状态中。最后,在数据上传成功后,软件立刻获取到数据。
(一)生态风险是风险社会的重要风险类型
尽管研究社会生态学的学者反对以社会为中心的思想和以自然为中心的思想这两者之间的对立状态,想要打破社会中心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僵局,但是他们从未突破传统的观念,从来也没有试图将自然主义和社会中心主义的成就有机联系并有序结合起来。生态危机的核心无法由来自自然科学所定义的实质性问题或结构主义反复强调的文化符号(即那种破坏自然的文化符号)这两者所独立组建,只有当我们同时考虑排他性和确定性时,在社会学家从事具体的研究时,与科学原则之间无法逃脱的矛盾相结合,才是他们所认可的构成生态危机的核心。从事社会生态学研究的学者们想要通过使“科学与知识”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才能破解自然主义与社会中心主义的僵局。也就是说“跟随晚期资本主义理论的脚步,一些在社会生态学领域进行理论和经验研究的作者已经证明了他们称为与自然的关系中的社会危机。”[1]37贝克在《世界风险社会》中提出与风险社会相关的四个核心概念:包括“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定义关系、危险的社会爆发和概括对福利国家的争论”[1]191。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保险商业化的趋势不断加强。很多地区也开始试水医疗保险的商业化。如果医疗机构违反了医疗服务合同,给患者造成了人生伤害,可以通过购买商业保险的方式分散风险。现在的商业医疗保险的状况不容乐观,因为患者提出的高额损害赔偿常常令保险公司措手不及,使得很多商业保险公司放弃了医疗保险业务。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把医疗服务合同的地位法定化,约定好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这样商业保险公司理赔的时候才会有依据,商业医疗保险也会慢慢发展起来。医疗保险制度的构建,是一个“三赢”的局面,可以分散医疗机构的经营风险,扩大商业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更有利于保护患者的利益。
在世界风险社会语境下,风险全球化时代已经全面到来,“作为经典工业社会的基本冲突并在相关制度内引起解决这些冲突的企图的‘好处’(收入、工作、社会保障)分配冲突被‘坏处’分配冲突掩盖了。这些冲突可以理解为责任分配(distributive responsibility)冲突。它们的爆发牵涉到如何分配、预防、控制和认可好处生产过程中伴随的风险(核技术、化工技术、基因研究、对环境的威胁、过度军事化以及西方工业社会之外的日益贫困化)。”[5]10“风险愈少为公众所认知,愈多的风险就会被制造出来。”[1]185风险意识对于公众也非常重要,若他们能提高警觉性,增强自己风险观念,培养风险意识,那么对于风险规避和解决将起到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我们再以温室效应为例。全球气温升高、极地冰山冰层溶化、海平面上升都源于温室效应。由此植物物种逐渐灭绝、动物物种越来越稀少、气候变得异常、自然灾害频发、沿海地域将被温带吞噬以及沙漠取代农场。气候灾难区域和气候难民频现,人类越来越不适应那曾经最为熟悉的生存环境,内心极度恐慌,甚至想要逃离,也由此富裕的北方将不得不接收大量的气候难民,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和国家将因此而爆发战争和可怕的暴力事件[1]83。温室效应带来的最为典型的气候变化便是全球气候变暖问题。
一是从必要性角度而言,由于《立法法》对于政府规章备案后审查、审查标准和程序、审查结果处理、不同审查主体审查结果冲突协调等均没有涉及,《法规规章备案条例》对于行政系统与人大系统备案审查工作之间的关系、审查结果的冲突解决以及协调机制等也均没有涉及,迫切需要从国家层面通过统一的立法来界定明晰。统一的立法安排能够为限制行政权滥用、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协调人大系统监督和行政系统监督关系提供一个较为合理的法制化平台。
再如核辐射、核反应堆和化学灾难事故。贝克指出,如同用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灾难事故说明全球技术以及生态风险社会的基本方面。在核力量领域、化学工业领域、生物技术产品领域所带来的重大生态威胁,已经在日常生活中持续可见了[3]31。在文明发展最先进时期,威胁我们“空白点”标记物频频出现,它们对人类的生存发展的影响非常大,拥有重工业区域也变成可怕鬼城,人们住宅区变成有毒废物区是由于突然爆发毒害事故和有毒废料垃圾随便倾倒,有毒化学灾难事故还会侵蚀土壤使土地无法耕种。那些来自被污染海域的鱼不仅仅会损害渔民的经济利益,更会威胁食鱼者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安全[2]42。当代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濒临灭绝,已进入了无法预测、难以控制和不可言说的局面[4]73。
生物多样性锐减问题。森林的破坏、近海污染加剧、生态系统退化、环境灾害频发、局部功能破坏、污染趋势加重植物物种的减少,动物物种也随之锐减。特别是随着近年来世界人口的剧增,人口数量越来越膨胀,对粮食的需求也越来越多,如果所产粮食产量无法满足膨胀的人口,人们就会向生物界索取,向自然界索取,在开发利用大自然的过程中,他们毁坏了森林植被,污染了水源环境,影响了生物物种的生存繁衍,造成生物多样性锐减,长此以往,也会威胁人类的生存。为此,在现时代有必要强化包括高科技企业创新生态系统风险产生机理在内的相关研究[12]。
(二)风险分配逻辑取代财富分配逻辑
贝克将阶级社会的驱动力总结归纳为两个字:“我饿!”又将风险社会的驱动力概括表达为三个字:“我害怕!”共性的需求为共性的焦虑所取代[2]57。贝克将风险社会风险类型归纳为三个层面:一是财富驱动型的生态破坏与技术工业危险,以酸雨危害、温室效应、森林缩小、生物多样性锐减、臭氧层空洞、人口膨胀、江河湖海污染以及遗传工程等可预见的风险和许多不可预见的危险因素。二是与贫困直接相关的风险。贝克以热带森林滥砍滥伐和有毒废料、核反应堆、化学工业、物理技术、生物工程等过时技术为例说明贫困与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深层关联。三是来自NBC(核、生物、化学)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这种武器并不是应用于真正战争,也并非用于实施恐怖活动。即便在战争结束后那些来自NBC武器所产生地区之间或者全世界自我毁灭性的威胁依然存在着,且它已然将超级大国之间所达成的武器条约变成一纸空文。除大国之间冲突所造成的生存威胁外,还有如宗教之间矛盾冲突、恐怖主义活动威胁、私人制造并藏匿危险的有杀伤力武器等威胁,越来越多此类因素给世界增加新风险来源。这三种不同类型风险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并相互影响,财富驱动型的生态破坏与贫困带来的风险联系紧密,而技术工业危险也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带来的威胁相互关联。对此贝克认为,生态环境破坏后,人们会为争夺维持生存所必需物质资源而爆发战争,抢夺食物和水源,贫困国家为了拥有足够粮食维持国民生存,也可能无所顾忌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长此以往很容易将资源开发殆尽,如果走到了绝望程度,这些贫困国家就极有可能采取军事行动掠夺生存资源,由此便又会危害环境。或者还存在其他一些情况,如生态破坏后也可能产生生态难民,从而引发大规模移民潮,这种情况也可能导致战争爆发。接着那些战败国不甘心接受失败,便会寻求突破,极有可能使出杀手锏——“最后的武器”[1]45,积极发展原子能武器和化学武器,用以消灭敌国或者对邻近国家及城市造成威慑力,这是一个令人恐怖的多米诺骨牌式黑暗循环。
通过统计1949~2015年MS7.0级以上地震事件(表5),得到MS7.0级以上地震事件发生的频次(表6),根据表5统计数据并结合泊松分布参数计算公式,得到云南省MS7.0级以上地震的泊松分布参数为0.106 1,每年发生MS7.0级以上大震概率为9.5%,具有每10年发生1次的特点。其中发生1次MS7级地震的概率为17.3%,2次以上的概率为2%(表7)。
(三)有组织的不负责任
贝克感慨道:“无论我们怎样看待臭氧洞、污染或食物恐怖,大自然已经不可避免地被人类行为污染了。”[10]“这恰恰是因为风险的积聚——生态、金融、军事、恐怖分子、生化和信息等方面的各种风险。”[11]贝克以森林的消失为例,说明作为工业化带来的不良后果是全球性的,波及全世界的,并且带来很多较为不同的政治社会后果[2]18。森林消失对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影响,包括气候异常、鸟类灭绝、林业产值削减,尤其是建设核电站和火电厂地区,污染更为严重,人们避之不及,这些地区区位价值也会直线下降。他以德国7%的土地为例,说明土地污染已致使人们无法继续耕种粮食蔬菜。他接着提出一个原理:“财产正在贬值,正在经受一种缓慢的生态剥夺。”[2]41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中,森林的毁坏、退化和植被、动物物种的灭绝,也给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不同程度的伤害,对人类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作为“有道德诉求的自然物”,作为组成自然的天然部分,人类切身感受到了伤害,他们的自然意识被深深地唤醒,如此,人类应当反省自己,并且对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2]89-90。
臭氧层损耗问题。臭氧层位于地球上空同温层,如果把它压缩则厚度不到一英寸。然而,这层薄薄屏障保护着我们不受太阳紫外线辐射伤害,由此臭氧层破坏将意味着对人类的健康产生许多不利影响,包括癌症和白内障等疾病,特别是患皮肤癌数量将会不断增加。更为严重的是臭氧层耗损将影响人的免疫系统。这会使人们更容易患上疱疹和艾滋病等已知疾病且在一系列新疾病、肿瘤和寄生虫面前束手无策,这些都是我们在受温室效应影响的世界中可能预料到的:热带疾病会传播到温带地区,而生活在温带地区的人们体内并没有对付这些疾病的抵抗力。
人口膨胀带来的环境问题。环境问题因人口增长的因素而变得更为复杂,如果说不是后者引起前者的话。这一因素既加重了环境的退化,又使更多的人遭受环境贫困之苦。因此,在人口增长中存在着发生各种类型冲突的巨大可能性,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竭力使自己继续不受环境衰退的影响,冲突的范围可能会进一步扩大。人口增长产生了一系列恶果。环境资源被滥用或过度使用。人均经济增长速度减慢,人均粮食产量停滞不前。社会服务事业负担过重,发展的总体速度缓慢。而这还是从最好的情况来考虑的。人类的数量以及他们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再加上为保证这些消耗而使用的技术,已经常常超出了地球的承载能力。
三、风险社会解决方案的生态学维度
贝克风险社会解决方案包括“反思现代化”和“世界主义”两个方面。全球风险使人类的生存条件发生严重的恶化,反思现代化理论深入分析第一次现代化弊端给当今世界带来的消极影响,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文明风险的全球化时代”[2]38,人们“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2]13,新型风险不断出现,威胁人类生存发展。“有毒的气体、水、土壤、植物和食品‘不懂得国界’。”[1]30因为事实上风险已然超越了民族和国家界线。世界主义方案的提出是鉴于上述风险全球化时代大背景的一种构想,这种构想需要全世界的人们克服固有的传统民族国家观念,团结努力,行动一致,融合成为一个国际治理机构,共同面对和解决已经出现的大量风险状况。“反思性现代化”理论和“世界主义”构想对于化解人类面临的严重危机和解决严峻的风险挑战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值得人类思考和借鉴。
(一)反思现代化理论的生态学维度分析
风险是由现代化的威胁力量所产生的一些后果。现代化在各领域中越来越多需要进行自我反思而具备反思性特点。我们在运用科技手段促进社会进步同时,也在不断对其安全性作出承诺。问题在于,我们只是在不断对颇具警觉性的、具备风险意识的公众作承诺,重申承诺,却没有践行承诺[2]16。“宿命的工业现代性能够使自身转变为一个包含冲突的、自我批评的风险社会。”[1]107“风险社会也是一个具有自我批评倾向的社会。”[5]16作为一种并不规范价值批判的风险批判,以风险威胁形式作为风险社会自我批判参照前提,以未来威胁而非以传统作为批判基础,以较为昂贵测量工具方法而不是以早已确认的价值去认识大自然中的毒性物质[2]218。贝克之所以提出反思现代化理论也是基于现代化给世界带来的得失成败。
当现代化发展程度越来越高,各种不确定因素越来越凸显,社会发展不可预测性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当人们对于风险感知与认识提高时,一系列质疑就会接踵而至了。对此贝克在《世界风险社会》中提出,在风险社会中人们之所以自我反思社会环境基础和评价传统习俗,在于他们认同科技和工业生产发展所带来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测性[1]102-103。 由此,贝克认为,社会反思性表现有三:基于全球生态危机加剧,生存风险威胁加大状况,全球相互依存应运而生,且可能形成世界公共领域;全球对文明自我危害意识的普遍性,可以从政治上对国际机构合作发展起到积极作用;逐渐消减政治边界,世界各国各民族由于地理位置、历史发展、宗教信仰、生活习惯等不同,一种亚政治形式的出现可能带来世界范围的“相互排斥的信仰的联合”[1]25。贝克将自己对反思现代化的认识阐述为:“反思现代化的‘媒介’不是知识,而是——几乎反思性的——无知。”[1]155“反思现代化包含两个要素:通过进一步的成功现代化(它对危险惘然不知)而对工业社会本身的基础造成的如反射般的威胁,以及认识的增长和对这种情境的反思。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的差别首先在于知识的差距——那是说,对于发达的工业现代性之危险的反思的差距……在这个意义上,风险社会的理论是日益变得自我批评的现代性知识的政治理论。工业社会把自身看作为风险社会及它如何评价和改革自身的问题仍处于争论之中。”[1]106贝克进一步指出:“如果我们把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自发的、无意的、未被觉察的和如反射般(reflex-like)的转变称为反思性(reflexivity)——以区别和不同于反思(reflection)——那么‘反思的现代化’就意味着对风险社会的后果的自我正视。”[1]97-98
(二)世界主义方案建构与实践生态学维度
贝克认为:“困惑可以被忽略,但在这个核、化学与遗传技术的时代的危险中的困惑却不容忽视……它们的力量是威胁的力量,它消除国家之间所有的保护区和社会差异。”[1]82在现实主义者看来,风险的威胁具有全球性,发达工业生产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污染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遍性,鉴于现代传媒业的发达带来的深远影响,生态环境的破坏,空气和水的污染,土壤的酸化,食品的不安全现象等情况普遍存在,并且是不分民族国家及等级界限的,这些现象是超越国界的真实存在的。在贝克看来,世界主义是一种伟大的思想,它的伟大之处在于突破了诸如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的一系列传统思想的禁锢,从而有望建立团结协作、统一安全的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目标,成为人类文明克服当前生存困境的一条出路[13]。从历史发展看,国家曾以民族国家为最主要形式,在全球化时代里,人类面对生态危机挑战,风险社会这个称谓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共同话语,全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生态风险等各类威胁人们生存的境况,不仅仅是个人和局部地区需要去直面生态危机,全球都需要接受生态危机的挑战,也就是说,无论是个人的生活还是全球领域的生产生活中都具有风险性,接受它所带来的后果和负面影响并积极寻求出路,既然风险具有全球性,需要全人类携手共同解决已经出现的和可能出现的无法预测的各种风险,所以风险社会通过世界主义主题将原本不相关的、没有联系的、跨越民族国家界限的生态风险问题结合起来。
贝克指出:“贫困是等级制的,化学烟雾是民主的。”[2]38在全球化背景下,许多发达国家企业跨国公司把能耗高、污染重的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或通过“合法贸易”向发展中国家出售在本国被法律所禁止销售的有毒产品;发展中国家囿于技术和经济水平低下,只能作为主要资源输出国与初级生产品输出国,并承担资源消耗与环境破坏后果。在这种不平等经济交往中更加剧生态危机,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陷入贫困和环境恶性循环。科技误用和滥用会引发严重生态问题。诚如贝克所说,世界风险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冲击较大,影响更加深远,使第三世界贫困化加剧,进而会传染给富裕社会,风险社区生成取决于世界风险因素增长,据此贝克提出“飞去来器效应”概念,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在世界市场受到极端不公平的待遇,被发达国家将污染严重的工业转移到欠发达国家中。事实上并非如此,风险不会使富裕国家幸免于此,“杀虫剂通过水果、可可和茶叶回到了它们高度工业化的故乡”[2]49。
在风险社会范围内,风险对于不同人们的影响是平等的,风险不会饶恕任何一个个体或民族国家,这是其最大特色,这也是任何政治力量都无法比拟的,风险社会使得社会分化和民族国家界限得以淡化,使得这些传统观念和界限变得相对化了。风险社会形成又出现世界主义思潮,其中以贝克的世界主义构想最为典型。贝克指出,传统观念和国与国之间政治或社会的界限难以解决世界风险社会面临的挑战[14]。这需要全人类联合起来去消除现代风险,各国人民必须放弃本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传统观念,团结协作,共同努力[1]4-6。 但世界主义方案也有局限性,很难放弃本国家本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观念,加之从小接受爱国主义思想熏陶,人们认为不维护自己国家利益便是背叛本国家本民族,所以贝克“世界主义”构想带有明显理想化色彩,很难在世界范围贯彻下去。跨越民族国家界限的“话语联盟”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才逐渐兴起并不断发展壮大,且在积极筹备关于全球问题基本轮廓,话语联盟成立对环境运动和跨国行动者提出高度制度化的基本诉求,并鼓励这些行动者采取积极的行动,在行动的同时还要不断重申自己关于反对对立者的权利,最终要取得行动的成功[1]31。贝克指出,在世界主义者看来,主要观点在于“必须存在一种政治的再创造,新政治主体,即世界主义党的一种构建和奠基。这些党超越国界代表跨国利益,在国内政治舞台上也发挥作用。因而,她只有作为国家的全球运动和世界主义党时,才在纲领上和组织上均成为可能。”[1]18-19战争爆发和暴力威胁问题带给人们打击仅仅是某一或某些范围,但生态危机给人们所造成苦难却是超越社会范围和界线的,如核威胁、化学技术、基因技术等不当使用给人类生存发展造成困难,这些威胁不再局限于固定领域,这些威胁力量已然忽视民族国家之间保护领域或是民族国家内部之中不同社会分级状况。如贝克所说,总归是“不懂得国界”的[1]30。
开展同课异构活动有利于教师互相切磋,相互学习。不同教师对同一教材内容的不同处理,不同的教学策略所产生的不同教学效果,可以帮助教师从多个角度把握文本,选择更合适的教学内容,采用更有效的教学方式,同时也能充分体现教师的教学个性。开展同课异构活动也有利于教师的个人成长与专业发展。同一教师对同一教材内容的认识要有发展,对学生情况的分析要切实,对教学内容的选择要适当,对教学方式的选择要有效,从而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追求同课异构的过程也是教师不断成长的过程。
贝克总结,生态环境问题的全球解决方法迄今为止已经遭遇三种反对意见:“第一种,认为有关的(非专业和专家的)知识是远远不能算是澄清了全球危险;不少人还提到专业知识的实际状况与大众关于危险和危机的想象之间的不相符合。第二种,认为环境问题的全球界定被批评为一种生态学上的新帝国主义,尤其是所谓‘第三世界’的行动者与政府持此种观点……第三种观点提出异议说,生态问题的全球性界定导致对‘自然保护区’的曲解,并走到它的对立面——一种世界管理上去了。于是这就建立起新的知识垄断——国际气候变迁委员会(IPCC)的高科技‘全球流通模型’,以他们的政治内部构建形式及其对解释与控制原则的要求(特别是关于自然和计算机科学方面)。”[1]31-32从污染工业视角看,只有破坏环境,付出生态代价才能满足人们对于金钱和物质欲望。这种现象所带来的后果是,政治制度彼此自治,存在于其机构和规模较大的生态学矛盾的布局中。风险社会政治状态也不仅仅局限于一国范围内,而应该放到世界范围内来理解,它已然超越了民族国家禁锢和局限[1]86。贝克指出:“我们都是环境的罪人。就像壳牌公司想向大海倾倒它的石油装置一样,我们也很想把可乐瓶掷出汽车窗外。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情况,这使得壳牌案(根据社会结构)变得如此‘透明’。”[1]56比如贝克曾提出为防止风险应共同采取积极行动来有效规避来自核能及有毒化学废料对我们的威胁[2]53。 他又提出疑问:“‘全球技术公民身份’直接政治的场域、手段和媒介是什么?世界风险社会的政治场域不是大街,而是电视。它的政治客体不是劳动阶级及其组织,不是贸易联盟。相反,文化的符号在大众媒体中被展现,同时工业社会的行动者和消费者累积的良心不安被卸载。对这种评价可以举例说明:第一,在危险的抽象的无处不在中,破坏和保护被象征性地调和。第二,在反对生态破坏的行动中,每个人也是自己的敌人。第三,生态危机引起一种文化的红十字意识。”[1]55随着风险问题的全球化,生态风险的影响正渗入到国内政治及国家安全领域,环境外交成为建立世界新秩序和构造未来国际格局的重要途径。在一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内部,工业增长利益同保护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这些国家环境保护舆论压力日趋增大,致使不少政党在竞选中也争相打出环境保护牌。
由表6可以看出,在其它变量不变的情况下,解释变量国内生产总值、年末人口数量和居民人均教育消费支出对被解释变量国家财政教育支出的影响显著.解释变量居民教育消费价格指数和财政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对被解释变量国家财政教育支出的影响都不显著,从回归模型中剔除,得到新的回归模型为
综上所述,随着生态环境在总体上呈现恶化趋势,威胁人类生存发展安全因素已经超出传统国防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的范围。贝克风险社会理论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现实出发,虽然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对当代社会发展仍具有深刻启示和借鉴价值。贝克作为风险社会理论提出者,其风险社会形成有其生态渊源,所蕴含的生态特征以及解决方案都与生态风险密切相关。从生态维度去解读贝克风险社会理论,不仅有利于我们正确辨析当代社会中复杂的生态风险现状,为生态风险研究提供有力依据,且有利于树立正确防御生态风险观念,加强生态风险预警机制,激励人们积极地应对生态风险。
参考文献:
[1][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M].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3][德]乌尔里希·贝克.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上篇)——关于人类生存、社会结构和生态启蒙等问题的思考[J].王武龙,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3).
[4][德]乌尔里希·贝克.“9·11”事件后的全球风险社会[J].王武龙,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2).
[5][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英]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M].赵文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6][德]乌尔里希·贝克.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下篇)——关于人类生存、社会结构和生态启蒙等问题的思考[J].王武龙,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5):67.
[7]薛晓源,刘国良.全球风险世界:现在与未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风险社会理论创始人乌尔里希·贝克教授访谈录[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1):44.
[8]王剑锋,徐飞.试论科学认识的不确定性与可接受风险[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6,(2):54.
[9]王娟.气候变化治理中公众对专家的信任研究[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6,(6):90.
[10][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再思考[J].郗卫东,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4):49.
[11][德]乌尔里希·贝克,邓正来,沈国麟.风险社会与中国——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对话[J].社会学研究,2010,(5):209.
[12]张运生.高科技企业创新生态系统风险产生机理探究[J].科学学研究,2009,(6):925-931.
[13][德]乌尔里希·贝克,[德]埃德加·格兰德.世界主义的欧洲:第二次现代性的社会与政治[M].章国锋,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84.
[14]BECK U.The Terrorist Threat-World Risk Society Revisited[J].Theory, Culture & Society,2002,19(4):52.
The Ecology Dimension of Ulrich Beck’s Risk Society Theory
YANG Li-jiea,BAO Qing-deb
(a.School of Marxism;b.School of Philosophy,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ohhot 010070,China)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risk society theory has its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background.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society has experienced two different stages, that is, the class and social problems as the focus of the first stage and th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as the focus of the second stage,which indicates the ecological risk origin of Beck's risk society theory.Forest depletion, population expansion, greenhouse effect, ozone depletion, nuclear radiation, nuclear reactors, chemical catastrophe and biodiversity loss and so on result in the phenomenon that the risk distribution logic replaces the wealth distribution logic.The common demand is replaced by common anxiety.There is the formation of organized irresponsibility in risk society for the common problems.That is to say, the fact that there isn't any individual or organization which could be responsible for risk problems shows ecological hazards in risk society.Even though there are some limitations in the ecology dimension of risk society solutions,such as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cosmopolitanism vision, there is still deep reference value which exists in risk society solutions.
Key words: Ulrich Beck;risk society; ecological risk; risk distribution logic; reflexive modernization;cosmopolitanism vision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971(2019)02-0114-09
收稿日期:2018-12-30
作者简介:杨丽杰(1987—),女,内蒙古鄂尔多斯人,博士研究生,从事生态哲学与风险社会的生态学维度研究;包庆德(1960—),男,辽宁阜新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生态哲学与风险社会的生态学维度研究。
[责任编辑:王 春]
标签:风险论文; 贝克论文; 社会论文; 生态论文; 国家论文;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论文; 内蒙古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内蒙古大学哲学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