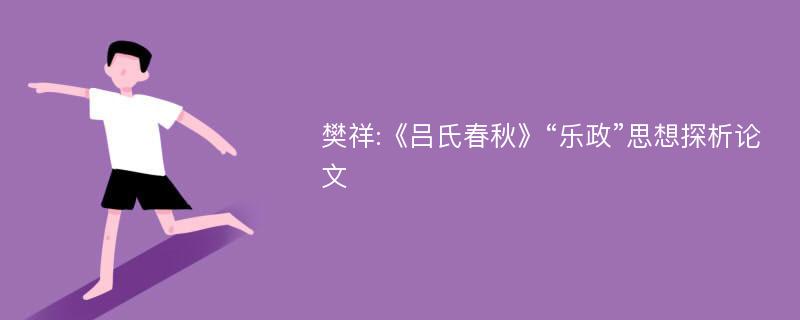
摘 要:“乐与政通”是我国古代“乐”之功能观的重要表征,实质是把乐与政治进行“联姻”,突出乐对于政治的教化作用。从《吕氏春秋》有关乐的论述来看,其所谈及的“乐由道生”“乐由心生”的这两种关于乐的创生理路以及对乐的审美本质属性“和”与“适”的阐发,最终都指向了“察风以观政”的乐政体式,从而揭露出《吕氏春秋》论乐的政治伦理诉求。
关键词:《吕氏春秋》;乐政;创生理路;和适
《吕氏春秋》是战国后期由秦相吕不韦集众宾客编纂的一部集众家之说的理论著作,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美学思想,尤其对“乐”作了十分详细的论述,包括《大乐》《侈乐》《适音》《古乐》《音律》《音初》《制乐》《明理》等八篇专论文章以及散见于其它篇目中的偶然感发。该书乐论部分主要阐明了乐的理论基质、起源与发展、审美本质以及审美鉴赏等相关问题,建构了较为系统的乐论体系。通过对《吕氏春秋》中论乐部分内容的梳理,笔者发现由“乐”所生发的一系列美学论题,最后都指向了“察风以观政”的乐政体式。因此,对《吕氏春秋》“乐政”思想进行一定的理论考量,不仅可以厘清“乐”的功能结构及其发展脉络,而且也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先秦乐政关系的理论认知。
吃饭的时候,他会无意间蹦出一句:“他们说我是小霸王,是坏蛋,妈妈,我不是的,我以后再也不欺负别人,不抢他们的东西了。”
一、《吕氏春秋》乐论的生成语境
吕不韦原是阳翟(今河南禹州市)的富商,因帮助当时在邯郸做人质的秦国异人(子楚,即庄襄王)登上王位,而一跃成为秦国丞相,自此走上了仕途之路。异人即位仅三年就因病过世,其子政(后来的秦始皇)遂承袭王位,因其年龄尚小,所以朝政之事多由相国把持,固被秦王政尊称为“仲父”。在其主政期间,他所实施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有效地促成了秦国经济、政治、思想等多方面的发展,为秦统一六国积蓄了丰厚的物质与文化资本。但随着秦王政日渐长大,其凶戾、残暴、独断的性格与尚法的主张都与吕氏的思想主张有所偏离,甚至针锋相对,这就使吕氏不得不对即将亲政的秦王政产生一定的顾虑。吕不韦清醒地认识到当前这种内外格局的变化,作为一国之相,他必须得为下一步进行打算。可以说,《吕氏春秋》正是在此种历史语境之下所形成的,“《吕氏春秋》的编纂固然有吕不韦盗名沽誉、牢笼门客、立言不朽、为国争荣、立政讽箴等动机,但更重要的还是……为了一统思想,为行将统一的秦王朝制订治国方略进而填补秦国无文化积淀之空白”。[1]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政治伦理诉求就成为《吕氏春秋》编纂成书的“拱顶石”,而“乐”作为政治传达的古老文化形式,自然也就被纳入了编纂范围之内。
众所周知,自周公旦制礼作乐后,礼、乐的内涵逐渐被固定化,“礼”成为具有等级层次的各种道德规范、制度、政治原则等的总称,“乐”则是根据不同的级别用来配合各种仪礼活动的乐舞表演,礼、乐的相合共同构筑了华夏文明的血脉。随着西周的没落、衰亡,礼乐的仪式意义渐渐失去效用,战乱成为时代的主题。鲁国的孔子对于曾经起着维系周代社会结构与秩序的礼乐文明的崩坍有所感触,于是通过对西周礼乐的重新审视,创造性地提出了“仁”这一概念,并用其去阐释礼乐,“礼”遂被用来作为个体行为的外部规范,“乐”则被用于调节内心情性的协和,二者既存在区别又互相联系。经由孔子对礼乐的再阐释,礼、乐遂成为之后各家探讨的对象,著书立言多有提及,如荀子《乐论》、墨子《非乐》、老庄道家关于“大音”“至乐”的描述等,它们都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去探寻“乐”的理论形态与精神内涵,从而拓展了乐的理论维度与价值构成,为后世士人论乐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当然,更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此时私学的兴起,私学的产生无疑有时代、政治、个人等多种的原因,抛开这些因素不论,私学导致的最直接的结果便是士阶层的活跃,而士阶层一般都受过相应的学术教育,礼、乐应当都含括在内,它们基本上都寄居于诸侯、卿大夫门下,为他们巩固政权、开辟疆域、制定各种典章制度出谋划策,进而“养士”之风成为当时一重要的文化景观。所以在论及《吕氏春秋》乐政关系之前,有必要对其所处的时代文化境遇进行简要的概观,正是通过这种粗线条的勾勒,我们可以看到《吕氏春秋》乐论的历史生成是特定时代政治与文化双向合力的产物。
二、“乐由心生”的论说理路与政治传达
“乐由心生”是先秦儒家乐论的理论出发点,他们认为人受到自然外物的刺激易引起内心情绪的波动,将这种感物而起的情感以“声”的形式表现出来,各种声音之间的流变、碰撞、整合,再配以相应的曲调、节奏、乐器、歌舞等,最终就产生了韵律和谐的“乐”。《吕氏春秋》接受了儒家关于乐的看法,“凡音者,产乎人心者也。感于心则荡乎音,音成于外而化乎内。是故闻其声而知其风,察其风而知其志,观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贤不肖、君子小人皆形于乐,不可隐匿。故曰:乐之为观也,深矣。”[2]这里,《吕氏春秋》阐明了乐的发生:音乐是心灵的产物,它是内在情感的形象化表述,并且具有一定的传导性,即通过观察个体的情感、志趣,可以了解该地区的风俗情貌,直至国家政治兴衰。因而,乐也就具备了政治伦理的意味:一方面,君主的治世方略可以经由乐得到人民的反馈;另一方面,老百姓也能够由乐而知君主的政行。
这一年虽然辛苦,但我们室的情报服务得到了师生和领导的认可,被评为校先进集体。我个人也在这一年根据情报服务中碰到的各类问题,对情报需求者的行为特征和心理特征等分析研究,撰写了《情报供需双方的交互作用》。实践越深入发现的问题就越多,引发的思考也越多。如果将这些思考转化成研究成果,工作中的收获就会很丰硕,反过来能进一步提高工作的热情和激发开展学术研究的动力。比如,在1989年一年中我就发表了6篇学术论文:《情报用户的信息反馈问题》 《文献检索教育的环境建设》《情报咨询决策阶段说》《大学学报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高校专利情报查新德几个环节》《信息选择过程中的几个制约因素》。
实践教学是衔接和融合相关知识,促进各项技能协调发展,凸显应用型人才优势,提高毕业生就业竞争力的关键。强化实践教学是全面推进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途径。目前内蒙古科技大学英语专业培养方案的实践教学比例较之过去有所提高,体现了学校专业教育对实践教学的重视。然而,目前实践教学环节还需要在2017年新颁布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以下简称《国标》)指导下进一步寻找各种途径培养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和实际应用能力。
11月5日,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之际,日本大阪国际经济振兴中心专务理事原法康一行来金山考察。原法康一行实地参观了花王(上海)化工有限公司,了解日资企业在上海金山的生产运营情况。
三、“乐由道生”的模式建构与政治表现
故而制乐的症结就在于“节欲”与“平和”,而平和又主要体现为审美主客体之间的合度。《侈乐》篇指出“凡古圣王之所为贵乐者,为其乐也。夏桀,殷纣作侈乐,大鼓钟磐管萧之音,以巨为美,以众为观,俶诡殊瑰,耳所未尝闻,目所未尝见,务以相过,不用度量”。[2]265-266古代先王制乐的本意就在于使人耳目愉快,自然这也是乐自身所包涵的美感特质的要求,而夏桀、殷纣王等人却放纵欲望,制作豪奢、场面宏大、不合乐器度量的侈乐为美,与乐的本质相背离,久而久之就会激起百姓的怨怒、忿恨,滋生各种叛乱的想法,“这就产生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悖论:统治者愈是要从音乐中追求超强度的快乐,结果往往愈是失去快乐;愈是想让生命得到超量享受,反而愈会加速丢掉性命”,[6]所以这两个国家最后都走向了亡国的道路。平和对审美主体而言,在于要顺乎天道,也即要了解事物的根本,从而内心自会公平、安定;对于客体对象来说,关键在于要合度,声音的大小清浊都要符合“和”与“适”的准绳,即符合“黄钟之宫”①的标准。只要审美主体与客体之间能够共同达到这种“和”的状态,那么雅乐、大乐即可创成。
这种“观风知政”的乐政思想更直接体现于《吕氏春秋》对郑卫之声、桑间之音的批判,它们完全背离了雅乐的创作程式与礼法秩序,其所弹奏出的淫邪、轻佻的音乐催生了各种社会弊病,成为国家倾覆的祸根。如在《先识》篇中周威公与晋太史屠黍关于“天下之国孰先亡”的谈话,屠黍指出紧随晋国灭亡之后的国家便是中山国,“天生民而令有别。有别,人之义也,所异于禽兽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昼为夜,以夜继日,男女切椅,固无休息,康乐,歌谣好悲。其主弗知恶。此亡国之风也。”[2]946上天生养万民并使他们有所区别,这本是作为人的根本要义所在,也是与禽兽所不同的地方,而中山国却颠倒黑白、放纵淫欲、纵情享乐,消弭这种先天的分别,违背正常的伦理规范,从而致使其亡国。这些不合伦理的行为实际上是中山国政治乃至君主德行的某种外化,故而屠黍能够从它的日常习俗窥探其灭亡的先兆。《吕氏春秋》指出了这种奢靡之乐对于政治造成的危害,故倡导君主要修身养性。君主作为封建王朝最高权力的象征,易恃才傲物、专断独行,如若没有相应的约束,便容易引起亡国之险。所以《吕氏春秋》在众多篇目中反复强调了君主要去欲、贵生这一思想,只有达到这种程度,君主才能不为外物所局限,进而能够知贤人而善用,以德行治理天下;反映于艺术创作之中,即是指君主贵生、节欲等养性之法能够趋避内心的褊狭想法,保持心灵的安定,而只有心定创作的乐才会和谐、雅正,最终达于理义,从而人们就会形成自觉的礼法意识,国家必然也会繁荣昌盛。
《吕氏春秋》对“乐”之由来的论说并不仅仅囿于儒家“乐由心生”的生发理路,它以道家的创生理论为基准,从宇宙论的高度对乐的生成进行了形而上的阐释。“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浑浑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萌芽始震,凝寒以形。形体有处,莫不有声。声出于和,和出于适。和适先王定乐,由此而生。”[2]255具体言之,这段论述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乐的产生具有数理基础。“度量”原指测量物体的长短、轻重,这里引申为各种律管的大小、尺度、容积等等;如《古乐》篇中提到黄帝命令伶伦制作音律,伶伦以山竹制成律管,其吹奏出的黄终律宫音,就是严格按照山竹的度量而制成。当然这并不代表乐就是由度量所产生,它产生的还只是“声”,乐的构成还需其它各种物质媒介材料之间的相互配合。当然这也潜在的表明,“数量关系一方面是音乐创生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也是体现乐与道德乃至政治关系的重要参照。”[3](二)乐的天道观。乐的本体存在源于太一,太一生出天地,天地生出阴阳,阴阳之间的起伏升降、聚合离散生成了有形体的万物,万物既然形成,势必要占有一定的空间,进而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声音。简单的说“乐”也就是经由“太一→天地→阴阳→万物→声音”等程序而形成。这种逻辑推演与道家创始人老子关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阐述具有明显的同构性,并且“太一”与道之间的关系甚为紧密,那么究竟何为道?“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名,谓之太一”,[2]256不注意看道家之“道”似乎与“太一”没有多大的差别,都是作为万物生成的原初形态,无形又无名。不过,仔细辨析它与老庄道家之“道”又存有差异,“在老子学说中,‘道’是无,是超乎‘一’的虚构的概念。而在《吕氏春秋》中,‘道’是‘有’是‘太一’、‘一’”。[4]那么太一又是什么?《易传·系辞上》提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唐代大儒孔颖达疏:“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5]由此可以看到“太极”就是指“太一”,也即是一种元气或精气,更明确的说“太一”也就是指宇宙世界形成的初始状态。至于何者为“一”,《圜道》篇提到:“一也齐至贵,莫如其原,莫知其端,莫知其始,莫知其终,而万物以为宗”。[2]172显然,道、太一、一在《吕氏春秋》中并不存在等级层次上的高低,他们内涵基本上是相同的,乐就是在其统摄下经由一系列自然现象的变化逐渐形成的。如《音律》篇所说“大圣至理之世,天地之气,合而生风,日至则月钟其风,以生十二律”。[2]325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乐不管是“生于度量”,还是“本于太一”,它的生成都需要遵循相应的法则、秩序,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这也就为乐政思想找到了先天依据。(三)乐的制定原则。乐既然是循理而制,那么就必须摒弃那些阻抑理的因素,以求达到平和顺道,继而才能创造乐。
因而,心定的问题就自然而然地被凸显了出来。《适音》篇指出心定的关键在于要安适顺心,而心适又得取决于行为的合宜与否,“人之情:欲寿而恶夭,欲安而恶危,欲荣而恶辱,欲逸而恶劳。四欲得,四恶初,则心适矣。四欲之得也,在于胜理。胜理以治身,则生全以;生全则寿长矣。胜理以治国,则法立;法立则天下服矣。故适心之务在于胜理。”[2]272所以说,不管是圣人还是百姓,欲望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公平的,大家都有且都期待美好的欲望,只是圣人能够克制己欲,然而普通人却常被其所蒙蔽。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吕氏春秋》并没有直接地否决欲望的存在,但对于欲望的把握却存在“适”的问题,如果未按照事物自身的情理去追求本能之欲,那么心就会反遭遮蔽、吞噬,纯任主观意志的需求进行日常的世俗活动,具有政教规范的乐自然也就不会产生,国家的礼法进而也就难以得到天下百姓的认同。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修身养性即是为了能够去欲望之蔽而达于内心的安适,而顺从事物的天性情理亦是为了内心的安定平适,而且更具本源性。
所以说,乐与政治相通,二者是互为表里的关系,“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平也;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国之音悲以哀,其政险也。凡音乐,通乎政而移风平俗者也。俗定而音乐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观其音而知其俗矣,观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托于音乐以论其教。……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特以欢耳目,极口腹之欲也,将教民平好恶、行理义也”。[2]273这里就指明了乐政的这种密切关系:通过观察一国的政治风俗,可以探求该国乐的特征、基调;另一方面,从该国乐所表现出的特性,也能够窥探出君主的德性以及国家政治的治乱兴衰。因此,古代圣王一般都会将乐作为实现政教清明的工具,乐它不仅仅只是单纯地满足感官愉快,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君主用其教化百姓,促使他们去恶扬善,广施德义,从而达到天下的安定和谐。
总而言之,《吕氏春秋》作为特定时空境遇之下产生的理论著作,本身就含蕴着浓厚的政治意味,其对于“乐”的理论认知,明显受到儒道两家乐论的影响,“乐由道生”“乐由心生”的两种创生模式并未各自为营,自成系统;相反,它们通过乐的审美本质“和”与“适”在“察风观政”的乐政体式上实现了“合流”,且二者都把矛头指向了因违逆天理而自取灭亡的国家、君主。可以说,《吕氏春秋》论乐的目的正在于此,以乐的政教作用作为君主治世的警示,从而潜在地揭示了吕不韦及编纂者的政治伦理诉求。
注释:
①黄钟之宫:古乐以音律来确定五音的高低,用黄钟律所制定的音叫做宫音,它也是其它音阶(商、角、徵、羽)生成的参照标准,按照“三分损益法”以次相生,从而就产生了“十二律”,而黄钟律又为古乐中最基本的乐调之一。
参考文献:
[1]王启才.吕氏春秋研究[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27.
[2]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335.
[3]韩伟.吕氏春秋乐论思想疏证[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2014,43(4):76-82.
[4]张双棣.中华经典藏书——吕氏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2007:47.
[5]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标点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89.
[6]刘成纪.重论吕氏春秋的音乐美学体现[J].中州学刊:文艺研究,2016(3):145-153.
Analysis of "Yue Zheng" in Lu's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FAN Xiang
(School of Arts,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1)
Abstract: "Music and communication" is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the ancient Chinese "music" concept of function, the essence of which is the "marriage" between music and politics, highlighting the role of music in political enlightenment. Judging from the discussion of music in Lv's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the two creative paths of music and the elucidation of the aesthetic nature of music, harmony and suitability, all point to the musical and political style of "observing the wind and observing politics", thus revealing the theory of Lv's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on the political ethics appeal of music.
Key words: Lu's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music administration;creating a physiological path;and fi tness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717(2019)05-0096-04
收稿日期:2018-12-18
作者简介:樊祥(1992-),男,安徽合肥人,文艺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文论,美学。
标签:春秋论文; 吕氏论文; 政治论文; 君主论文; 秦国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先秦哲学论文; 杂家论文; 《牡丹江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论文;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