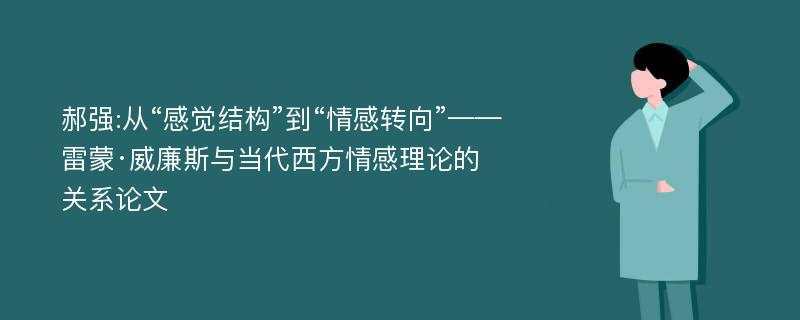
摘 要:“感觉结构”是雷蒙·威廉斯文学与文化思想中的核心概念之一,他提出这个概念的目的,是把感性的经验同理性的结构相结合,强调某种不能被意识形态所涵盖的要素。然而,威廉斯对于这个概念又过于注重经验描述,缺少系统的理论阐释,这也遭到了伊格尔顿和霍尔等人的批评。近年来,随着人文社科领域之“情感转向”的兴起,文化研究的重心从语言结构转移到了情感经验,这就为重新审视威廉斯“感觉结构”概念的当代意义提供了契机。
关键词:雷蒙·威廉斯;感觉结构;文化唯物主义;文化研究;情感转向
作为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奠基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一直试图重新思考文化与社会的关系,这种思考方式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模式,特别是其提出的“文化唯物主义”这一批评方法,使得文学研究开始摆脱传统形式主义的束缚,走向更为广阔的文化、社会空间。但囿于时代和个人知识体系的局限,威廉斯的文化分析也遭受了多方批评,正如霍尔等人认为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都不能满足文化研究的需求,所以要采用新的分析方式。而当文化研究从英国走向全球,特别是近年来人文社科领域出现的“情感转向”,使得威廉斯的“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注]国内对此概念一般有两种翻译:即情感结构或感觉结构。例如倪伟(《漫长的革命》译者)、王尔勃(《马克思主义与文学》译者)、付德根、段吉方等人就采用了“感觉结构”的翻译,而刘进(著《文学与“文化革命” 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学批评研究》)、赵国新(著《新左派的文化政治 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理论》)和阎嘉等人则采用“情感结构”。在威廉斯看来,feeling和experience接近,但是经验一般含有过去时态的意味,而感觉强调的是现在状态。在中文语境中,情感一般与经验无关,而是偏向主体某种静态的属性,威廉斯重视的是个体/社会的经验、体验的变化,所以本文采用了感觉结构这一翻译。再次被人们提及。把“感觉结构”和最新的“情感转向”相联系,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威廉斯理论的价值与局限,思考经验和情感对当下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
正如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一样,情感转向也揭示了当下相关研究领域一些新的研究趋势,在对情感的聚焦中,人们关注的问题正发生变化。恐怖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结的兴起,情感经济或情感劳动的出现,忧郁、愤怒、快乐和爱等情绪成为了人们行为的主要推动力……当理性被感性所取代,当物质生产转为情感生产,当情绪脱离个体成为一种社会建构要素时,我们确实需要一种理论,去理解人们是如何被触动、影响、刺激的,去理解人们面对种种“遭遇”时是如何感受和行动的。面对社会文化的这种变化,情感转向的代表人物布莱恩·马苏米(Brian Massumi)曾言,“我们如今的情形,其特征是过度沉溺于情感。问题是没有一个可以专门指称情感的文化—理论词汇”[1]。但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威廉斯就曾试图用“感觉结构”来描述人们的情感和经验。所以,从“感觉结构”切入,不仅是为了描述威廉斯某一概念的发展过程,而是为了探讨其在当下语境中的意义,为理解当下社会和文化中的种种变化提供一条新的思路。
一、“感觉结构”概念的演变
威廉斯的文化理论有其具体的历史语境。一方面,“文化唯物主义”批判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模式关系,文化不仅是被经济基础反映的意识形态和精神范畴,而是可以理解为某种物质性的东西或过程。另一方面,由于文化是指各种形式的文化,所以利维斯(F.R.Leavis)的文化精英主义也是其批判对象,高雅/低俗文化或精英/大众文化的界限在此被打破了。那么,威廉斯是如何阐释其文化理论的呢?这就涉及到其思想的核心概念——“感觉结构”,它不仅是理解“文化唯物主义”的关键,也贯穿于威廉斯整个学术思想。同时,从感觉经验出发分析文化、文本,也明显与当时欧陆哲学的结构主义分析方式不同,因为结构主义去除了人的主体性,情感更是被放逐到了理性统治领域的边缘,这也是当代情感理论所要批判的。
提供适合的睡眠环境,住院的神经衰弱患者绝大部分有睡眠障碍,且均为睡眠问题焦虑,我们应尽量给患者提供适当的睡眠环境,如安静、冬暖夏凉的房间,不和其他精神运动性兴奋患者同一病室。除了中午小睡一会(不超过半小时)外,白天的其他时间不要睡觉或打盹,以免影响晚上的睡意及睡眠时间。指导患者进行睡前准备,如:喝热牛奶,忌饮浓茶、咖啡,用热水泡脚,听轻音乐,睡前不做剧烈运动等。
从字面上看,“感觉结构”和“文化唯物主义”的构词法类似,都采用矛盾修辞的方式,由一对含义相反的词语组成:感觉一词接近非理性的、不断变化着的个人经验,结构则偏向理性的、稳定的社会关系;文化一词在传统马克思主义者那里近似于意识形态或精神,而唯物主义则强调文化的非意识和物质性。通过这种把两个矛盾概念糅合的方式,威廉斯其实是想要弱化传统理论中物质与意识、个人和社会、感性和理性、精英和大众等一系列二元对立模式。
而伊格尔顿和霍尔等人一方面批判了“感觉结构”缺乏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则认为对感觉经验的过度重视会导致肤浅的浪漫主义和人道主义。所以回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回到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或者是把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结合是十分必要的。其实,“感觉结构”所欠缺的理论体系也正是文化研究理论所欠缺的,后来人们也经常会批判文化研究理论体系不够清晰。但正如霍尔所说的,文化研究“拒绝成为任何一种主导话语(master discourse)或元话语(meta-discourse)。是的,作为一个规划项目它永远向那些未知的、那些还不能命名的领域敞开大门”[9]。当结构主义重视结构整体,忽略人的主观能动性时,就可能形成某种主导性的话语,所以可以看出霍尔对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都是持一定怀疑的。面对“感觉结构”的问题或可能存在的局限,伊格尔顿和霍尔其实是以“后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提出解决办法,前者试图重新定义基础/上层建筑的关系,后者则发展了“接合”(articulation)理论,[10]即多种因素可以在一定语境中统一在一起(例如某类小说既非表达文化的控制,也不表达抵抗,而是一个更为复杂的斗争场域)。这种应对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学、文化现象分析打开了一条新的思路,特别是在分析亚文化、族裔流散、身份认同等问题时尤为适用。
威廉斯试图将主观经验引入文学、文化批判中,是为了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中的“上层建筑”和结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相区别,是为了把感性的经验与理性的结构相结合,这使得“感觉结构”这一概念似乎具有某种独特的魅力。但是正如伊格尔顿和霍尔所批判的,威廉斯的论述还是不够清晰、缺少理论的系统性,更多是从感觉的整体性出发。这是由威廉斯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其知识背景所决定的,他试图把感觉经验或文化的物质性提到首要地位,但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他试图对文化进行整体性分析,但忽略了文化的内部冲突和斗争。这些方面的局限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威廉斯理论的进一步传播和阐释,直到近十几年来,学界“情感转向”的兴起,使得“感觉结构”这一概念重新为人所关注。
在《漫长的革命》中,威廉斯进一步论述了感觉结构在文化分析时的重要作用,认为“感觉结构就是一个时代的文化:它是一般组织中所有因素带来的特殊的、活的结果(living result)”[3]57,这一时代的文化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把握,一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所经历、理解的文化;二是被文本(包括文学、建筑、服饰等文本)记录下来的文化;三是经过后人选择的文化。威廉斯认为人们只有真正身处那个时代才能切身经验、感受那一时代的文化,经过文本记录的文化其实已经失去了生命力,类似于柏拉图艺术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关系,文献式的文化只是其所记录的时代的残存影像,而后人在阅读这些文本的时候其实已经受到当时利益体系和价值体系的影响,无法真正触及那一时代真实的文化。而强调感觉结构是“特殊的和活的”则意味着重视主体鲜活、微妙、变化着的个人体验,而不是被抽象化了的意识形态、文化模式、社会性格。当一个时代过去后,是可以通过这一时代的文本来发现其感觉结构的,由于感觉结构是不断变化着的,所以对文本中感觉结构的考察其实是对历史的考察,也是对当下的考察。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特殊的感觉结构。在西方传统中,艺术与现实总是对立的,所以才有再现说和表现说两种重要传统,但是这种分类还是不够的,因为“它仍然是以假定的二元论为基础的,即认为艺术和现实或是人与其所观察的世界之间是分离的……我们应该把人类经验看作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过程”[3]29-30,通过对艺术的重新定义,其实是想把艺术和日常生活相联系,艺术不仅仅是生活的反映,还要求与社会积极互动,在这种对艺术公共性考察的过程中也就逐渐形成了威廉斯的文化概念,文化是一种与人们日常经验相关的生活方式。
我们在理解某一时代文化时,总是从这个时代的某一方面或某一因素入手,是把每一个因素当做结果来认识,但在当时的经验中这些因素都是不断变化着的,是与社会整体不可分割的。威廉斯认为小说其实是一种历史史料,小说反映了19世纪英国大众的感觉结构,这种感觉结构才是真实的,而官方的宣传往往是虚假的。官方宣传大英帝国是最先进伟大的,但狄更斯、艾略特的小说中其实不是这样。某种感觉结构是不同于当时官方意识或价值的,例如19世纪初人们想要表达自己的某种经验,但是缺乏文化方式或手段,于是借用文学作品表达自己的类似经验,所以劳动人民喜欢雪莱作品中的单纯风格,工人阶级则喜欢拜伦的讽刺手法。
文章中,我们在智能合约的编写过程中,定义了文件、纪录、成员和用户4个结构体变量,分别存储电子数据文件的关键信息、电子数据文件分片的关键信息、用户资料和电子数据文件的所有关系。基于上述4个变量,我们依次编写了电子数据信息的上传、电子数据信息的查询、电子数据的授权、用户信息的更新和用户信息的查询。考虑到以太坊数据写入的速度较慢,容易影响用户体验,因此采用异步请求方式(sendAsync)执行事务,以此来加快电子数据的查询传输速率。
戏里的翠屏,靠着勇敢坚毅的表现赢得了掌声,而戏外的赵多娜,也同样凭借在这部戏中的精彩演绎,完成了她事业上的华丽晋级。她在实现表演风格的优雅转型的同时,也打开了更多的知名度。
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威廉斯用一节的内容整合了“感觉结构”的内涵,把其作为文化理论的重要术语之一来分析。根据一般的观点,文化、社会或者观念总是呈现为过去时态,是业已完成的固态结果,而与之相对的现在时态的经验、感觉则是不断变化着的。每一代人的语言、习俗、文化与上一代人相比都在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可以被定义为感觉结构[structure(s)of feeling]的变化。这一术语很难理解,但选用‘感觉’(feeling)一词是为了强调同‘世界观’或‘意识形态’等更传统正规的概念的区别”[4]141,是为了把现在与过去时态区别,是为了把动态的过程与凝固的结果区别。而“结构”则意味着某种特定的内部关系,一种既相互连接又充满斗争矛盾的关系。威廉斯对“感觉”一词的选用其实也是无奈之举,因为当时并没有找到一个更准确的词汇,正如他所说,“我们谈及的是关于冲动、压抑和腔调等个性气质因素,尤其是意识和关系中的情感因素(affective elements)——不是与思想观念相对立的感觉,而是作为感觉的思想观念和作为思想观念的感觉”[4]141[注]译文有改动。可参考Raymond Williams,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 132.他注意到了“情感”问题,但最终还是选用了“感觉”来描述经验、情感的变化,来与传统的意识形态相区别。
美国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就是最早关注情感问题的学者之一,正如他在《文化研究的未来》所说的,“在当前的语境下,流行似乎具有越来越强烈的感染力,政治与娱乐结构、幻想以及多形态快感的结合越来越紧密,而非意识形态……一个小小的逸事令政治问题的流行形式似乎已经从‘你在想什么’转变成‘你感觉如何’”[12]230。当我们理解当前的政治文化时,意识形态、表征等词语已经不能完全表达其复杂性,情感正成为新的理解维度。
威廉斯在《电影序言》首次提出感觉结构,认为它和人们的共同经验相关,文学和电影都是当时社会共同经验的载体。而在《漫长的革命》中则进一步把感觉结构的适用范围扩大到社会文化的分析中,主张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感觉结构,时代和人们经验的变化也会使得感觉结构处于不断变化中。而到了《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感觉结构进一步与主导意识形态分离,成为与尚未定型的新兴文化相关的现实经验。可以看出,在不同时期,威廉斯对这一术语的理解是有所不同的,从早期用感觉结构来分析文学和电影,到后来通过文本来解释社会文化的结构,感觉结构更多是作为威廉斯分析文本和社会的一个工具。这种从感觉经验出发的分析方式为当时的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但也同时遭到了一些理论家的批判。
二、“感觉结构”的局限:对文化唯物主义与文化主义的质疑
在重视日常经验的同时,强调文化的物质属性,这是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的核心。而文化唯物主义有时也被称为文化主义,意在与结构主义的研究范式相区别。作为文化研究领域的奠基者,威廉斯为文学和文化分析提供了新的思路,但其以“感觉结构”为核心的文化唯物主义/文化主义也遭受了同时代的其他理论家的质疑。
例如,从文学文本是否就可以回到真实的历史?每一代人是否分享着共同的感觉结构?从经验出发是否能得出社会运行的规律和结构?这些疑问在威廉斯晚期著作中得到了部分回应,他强调自己主要讨论的是新兴工人阶级的感觉结构,是为了解释科学理性和主导意识形态忽略了的一些现实问题。但正是由于从经验中无法准确得出一切,威廉斯的文本分析中也运用了大量的统计数据,这也是经验与结构之间无法回避的矛盾。
所以他的学生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就曾批判威廉斯感觉结构这一理论更多是从经验出发,缺少理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甚至认为整个英国的学术传统都是以经验分析为主,缺少像欧陆哲学那样的分析综合,正如其在《批评与意识形态》中所说,“在当下试图建构唯物主义美学时,任何一个英国马克思主义者都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在这一领域中,不仅有很多问题是充满不确定性的,而且从英国传统切入本身就自动把自己排除在了讨论之外。英国让人感觉它缺少一种传统,只是欧洲容忍的房客,一个早熟但寄生的外来者”[5]。的确,威廉斯的感觉结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确实如伊格尔顿所批评的那样:太注重经验分析,理论不够系统。这一方面是由于威廉斯是以文学研究者的身份提出感觉结构这一概念,其本身就必然会更注重文本和经验感受;另一方面是由于情感或感觉本身的不确定性和变化性,这就使得感觉结构很难有一套清晰的理论框架,这也是今天西方情感理论所面临的问题。不过,当伊格尔顿在2003年出版《理论之后》时,他也同样强调要面向现实经验,当理论的黄金年代过去后,我们要突破后结构主义理论的晦涩乏味,所以在感觉结构提出半个多世纪后,它其实又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伊格尔顿除了批评威廉斯的理论缺乏体系性外,还针对其感觉结构为核心的文化唯物主义进行批判。因为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注重的是文化的物质属性,注重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经验、感觉,注重文化的基础作用。所以他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基础与上层建筑”》一文中批判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概念,“任何导向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现代方法,都必始于起决定作用的基础和被决定的上层建筑这一命题的思考。但事实上,从严格意义的理论视角来看,这不是我们应选择的起点”[6]。与此相反,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捍卫者,伊格尔顿则认为威廉斯过度强调文化的物质性,也过度简化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模式。因此,“文化主义的要害是浑然不顾以下情况,即:不管人类是何种生物,他们首先是自然的物质的客体;如果不站在客观的立场看问题,自然的客体和物质的客体之间的关系便无从谈起;包括客观化的关系问题也无从谈起;再者,人是自然的物质的客体这一事实便成了人类有可能投身于更多一些创造性而少一些令人乏味的一切事物的先决条件”[7]。所以,伊格尔顿不认同威廉斯所提出的文化可以取代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讨论模式,但这种批评其实是过于苛刻的,因为威廉斯提出感觉结构和文化唯物主义有其具体的历史语境,是针对当时僵化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而言的。伊格尔顿其实是以一个坚定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对威廉斯提出质疑,这也符合其对经验主义的一贯否定态度。
如果说伊格尔顿认为威廉斯过度重视文化的基础地位和物质性,那么,被称为“文化研究之父”的霍尔(Stuart Hall)则认为威廉斯的文化谈得还不够彻底。所以在其著名的《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一文中,霍尔认为“文化主义者将各种意识形式和文化都定义为集合体。但是,他们到此就止步不前了,在文化和语言方面远没有提出根本性的问题,即主体被他/她在其中思考的文化范畴所‘言说’,而不是‘言说它们(范畴)’”[8]。威廉斯在提出感觉结构这一概念时,虽然能看到其对结构的重视,但在霍尔看来,这种结构仍然是一种文化整体的结构,仅仅谈论文化的整体性是不够的,还应该强调结构内部的冲突和对立。如果仅仅把感觉或者文化视为一种整体的社会经验,而缺少具体的结构分析,那么这就是一种肤浅的人道主义。也就是说,在整体的文化中,个体的特殊性消失了,成为被动言说的主体,而不是主动行为者。这也是霍尔后来在分析大众文化时,吸收了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理论的原因,通过对两种范式的综合,使得文化研究摆脱了文化主义/结构主义范式之争的危机。
感觉结构其实并没有一个准确、清晰的定义,但概括来说,其主要指一种不断变化着的社会经验,一种当下状态的实践意识。如果从威廉斯提出这一概念时的对话对象来考察,可以更进一步了解感觉结构的特点,也可以发现其理论局限的原因。首先是以考德威尔(C.Caudwel)为代表的英国传统马克思主义,威廉斯所反对的正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简单关系,强调感觉经验和文化的物质生产性;其次是以利维斯为代表的文化精英主义,感觉结构强调的是普通人的生活经验,而不是少数精英或者传统的高雅文学形式;最后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意识形态理论,在阿尔都塞看来,我们都是在意识形态的控制下去认识自我与世界,主体也是虚假的幻觉,是被意识形态所塑造的,人们认为自己可以主宰自己的选择,主宰自己的思想和人生,这其实都是统治者主导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但这其实夸大了意识形态的主导功能,忽视了人们在主导意识形态下的反抗力量。而威廉斯的感觉结构是和新兴文化相关联,这种感觉还未形成统一固定的集体意识形态,但这种共同的感觉又是有一定结构关联的,而不是毫不相关之物。所以从某种程度来看,威廉斯的理论受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文化霸权的思想影响更大,文化霸权是国家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不断斗争、协商的结果,而不是像阿尔都塞强调意识形态的无往不胜,感觉结构和文化霸权类似,是在主导意识形态和当下大众经验的矛盾场域中出现并不断变化的。除此之外,威廉斯还试图打破一系列的二元对立思维,认为感觉既可以是社会性的也可以是个体性的,情感结构既包含感性、瞬间的体验,也包含理性、稳定的结构关系。但从当代情感理论的发展来看,威廉斯的最大贡献是强调了感觉结构是“不断变化的过程”,因为传统的文学或文本分析是把经验当做固定的、完成的东西来对待,就像人们把情感当做某种固定的属性或状态来对待一样。
深化水利建设与管理体制改革 为水利改革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孙继昌(23.9)
从威廉斯的著作来看,无论是最早期的《电影序言》(1954),还是后来的《文化与社会》(1958)、《漫长的革命》(1961)和《马克思主义与文学》(1977)等著作,“感觉结构”都一直贯穿其中。在《电影序言》中,威廉斯第一次提出了“感觉结构”这一术语,认为我们在分析每个时代的艺术或者文化时,只是“把每种因素当做沉积物来考察,但是在鲜活的时代经验中,每种因素都是溶解于其中的,是某个复杂总体不可分离的一部分”[2]。例如电影在当时作为一种新的戏剧形式,其出现不仅与技术变革相关,还与整个社会及人们的感觉结构的变化相关。这种感觉结构是总体性的共同经验,不能被分割概括,而是要在鲜活的生活经验中去把握,各种文本正是记录这些鲜活经验的载体,所以分析文本的感觉结构也就成为了把握时代经验的重要途径。
三、“情感转向”的兴起与威廉斯的当代意义
从“感觉结构”概念的发展以及人们对这一概念的态度出发,其实可以看出当时文化研究理论的兴起与危机。威廉斯提出“感觉结构”,强调文化是“日常的、整体的”生活方式,是为了与利维斯的文化精英主义、考德威尔等人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相对抗。当美国的大众文化在战后全面进入英国社会,当福利国家概念盛行、工人阶级反抗热情消退,传统的精英主义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已经不能解释当时的社会现象,所以威廉斯认为要从日常经验出发重新审视社会和文化,这是“感觉结构”概念兴起的背景,也是英国文化研究兴起的背景。
根据Q系统支护图,Ⅰ类—Ⅳ类围岩不需要钢肋或钢拱架,Ⅴ类围岩需要钢肋或钢拱架,因Ⅴ类围岩覆盖的Q值范围较大,如果依据Q<0.1进行支护设计,可能会造成过度支护,因此Ⅴ类围岩设计以Q=0.1为基准,如果实际开挖Q值出现低于0.1的情况则重新制定相应的支护方案,Q<0.1时,围岩在锚喷支护的基础上再增加钢肋或钢拱架加强。钢拱架的间距可采用1.3 m。
1.无菌采取病猪的心血、肝、脾、淋巴结涂片,革兰氏染色及美蓝色显微镜检查,可见少量单位或2~3个并列的革兰氏阳性球菌。
进入20世纪末,特别是近十多年来,文化研究的重心又发生了转移,情感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因为人们越来越发现传统的分析工具和理论不能体现人类经验的核心问题。几乎所有人文学科都在讨论情感问题,人类学、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传播学、教育学和文化研究等学科及研究领域都相继出现了所谓的“情感转向”(affective turn)。现代社会的剧烈变革这一过程不仅是物质、文化和符号等一套系统的转变,还是社会情感空间的转变和建构,人的内在需要、人本身的复杂性、完整性被置于了一个更加重要的地位。有学者就认为,在当下,“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中充斥各种关于情绪(emotion)、气氛(atmosphere)、感觉(feeling)的理论,而且常常和威廉斯关于物质、社会和情感结构的想法大致相符”[11]2。当然,这里的情感不仅仅指人们的喜怒哀乐等被命名了具体情绪,而是关注情感力量的变化过程,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暂时没有被语言命名的领域。
在这里,感觉结构已经不完全是威廉斯早期著作中的“不可分割的共同经验”,而是与新兴的文化因素有关,“感觉结构可以被定义为溶解流动中的社会经验,被定义为同那些已经沉淀出来的、更加明显可见的、更为直接可用的社会意义构形迥然有别的东西,所以不管怎样讲,并不是所有的艺术都与同时代的感觉结构有关。大多数现行艺术的有效构形都同那些已经非常明显的社会构形,即主导的或残余的构形相关,而同新兴的构形相关的(尽管这种相关常常表现为原有形式当中出现的改形或反常状态)则主要是溶解流动状态的感觉结构”[4]143。感觉结构在这里总是和新兴文化或新阶级相关,而不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官方文化,因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已经固化定型,而新兴的文化则仍处于变动之中。所以后来也有很多人认为威廉斯的感觉结构天生带有反对霸权的色彩,因为感觉结构所处的新兴文化与主导文化时刻都处于斗争之中。
那么,这种新的情感理论与威廉斯的感觉结构有什么区别呢?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社会学教授派翠西亚·蒂奇内托·克劳馥(Patricia Ticineto Clough)就在其主编的《情感转向:社会的理论化》(TheAffectiveTurn:TheorizingtheSocial)一书中收录了诸多社会学、文化研究领域学者对情感讨论的文章,她认为这些文章“探索了最近批判理论的情感转向,特别是情感的概念化,这种概念化遵循的是从德勒兹、瓜塔里回到斯宾诺莎、柏格森的理论路径……对这些学者而言,情感一般指身体感受/影响(affect)和被感受/影响(affected)的能力,或是身体行动、参与、沟通能力的增强和减弱”[13]。可以看出,这里的情感绝不仅仅是我们一般所理解的人的喜怒哀乐等情绪,而是指情感力量的变化,既可以是主动感受,也可以是被动受影响,既注重静态的情绪,也注重动态的感受。而威廉斯的感觉则更抽象概括,与经验类似,与世界观和意识形态类似。两者概念的差异也蕴含了理论背景的不同,如果说威廉斯的感觉结构是受到当时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转向的影响,那么最新的情感理论则可以从德勒兹(Gilles Deleuze)追溯到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这是一条与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和马克思完全不同的理论路径。
图10为两种电流供电情况下振动加速度频谱。对比正弦波供电,当逆变器供电时,振动幅值整体增加。不同电流供电下振动加速度的最大幅值点均出现在8 500 Hz,9 533 Hz,10 700 Hz,11 400 Hz附近,接近模态分析结果中0阶和8阶固有频率。开关频率10 kHz附近振动加速度增加较大,究其原因是引入逆变器开关频率的谐波电流加剧了高频段的结构共振。
虽然德勒兹和威廉斯大致都在同一时期对情感和感觉结构进行研究,但二者几乎没有交集,前者多被视为后现代理论的代表人物,而后者则是文化研究理论的奠基者。德勒兹重新激活了斯宾诺莎《伦理学》中的情感概念(情感是一种行动的力量),但又赋予了情感更多含义,认为情感是“非人的”(nonhuman),是生成(becoming),是强度(intensity),是纯粹力量的潜在(virtual)变化。情感是“非人”的,意味着我们应该跳出主体和人的视角,以一种他者的目光,或者从微观的视角出发去考察情感;情感是“生成”,意味着情感是处于持续变化的过程中,而不是某种已经确定静止的情感状态;情感是“强度”,意味着情感充满着性质差异,不能用数量来测量表示;情感是“潜在”,意味着情感力量的变化和不确定性,是充满活力和潜能的。
所以,情感对德勒兹而言不再是主体内部的某种情绪,不是人能够拥有或者否定的对象,而是可以理解为一种重新定义我们身体甚至生命的方法。从情感出发,我们的身体可以“通过经纬度来界定,也即,那些归属于它的物质元素的集合,这些元素处于某些动与静、快与慢的关系之中(经度);它所能产生的强度性的情感的集合,这些情感处于某种力量或某种力量的程度之中(纬度)”[14],经度是物质元素的动静关系,纬度则是情感力量的强度变化。例如,当我们把台风理解为广泛意义上的“身体”时,会把它定义为某些空气分子和水分子的集合,正在由东北向西南运动,有几级强度。这就是一种微观的分析方式,通过运动速度和情感强度,可以更好的揭示生命本身的复杂多变。当我们从宏观的概念——只用台风来定义这种自然现象时,必然会导致其复杂性和丰富性的缩减(所以应该描述其运动和强度,才能把此一台风同彼一台风区别开来)。正如我们用男人/女人、进步/落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等宏观概念来分析某一事物或现象时,个体的差异和独特性就会被相似性所取代。所以依据德勒兹的观点,事物的本质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微观层面的分子运动和情感强度。这样,情感的意义就凸显出来了。
而威廉斯也试图反对传统的意识形态或主导文化的叙述方式,当他解释新兴文化的现象时,关注到了人们语言、习俗和文化上出现的新变化,于是创造出“感觉结构”这一术语。“感觉”是关于个人的冲动、压抑等情感因素,“结构”则是指某种内部的张力关系。虽然在理论层面,威廉斯并没有对此展开更进一步的阐释,但在反对主导话语模式,试图描述新兴文化,注重变化的力量这些方面,威廉斯和德勒兹还是有相似之处的。只不过严格来讲,威廉斯的“感觉结构”并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理论体系,也不如德勒兹的“情感”概念具有理论张力。
虽然“感觉”和“情感”在含义和理论背景上都有着明显的差异,但是感觉结构最显著的特征也不在于是否有情感存在,正如美国另一位情感理论研究者塞娜·恩盖(Sianne Ngai)所说的,“威廉斯并没有分析情绪(emotion)或情感(affect),而是有策略地运用感觉现象的整体来拓展社会批判的存在领域和方法”[15]。的确,威廉斯在选用“感觉”这个术语时也只是为了使其与“意识形态”等概念区别,他想寻找一个类似“经验”“情感”的词语来建构其理论,但经验偏向于过去时态,而一般的情感则太个人化,“感觉”也只是勉强可以表达文化的变动性、瞬间性、当下性特征。其实,如果从今天西方批判理论研究领域来看,我们可以为威廉斯寻找到一个更合适的词语,这个关键词就是“情感”(affect)。
那么,为什么说“情感”是威廉斯一直寻找但又未采用的词语呢?从威廉斯的思想背景来看,他主要是受英国经验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影响,通过强调文化的经验感受来调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矛盾(如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当代的情感理论所采用的是affect一词,这个词源于德勒兹对斯宾诺莎情感理论的重新阐释(是德勒兹首先把情感和类似概念区别开来),对于威廉斯来说,无论是斯宾诺莎还是德勒兹,都不是他当时所重视或能借鉴的。但“感觉结构”强调变化,注重感觉的个人性与社会性,这都与最新的情感理论在诸多地方不谋而合,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感觉结构”在当下的意义。
一只巨大的白鹫当先从天空俯冲而下,落在了天葬台对面的高坡上。巨大的翅膀,鼓起狂烈的风,将坡上的荒草吹倒了大片。随后,更多的白鹫随之落下。它们站在高坡上,探头缩脑地朝着天葬台上的尸体张望。
具体来看,相比于威廉斯的感觉结构,新的情感理论更加明确了情感的范围。根据格罗斯伯格的归纳,大致存在以下几种关于情感的假设:“首先,它是非表征的(或译为非再现)、非认知的、表意的;其次,它不是自觉的和无意识的,因此是无主体的和先于个体的,虽然它可能是主体化的;最后,最为强调存在,或以密集的质量存在。”[12]196从这些枯燥、拗口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新的情感理论绝不仅仅是指主体的喜怒哀乐之情,而是有着更为复杂、深刻的哲学思考。简单来说,情感不再注重理性思考,而是研究感官和身体体验;不重视表征或再现的对象,而是关注情感本身;不谈论事物的本质,而是谈论事物的强度……当我们用理性来衡量情感,当我们用同一性来取代生命和人的复杂性,当我们用确定的本质来研究不确定的当下时,解释的有效性也正面临越来越多的质疑。大众文化理论兴起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传统的理论已无法完全解释新兴文化,这一问题在当下更是显得尤为迫切。面对恐怖主义、特朗普当选、网红现象以及各种情感爆发导致的公共事件,我们发现人们的行为语言变得越来越非理性化,如何处理一直以来被理性所放逐的灰色地带,这就需要一种新的情感理论,需要人们重新关注个体的复杂性和差异性。
威廉斯的贡献在于唤醒对人的重视,强调感觉和经验的重要性,并认为这种感觉经验永远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因而文化也不仅仅是被定型了的、过去时态的文化,而应该是当下的、具有无限可能的文化。而新的情感理论正是着眼于情感的不确定性,注重情感的变化过程,可以说是把威廉斯的“感觉结构”这一术语具体化、概念化了,使得感觉或情感等概念具备了“理论旅行”的可能。所以,我们并不是要解释“情感”或者“感觉”是什么,而是为了探索情感理论对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在这一语境下,“我们更倾向于采用在一般意义上被雷蒙·威廉斯所唤起的情感概念(notion of affectivity)——作为操纵我们习性的精密设施,作为社会情境中在场和参与的方式”[11]8。或者如威廉斯所言,“一个成功的社会主义运动不仅是一场实际的、有组织的运动,也将是一场充满情感/感觉(feeling)和想象的运动。不是那种微弱意义上的想象和情感——‘想象未来’(这是浪费时间)或者‘事情的情感/情绪面’(emotional side)。相反,我们必须了解并相互提醒:一种政治与经济结构之间的联系、文化与教育结构之间的联系,还有情感/感觉与相互关系之间的联系,这也许最困难,但它却是我们进行任何斗争的直接资源。”[16][注]译文有改动。参见Raymond Williams,Resources of Hope: Culture,Democracy,Socialism. London & New York: Verso,1989,p. 76.的确,把握情感与其他要素的联系是困难的,但这也是我们分析文化冲突与可能性时的有力理论资源,是我们未来希望的源泉。
【参考文献】
[1] 布莱恩·马苏米.虚拟的寓言:运动,情感,感觉[M].严蓓雯,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33.
[2] WIllIAMS R,ORROM M.Preface to film[M].London:Film Drama Limited,1954:21.
[3] 雷蒙德·威廉斯.漫长的革命[M].倪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4] 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王尔勃,周莉,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5] EAGLETON T.Criticism and Ideology[M].London:Verso,1978:7.
[6] WIllIAMS R.Base and superstructure in marxist cultural theory[J].New Left Review,1973,82:1.
[7] 特里·伊格尔顿,张丽芬.再论基础与上层建筑[J].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02(1):452-462.
[8] 斯图亚特·霍尔,孟登迎.文化研究:两种范式[J].文化研究,2013(1):303-325.
[9] 斯图亚特·霍尔,孟登迎.文化研究及其理论遗产[J].上海文化,2015(2):48-62.
[10] 斯图亚特·霍尔.接合理论与后马克思主义:斯图亚特·霍尔访谈[M]∥周凡,李惠斌.后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196.
[11] SHARMA D,TYGSTRUP F.Structures of Feeling:Affectivity and the Study of Culture[M].Berlin:De Gruyter,2015.
[12] 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文化研究的未来[M].庄鹏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13] CLOUGH P T.The Affective Turn:Theorizing the Social[M].NC:Duke University Press,2007:1.
[14] 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千高原(卷2)[M].姜宇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367.
[15] NGAI S.Ugly feelings[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360.
[16] 雷蒙·威廉斯.希望的源泉:文化、民主、社会主义[M].祁阿红,吴晓妹,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84.
FromStructureofFeelingtoAffectiveTurn:TheRelationshipbetweenRaymondWilliamsandContemporaryWesternAffectTheory
HAO Qiang
Abstract:Structure of feeling is the core concept of Raymond Williams′s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oughts,which combines the perceptual experience with the rational structure and emphasizes certain elements that cannot be covered by ideology.However,Williams over-emphasized the empirical description and failed to systematically produce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which was also criticized by Terry Eagleton and Stuart Hall.In recent years,the rise of the affective turn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as caused the shift of the focus of cultural studies from the language structure to the emotional experience,which provides a new opportunity to re-examine the significance of William’s structure of feeling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Keywords:Raymond Williams;structure of feeling;cultural materialism;culture studies;affective turn
中图分类号:G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19)04-0012-08
作者简介:郝 强,山西大学新闻学院讲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文学博士,从事文化研究与当代西方批评理论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文化诗学视阈下的21世纪西方文论思潮研究”(16JJD750010)
[责任编辑 林雪漫]
标签:文化论文; 感觉论文; 结构论文; 情感论文; 威廉斯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心理学论文; 心理过程与心理状态论文;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论文;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文化诗学视阈下的 21 世纪西方文论思潮研究"; (16JJD750010)论文; 山西大学新闻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