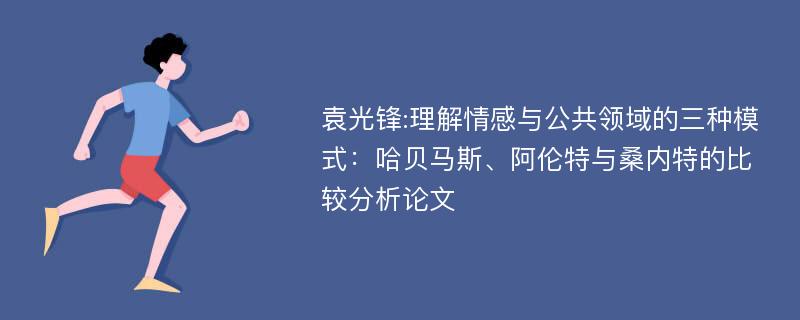
摘 要:情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得到越来越多的严肃的对待。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被认为是理性主义的范式,重视认知的层面,但哈贝马斯关于“共情”、“角色承担”的讨论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关于情感与公共领域的线索。阿伦特批评了法国大革命中的“同情”政治,但阿伦特对于情感的看法并非如此简单,在其他的文本中,阿伦特向我们展现了其对情感的其他观点。桑内特主要讨论了“亲密关系”与公共领域之关系,认为现代社会的“自恋”和对于“亲密性”的追逐导致了公共人的衰落,这有助于我们理解电子媒介时代的交往与公共领域。对三者的对比分析,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情感与公共领域的更为多元的理解。
关键词:情感;公共领域;公共生活;亲密关系
一、情感与公共领域
在关于公共领域的讨论中,情感经常被视为“一个麻烦制造者,侵入了不属于它的地方,破坏了我们对于审议能力的不受干扰的运用”[1]。广为接受的是哈贝马斯的理性主义范式。但近些年来,随着人们对于“情感”的认知日益加深,“理性-情感”的二元论遭受质疑,情感在公共商议、公共领域中的价值开始被重新阐释[2]。情感不再被认为仅仅是损害健全的认知,相反,它也是健全认知的必要构成部分;亦有研究回到启蒙情感主义的传统,认为“同情”有助于普遍的道德原则的形成[3]。这些研究对话的主要是以哈贝马斯、罗尔斯为代表的理性主义传统。但在《公共人的衰落》“中文版序”中,桑内特自言:“你们可以把西方对公共生活的理解当成一个精神的等边三角形。其中一条是哈贝马斯的边,‘公共’的构成要素就是人们试图超越他们自身的物质利益的斗争。第二条是阿伦特的边,‘公共’由一些特殊的市民组成,这些市民彼此之间进行非人格的、平等的对话,他们拒绝用他们的同一性语言来交谈。第三条是以我和我的学派为代表的边,‘公共’是形象而具体的,它主要研究人们和陌生人说话的方式。”[4]哈贝马斯、阿伦特与桑内特构成了公共领域、公共生活研究的三个主要理论脉络。
阿伦特和桑内特对于情感也有很多的讨论,但“情感与公共领域”这一脉络的研究对两者关注不够。人们熟知的是阿伦特在《论革命》中对于“同情”的批判,但阿伦特的其他著作则显示她对于“情感”的理解没有那么简单。桑内特讨论的是“亲密关系”对于公共领域的影响,身处电子媒介时代的人们理应更关注这样一种探讨情感与公共领域的视角,但实际上却较少看到相关的研究。此外,哈贝马斯自己对于“情感”的理解也非“理性主义”的标签所能涵盖,哈贝马斯的后期文本显示了他对于情感的复杂态度。现有的研究却往往把哈贝马斯贴上“理性主义”的标签,通过重新阐释“情感”与其对话,没有能够关注“情感”在哈贝马斯思想中的不同面向。本文回到公共领域理论的这三个起点,分析哈贝马斯、阿伦特和桑内特是如何论述情感与公共领域、公共生活之关系的,希望通过对三者的比较分析,展示情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多种关联模式,这有助于建构我们在讨论公共领域和公共生活时对于“情感”的想象。
二、哈贝马斯:“共情”与“角色承担”
哈贝马斯在探讨公共领域、审议、交往行为的时候,非常强调理性和认知的价值。马库斯(Marcus,G.E.)指出,哈贝马斯的姿态是众所周知的:为了让公众做出理性的决策,必须创造近乎完美的言语条件,所谓的“近乎完美的言语条件”是指在其中,所有参与者的理性协商是公共政策的唯一决定因素,人们能够表达理性和实践审议,非常明确的是,在哈贝马斯的思想中,情感会破坏理性[1]。哈贝马斯甚至被称为“认知主义的理论家”(cognitivist theorists)[5]。的确,哈贝马斯非常看重理性的能力,在其著作的表述中,也主要使用了与“理性”相关的术语,但就此认为“情感”在他的思想中没有多少意义,也是不确切的。
集中式新能源发电产生的纯技术问题基本都与新能源发电和传输中使用电力电子器件相关,体现为:遇交流系统故障时,换流站容易出现换相失败;换流站交流出线重合闸失败时,交流出线断路器可能不能成功开断短路电流,从而导致故障范围扩大;新能源发电的某些电力电子特征会影响电压稳定及产生次/超同步振荡;新能源发电相关设备的非线性、直流与非工频性会带来谐波。
可得出4种典型负荷分布状况时,LGJ-240架空裸导线的最大允许供电半径随中压线路负荷的变化趋势,具体情况如图5所示。
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划分了三种公共领域的类型:代表型公共领域、文学公共领域与政治公共领域。新闻传播学、政治学等研究领域常使用的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多指“政治公共领域”,但文学公共领域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它是进入政治公共领域的中介,哈贝马斯说,“以文学公共领域为中介,与公众相关的私人性的经验关系也进入了政治公共领域。”[6]与政治公共领域不同,文学公共领域主要是对人性、私人性的讨论,通过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哈贝马斯认为,“作者、作品以及读者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内心对‘人性’、自我认识以及同情深感兴趣的私人相互之间的亲密关系。”[6]在“他们组成了以文学讨论为主的公共领域”中,“通过文学讨论,源自私人领域的主体性对自身有了清楚的认识”[6]。这种对于私人性、人性的认识,虽然不具有政治公共领域的功能,但也是一个启蒙的过程。文学公共领域主要由小说和新闻构成,其中,最重要的不是“理性”的逻辑和认知,而是“不断地交流情感体验。”[7]可见,“情感”的交流在文学公共领域的形成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它亦有助于启蒙主体性的建构。在政治学和新闻传播学领域的研究中,文学公共领域的概念虽然没有得到像“政治公共领域”一样的重视,但也有一些学者认识到了这一概念对于理解电视公共领域、特定时代的文学作品的意义。比如麦圭根将这一概念扩展为“文化公共领域”,建议我们重视审美的、情感的传播方式在公共领域中的意义[8]。
阿伦特对于法国大革命中的“同情”的担忧本质上是对“怜悯”的反公共性、反交流性的担忧。要理解阿伦特对“同情”的批评,需要先理解阿伦特的思想渊源和背景。从某种意义上讲,阿伦特对于“同情”和“怜悯”的批判也部分来自西方的传统。Heins指出,阿伦特生活在一个这样的世界:情感是非理性的、动物式的,是对理性的破坏,因此,情感被与大众的黑暗力量联系在一起[15]。根据阿伦特的观点,如果由“情感”支配,公共事务就不可能是民主的,不管它有多高尚[15]。她总是警告集体情感的唤醒带来的理性的颠覆[15]。阿伦特的思想根底依然没有脱离西方理性主义的传统,是在理性主义的框架下来讨论情感的,“阿伦特在很多方面都延续了情感与理性的经典区分,以及相应的公共领域的理念,即只承认理性”[15]。
哈贝马斯赋予情感以一定的价值,与他的交往行为理论和“角色承担”的概念有关。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中,“角色承担”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哈贝马斯的对话伦理要求参与者能够进行角色承担,即每一位参与者能够站在他人的立场,“每个人都必须将自己置于他人的位置”[9]。在哈贝马斯的话语模式中,这种换位思考要具有普遍性和相互性,才能够将它融入到达成理性共识的过程之中[9]。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即同情、共情)对于达到更好的“角色承担”和“换位思考”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要“站在他人的位置”就不仅需要知道他人的态度、价值观、认知,还需要体会“喜怒哀乐”。哈贝马斯承认,“同情”在话语伦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能够支持“角色承担”和提供团结的基础,“同情”能够帮助参与者站在他人的立场[10]。当然,我们也不能高估哈贝马斯对于情感的评价,对于哈贝马斯来说,“角色承担”首先是一个认知的活动,他限制了情感的角色[10],“即便感情在公众审议中的地位得到了一定的承认,但很明显哈贝马斯的政治理论更依赖于公民的理性,而非感情和想象力”[3]。即便如此,哈贝马斯关于同情能力与角色承担、审议之间的关系,依然为我们理解情感在公共领域、公民审议中的意义提供了新的视角。
三、阿伦特:情感的反交流性与情感缺乏的后果
1.教师由单能型向多能型转变。随着移动时代的到来,教育教学领域有了更大的改变,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除了具备专业知识、职业技能和素养外,还应掌握现代教育技术和计算机应用等,成为多技能型的教师。教师应该以学生为主,根据学生个性差异安排不同的学习听读内容,鼓励学生做感兴趣的事情。充分利用大学生爱玩手机的心理,让学生利用手机学习功能练习听读英语。[4]
阿伦特批判法国革命中的“同情”,其实批判的是进入公共空间的“同情”。阿伦特“并不否定对具体个体的同情,而否定同情在公共领域里转化为抽象的、观念的怜悯”[13]。作为一种激情,“同情”被引入政治之后,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它的沉默的本质和反交流的特征。阿伦特心中理想的公共空间是可以“言说”的,人与人既能够被联系在一起,同时彼此之间又有“距离”,相互独立。但“同情”这一情感在本质上却有以下几种特征。首先它取消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阿伦特认为,“由于同情取消了距离,也就是取消了人与人之间世界性的空间,而政治问题,整个人类事务领域都居于此空间之中,因此,从政治上说,同情始终是无意义和无结果的。用梅尔维尔的话来说,它无法建立‘持久的制度’。”[12]“同情”“取消了彼此间的利益,后者既把人分开又将他们联合起来。因为同情是一种移情,它取消了距离,缺少那些只有在个体之间的空间中才能出现的品质,尤其是言说的能力,因此,同情就无法进行‘各种预见性或争辩性的言说,而通过言说,一个人才能与另一个人讨论有关双方都感兴趣的事情,因为……它在他们之间。’”[14]其次,“同情”也是沉默的和反交流的,它不喜言说。阿伦特指出,“同情是以高度的激情全身心地投向受苦者本人。痛苦借助纯然自我流露的声音和手势,得以在世界中呈现和被聆听,只有在不得不对之作出回应的时候,同情才会发言。一般说来,同情并非要改变现世的条件以减轻人类的痛苦。不过,如果让同情来做,它就会尽量避免那冗长乏味的劝说、谈判和妥协的过程,即法律和政治的过程,而是为痛苦本身发言,这就要求快捷的行动,这不外乎付诸暴力手段。”[12]
当然,对于哈贝马斯来说,最看重的是政治公共领域的功能。人们对于哈贝马斯“理性主义”的印象,部分也是来自他关于政治公共领域的论述。但哈贝马斯的其他著作则向我们呈现了他对于“情感”的较为复杂的态度。在后期著作中,被贴上“理性主义”标签的哈贝马斯也承认了人的同情能力的价值,弗雷泽指出,“哈贝马斯在晚期著作中承认‘如果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同情,那么任何审议都不可能得出值得普遍认同的结果’。”[3]哈贝马斯认为,成熟的道德判断是认知和情感的结合,他说,“没有每一位人对其他人的共情,审议中就不会有得到普遍同意的解决方案”[9],“这种将认知运作与情感倾向和态度结合起来为规范进行辩护和应用的做法,是成熟的道德判断能力的特征”[9]。
阿伦特对于“情感”的反对并不仅仅表现在其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中。她对于纳粹、犹太人、德国等问题的不少反思,常被人批评是“冷酷无情的”(heartless),对于这些批评,阿伦特回应道,“通常来说,在我看来,‘心’在政治中的作用是值得怀疑的。你和我一样清楚,那些仅仅报告某些令人不快的事实的人,经常被指责为缺乏灵魂,缺乏‘心’,或者缺乏你所说的‘Herzenstakt’。换句话说,我们都知道,这些情感是多么频繁地被用来掩盖事实真相的。”[16]易言之,在阿伦特看来,情感会让我们远离“事实”,面对“事实”,我们需要的是“无情”。对阿伦特来说,选择面对“现实”,就需要拒绝亲密关系和“同情”(empathy)[16]。
阿伦特警惕激情和情感对于原则的破坏[11]。她对政治中情感的批评尤其表现在她对于“同情”的批判上。在其著名的《论革命》一书中,阿伦特对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进行了对比和讨论。与美国革命的“克制”相比,法国大革命向我们展示了更为充沛的革命的激情,尤其是弥漫的“同情”。阿伦特指出,“同情的激情到处蔓延,使一切革命中的仁人志士蠢蠢欲动。”[12]阿伦特认为,在法国大革命中,对于“理性”的贬低和对于“同情”“激情”的张扬,使得法国大革命表现出与美国革命不同的形态,法国革命充满了情感的色彩,同情、愤怒、怜悯、暴力,这些类型的情感都塑造了法国大革命。
但阿伦特在德国战后完成的文章显示了她对“情感”的态度并不是像人们之前认为的那么简单。阿伦特在德国战后完成了《纳粹统治的后果:来自德国的报告》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阿伦特向我们传达了其更多的关于“情感”的信息[15]。战后,德国人并没有能够面对德国的历史和现实,相反,阿伦特认为他们在逃离现实。阿伦特指出,德国人逃避现实的最让人震惊和恐惧的一面是把“事实”当做好像只是一种“意见”(opinions),比如谁开始了最后一次战争,这绝不是一场激烈的辩论,但却有着令人惊讶的各种各样的意见,在德国南部,一位相当聪明的女性说是俄国人发动了战争。这样的观点都以“每个人都有表达观点的权利”作为借口[17]。在阿伦特看来,这是一严肃的事情,不仅因为它经常让讨论变得无望,更重要的是因为德国人真的以为这种混战、这种关于事实的虚无主义的相对论,是民主的本质[17]。
结语:在今后的学习、生活、工作中,将充分发挥学生党员在学生公寓管理和公寓文化建设中的先锋模范作用,从自身做起,积极带动周围同学在实践中“履行宗旨、锻炼党性、提高修养”如何把优秀大学生凝聚在党的旗帜下,是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的重要使命。
桑内特并没有把公共领域的概念限制在政治领域,他没有把所有的“情感”都视为威胁公共生活的因素,反而认为“公共的政治在某种程度上是关于感受他人的情感、欲望、意图以及痛苦”[18]。不同于阿伦特认为的情感的不可言说性,桑内特认为,情感是可以公开表达的,我们与“陌生人”的交往包含我们对情感的表达,并且公共领域中的情感表达与亲密关系领域有区别,“公共世界中的表达是表述一些具备自身的意义、无关乎表达的人是谁的情感状态;而亲密性社会中的情感呈现使得情感的实质取决于呈现它的人。”[4]
四、桑内特:亲密关系与公共领域
在“亲密性的专制统治”[4]之下,人们开始排斥与陌生人交往,因为陌生人带来的是威胁,而不是温暖和亲密的情感体验。桑内特指出,“如果人们过于沉浸在共同体内部面对面的亲密关系中,那么他们就会不愿意去体验那些可能在较为陌生的地方发生的挫折。”[4]相较于与陌生人相处的公共生活,人们更喜欢亲密关系主导的群体生活,在群体中,人们拒绝外部世界的加入,没有改变外部世界的意愿,“群体中的人们通过拒绝那些并不处在群体之内的人而获得了一种友爱的感觉。这种拒绝为群体创造出一种独立于外部世界、免遭外部世界打扰的要求;群体因而不再要求外部世界发生改变”[4]。但,更令人担忧的是,对于“外部世界”的拒绝永无止境,因为,“共同体的成员之间越是亲密,他们的社会交往就会越少。因为这种通过排斥‘外来者’而得以完成的友爱过程从来不会终结,原因即在于‘我们’的形象从来不会固定下来”[4]。为了获得亲密关系,现代社会的人们一方面表现出“自恋主义”,桑内特把“自恋”(自我迷恋)称为“当今时代的新教伦理”[4],认为自恋毁灭了我们的表达技巧,它宣称“废除人们之间的障碍”,但“只会将社会的统治结构照搬进人们的心理”[4]。另一方面,人们也在不断地向他人揭露自己的情感。桑内特把这称为亲密性社会的“两重结构”:“自恋主义在社会关系中被启用了,而向他人揭露自己情感的体验则变得极具破坏性。”[4]
在《论暴力》中,阿伦特又进一步明确了感情与理智的关系,以及感情的价值。阿伦特说:“没有感情既不会导致理智,也不会促进理智。面对‘难以忍受的悲剧’而表现出‘超然与镇定’,也就是说,当不是出于控制而是出于明显的不理解的时候,这种表现就可能是‘恐怖的’。一个人要作出理智的反应,他首先必须被‘感动’。感情的反义词无论如何都不是‘理智’,它或者是感动能力的缺乏,这往往是一种病理现象;或者是多愁善感,这是一种堕落的感情。”[14]这段话的意思是很明显的,阿伦特并不认为“感情与理智”是对立的关系,她既反对没有感情的“理智”,也反对泛滥的感情。就此而言,阿伦特的观点已经与新近的认知心理学、脑神经科学以及受此影响的政治哲学的观点非常接近了。
具象美术作品中的图像符合眼睛看到的情况。中国画里的工笔画属其范畴,其特征是将客观物象的细微之处描绘得非常充分,物象的比例大小、空间的表现都与实际相吻合。但具象美术又不同于摄影,它不是简单的复制客观物象。美术家画什么(人物或场景),都与要表达的主题和目的有关。如五代.周文矩《重屏会棋图》,此图描绘了五代南唐中主与诸弟下棋的情景。画中一丝不拘地表现了人物的活动和人物之间的呼应关系,环境中的陈设与人物衣纹都得到细致入微的刻画。中主端坐正中观棋,画庞丰满,细目微须,仪态气度出类拔萃,与《南唐书》说他"美容止,器宇高迈,性宽仁,有文学"颇为相符。这幅画充分发挥了具象美术纪实存真的独特功能。
桑内特具体分析的是亲密关系对于公共领域/公共生活的影响。他特讲述的公共领域衰落的故事从18世纪中期的巴黎和伦敦开始,这是城市公共生活最繁荣之地。此时,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限尚比较分明,“非人格”支撑着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平衡[4]。但到了19世纪后期,“人格出现在公共领域”[4],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平衡被打破,“人们变得越来越不会表达。人们在乎心理状态的真诚,他们的日常生活变得和表演无关”[4]。陌生人和社会的复杂性对人们来说成为了一种威胁,相反,“那些能够揭露自我、有助于定义自我、发展自我或者改变自我的体验则受到人们的极度关注”[4]。这些变化,最终导致亲密关系成为主导公共领域的原则。真诚、每个人的内心需求、温暖等都成为人与人之间进行交往的要求或目标。桑内特甚至认为有一种“亲密性的意识形态”,他说,“如今人们普遍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是一种好事。如今人们普遍期望从自己和他人的亲密体验和温暖体验中发展出个体的人格。如今人们普遍抱有的迷思是社会的各种坏处都能够被理解成非人格、异化和冷漠的坏处。这三者加起来就变成了一种亲密性的意识形态:全部种类的社会关系越是接近每个人内在的心理需求,就越是真实的、可以信赖的和真诚的。”[4]
桑内特使用的“公共领域”概念,对应的英文术语并不是“public sphere”,而是“public domain”。哈贝马斯、阿伦特主要在政治的层面讨论公共领域,相较而言,桑内特的公共领域和公共生活不仅仅是在政治的意义上。根据桑内特的界定,公共领域是由熟人和陌生人构成,包括一群相互之间差异比较大的人[4]。这一界定的“公共领域”并没有明确的政治功能,而是与“陌生人”一起相处的空间,我们从桑内特对“公共”的定义也可以看出来,桑内特认为,“公共”“意味着一种在亲朋好友的生活之外度过的生活”[4],“‘公共的’行为首先是一种和自我及其直接的经历、处境、需求保持一定距离的行动,其次,这种行动涉及对多元性的体验。”[4]相较于哈贝马斯和阿伦特,桑内特所言的“公共”和“公共领域”都是更广泛的概念。
战后的德国不仅有“事实”与“意见”的混乱,还有道德上的混乱和情感缺乏的问题。Heins指出,战争结束几年之后,在她的《来自德国的报告》中,阿伦特对她遇到的许多德国人普遍缺乏情感和冷酷表达了震惊和困惑,她显然认为这种公民的冷酷是一种严重的政治病态[15]。同一份报告还提到了另外两个重要的考虑因素,这些因素揭示了阿伦特对情感的政治批判的复杂性,在这篇文章中,对阿伦特来说比情感更可怕的东西是完全没有情感[15]。阿伦特说,“这种普遍的情感缺乏,至少是明显的无情,有时被廉价的多愁善感所掩盖,是最明显的外在症状,即一种根深蒂固的、顽固的、有时甚至是恶意的对曾经真实地发生的事情的拒绝面对和屈服。”[17]此时,我们可以发现,阿伦特似乎不是认为“无情”才能让我们面对事实了,相反,她认为在战后德国普遍的明显的“无情”才是对事情的拒绝。Heins指出,经过纳粹的统治之后,德国民众的情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阿伦特注意到战后德国情感的缺乏与“逃离现实的流行”之间的关系。既不感到愧疚,又屈从于灾难性破坏的悲痛,这使得人们不去承认他们历史和当前状态的基本真相,助长了“严重的道德混乱”[15]。战后的德国人不仅逃离现实,而对德国被摧毁的事实,他们还陷入到一种反射式的(reflective)、表面的自怜之中。但是在法国和英国,人们则对战争中的破坏感受到更大的悲伤。德国人还表达非常自负的希望,那就是德国将变成欧洲最现代的国家[17]。基于对战后德国人的情感症状的分析,阿伦特期待新近的认知心理学家的洞见,他们认为情感远远不是只会让我们盲目地面对现实,当新的目标形成和我们的生活必须被重组的时候,它经常帮助我们处理意想不到的事情[15]。
电子媒介技术塑造了我们与“陌生人”的交往关系,极大地增加了我们与“陌生人”接触的机会,但桑内特并不认为电子媒介有助于公共生活的恢复,他认为,“电子传播技术正是一种促使人们不再有公共生活的概念的技术手段。媒体大大加深了社会群体之间的相互了解,但也毫无必要地削弱了它们的实际交往。”[4]桑内特似乎更认可“实际交往”的价值。我们即使不同意他的这一观点,桑内特关于亲密关系、交往与电子媒介的论述,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电子媒介与公共生活的视角。
五、情感与公共生活的多元想象
通过分析哈贝马斯、阿伦特、桑内特的公共领域理论与情感之关系,本文呈现了公共领域与情感关联的三种模式,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这三种模式从不同的侧面观照了情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联系,呈现了情感在公共领域和我们的公共生活中具有的不同价值,有助于建构我们关于“情感”的想象。
哈贝马斯主要是在认知的层面和交往行为的过程中谈论“情感”。尽管哈贝马斯具有很浓厚的理性主义的色彩,但“理性主义”的标签无法完全涵盖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与情感的关系。交往行为中的“理解”和“角色承担”需要情感机制的参与。这样一种公共领域与情感的关系模式,可以激发我们关于“情感”的新的想象。在全球化和电子媒介的时代,许多边界都在模糊,不同文化、不同群体之间的交往更为频繁,跨国的公共领域也在一些议题上形成。重新想象“情感”在认知、理解、交往行为中的价值,将会有助于我们为这些议题提供新的答案。哈贝马斯关于“文学公共领域”中情感的交流与启蒙的关系,也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一些时代的文学作品、文化产品和公共领域的关系。
阿伦特很少明确谈及情感与公共领域、公共生活之间有何种具体的关系,但经由对她的思想的分析,显而易见的是,阿伦特并没有否定“情感”的价值,阿伦特对于法国革命中的“同情”的批判并不代表她对情感的所有看法。没有“情感”的政治反而是危险的,“情感”能够让人们面对政治生活中的“事实”,而非让人们远离“事实”;情感也有助于人们拒绝“政治冷漠”。阿伦特对于“情感”的洞见,尤其适合我们分析特定年代的情感症候与公共生活的关系。
桑内特主要是在公共表演的意义上谈论情感与公共领域之关系。“亲密关系”和“自我迷恋”导致人们拒绝面对陌生人、拒绝参与公共生活,造成了公共人的衰落。这一关联模式对于我们理解电子媒介时代的公共领域、公共生活非常有意义。随着新的媒介技术的产生与广泛应用,人们的关系建构和行为在往新媒介转移,“面对陌生人”成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要经历的事情。如何面对“陌生人”?在“陌生人的世界”,人们如何建构亲密关系?新的形态的亲密关系又是如何影响了人们参与公共生活的方式?桑内特为这些问题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思考路径。在中国,目前最重要的交往媒介是微信,人们在微信上展示自己的私人生活,人们积极地为他人“点赞”,这些建立社会关系的行为如何影响了人们的公共生活,易言之,微信如何改变了人们之间的亲密关系进而影响了公共领域的形态,这些都可以从这一关联模式中得到启发。此外,媒介与社会之间也是互构的关系,放在更广阔的社会变迁视野来看,桑内特的路径也提示我们关注更广泛的社会变迁、媒介变迁与公共生活的兴衰,媒介、城市、家庭、工作制度、公共生活之间的复杂关系,成为我们观察中国公共生活变迁机制的切入口。当下中国,城市日益繁荣,但“宅”文化也在兴盛,类似的“悖论”或许可以从桑内特那儿寻求到答案。
由于城市商业银行的特殊性,自身的风险管理能力和盈利能力相较股份制银行均较差。区块链技术增加了金融风险的传染性和隐蔽性,其在银行的实质性应用将使传统的技术风险、信用风险、法律风险、操作风险披上科技的外衣,导致城市商业银行风险防控再一次重塑。
参考文献:
[1]Marcus G E.The Sentimental Citizen: Emotion in Democratic Politics[M].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0: 5,6.
[2]莎伦·R.克劳斯.公民的激情:道德情感与民主商议[M].谭安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1-29.
[3]迈克尔·L.弗雷泽.同情的启蒙[M].胡靖, 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1-220,217,217.
[4]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M].李继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2(中文版序),21,22,120,428,135,207,49,306,359,460,405,367,367,454,458-459,363,389.
[5]Krause S.Desiring Justice: Motivation and Justification in Rawls and Habermas[J].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 2005,4:364.
[6]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王晓珏,刘北城,宋伟杰,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55,54,55.
[7]Lee, Haiyan.All the Feelings That Are Fit to Print: The Community of Sentiment and the Literary Public Sphere in China, 1900-1918[J].Modern China, 2001, 27(3): 291-327.
[8]Mc Guigan J.The Cultural Public Sphere[J].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005, 8(4): 427-443.
[9]Habermas.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M].Translated by Christian Lenhardt and Shierry Weber Nicholsen.Cambridge: Polity Press,1990:182,viii-ix,viii,202.
[10]Morrell M E.Empathy and Democracy: Feeling, Thinking, and Deliberation[M].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0: 76,76.
[11]Reshaur K.Concepts of Solidarity in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Hannah Arendt[J].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2,25(4):723.
[12]阿伦特.论革命[M].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58,73,73.
[13]孙传钊.阿伦特两论[J].中国图书评论,2011(1):40-48.
[14]菲利普·汉森.历史、政治与公民权:阿伦特传[M].刘佳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247-248,165.
[15]Volker Heins.Reasons of the Heart: Weber and Arendt on Emotion in Politics[J].The European Legacy.2007, 12(6): 716,723,723,725,715-728,725,725,725,725.
[16]Deborah Nelson.The Virtues of Heartlessness: Mary McCarthy, Hannah Arendt, and the Anesthetics of Empathy[J].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2006, 18(1): 92,89.
[17]Hannah Arendt.Essays in Understanding: 1930-1954[M].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erome Kohn.New York:Schocken Books, 1994: 251,251-252,249,251.
[18]Junxi Qian.Re-visioning the Public in Post-reform Urban China: Poetics and Politics in Guangzhou[M].Singapore: Springer,2018:14.
Three Modes of Understanding Emot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Comparative Analysis of Habermas,Arendt and Sennett
YUAN Guangfeng
Abstrac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 is increasingly taken seriously.Habermas's public sphere theory is regarded as the paradigm of rationalism,which attaches importance to cognition,but his discussion of“empathy” and“role taking”provides us with more clues about emot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Arendt criticizes the politics of compassion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but her views on emotion are not so simple.In other works, Arendt shows us her other views on emotion.Sennett mainly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imacy and public sphere, and believes that the “narcissism” and the pursuit of“intimacy” in modern society led to the fall of public man.This is valuable for us to interpret the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sphere in the era of electronic media.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provides us with a more diversified understanding of emot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
Key words: emotion; public sphere; public life; intimacy
DOI:10.19503/j.cnki.1000-2529.2019.04.0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于‘情感’视角的当代中国公共舆论研究”(16CXW021)
作者简介:袁光锋,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江苏南京210023)
(责任编校:文晶)
标签:阿伦论文; 马斯论文; 情感论文; 领域论文; 内特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第4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于‘情感’视角的当代中国公共舆论研究”(16CXW021)论文;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论文; 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