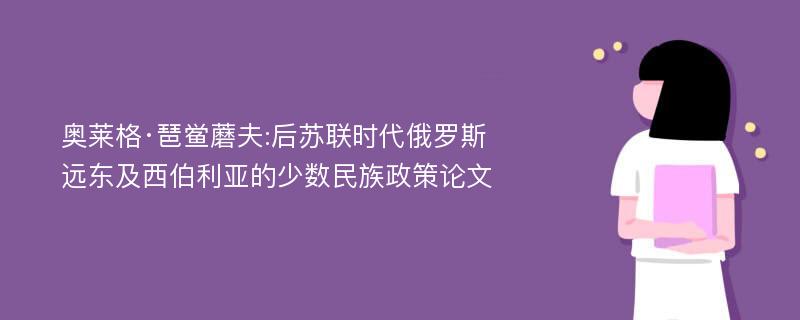
摘 要:对民族/国家边界再生的认知是一个封闭的自我指涉过程,它产生于自身的内部操作,而不是通过信息的输入/输出与其他对象的相互作用的结果。以后苏联时代俄罗斯对远东和西伯利亚的民族政策为例,来阐明这一过程不仅是谈判或社会建设的结果,而且是一种认知结构与民族/国家群体之间形成的复杂的相互关系。同时也阐释了俄罗斯民族政策在社会中产生失望的背景下,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形成的原因。表明失望的期望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回归国家话语后,有助于维护政府的合法性、国家/民族观念的合法性,并激励社会继续进行国家建设进程。
关键词:民族政策;俄罗斯远东;后苏联时代;民族;心理特征综合体
自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先后经历了对爱国主义的失望以及近年来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民族国家的矛盾、对全球市场环境的强烈依赖、少数民族和移民群体的存在、不平等和地区差异的增大、极端的个人主义以及生态问题,都可能使这个社会认识到他们对民族团结和国家独立的信仰是不现实的。然而,任何试图证明已存在的或仍处于设想中的国家和民族边界特征的尝试,以及解构边界特征的尝试,往往都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反而会强化对国家和民族的社会信仰。本文试图以俄罗斯民族政策为例,来说明国家与民族边界的持续存在,实际上是认知结构与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的持续存在。这一现象也与俄罗斯民族志学者史禄国(S.M. Shirokogorov)在近1个世纪前所谈到的“心理特征综合体”相呼应。
在以往俄罗斯民族政策的研究,[注]可参考Jeon B.S. ‘Problemareemigraciikoreycevvrossiiiihetnicheskayaidentichnost’ [Problems of Korean Re-emigrations in Russia and Their Ethnic Identity]. BuryatUniversityReview. no.14(2011):128-131;20. Li, N.G. ‘Etnicheskaya identichnost kak factor sociokulturnoi integratsii’ [Ethnic Identification of Korean Community as a Factor of Sociocultural Integration]. TheoryandPracticeofSocialDevelopment.no.7(2013):48-50。民族国家的形成一般被视为主要民族与少数民族为了构建国家认同性而采取互动策略和谈判的过程。这种互动方法把社会复杂性简化为个人动机,虽然所有的个人动机可能会有不同的经济、宗教、道德、艺术或政治背景[1],但是它们联合起来就会影响所有民族成员的民族性。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它可以深入分析个人的兴趣和情感,但同时也受制于其片面性。它把国家和民族文化形成的过程看作是互动(协商或争端)的结果,从而把民族边界的社会复现性归咎于社团中的个体,然而社团中所有成员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其行为的任意性是不具有共同点的。此外,这种互动方法还根据个体和集体、社会和国家、少数民族和主要民族之间的差异以及个体之间的差异,把经济、政治或宗教简化为对某一既定民族的特定形式的描述。
例如,Niklas Luhmann认为互动主义方法的主要问题在于其将社会简化为个体及其交互作用的总和,并将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这种差异描述为社会身份和个人身份之间的区别。然而,只是因为个人知道如何处理这种差异,社会才能不仅仅作为互动而出现。这种概念的形成仍然是具有社会心理属性的,不适合用来理解社会系统中的高度复杂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不能简单地归咎为个体或个体之间的互动。
没有专门的有关欧洲室内空气质量的法规。在英国,没有一个政府机构负责。公共卫生成果框架(Public Health Outcomes Framework)(2016—2019)令地方当局负责改善空气质量;英国建筑法规部分ADF规定,在施工完成后8 h内,总VOC排放量应低于300 μg/m3。
俄罗斯人类学家史禄国在20世纪初提出的族体理论[2]33-41为互动主义范式提供了新的选择。该理论探讨了被认为是社会复杂性问题的民族划分现象。他把族体定义为一个民族内或民族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过程。族体的存在具有平衡性,也就是说,族体能够很好地适应其内部条件和环境,而且对于外部环境而言,族体也是最具生命力和最稳定的组织。这就意味着历史上任何时候的民族进程都不是民族成员之间谈判的结果,而是民族系统对其所处环境的不同反应。这里所说的“环境”是指一个民族的物质文化发展、社会组织以及心理特征综合体。这与20世纪下半叶发展起来的封闭式自我指涉系统理论相呼应,这就意味着史禄国的理论有助于将以智利生物学家Maturana和Varela[3]、英国数学家George Spencer Brown[4]、英国人类学家Gregory Bateson[5]、美籍奥地利科学家及社会控制论的缔造者Heinz von Foerster[6]、荷兰社会学家Felix Geyer[7]和德国社会学家Niklas Luhmann[8]为代表的有关社会复杂性问题研究的丰富理论体系纳入人类学研究范畴。
族体理论注重区别是好的,但还远远不够。把族体描述为一个系统实际上仍然强调了系统的稳定性、系统控制和系统维护,族体围绕“平衡”这一概念在特定的范围内波动,而“平衡”起源于“动态平衡”[2]35或“心理特征综合体的不平衡”[2]739-745这两个概念。值得引起重视的是,民族平衡是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这两种力量合力形成了它的动态性。这两种力量就是巩固民族统一的向心力和瓦解民族的离心力。史禄国运用社会控制论传统的语言已经开始从一阶控制论向二阶控制论过渡,但这种过渡尚未完成。换言之,在描述负反馈回路和正反馈回路之间的相互作用时,这种状态就显露出来了[9]。
⑩松冈环:《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侵华日军原士兵102人的证言》,新内如等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63~64页。
采访中的问题提出,本来就是网上搜索攒出来的,老总追问就露馅。针对我们关心的问题,发出后产业界不关心;针对产业问题,同代人不感兴趣。
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土著民和移民两个少数人群代表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模式来体现民族差异与追求民族团结之间的关系。例如,普里莫斯基和哈巴罗夫斯基地区的乌德格或纳奈等通古斯人的当地政权充分说明了保护民族文化是进一步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关键条件。然而,像俄罗斯高丽人这样的移民群体却采取了相反的立场,即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民族因素。种种立场取决于政府将少数民族纳入官僚等级制度的能力。根据俄罗斯地区官员的逻辑,土著民在经济和政治上依赖政府,而政府在其行动中享有自由。少数民族机构的进一步发展只会增加这种依赖性和独立性。由于韩国和朝鲜之间的关系,俄罗斯高丽人很难融入官僚机构。这意味着俄罗斯政府竭尽全力阻止民族聚居区的形成。
把“适应”这一概念重新定义为自我指涉过程有助于解决这一弱点。史禄国指出,对民族系统的适应是两个同时发生的运动的统一:一是复合体进一步复杂化的运动;二是复合体和构成成分简化的运动。这种自体生成的对适应过程的理解不可能在两种相反的运动中形成平衡的关系,所产生的差异也会在各种社会复杂性水平上形成不对称关系。民族将系统和环境之间的区别再生为统一,这就在两者区别上造成了不对称性,因为系统中的复杂水平总是小于环境的复杂水平。因为民族系统的统一是民族单位与其环境的区别的统一,所以区别的统一意味着这种不对称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不稳定性)总是存在于民族进程的每一个操作中。作为在选择上存在压力,或者作为用来进一步复制和减少自身复杂性的信息,这种不稳定性(未选择的信息)会返回到民族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不是一个平衡的系统,而是一个极其不平衡的系统。
尽管在操作上还具有不稳定性,但这也有助于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外部观察员问题和国家/民族边界的稳定性问题。一个国家/民族的成员可以将自己区别于其他拥有自己稳定环境的群体,但是其信息选择的标准仍然不是很明确,因为每个观察都存在着一个“盲点”。一个国家或民族必须使自己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但是又不能在他们区别的范围内做出区分[11]。如果他们试图观察一个区别,他们必须再找出另外一个区别来观察这个区别,这个区别本身对他们来说是看不见的,并且有自己的“盲点”。区别过程的不可观测性和不可识别性使国家/民族的成员得以保留先前做出的区分,并且不加理解地依赖它,以便提供进一步区分的稳定连通性。
例如,俄罗斯采取了用种族差别来限制社会流动的方法。少数民族成为国家统治政党的成员和高级幕僚,被允准参与由联邦预算支持的各种大型商业项目,而俄罗斯的国家政治秩序取决于联邦政府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共识。该共识的目的是为了应对为获得政治和经济利益而带来的社会不平等和政治不稳定的风险。真正的发展意味着积极向上的社会流动和更大程度的民主化,而这种发展将导致更强烈地要求重新分配财富和权力。这就是为什么绝大多数发展民族文化的政府项目只会对社会产生有限的影响。为了做到这点,俄罗斯联邦和地区的民族政权围绕大城市、港口和具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地区建立“经济特区”来试图吸引外国投资者的投资,并把这些投资者置于多民族官僚机构的管理之下。
然而,这种新的政治体系却对民族共和国有很大的歧视。在2010年代初,联邦政府和国有企业发起了几项运动来控制一些最大和最有利可图的自然资源公司以及属于民族共和国当局的金融机构[35]。换言之,民族共和国当局付出了巨大努力最终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开始把矛头指向民族共和国以及他们的财产,而这些财产是民族共和国的半独立地位的经济基础。自2013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外国制裁的压力造成了各种经济困难,这迫使政府支持的公司寻求其他经济机会以补偿自身业务效率的下降并开始垄断这个国家利润最丰厚的资产。同时,民族共和国的领导人发现他们几乎对这些制裁毫无防御能力。他们所属的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根据其自身的内在逻辑起作用,这种逻辑要求他们对统治阶级有高度的忠诚度,要求其成员具有高度的文化同质性和相同的价值观。因此,民族共和国的领导人再也不能像20世纪90年代初那样调动民族因素,因为他们的财富和政治权力取决于他们是否属于高层政治团体。
一、俄国的民族政策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俄罗斯是尝试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建设民族国家的一个典型例子。作为苏维埃国家更广泛的民族阶级斗争的一部分,“文化素材”对组织少数民族内部的劳资阶级斗争、现代性和传统阶级斗争具有重要意义[13]。在苏联斯大林时期(1928-1953年),政府不鼓励自愿的民族同化,提高了非俄罗斯人民的民族意识。根据这一方法,少数民族被授予自己的国家领土,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拥有自己的民族学校和民族精英。这些民族政策遵循了民族文化建设的苏维埃原则,是俄罗斯社会主义政府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劳资矛盾发展到极致便形成了一种社会主义文化。根据斯大林的主张,不同的民族文化应该把这种斗争作为政党这一整体的不同组成部分[14]。
然而,夺取政权和重新分配资源并没有形成国家的统一。试图消除阶级差别的各种努力和尝试最终不但没有消除阶级差别,反而产生了新的不平等,而这种新的不平等不能简单归结为传统的阶级差别。其结果是团结的道德必然性失去了合法性,社会主义口号下的民族团结的可能性也失去了合法性。社会主义制度崩溃后,俄罗斯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这对正在经历巨大变革的民族政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政府没有试图克服社会的不平等现象,相反地,政府构建了一种民族主义的版本,允许利用这些不平等现象作为同化少数民族和进一步实现现代化的工具。
本文试图以俄罗斯远东民族政策“民族团结”为例,说明这种自我参照的认知机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它揭示了旨在调节国内民族关系的民族政策如何造成了令人失望的结果,这种民族政策既不能达成民族和谐也不能带来民族团结,只能是以追求“和谐”和“统一”为幌子,产生各种内化了的失望情绪。俄罗斯的国家和社会都认为,俄罗斯民族政策的主要目的和最期待的结果是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它意味着,欧洲现代性塑造的心理特征综合体的功能在于寻找调动社会资源的途径,以便利用基于递归认知回路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潜力。这使得国家建设过程更加依赖于各种失望和自我批评,因为作为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新动力来源,它增加了偶然性,从而也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来区分。令人失望的期望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回归到国家话语,这有助于维护政府的合法性、国家/民族观念的合法性以及激励社会继续进行国家建设[12]。
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国家统一(瓦解)”
地方政府利用这种民族自治的要求来表明自己反对民族分裂提倡民族团结的立场。地方政府、警方、甚至是朝鲜裔的俄罗斯领导人都对俄罗斯的朝鲜人表现出消极的态度。他们把民族划分视为俄罗斯国家政权的主要威胁之一。地方警察将其视为政权更迭的原因之一,这尤其表现在车臣共和国的冲突期间以及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分离主义运动盛行的一些地方。他们中的一些人发表反对性文章,认为在普里莫斯基地区建立朝鲜民族自治实际上是朝鲜和韩国为扩大其势力范围而策划的阴谋。俄罗斯当局相信,普里莫斯基地区将成为朝鲜裔俄罗斯人对抗两个朝鲜国家的社会经济和精神影响的斗争场所。因此,他们建议制定更加严格而不是更加宽松的移民法[28]。
这就使得族体理论不能解决一阶控制论的弱点并充分发挥二阶控制论的优势。为了掌握民族系统的复杂性,对内稳态的强调以及随之对负反馈回路的强调都使理论观察者产生了依赖性。正如Felix Geyer所说,系统边界的绘制方式明显地依赖于观察者、依赖于时间,最重要的是依赖于问题[10]。在这个范式中,从技术上讲,史禄国很难提供令人信服的标准来帮助确定系统是否处于平衡状态,而不是根据在适应环境过程中民族系统的波动或精神和心智的反应 (有意识或无意识)来定义。同时,也很难解释为什么民族在繁衍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提供许多事实,这些事实表明当某一特定民族的成员的行为方式与其 “遗传生理-心理特质综合体”所期待的方式相反时,用于民族自我描述的选定信息与实际行为相矛盾。
在土著民族的聚居区内,其民族文化的发展一贯被受到控制。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政府提出了通过国家公园体系来保护土著民族文化的理念[16]。虽然在1970年代早期,苏联就建立了第一个国家公园,但是一直到后苏联时代,才在恢复传统民族文化的背景下提出了环境保护与民族文化保护相结合的思想。建立国家公园的目的是要在经济和政治上把土著人的传统生活方式以及他们与俄罗斯主要民族的关系置于俄罗斯官僚体系的控制之下。他们与俄罗斯大多数官僚阶层的政治和经济的控制下生活方式的关系。在国家公园内,对土著少数民族事务负责的国家机构是俄罗斯联邦的自然资源部,其工作的依据是1995年3月14日的第33部“关于保护自然领土”的联邦法律。例如,这部法律的第三章第三项条款允许自然资源部为保护自然、历史和文化资源和规范旅游和教育活动而利用国家公园限制经济活动及其他无关活动[17]。
(国家公园内)民族(文化保护)与自然环境(保护)的结合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在国家公园的框架下,土著居民的传统生活方式置于自然资源部的监管之下,这就意味着俄罗斯政府将人视为野生自然的一部分,保护民族文化是珍稀物种保护的一部分。这种方法的逻辑表明为了使土著居民和自然环境免受文明的负面影响,民族文化和自然环境需要以俄罗斯官僚机构为代表的文明社会的援助。由于土著居民和自然环境无法以自己的力量来规避文明的负面影响,他们只能借助外部干预来使自然环境保持自然性,使土著居民保持原有的传统。土著居民传统的生活方式与他们所居住区域的自然地理特征相适应,这意味着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对违法行为的制裁来保障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18]。
例如,俄罗斯远东的一些国家公园,比如普里摩斯基地区的“乌德格传说”和哈博罗夫斯基克拉伊的“安尤伊”,其主要目标就是要保护土著民族纳奈和乌得格。而诸如“虎地”或“豹地”等其他国家公园首要目标是保护野生动物,比如阿穆尔虎和远东豹。人与动物之间的这种模糊的相互关系使得北罗迪翁苏连兹加的土著民族支持中心的主任于2014年4月26日在海参崴举行的关于土著民族和国家公园的圆桌会议上宣称老虎比人享有更多的保护,但是这恰恰与宪法所规定的相反[19]。
然而,从俄罗斯联邦/地方政府、俄罗斯主要民族到俄罗斯的土著居民,几乎所有的参与者都对国家公园这一项目产生了令人失望的期望[20]。首先,远东地区的乌得格和纳奈两个土著民族在公园的经历表明,比起积极的方面来国家公园有更多的消极方面:它不仅没有保护土著民族的民族文化,反而严重限制了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而且使他们处于生存的边缘。大多数的土著民族认为国家公园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劣势。比如,在国家公园内他们用来狩猎的地区是有限的,而且他们需要获得狩猎许可证才能继续狩猎。国家公园一直在大规模的砍伐树木和非法捕鱼,这些行为破坏了乌得格和纳奈两个土著民族的传统的生活区域。同时国家公园也未能保护土著民族的神圣之地免遭外来者的破坏,土著民族认为这种破坏是对他们传统的不尊重,给他们带来精神创伤[21]。
俄罗斯的主要民族对国家公园也极其失望。土著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被认为是满足当地居民自给自足的平衡的生态系统开发,对这种广为流传的观点一些俄罗斯政治活动家和知识分子持批评态度。事实上,经济因素在对传统民族商品和诸如狩猎这种传统劳动的产品的高需求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此外,国家公园的旅游和娱乐作用也带来了新的获利机会。例如,他们可以不再为自己的需求而狩猎,而是组织游客参与体育性质的钓鱼或狩猎活动。另一方面,就业机会的缺乏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商品化,同时出现了以经济目标为导向的生态开发。这促使土著人违反以前的生活准则,最终给自然界带来负面的影响[22]。
为探索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保障耕地资源安全,针对钱塘江流域耕地变化情况,借助空间分析、多元统计以及结构方程模型等手段,构建耕地变化驱动因子作用机制的通径模型,分析了钱塘江流域耕地变化的时空动态格局,揭示了耕地变化驱动因素之间的复杂耦合关系。
然而,这些对国家公园项目的种种失望只是加强了官僚控制的合法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效率不是俄罗斯官僚体制所追求的目标,其主要目标是保持这种模棱两可的局势,而这些局势会使远东地区的土著民族和俄罗斯主要民族产生冲突和失望的情绪。政府一般会利用国家公园内的违法案件、腐败、少数民族与主要民族之间的冲突以及对自然界的无节制开发等案件作为证据来证明社会自身不能克服存在问题,并且相互之间不能达成共识。如果没有政府的管理和控制,社会将不仅损害自身的利益,而且会给自然界带来破坏。这意味着少数民族和主要民族都显然需要一个更高的仲裁人来解决冲突局势。地方和联邦当局通常会在冲突发生的时刻以仲裁人的身份出现,许诺要考虑公众舆论、建立另外一个新的工作团段、通过新的法律甚至要建立新的国家公园。这实际上使公众对一个新的官僚机构的管理产生新的积极的期望,到最后这种官僚机构可能会利用民众产生的又一次失望来建立新的期望,周而复始,以此往复[23]。
政府对游说的管控主要是以透明原则为基础。但是如作者所指出的:第一,通过立法可以要求游说人公开其游说活动以及与政府官员的重要接触。这样透明却不一定会收到问责的效果。第二,对游说活动的管控最有效的途径,应该是把重点落在政府官员而不是说客身上,因为前者对公众负有信托责任 (fiduciary obligation),而后者没有。
俄罗斯政府利用生活在俄罗斯远东的俄罗斯高丽人来吸引韩国的投资。20世纪80年代末苏维埃政治局重新考量与韩国的关系,并建立了两国间的直接贸易关系;自1991年俄罗斯联邦和大韩民国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俄罗斯政府一直对韩国的大规模投资寄予厚望。俄罗斯联邦和地方当局把高丽人开始在库页岛上的居住和俄罗斯高丽人再一次从中亚到普里莫斯基地区的迁移看作是韩国参与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佐证。另一方面,他们尽量避免过分强调民族因素,韩国政府一般不和俄罗斯高丽人直接互动,而是通过俄罗斯当局或已融入俄罗斯政治主流的俄罗斯高丽政客们进行政府间层面的合作。
这造成了国家和跨国民族边界之间的矛盾,这一点在俄罗斯高丽人文化自治组织的例子中尤为明显。1996年,为了将俄罗斯的高丽侨民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制度化,联邦政府接受了“自治法”[24]。民族文化自治组织(NCA)是非政府和非地域机构单独形成的民族边界。当俄罗斯高丽人在经济或政治上需要地方/联邦政府的援助时,该法律以矛盾的方式将其纳入俄罗斯官僚机构,但它没有规定如何实施这种援助。这给俄罗斯高丽人造成了非常偶然和危险的情况,因为俄罗斯可以将他们的活动解释为对国家主权的威胁。它提高了民族精英和区域/联邦当局之间非正式妥协的重要性。然而,俄罗斯官僚机构的偶发作用促使这些自治组织依靠于朝韩两国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援助,朝韩两国的这些组织使他们参与不受俄罗斯政府控制的朝鲜族政治和经济活动。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俄罗斯当局的负面预期,从而促使俄罗斯当局加强对俄罗斯高丽人组织的控制,并再次将它们政治化[25]。
然而,这种一直存在的模糊性只会鼓励韩方在与俄罗斯的关系中依赖跨国民族因素。至少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韩国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就提倡在普里莫斯基地区建立韩国自治,他们认为这对俄罗斯和韩国都是非常重要的。民族因素的存在使得韩国一方不仅仅把在俄罗斯远东的经济活动描述为简单的获利,更是将其视为朝鲜民族统一这一更高目标的一部分。从经济角度看,建立高丽人自治可以吸引韩国对普里莫斯基地区的大笔投资,这对于此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诸如跨韩铁路和跨西伯利亚铁路等俄韩项目的实施都有重大的意义。民族主义的观点认为这种自治将是统一朝鲜半岛进程中的重要一步。高丽民族自治被认为将是统一的朝鲜国家的第一个案例,韩国的资本和朝鲜的劳动力将在中立区域内合作共赢。
高丽民族自治的理念在俄罗斯高丽人中也有支持者。这个项目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朝鲜族历史上周期性地出现。每个时期都强调了建立高丽自治合法必要性的不同方面。20世纪30年代初的苏联时期,最早的自治的要求是劳动力自我组织的逻辑产物,苏联的高丽民族自治实际上就是高丽工人自我组织的政治阶级斗争的形式。中亚地区的苏联高丽知识分子在20世纪50年代末组织了所谓的“请愿运动”,他们声称建立民族自治是为了纠正斯大林主义在去斯大林化运动中的遗留问题[26]。苏联朝鲜族自治是为了纠正1937年高丽人集体流配造成的民族文化偏离社会主义的现象,实现社会主义政治和民族文化之间平衡的相互关系。第三次民族自治的要求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苏维埃解体背景下出现的。对自治的要求与1993年9月俄罗斯政府所强调的“俄罗斯高丽人复兴”的精神相吻合。正如一位俄罗斯高丽知识分子所宣称的,“苏联朝鲜人民的复兴意味着恢复所有被遗弃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包括恢复高丽人区域和民族农业苏维埃的权利”[27]。
俄罗斯始终处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外围,这也是影响俄罗斯形成这种民族政策格局的关键因素之一。俄罗斯一方面声称远东地区的发展是俄罗斯21世纪最重要的国家目标,但另一方面又竭尽全力限制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大规模的国有资产私有化,特别是工业、能源和金融部门的私有化,使权利和财富越来越集中在上层官僚手中。真正的发展意味着上层社会的动荡和更多的民主化,同时也意味着财富和权利的重新分配,这势必会带来政治上的不稳定风险。侵吞利用主要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民族边界是保存高层官僚财富和权利的权宜之一。通常情况下,政府会采用经济特区这一发展策略,围绕大城市、港口和具有丰富自然资源的疆域选择一些地区,配以专门立法、优惠政策以及训练有素的劳动力等特殊的经济环境,但是最关键的是大多数人口却被限制进入这样的地区[15]。
三、民族共和国的例子
民族文化是民族共和国领导人与联邦政府就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分配问题进行谈判时的重要工具。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重新考虑俄罗斯联邦政府与各地区之间现有权力划分的必要性显现出来。前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RSFSR)的22个自治共和国已成为俄罗斯联邦发展新政治权力体系的关键因素之一。新当选的总统叶利钦不得不面对分离主义的威胁,否则俄罗斯将重蹈苏联的覆辙。这迫使他寻求包括民族共和国领导人在内的地区领导人的支持和协助,其交换的条件是提供给民族共和国相当大的政治决策权和自主权,以及把民族共和国疆域内最有利可图的苏联资产私有化[29]。因此,在1990年代初,大多数民族共和国领导人与莫斯科签署了一批条约,其目的是与联邦政府建立新的分权制度。具体而言,萨哈(Yakutia)共和国与联邦政府签署了两项条约,授予了共和国宪法保障的以前最大的政治自治权(1992年4月27日),并且通过了萨哈领导人对钻石工业的控制权,而俄国的钻石工业是世界上最大的钻石工业之一[30]。
新确立的政治制度为政治的合法性提供了另一根源,同时也提供了独立于社会的经济资源。21世纪早期标志着苏维埃资产的大规模私有化使民族共和国完全融入了成熟的统治阶级政治体制。出口自然资源以换取外汇已成为普京政权的主要经济基础。各民族共和国作为这一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在外国投资和出口工业的法律和经济制度方面享有特权地位[33]。从那时起,民族共和国的领导人不再需要社会的支持,这大大降低了他们对发展以民族文化和语言为基础的政治制度的兴趣。相反,他们沉迷于对当地民族文化的利用,把民族文化作为忠于联邦政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和普京个人但不忠于社会的象征,认为民族文化是使他们成为主流政治成员的充分条件[34]。
随后,各民族共和国为俄罗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治来源。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诸如“鞑靼斯坦”这样的大多数地区领导人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把联邦和地方政权发展成为了统一的单一政治实体。很显然,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财产大规模私有化导致了高度的经济不平等,并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失望,这在政治上造成了极大的不稳定性。这使得联邦和地区的精英阶层开始保护私有化财产,以使其不受社会和统治阶级中不满于现状的反对者的影响[31]。这意味着民族共和国的领导人必须从反对和抵制莫斯科当局的态度转换为忠于和支持当局的态度,进而重新考虑民族文化的含义。因此,大多数地方民族当局都加入了新成立的“统一俄罗斯”这一政党,支持弗拉基米尔·普京担任总统,以便于反对修正20世纪90年代初大规模的财产私有化,从而保护其财产以及他们在俄罗斯主流政治中的成员地位[32]。
本文以俄罗斯3个不同类型的少数民族为例,从少数民族参与政治进程的角度,阐述了民族因素对俄罗斯民族主义发展的作用。这3个少数民族分别是土著人、移民、西伯利亚及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共和国。他们反映了民族文化在俄罗斯民族主义发展中的3个不同方面。移民群体反映了没有稳固疆域的民族文化的政治化;土著人在特定疆域内具有政治权力,但没有正式的政治机构和主流政治的成员,同时也缺乏稳定的经济基础。各民族共和国在固定的疆域内有自己的政治领导者,具有稳定的经济和政治机构,同时在地方和联邦两级的俄罗斯统治阶层中也有自己的成员。
按照以往的农村公路规划思路,本文选取连通度法、国土系数法、时间序列法(指数平滑模型、非指数平滑模型)、趋势外推法对通州区的公路网规模进行预测[7-10].
例如,联邦政府新的中央集权战略就是用新一代的技术官僚来代替20世纪90年代上台的前几代民族共和国领导人,这些技术官僚与某个地区没有或几乎没有联系,但忠于莫斯科,并无条件的执行中央集权的各种决议。比如,2017年3月6日,谢尔盖·小伊万诺夫被任命俄罗斯和萨哈(雅库提亚)共和国首屈一指的钻石公司的领导者,这个钻石公司的钻石产量占该国钻石产量的95%,占全球钻石开采量的28%。新任命的经理与雅库提亚没有关系,但作为俄罗斯高级政治家、前总统办公厅主任谢尔盖·伊万诺夫的儿子,他与俄罗斯金融体系有着密切的正式关系,并与联邦行政部门有着非正式的联系。雅库提亚权力集中化的另一个步骤是总统博里索夫在一系列丑闻之后辞职,博里索夫被一个出生于列宁格勒名为艾森·尼古拉耶夫的雅库特技术官僚所替代[36]。
最终,联邦政府决定这种政治体系不仅要涉及高层政治家,而且要涉及到整个社会。在2010年代的后期,联邦政府在新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帮助下采取了新的措施来降低民族文化的政治作用。为了应对外国对俄罗斯公司不断加强的制裁以及由于经济衰退而导致的社会失望情绪,莫斯科需要降低反政府活动的潜在风险。高层政治家不再需要民族文化作为忠诚于联邦权力的标志,而是期望依靠民族国家疆域内的高度集中的文化同质的空间。在修正了支持莫斯科的民族共和国的经济基础之后,联邦政府又采用了另外两种战略使文化同质制度化,并剥夺了民族共和国所认为的民族认同的关键要素:语言和领土。
伴随着现在社会的进步与企业的飞速发展,对现在的企业基层党建政工工作有了新的任务,进行基层党建工作的工作人员不能有效改变传统的工作方式与内容,肯定是无法有效发挥党建政工工作的作用。现在许多的企业仍然使用传统的书面文件、工作会议的方式进行党建政工工作,这种“假、大、空”的方式已经不能保证党建工作的有效性了,因此就需要改革这种形式化、表面化党建政工工作方式,增强企业基层党建政工工作的质量。
首先,2018年初,莫斯科颁布了所谓的“母语法”,禁止强制学习当地民族语言,民族共和国在教育上的自由度降低。同时,法律赋予联邦政府对民族地区施加额外压力的机制。从2018年起,任何个人都可以直接向联邦的监督机构投诉强迫学习当地语言的案件,这些案件可以证明对民族共和国实施消极制裁是正当的。其次,经济发展部也于2018年提出俄罗斯联邦新的领土划分,将国家划分为14个行政区。这种划分和包括民族共和国在内的现有地区的边界是不一致的。虽然直至2018年底该项目的前景仍不明朗,但很明显,这是减少各地区和各民族共和国政治权力的另一举措,至少在文字材料上通过剥离一部分民族共和国的领土来提升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均质[37]。
(一)玉米3-5叶期:50%乙草胺乳油80-100ml/亩,或33%除草通乳油100-150ml/亩,对水40-50kg,喷洒行间地表。
四、结论
本文试图说明俄罗斯民族政策和民族/国家边界的重新制定是作为自我参照操作(心理特征综合体)的深层认知机制的表现。心理特征综合体的基本运作划分了民族系统与环境的区别。由于民族系统中的复杂程度总是小于某一个环境,因此每一次操作都造成这种区分双方的不对称性。为了将来的重新调整和减少自身产生的复杂性,这种不稳定性作为压力又回归民族系统来选择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和社会制定和实施民族政策也是基于这种自身产生的不稳定性。民族政策在主要民族和少数民族中都造成了失望情绪。失望的期望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回归国家话语,这种意识形态有助于维护政府的合法性、国家/民族观念的合法性以及激励社会继续进行国家建设。
俄罗斯民族政策的目的是使少数民族正式或非正式地依赖于国家。为了做到这一点,联邦/地区当局将民族组织或个人纳入官僚阶层,从而使其政治化。民族差别有时具有国家间的纽带作用,成为平衡权利的来源,但是政府不能确保少数民族成员始终保持政治忠诚。这种偶然性产生了负面的预期,迫使当局把民族差别当作可能发生的冲突的根源,这就要求少数民族更加依赖强调“民族团结”的俄罗斯。
本区已知共生矿物57种[5](表1),其中主要有用矿物有钽铌铁矿、锰钽矿、黑钽铀矿、铌钽锡石、锆石等。
参考文献:
[1] Yoon, I.J. ‘K'orian Diasǔp'ora: Chaeoe Hanin i Iju, Chǒgǔng, Chǒngch'esǒng’[The Korean Diaspora:Migration, Adaptation, Identity of Overseas Koreans]. Koryeo Daehakgyo Chulpanbu, 2004, 17.
[2] Shirokogoroff S M. Psychomental complex of the Tungus[M].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1935.
[3] Maturana H R, Varela F J. Autopoiesis and cognitio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living[M].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1980:xxii.
[4] Brown G S. Laws of form[M]. New York: Dutton,1979:1.
[5] Bateson G. 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Collected essays in anthropology, psychiatry, evolution, and epistemology[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2:455-471.
[6] Von Foerster H. Understanding understanding: Essays on cybernetics and cognition[M].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2003:287-304.
[7] Geyer F. The march of self-reference[J]. Kybernetes, 2002, 31(7/8):1021-1042.
[8] Luhmann N. Social systems[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9] Maruyama M. The second cybernetics: Deviation-amplifying mutual causal processes [J]. American scientist, 1963, 51(2):164-179.
[10]Geyer F. The challenge of sociocybernetics [J]. Kybernetes, 1995, 24(4): 6-32.
[11]Luhmann N. Autopoiesis als soziologischer Begriff [J]. Sinn, Kommunikation und soziale Differenzierung. Beiträge zu Luhmanns Theorie sozialer Systeme, 1987: 307-324.
[12]Moeller H G. The Radical Luhmann [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28.
[13]Lenin, V.I. Kriticheskiye zametki po nacionalnomu voprosu [Critical Remarks on National Issues]. Vol. 24.Moscow: Political Literature Press, 1967],144.
[14]Stalin, J. ‘Marksizm e nacionalny vopros’ [Marxism and National Question:Collected Works]’. Moscow:Political Literature Press,1958,2:290-367.
[15]Shelomentsev A.G., Terentiyeva T.V., Kozlova O.A., Makarova M.N., Mezhregionalnoye sotrudnichestvo kak institute realizatsii strategii razvitiya regionov Dalnego Vostoka [Inter-Regional Cooperation as an Institute of Implemen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ar East Reg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and Fundamental Researches. No. 11- 3 (2014):417-422.
[16]Tranin, M. ‘Nacionalniye parki: Problemi e perspektivi‘[National Parks: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Moscow: Nauka Press, 1991, 71.
[17]Fyodorova S.N., Etnokulturniy turizm kak perpsektivnoye napravleniye vnutrennego e viezdnogo turizma v Resuplike Sakha (Yakutia) [Ethnocultural Tourism as a Perspective Direction of Inner and Inbound Tourism in the Republic of Sakha (Yakutia)]. North-East Federal University Review. No.1-10 (2013):39- 43.
[18]Sidorenko Sergey, vice-governor of Primorsky Territory Government ‘Nacionalny park pomozhet sohranit prirodu Bikina’ [National Park will help to Preserve Nature of Bikin River] Press release of Primorsky Territory Government, April 18, 2014.
[19]‘Nacionalny park e korenniye narodi. Riski I vozmozhnosti’ [National Park and Indigenous people: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Roundtable at Centre for Support of Indigenous Peoples of the North. Press release, 26 April, 2014.
[20]Ispolnenie porucheniya Putina v Primore zashlo v tupik [The Instructions of President Putin are Deadlocked in Primorsky Territory], Deita News, May 14, 2014 , http://deita.ru/news/society/14.05.2014/4687551-ispolnenie-porucheniya-putina-v-primore-zashlo-v-tupik/ accessed on 29 December 2014.
[21]Seleznyova. ‘Udegeiskaya legenda uniztozhit Udege?’[Udege Legend will destroy Udege?]. Arsenievskie vesti,no. 18 (1102) 2014.
[22]Poddubikov, V. ’Korenniye narodi na puti ustoichivogo razvitiya: tradizionnoye-prirodopolzovaniye b problem sohranenia prirodno-kulturnogo nasledia (opit Altai-Sayanskogo regiona’ [Indigenous People on the Way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raditional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the Problem of Natural-Cultural Legacy Preservation. On the Example of Altai-Sayan region] Contemporary Studies of Social Problems № 3 (2012): 61-69.
[23]Kalachinsky Andrey, ‘Nacionalny park na milion. V doline reki Bikin nakonets budet sozdan nacionalny park razmerom 1 milion gektar’ [One Milion for National Park. The National Park will finally be Constructed in the Valley of Bikin River ... on 1 Million Square Hectares] EastRussia News, 24 March 2015, http://eastrussia.ru/region/5/7248/, accessed on 30 March 2018.
[24]O Nacionalno-kulturnoy avtonomii [On National Cultural Autonomy] Federal Law June 17, 1996 №74.
[25]Filippova E, Filippov V. National-Cultural Autonomies in Post-Soviet Russia: A Dead-End Political Project[C]//Association for Study of Nationalities conference, Sciences Po, Paris,2008, 4.
[26]Lee I.G. ‘Terǒshiaǔi yǒnhaeju pulbǒpch'widǔk kwa yǒnhaeju haninjach'iju sǒllip munje’ [Illegal annexetaion of Primorsky Territory by Russia and Problem of Establishment of Korean Autonomy in Primorsky Territory]. The Kor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36-3 (1997): 295-331.
[27]Nam, S. Koreyskiy natsionalny raion: puti poiska issledovatlia [Korean National Region: The Path of a Researcher] Moscow: Nauka, 1991, 21.
[28]Zabrovskaya, L. “Rosiyskiye koreici e ih svyazi s rodinoy predkov (1990-2003),” [Russian Koreans and their connections with motherland]. Problemy Dalnego Vostoka,2003(5): 39-50.
[29]Koroteeva V. ‘Economicheskiye interesi i nazionalism’ [Economic interests and nationalism]. Moscow: The Russian State University for the Humanities, 2000:76-82.
[30]Yazikova A, ‘Nazionalno-etnicheskiye problema: Rossiyskiy e mirovoy opit ih uregulirovaniya’ [National - ethnic problems: Russian and International Solutions]. Moscow: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udies, 2003:24-25.
[31]Drobizheva L. and others, 'Democratizaciya i obrazi nazionalizma v Rossiyskoy Federazii 1990 godov' [Democratization and Images of Nationalism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during 1990s]. Moscow: “MISL”, 1996, 135.
[32]Belkovsky S.'Sushnost rezhima Putina' [Essence of Putin's Regime]. Moscow: “Algorythm”, 2012, 33.
[33]Yegor B., President of Sakha-Yakutia. 'Nuzhen mehanizm obespechivayuhiy prodvizheniye yakutskih proizvoditeley brilliantov na mirovoy rinok' [We Need Mechanism of Yakutia Diamonds Promotion into Global Market]. Kommersant-Vlast (35), 2014:18-20.
[34]Glebova I. ‘Partiya vlasti: potenzial “pamyati” i aktualnaya politicheskaya praktika’ [Party of Power: Potential of “Memory” and Current Political Practices] //Russian Power and Bureaucratic State. Collection of works of the Russian Studies Laboratory-Part 2. Edited by V.P. Makarenko. Southern Federal University. Rostov on Don: 2015: 230-253.
[35]'Chorniy peredel' [Black Repartition]. Nasha Versia, 13-19.10.2014 no.39 (464):9.
[36]Perzev A. 'Kreml naznachaet gubernatorami molodih tehnokratov-novoye pokoleniye upravlencev. Na samom dele net' [Kermlin Appoints Young Technocrats as Governors-New Generation of Managers. In Fact-No!]. Meduza, June 3, 2018 (https://meduza.io/).
[37]Goryunov M. 'Ni slova po tatarski. Kreml vozvrashaetsa k imperskoy yazikovoy politike' [Not a Single Word in Tatar Language. Kremlin Returns to Imperial Language Policies]. Novaya Gazeta, August 22, 2018 (no.91):10.
MinoritypoliciesoftheRussianFarEastandSiberiainthepost-Sovietera
Oleg Oyster1,LI Yan-fei2
(1.NorthIceOceanResearchCenter,LiaochengUniversity,Liaocheng,Shandong,252000,China; 2.ForeignLanguageCollege,LiaochengUniversity,Liaocheng,Shandong,252000,China)
Abstract: This work is an attempt to describe the cognitive aspect of ethnic/national boundaries reproduction as a closed self-referential process that produces itself from its own internal operation and not from interaction with other objects through input/output of information. It shows on the example of ethnic policies in the Russian Far East and Siberia in the Post-Soviet period that this process is not simply the result of negotiations or social construction but complex interrelation between cognitive structures and the formation of ethnic/national groups. The article also shows how nationalist sentiments become stronger in spite of disappointments that ethnic policies produce in society. It demonstrates that disappointed expectations return into national discourse as political ideologies that help preserve the government's legitimacy, legitimacy of the idea of nation/ethnicity and motivate the society to continue the nation-building process.
Keywords: Ethnic policy; Russian Far East; Post-Soviet period; Ethnos; Psychomental complex
收稿日期:2019-02-27
作者简介:奥莱格·琶鲎蘑夫(1981-),男,俄罗斯人,聊城大学北冰洋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社会文化人类学、国际政治,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李燕飞(1973-),女,山东聊城人,聊城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社会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C9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9)03-0055-09
[责任编辑:王 健]
标签:俄罗斯论文; 民族论文; 土著论文; 共和国论文; 国家论文;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9年第3期论文; 聊城大学北冰洋研究中心论文; 聊城大学外国语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