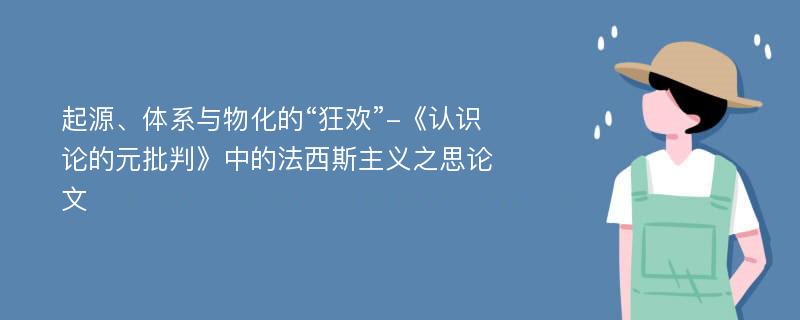
起源、体系与物化的“狂欢”
——《认识论的元批判》中的法西斯主义之思
侯振武 黄亚明
【摘要】 在《认识论的元批判》中,阿多诺以胡塞尔现象学为契机,展开了对起源哲学的批判,其中渗透着批判法西斯主义的内在逻辑。起源哲学对“第一者”的狂热追求使其对同一性原则做了“越界”运用,这正是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基点。起源哲学与法西斯主义的这种同构性,更为突出地表现在具有强制的齐一性与排他性的“体系”。这种体系以第一者为起源,但这第一者存在着不可克服的悖论。法西斯主义的这种结构及其悖论,实际上植根于物化的资本主义社会,是这一社会的意识形态与存在结构的极端表现。
【关键词】 《认识论的元批判》;法西斯主义;起源哲学;体系;物化
阿多诺对法西斯主义的反思批判,是贯穿其理论生涯的主要论题之一。从20世纪30年代因纳粹上台而被迫流亡,到战后回国,法西斯主义多次呈现在他的理论视域中。而有一部著作,在我们关于阿多诺法西斯主义批判的研究中应当受到重视,但却遭到了长期的忽视,这就是《认识论的元批判》(以下简称《元批判》)。这是阿多诺在1956年出版的一部以胡塞尔现象学为批判对象,进而批判整个唯心主义认识论传统的著作。从时间上看,《元批判》与阿多诺对法西斯主义反思的时间跨度高度吻合。它的形成历经二十余年,始于阿多诺流亡英国牛津期间(1934-1937年)。这一时期阿多诺写就了诸多手稿,它们构成了《元批判》第1、2、4章的基础。回国之后,他为《元批判》写了导言和第3章。从思想上看,阿多诺对胡塞尔现象学的批判不是一种单纯的学院兴趣,而是有着现实关切,这就是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经过十数年的颠沛流离以及理论反思,阿多诺在20世纪50年代重回胡塞尔现象学批判并将二十年前的手稿整理发表,绝不是类似于卢卡奇重版其《历史与阶级意识》那样认为仅具有“史料价值”。正如马丁·杰伊所说,阿多诺将整个现象学运动看作“资产阶级思想为了挽救自己衰弱的命运而做的最后一次徒劳的努力”,而且“现象学与法西斯主义有着隐秘的联系”,因为二者都是“资产阶级社会终极危机的表现”[注] Martin Jay, 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A History of the Frankrut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1923-1950),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 1976, p.70. 。《元批判》一书虽然仅有一处提及“法西斯主义”,但透过阿多诺对胡塞尔现象学的批判,我们依然能够体察到他批判法西斯主义的逻辑所在。当然,相较于现象学,法西斯主义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现象,因为其不仅有内在的理论逻辑,而且有着实践的表现形式。为此,本文将基于《元批判》,呈现阿多诺是如何剖析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基点、实践形式与社会条件的。
尺寸:Ø1.4m×2.7m。设计负荷,1m3/(m2·h)。配30 m2压滤机1台,同时处理生化污泥。
一、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基点:起源哲学
“法西斯主义试图实现起源哲学。最古老的、也是存在时间最长的东西,应当直接地、如实地进行统治。因此,篡夺第一者的倾向变得明目张胆了。”[注] Theodor W. Adorno, Zur Metakritik der Erkenntnistheorie ,Theodor W .Adorno :Gesammelte Schriften , Bd.,5, Rolf Tiedemann, Hg.,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0, S.28. 因此,阿多诺将法西斯主义这场爆发在20世纪的历史灾难,与贯穿着整个哲学史的起源哲学联系起来。在《元批判》中,阿多诺将起源哲学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当然,他更为关注的是“现代的”起源哲学,即唯心主义认识论。他指出,这种认识论传统“希望通过反思主体——而不是将它从第一者概念中清除出去——来将绝对第一者提升为绝对确定者。但同时,在这种反思的进程中,同一性强制扩展开来”[注] Ibid.,S.30. 。作为这种认识论传统的最为彻底的代表的,就是胡塞尔现象学。因此,我们无需回顾哲学史,仅通过考察胡塞尔现象学就可一窥起源哲学的特征。根据《元批判》,起源哲学的特征至少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追求“第一者”,并将之作为无可置疑的“起源”(Urspung)。在起源哲学中,“起源”概念无疑是最重要的,这是整个起源哲学体系据以建立并最终归宿其上的“始基”,这是一个不受质疑的确定的开端。在此意义上,起源就是“第一者”,相对于体系中的其它部分,它既具有时间上的原初性,又具有逻辑上的至上性。因此,我们可以将起源哲学与第一哲学(prima philosophia )等同视之。胡塞尔将第一哲学之名回溯到亚里士多德,并据此指出这种哲学是“一种关于开端的科学学科”[注] [德]胡塞尔:《第一哲学》上卷,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3页。 ,而他竭力建构的就是这样一种“科学”。为此,他试图将康德开启的主体主义的第一哲学方向彻底化,建构一种“在超越论的主观性中建立真正的客体性之原则的可能性的超越论的科学理论”[注] 同上,第293页。 。也就是要确定现象背后的不可再怀疑、不可再还原的“阿基米德点”,即先验自我。胡塞尔甚至认为,“一切本质研究就无非是对一般先验自我的普遍本质的揭示”[注] Edmund Husserl, Cartesian Meditations :An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y , Dorion Cairns, trans., Martinus Nijhoff, 1977, p.71. 。胡塞尔对第一者的这种追求,不仅是胡塞尔现象学自身的特点,也是其所代表的整个唯心主义认识论传统的追求。
在竹书的起源叙述中,汪忍坡被塑造成傈僳族反抗不平等的民族英雄,强调了本土的力量和智慧,并且与其本土宗教活动有密切联系,但这也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表现出来的反抗意识。尽管如此,无论是西方传教士创造的拼音文字还是本土所造的字,都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综上而言,起源哲学与法西斯主义经历着同样的命运,这就是,体系的建构必须通过齐一与排他的活动来实现,而这一过程看似是体系的不断完善,实际上恰恰是其不断走向失败的过程。这是起源哲学与法西斯主义自身无法克服的悖论。不过,阿多诺并未止步于此,他认为,它们都是同一种社会状况的两种极端表现形式,这就是物化的资本主义社会。
然而,这种看似逻辑严密的、确立了主体掌控客体的哲学行话,却是罪愆深重:它“奏着全无内容的神学音调,除了自我崇拜之外没有其它任何内容。它捏造出第一者的肉身化在场,而第一者既非肉身也不在场。它的权威类似于被管制的世界的权威,这个世界只依赖于管制这一事实本身。从社会角度来看,完成了的抽象之物的‘登基大典’,也使得无视其社会内容的单纯组织形式登上了王位,这种社会内容出于好的理由而被忽视了”[注] Theodor W. Adorno, Zur Metakritik der Erkenntnistheorie ,Theodor W .Adorno :Gesammelte Schriften , S.42. 。在阿多诺看来,就当时的社会现实而言,极端地实现了这种罪恶的就是法西斯主义运动。独裁者的卡里斯马形象、整齐划一却全无自由的组织形式、对异议者及犹太人的迫害等等,这些看似远离哲学的法西斯主义要素,无一不透露着起源哲学的印记。即便我们不能说起源哲学必然会产生法西斯主义,毕竟这一灾难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阿多诺的视野中,起源哲学与法西斯主义有着不可否认的同构性,使其能够作为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基点。如果说,这种理论上的同构性还仅仅是一种可能性,那么,法西斯主义的实践则证明了这种同构性的现实性。
二、法西斯主义的实践形态:体系
权力作为法西斯主义体系的起源具有类似的悖论。一是权力的权威性与个体的个体性之间的悖论。法西斯主义的权力的权威性是普遍的,而这种普遍权力之权威性的获得,是法西斯主义组织通过各种方式吞噬了人们的反抗能力的结果,由此从孤立无援的人们身上获得了整合的奇迹。换言之,法西斯主义权力之权威来自于人们对自己的正当权力与自由的放弃。同时,权力虽然是法西斯主义体系的真正起源,但在现实中,它需要一个具体的个体来承担。就此而言,权力在双重意义上是被个体的个体性中介了的。在这种中介过程中,权力遭遇了悖论。独裁者的个体形象“提供了一种替代物,他所表现出来的,正是现实中其他一切人被禁止做的”[注] Max Horkheimer, Theodor W. Adorno, Dialektik der Aufkl ärung :Philosophische Fragmente , S. 224. 。也就是说,权力始终未能消除个体性,而是以某个独裁者的形象来表现这些个体性,以此将个体性纳入体系当中。但是,这也就意味着,权威承担独裁者角色的个体的个体性、与被纳入法西斯主义体系的其余个体的个体性都存在着冲突。独裁者形象实际上是利用权力来违背权力的禁令,其余人的个体性也并未真正消失,而是始终作为权力的异质者与之对抗,否则也就不会有禁令的存在。这就涉及第二组悖论,即权力的所谓真理性与其欺骗性之间的悖论。在起源哲学中,“由于基底比提到它之上的东西更为真实,原初性就与真理结合在一起了”[注] Theodor W. Adorno, Zur Metakritik der Erkenntnistheorie ,Theodor W .Adorno :Gesammelte Schriften , S.27. 。同样地,独裁者承载的权力对于法西斯主义党羽及其操控的乌合之众来说就意味着最高真理,是其一切行为的最高法则。但是,“真理的起点变成了欺骗的起点”[注] Ibid., S.25. 。这就是说,这种真理的效力是通过欺骗的方式获得的,这不仅是指对被纳入法西斯主义体系的个体的欺骗,也包括将不能纳入体系的个体宣扬为偶然之物的谎言。法西斯主义体系内部的冲突,以及对法西斯主义的抵抗,正是表明了法西斯主义的权力及其体系的这种所谓“真理”的虚假性。
首先,体系具有以起源为最高标准的齐一性。“起源哲学的观念以一元论的方式指向纯粹同一性。”[注] Theodor W. Adorno, Zur Metakritik der Erkenntnistheorie ,Theodor W .Adorno :Gesammelte Schriften , S.30. 作为这种观念的实现,体系拥有强大的同化能力,也就是将容纳进自身的所有东西改造为质上与起源相符的,从而虚构起一个个连贯的演绎环节。在胡塞尔现象学中,这表现为先验自我基础上的“实事本身”组成的体系。在阿多诺看来,这些所谓的“实事本身”并非真正现实的活生生的经验,而是先验自我的构造物。所以,胡塞尔关注的还是概念,没有真正做到从经验出发。现象学虽力图接近经验,最终却空有其表。由此,先验自我不仅取代了现实的人而成为真正的主体,而且排除了被纳入体系的经验的特殊性。
受动载影响,左帮片冒严重,因此左帮锚杆在安装后,1、3号受力逐渐减小,甚至趋于0,基本失效(图10)。2号未失效,受力约15 kN。这与数值分析中左帮锚杆受力较小相吻合。
在与索恩-雷特尔的一次谈话中,阿多诺提出,“范畴的建构……要求撇开(遗忘)它们的社会性发生(Genese),撇开一般的发生。而历史唯物主义是对发生的回忆。”[注] [德]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谢永康、侯振武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6页,译文有改动。 这里的“对发生的回忆”,就是指对概念范畴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的追索。在《元批判》中,阿多诺正是遵循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理念,探究了起源哲学与法西斯主义共同的社会条件,即物化的资本主义社会。
在《元批判》中,阿多诺虽仅在一处引用了卢卡奇,但通观全书,我们可以发现,阿多诺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更多的是卢卡奇式的,这尤其表现在阿多诺对物化概念的使用上。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注]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50页。 。同时,以这种物化的社会存在结构为基础,形成了一种同构的物化意识,这种意识将人创造的物视为独立于人的,甚至能够掌控人之命运的东西。基于此,我们可以从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结构两方面,呈现阿多诺是如何证明法西斯主义是怎样发生于物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
如果说哲学上的排他性因取消物世界尚且对现实世界无所大碍,至多是遮蔽了人们对于现实世界的真正认识的话,那么,法西斯主义对异质者执行的排除就是残酷的。在这里,反犹主义成为阿多诺剖析法西斯主义体系的排他性的典型案例。在反犹主义观念中,犹太人被视为绝对的他者,是与纯粹的体系格格不入的偶然物。对于法西斯主义统治来说,它是“一种不祥预兆。统治总是秘密的,它最终公开坦白的是:它是极权主义的。所有与之不相类似的东西,即最难以等同化的东西,都被它归于偶然”[注] Ibid., S. 89. 。容忍偶然,也就意味着容忍非同一性,而这无疑与体系赖以成立的彻底的同一性原则及其齐一性特征是矛盾的,因此,偶然是必须被消灭的。对于犹太人,法西斯主义通过种族灭绝来实现这一点:“种族灭绝是绝对的一体化……奥斯威辛集中营证实纯粹同一性这一哲学原理就是死亡。”[注] Theodor W. Adorno, Negative Dialektik , Suhrkamp, 1966, S. 353.
最后,体系的起源本身具有不可克服的“二律背反”。《元批判》的副标题是:“关于胡塞尔及现象学诸多二律背反的研究”,这整部著作都是在揭示胡塞尔现象学及其代表的起源哲学体系的种种“二律背反”。而要彻底地批驳起源哲学,那就要从其“起源”上着手,在体系建构之初就否定其正当性。阿多诺揭示起源之二律背反的方法,不是关注其内容即什么被当作起源,而是关注其结构本身的悖论如何导致自身毁灭。在阿多诺看来,起源包含两组二律背反。一是起源的超越性与经验的现实性之间的悖论。作为起源,无论它是存在还是思想、主体还是客体、本质还是事实,都意味着对活生生的经验的超越。阿多诺认为,这种超越实际上是一种同一性原则支配下的概念活动的结果,是人的思维对现实经验进行同一化操作的产物。就此而言,起源的超越性恰恰依赖于它自认超越了的那些现实的经验,超越性总是被现实性所中介的。但如此一来,被认定的起源就不再是绝对起源、不再是第一者。因此,起源哲学难免走向独断论:“假设独断的超越性,假设与经验相对的思维”[注] Theodor W. Adorno, Zur Metakritik der Erkenntnistheorie ,Theodor W .Adorno :Gesammelte Schriften , S. 171. 。这也就带来了第二组悖论,即起源的原初性与其抽象性之间的悖论。根据起源哲学,起源是一种自在自为的存在,其不仅不依存于其它任何事物,反而由于其原初性,它还是构建世界的基点,因此应当是反对抽象性而指向具体性的。但在阿多诺看来,这种起源由于其独断地主张超越性,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虚弱的抽象物。并且,它为了维持超越性与纯粹性,必须执行齐一与排他活动,如此一来,起源只能是变得越来越抽象,而“变得越是抽象,它所能解释的就越少,也就越不适合作为基础”[注] Ibid., S.22 。基础不稳,遑论体系?这种体系至多是“处于废墟中的体系”[注] Ibid., S.215. ,只是将一系列“瓦砾”集合起来。这种体系无论看似多么具体,它始终是脱离了真正的经验现实的,因此,它的“拥有一切”根本上来说就是“一无所有”。
起源哲学通过第一者的确立与同一性原则越界使用,构建了吞噬一切的体系。众所周知,在《否定的辩证法》中,阿多诺对体系展开淋漓尽致的批判,“反体系”成为阿多诺思想的标签。实际上,正如威尔克(Sabine Wilke)所说,在《元批判》中,阿多诺“第一次演示了这种自觉的、反体系的批判”[注] Sabine Wilke, “Adorno and Derrida as Readers of Husserl: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 Boundary 2, Vol. 16, No. 2/3, p. 79. 。这里,阿多诺主要批判的体系,是胡塞尔的现象学认识论及其所代表的整个唯心主义的认识论体系,因而更多地是一种理论向度上的批判。关于体系的实践后果,阿多诺只是零散谈及,不及《启蒙辩证法》《否定的辩证法》等丰富。鉴于这些著作中批判理路的连续性,我们可以从《元批判》出发,结合《启蒙辩证法》《否定的辩证法》,考察阿多诺对法西斯主义的实践形态即体系的批判,由此可知法西斯主义是如何实现起源哲学,以及这种实现如何必然会归于失败。
其次,对同一性原理的“越界”运用。起源哲学要达成对作为起源的第一者的确证,必须通过一定的机制来实现,以使其具有合理严密的逻辑性。阿多诺认为,第一者概念的用法本身就已表明了这一机制,这就是对同一性原则的“越界”运用。运用同一性原则认识世界,这对于人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人的理性和生命的有限性使得我们不可能去认识每一个个别事物。同时,任何概念的形成都意味着将不同对象之间相互异质的内容过滤掉,提取其中共同的方面。因此,任何概念都不可能把对象的一切特性都纳入到自身当中,相对于概念的有限性而言,未被纳入到概念中的东西总是无限的。在阿多诺看来,起源哲学在使用同一性原则时,显然丧失了这种界限意识。起源哲学认为,“所有东西都应当全然地从哲学上被断言为第一者的原则中产生出来,无论这第一者被称为存在还是思想、主体还是客体、本质还是事实”[注] Theodor W. Adorno, Zur Metakritik der Erkenntnistheorie ,Theodor W .Adorno :Gesammelte Schriften , S.15. 。起源哲学使用的是彻底的同一性原则,由此,第一者就是被纳入到以它为基点建构的体系中的东西的最高统治者,而且,这些被统治者就其本质而言,是与第一者同一的。阿多诺认为,胡塞尔现象学的诸前提中,最为基本的就是作为主体的先验与作为客体的现象之间最终能够建立起一种同一性,并且,这种同一性是由先验自我构建并由它掌握统治权的。
三、法西斯主义的社会条件:物化的社会
淋醋的工艺流程包括:成熟醋醅、浸泡(加入炒米色、食盐、传淋付水)、传淋、生醋,此阶段涉及的传统设备有淋池、大缸及炒色灶等,可用机械设备有不锈钢泵、半自动化炒色锅。
其次,体系具有对不可容纳之物的排他性。这种排他性可以看作是体系的齐一性的另一面,因为它需要通过运用同一性原则排除异质者来达到自身的同质化。就此而言,体系也意味着划界,不能被纳入体系的个体,只能被当作偶然的东西,因而是必须被清除的。胡塞尔现象学的“悬搁”方法正是显示了体系的这种排他性。所谓“悬搁”也就是对所有无法确证之物“加括号”、悬而不论,最终获得绝对纯粹的、不能再被还原之物。阿多诺认为,凭借这种方法,世界“根本不会发生什么变化:它与其说是被设计为负责任的理性批判,不如说是取消了物世界”[注] Theodor W. Adorno, Zur Metakritik der Erkenntnistheorie ,Theodor W .Adorno :Gesammelte Schriften , S.198. 。因此,这种悬搁所获得的只是第一者的自我游戏、自我循环,它通过排除异己之物来维持自身的抽象的纯粹性。
首先,唯科学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的意识形态,法西斯主义执行了这种意识形态。阿多诺认为,科学有两个突出的特征,即命题间的连续性和操作上的可重复性,这个特质都要求排除“无联系的东西,即不可结合的东西”[注] Theodor W. Adorno, Zur Metakritik der Erkenntnistheorie ,Theodor W .Adorno :Gesammelte Schriften , S.51. 。如果一个命题无法与既有的其它命题相连贯,那么按照融贯论的真理观,它就不会被视为科学的。如果一个对象或实验结果不能在未来的同样的操作中被重复,那么它就不会被视为可靠的。简言之,科学方法就是要排除不能纳入知识体系中的异质者,“不适合的东西,只能作为‘素材’出现在边缘,它在原地等待,如果没有恰当位置,它就会被抛弃”[注] Ibid., S.50-51. 。而这两个特征所呈现的,是一种可计算性原则、量化原则,甚至极端而言就是数的原则,通过不掺杂任何主观“残余”的形式化运算,获得客观有效的结果。
类似地,在法西斯主义的体系中,也存在着第一者及其操控的同质化“实事”:权力与服从权力之权威的“乌合之众”。在法西斯主义运动中,表面看来,居于第一者地位的是独裁者,但阿多诺认为某个具体的独裁者“不过是权力占据的某些空位”[注] Max Horkheimer, Theodor W. Adorno, Dialektik der Aufkl ärung :Philosophische Fragmente ,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S.294. ,换言之,真正作为起源的是权力,而非某个人。由于权力的执行需要具体的人来承担,因此才虚构出独裁者的作为领导者的形象。在起源哲学中,第一者的设定实际上是任意的,它只有在其构建的体系内才能作为起源,反之,它只有通过演绎出其它内容才能证明自身是第一者。在法西斯主义中,权力作为第一者,通过发号施令来彰显自己的起源性。因为井然有序,这个任意的第一者具有了理性的假象,其结果便是法西斯主义“与纯粹理性更加相符,因为它把人当作物,当作行为方式的集合”[注] Ibid., S.106. 。换言之,法西斯主义构建了一种受到操控的同一性秩序,在其中,所有人都必须各安其位。在阿多诺看来,这是对纳入这个秩序中的个体的个性的否定。由此,这些个体不再是具有独特个性的人,而是成为同质化的乌合之众。
公正地说,科学的这两个特征和可计算性原则,对于我们获取科学知识而言是无可厚非的,否则我们无法组织起确定的、严谨的科学知识体系。但是,一旦这种科学观念与起源哲学观念结合起来,便产生了唯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起源哲学中的起源及其体系被视为自在的,在唯科学主义中,科学体系具有了这种自在性。这种自在性,在起源哲学中是通过同一性原则及其齐一性与排他性活动实现的,而在唯科学主义中,同一性原则化身为可计算性原则,齐一性与排他性则表现为命题间的连续性和操作上的可重复性,因为这两个特质正是通过对科学观察对象之间的质性差异以及不可普遍化的特质的排除实现的。进而追之,唯科学主义这种意识形态,从认识的社会性角度来说,是脑力劳动物化的结果,是一种科学拜物教。科学体系是我们认识活动即脑力劳动的结晶化。但在拜物教视野中,脑力劳动产品的科学,变成了与商品一样“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7页。 ,这种观念没有看到科学背后的脑力劳动及其分工,没有看到科学体系形成的社会历史过程。归根结底,唯科学主义遗忘了现实的人,“遗忘的机制成为了物化的机制”[注] Theodor W. Adorno, Zur Metakritik der Erkenntnistheorie ,Theodor W .Adorno :Gesammelte Schriften , S.74. 。
在阿多诺看来,唯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法西斯主义中以一种残酷的方式实现了。法西斯主义“任凭计算原则畅行无阻,并且惟科学是从。它的准则就是粗暴残酷的效能”[注] Max Horkheimer, Theodor W. Adorno, Dialektik der Aufkl ärung :Philosophische Fragmente , S. 106. 。对于法西斯主义运动来说,集中营的屠杀与流水线生产具有了相同的意义,科学的计算原则与分类方法带来了效率,“科学方法”成为了执行野蛮命令的最佳方式。相应地,“人”被遗忘了,“在集中营中死掉的,不再是个人而是样品”,因此,“通过管理对数百万人实施的谋杀,使得死亡成了一件不再那么可怕的事情”[注] Theodor W. Adorno: Negative Dialektik , Suhrkamp, 1966, S. 353. 。在集中营中,死亡对于面对死亡的个人而言或许还有可畏惧性,但对于法西斯主义刽子手来说,个人正如科学中的实验品一样,已被抽象为可互换的和可替代的。阿多诺认为,“这种抽象可回溯到商品形式当中,后者的同一性存在于交换价值的‘等同’中”[注] Theodor W. Adorno, Zur Metakritik der Erkenntnistheorie ,Theodor W .Adorno :Gesammelte Schriften , S.76. 。当然,无论是抽象方法还是商品形式,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产物,不过这些内容正是在物化的社会存在结构中变得极为悖论性的。
大量研究提示hsCRP及Lp-PLA2与斑块的稳定性相关联,在斑块不稳定时两者均明显升高,而斑块趋于稳定时两者均明显下降,在急性冠脉综合征[1,2]及急性脑梗塞患者中均观察到该现象。本研究旨在揭示hsCRP及Lp-PLA2的检测有助于客观有效的判定颈动脉粥样硬化的疗效。现报告如下。
其次,资本主义的社会存在结构是物化的,法西斯主义是其极端表现,也是其矛盾的集中爆发。在阿多诺看来,物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结构充满了种种悖论,而其中最具悖谬性的是人的生存状况。人作为社会性存在者,本应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而且,在现代社会中,先进的生产力、发达的交通工具以及以交换价值为枢纽的商品经济,使人们的交往突破了血缘关系或宗法关系、地域关系的限制,人们之间的交往相较于传统社会更为频繁、更为紧密了。然而,阿多诺认为这只是一种社会性生存的假象,这一假象背后的实情是,“在这个世界中,人们彼此之间是相互陌生且不确定的,并且,每个人仅仅关心自己的个别利益”[注] Ibid., S.235. 。
在这里,阿多诺实际上继承了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原子化状态的判断。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分工的发展,生产者被固定在一个特殊的部门或领域中进行生产。由此,个人不再能独立地生产出自己所需的产品,同时,每个人的生产所创造的产品也不再是为自己使用,他需要通过交换,用自己的劳动产品换取他人的劳动产品以作为自己的生活资料。在交换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看似是“各取所需”、相互依赖,但实际上,“这种社会联系表现在交换价值上,因为只有在交换价值上,每个人的活动或产品对他来说才成为活动或产品;他必须生产一般产品——交换价值,或孤立化和个体化的交换价值,即货币”[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3页。 ,交换使自然劳动成为抽象劳动,成为为了交换而进行的劳动,抽象的劳动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毫不相关的单个的原子式的个人,共同体的存在成为可有可无,唯一的联系就表现为流水线上的分工与合作。个人的劳动和个人价值与社会历史经验的联系逐渐被遗忘,抽象化的劳动和交换使人们更关注于孤立的个人行为。为了交换而进行生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由交换所带来的物的关系所控制,人的关系表现为物性的,原属于人之为人的真正本质的内容也被物的形式所遮蔽。
9~10月份,西红柿定植阶段,在苗高20厘米左右,6~7片真叶或苗龄50天后,选好苗壮苗,晴天的上午进行。定植时采取大小行、小高垄方式,即大行70厘米、小行50厘米,垄高10~15厘米,每垄定植两行,株距50厘米,每亩定植2200株为宜,定植后及时浇缓苗水,气温控制在25~28℃以上,以利于缓苗生长。缓苗期结束,开始盖地膜,并适时浇水。
但是,这种孤立化和物化状态,对于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人总是企图突破孤立,重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此即社会化倾向。由此形成了孤立化与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操控整个世界的能力的增强,其试图解决这一矛盾,“发达的资产阶级自我意识不再能够满足于抽象概念的拜物教,……这种意识必须掌握实事本身”[注] Theodor W. Adorno, Zur Metakritik der Erkenntnistheorie ,Theodor W .Adorno :Gesammelte Schriften , S.193. 。胡塞尔现象学与法西斯主义都可以视为这种意识的体现,因为它们都构造了一个无所不能的起源和一个无所不包的体系。在这种意识看来,只有通过这种普遍化才能使孤立的个体“提升”为普遍的主体,从而保持稳定与安全。但在阿多诺看来,它们是“资产阶级社会所必然产生的幻象”[注] Ibid., S.217. 。之所以是幻象,是因为这种普遍化只是抽象的虚假的社会化,这种看似普遍的起源,遮蔽了主体原本应有的社会性、现实性与历史性,它们依然遗忘了真正的社会现实经验,遗忘了自己的“发生”。法西斯主义的整合反映了普遍化的要求,同时它又是以人的孤立化和物化状态为前提的,因此这种整合不过是将“个人拼凑起来,全然没有体现出人的真正品质,就像价值全然没有体现出用品的真实品质一样”[注] Max Horkheimer, Theodor W. Adorno, Dialektik der Aufkl ärung :Philosophische Fragmente , S. 44. 。这实际上是用物化的社会中产生的物化的意识来克服物化导致的悖论,这恰恰表明,在资本主义物化条件下,孤立化与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是无法真正解决的。如果坚持这种悖论式的解决方案,那么法西斯主义的悲剧就将不断重演。因此,阿多诺对起源哲学、对法西斯主义的持续批判,真正指向的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及其对人的毁灭。
从《元批判》的文本上讲,相较于对胡塞尔现象学的批判这条“明线”,法西斯主义之思是一条“暗线”。不过,正是这条“暗线”代表了阿多诺社会批判思想的特征,这就是将意识批判与社会结构批判结合起来。法西斯主义作为既具有理论基础又有实践形态的历史灾难,无疑正需要这一双重批判,才能对其产生与失败的原因及其本质做出充分解释。霍克海默曾指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对社会的解释,“不只意味着一个逻辑过程,而且也意味着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注]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批判理论》,李小兵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202页。 。也就是说,社会批判理论既要对被批判对象的理论表现形态进行批判,而且还要对被批判对象本身的现实结构进行批判。霍克海默对社会批判理论的上述规定与阿多诺最初写作《元批判》是同期的,在这个意义上看,《元批判》中的双重批判,是阿多诺、也是法兰克福社会批判理论践行的“第一幕剧”。
中图分类号: B516.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660(2019)04-0012-07
作者简介: 侯振武,河北唐山人,哲学博士,(天津 300350)南开大学哲学院讲师;
黄亚明,吉林白城人,哲学博士,(天津 300387)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法兰克福学派主体间哲学研究”(63192129)
(责任编辑 巳 未)
标签:《认识论的元批判》论文; 法西斯主义论文; 起源哲学论文; 体系论文; 物化论文; 南开大学哲学院论文; 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