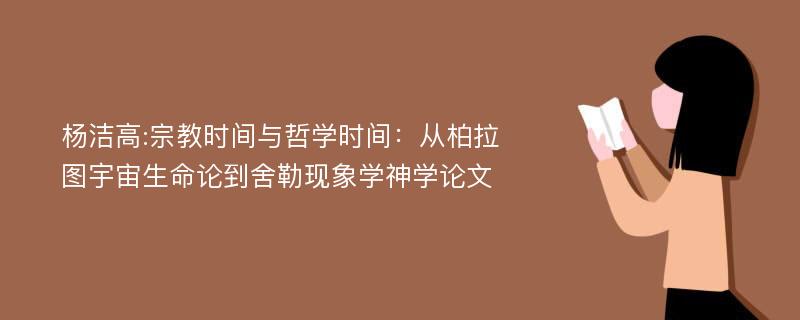
●哲学研究
摘 要:柏拉图的两种永恒之分提示着两个基本时间视域:一是原本的永恒作为时间总体所显现的神学时间视域,一是时间总体性的绵延作为时间现在成像的哲学时间视域。亚里士多德从柏拉图引出纯粹哲学的物理时间。奥古斯丁则力图以心灵时间取代物理时间,来复归柏拉图的神学视野。舍勒的现象学神学从生命出发,在奥古斯丁基础上提出“位”的“永生”,通过“位格”这一人神共有之物,弥合了世俗哲学与信仰神学。
关键词:柏拉图; 两种永恒; 奥古斯丁; 舍勒
一、柏拉图宇宙生命论中的两种永恒
时间意义源自永恒。现代哲学与神学力图探讨深邃复杂的时间之谜时,都需要回溯到柏拉图的两种永恒之分。在《蒂迈欧篇》中,柏拉图设想:在宇宙被创造出来之前存在一个永恒生物,被至善的造物者用来作为宇宙原型。造物者试图使宇宙尽可能像它的原型。但宇宙作为被造物必定有一个开端,而真正的永恒却无开端亦无终结,因此永恒不可能完全赋予宇宙。为了弥补,造物者“为那留止于一的永恒造了依数运行的永恒影像”[1]288,这个影像被称为时间,分成年、月、日等。这作为永恒之影像的时间可以被视为一个由不断生成的时间部分拼凑起来的无限。在这一无限中,可以获得两个时间概念,其一是作为单个时间存在的现在;其二则是由无数个现在连缀而成的时间之总体。这一时间的总体性存在是依据永恒为其理想性质的,因而也可被视为永恒性的存在。
一般认为过去和将来是时间的构成部分。但过去和将来都被柏拉图称为“时间的生成方式”。在他看来,过去、将来与现在不是同等地位的概念,现在就是时间本身。现在依过去和将来两种生成方式展开的运动并非周而复始和一成不变,而是不断变化。时间的生成意味着时间能够产生出不同于自己的部分,因此我们才能说事物存在于不同的时间(现在)之中。而过去、将来这两个概念则是用来区分不同时间之关系的。每一个时间都处在和它之前的时间的过去相续性、以及和它之后产生的时间的未来相续性这两种关系之中。柏拉图认为,原本的永恒不存在过去和将来,人们常常错误地用过去和将来这两种时间生成方式,来理解作为原型的永恒,因此必须作出一个两种永恒的区分:作为原型的永恒不运动、不变化、固守于一;而时间连续性之永恒则是生成变化的无限延续。
柏拉图对两种永恒的区分提示着两个基本时间视域的产生,一个是原本的永恒作为时间总体存在所显现的神学时间视域,另一个则是时间总体性的绵延作为时间现在成像的哲学时间视域。不同的神学家或哲学家在构建其时间概念或观念时,其思想的整体性所指涉的时间视域都有所不同。但从根本性方向来看,皆可溯源至柏拉图作为神学和哲学时间视域的两种永恒观念。
数学抽象是数学的基本思想,是形成理性思维的重要基础,反映了数学的本质特征,贯穿在数学产生、发展、应用的过程中.通过高中数学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在情境中抽象出数学概念、命题、方法和体系,积累从具体到抽象的活动经验;养成在日常生活和实践中一般性思考问题的习惯,把握事物的本质,以简驭繁.因此,数学抽象思维训练是培养学生提出问题能力的重要途径和方法.
二、亚里士多德从柏拉图时间观引出纯粹哲学时间视域
在柏拉图那里,奠基于两种永恒观念的时间视域是叠加构建的,关于时间起源,造物者的神亚里士多德则完全抛开神话,从柏拉图连续性永恒的时间观念,引出纯粹哲学意义的物理学时间视域。这一视域由时间与运动、时间与事物存在等关系构成。当时间作为被造物时,其意义由造物者赋予。当时间作为物理现象时,其意义则取决于物理实体与运动的关系。显然亚里士多德关注的是后者。
柏拉图的错误在于将时间概念化,并将之运用于物理世界。②问题是,物理世界有时间吗?亚里士多德认识到,没有对运动的计算就不好说有时间。而“计算”显然是属于人对世界的认知方式,因此,时间不过属于人的生命与世界的“之间”问题。换而言之,“之间”性是时间第一性,或者说是时间存在的意义。柏拉图的宇宙生命论将物理世界与生命世界合一,试图跨越和掩盖这个“之间”。③但是,时间问题实际上除了人和世界的“之间”,还有一个人与人的“之间”。这两个间性的存在,正是所有时间问题的根源。人与世界的“之间”时间可以称之为客观时间,而人与人的“之间”时间则可以称之为胡塞尔的先验时间。
他首先指出柏拉图和笛卡尔分别代表了时间观念的两种误区。
小反刍兽疫病作为一种急性接触性传染病,健康羊一旦染病,死亡率非常高。因此,应积极做好疫病防控工作,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通过全面实行免疫接种、搞好环境卫生消毒工作、加强饲养管理、及时诊断、控制源头、控制疫情、加强疫情监测等有效手段,最大限度降低疫病的发生几率,避免疫病的进一步扩散,确保牧区养殖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亚里士多德这个时间定义看似与柏拉图“依数运动着的永恒的影像”一脉相承,其实大异其趣。在柏拉图那里,作为被造物的时间与其他被造物一样具有物理上的实在意义。亚里士多德的时间却仅仅是观念性概念。亚里士多德注意到对时间问题的讨论不能在物理上进行,而必须从形而上学来加以阐明。在《形而上学》中,他力图论证时间并不参与到永恒的物理世界之中。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在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连续性中存在、并参与事物本身变化而自身不变的东西才能真正谓之与永恒相关联。这样一种内在于事物的存在者被他称为原子。原子以及原子构成的全部宇宙都是永恒的。于是时间就这样被亚里士多德逐出了物性领域、逐出到永恒之外,只是作为事物运动参照系的“数”。
小学老师都有一颗长不大的心,只有这样才能和小学生亲近。小学生都是好动的。在课堂上,他们不会放弃一点点可以动的机会,那么老师就可以充分运用小学生的这一点心理,在动中教会他们知识。如在汉语拼音第6课教j、q、x的儿歌时,老师可以和学生一起做动作来加深印象:星期天(一起做7的手势),洗衣裳(做两手搓衣服的动作);洗衣机,嗡嗡响(加入手指转动的动作);妈妈洗衣,我帮忙(两手放在胸口,做“我”的动作)。除了动作,面部表情也蕴含了大量的情感信息,老师和学生一起运用表情和动作来增进课堂教学的情感交流,使拼音教学课堂充满生机!
三、奥古斯丁基于柏拉图而理解的神学时间观念
奥古斯丁不赞同亚里士多德的物理时间,转而折返至柏拉图,力图借心灵观念来弥合时间与永恒的间距,也弥合神学与哲学的间距。
人的生命究竟是什么?奥古斯丁说:“记忆的力量真伟大,它的深邃,它的千变万化,真使人望而生畏;但这就是我的心灵……”[3]194奥古斯丁将记忆、心灵、生命视为一体。这使记忆概念获得了本体化。奥古斯丁还认为记忆中存在着一切经验事物的影像,一切知识、学问都存在于记忆中。至于数字、关系和法则、各种情感等,则并非感觉镌刻在人记忆之中的,而是属于记忆自身所有。尽管外物并不真的在记忆中存在,但一个人忘记了他丢的东西,如果他记不起来的话,他就不能找到它,因为他即使见到这个东西,他也不知道是他要找的。由此他推导出人神之间的寻觅之路。人究竟要到哪里寻觅上帝?如果在记忆之外寻觅,被记忆抹去的东西显然不可能找回。那么人就只能是记忆中寻找上帝。奥古斯丁接着追问:“(上帝)你驻在我的记忆之中,究竟驻在哪里?”[3]208上帝不是物质的影像、不是情感,因此不能如影像、情感一样存在于记忆之中,但是,奥古斯丁说,上帝在记忆中实际上是无所不在的,他是人内心中真理的存在。在神学视域中,真理并非通过对外在世界的推理来抵达,而是经由内省和信仰来完成。真理是上帝的启示,是上帝在人生命中的直接存在。真理又是永恒存在的,或者说,永恒以真理的形式存在于人的生命和心灵中。
奥古斯丁的时间之思开始于“天主创造天地之前做什么?”[3]240。他从神学与哲学双重意义上考察永恒与时间的关系。上帝是永恒者,那么耶稣降生为人的事件,是否意味着永恒进入到了时间之中?奥古斯丁认为,上帝所启示的亚当——耶稣——末日审判的历史进程是确定的,在亚当之前和末日之后不存在历史。历史借时间变化而形成。因此,亚当之前没有历史,也就是说没有时间。而末日审判之后没有历史,却有了永恒:永福和永罚,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只要时间一成不变,就上升为永恒?奥古斯丁遵其神学立场继续探讨。上帝是永恒者,在上帝存在中不存在时间。时间是人在世界的存在方式。末日意味着人世和时间终结。因此,时间是时间,永恒是永恒,时间不能变成永恒,永恒当然也不能变成时间。但奥古斯丁想要找出,有无一种存在,它将使永恒和时间成为其存在的两种不同的可能性?或者说,有没有一种存在,它既可融入永恒,也可破碎为时间?奥古斯丁的回答是肯定的,他将这种存在归于人的心灵。
舍勒的现象学神学从生物的生命出发,在奥古斯丁基础上加入了一个“位格”①概念,提出“位格”的“永生”[4]998。通过“位格”这一人神共有之物,舍勒弥合了世俗与天国的距离,将永恒与永生合二为一。
人是管理活动中最为关键的因素,管理人员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了管理水平的优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高校教学管理水平的竞争,实际上就是教学管理人员素质的竞争。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相对稳定的教学管理队伍是大学教学质量的有效保证。然而,目前大学教学管理队伍普遍存在的专业能力不强、发展空间狭小等问题,已影响到大学教学管理组织效率与创新能力及大学教学水平的进一步发展。
对寻觅上帝之问的回答要引出的是对时间何以存在的解释。既然上帝作为绝对者、上帝真理作为永恒者只能在心灵和记忆中寻找,那么在奥古斯丁看来就没有什么能外在于心灵了。
奥古斯丁由此否认时间存在于外在世界中。他认为时间是心灵的伸展。他将时间与人的自由意志联系在一起。自由意志只存在于人心中,自由意志在人的心灵中实际上就只是纯粹的能动性,这一能动性的中心点是“关注”,心灵总是能动地关注着世界。关注产生了三重现在,换而言之,关注产生了时间:关注的当前产生了“现在的现在”;掠过的是“过去的现在”;在记忆中伸展,又在期待中延伸的则是“将来的现在”。心灵把它经历过的事物逐一分配到这三重现在之中,看似时间与事物紧密联系在一起,实则只是心灵本身通过关注给外在对象分配了时间的标记。奥古斯丁说:“过去事物的现在就是记忆,现在事物的现在便是直接感觉,将来事物的现在便是期望。”[3]247可见三重现在本质是心灵的三种行为。这三种行为实际上都是表象行为,奥古斯丁认为我们对时间的度量正是通过留存在心灵中的表象来实现的。他说:“我所度量的……是固定在记忆中的印象。”[3]251按照奥古斯丁的诠释,如果将未获拯救的人对真理的寻求视为人类生命之最为急切、最符合人的本质冲动的行为,那么奥古斯丁所说的三种关注方式(记忆、直觉与期待)生产出来的时间可视为未获拯救的人的存在方式和可能性;而永恒则是人的生命中还未开启的一种存在。这一存在方式的开启在基督徒看来当然是仰赖基督耶稣。因此也可以说时间和永恒之不可能的衔接由于耶稣的诞生而变成了可能。奥古斯丁显然虚化了物理时间,将之收,并准备在内心的平静中熄灭时间之光以待永恒的开启。
四、舍勒现象学神学的位格之永生
奥古斯丁先行于后来的康德和海德格尔等人,将时间存在问题置于生命存在的可能性上阐明。
亚里士多德还否定了时间有开端和终结。亚里士多德认为时间具有向过去追溯的无限和向未来生成的无限。这并不是说时间坐拥了两种可分离的无限。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无限是不可分的,因为把无限一分为二,这两个部分也应该还是无限,按照部分必小于整体的原则,分出的两个部分的无限则应小于原来的无限,但是说一个无限小于另一个无限显然说不通。②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对无限的分割论证之所以错误在于把无限当作了实体,只有作为实体存在的个别事物才具有小于其整体的部分。亚里士多德从具体事物上进一步论证:无论是复合物体还是单一物体,都不能现实地是无限的。复合物如果是无限的,那么构成它的每一种元素都是无限的,而复合事物由至少一个元素构成,这就等于说,一个无限由两个以上的无限构成,而这种说法是无意义的。关于单一物体也不可能是无限的,亚里士多德则从事物构成诸元素的对立关系上论证。比如火和水,如果火是有限的,水是无限的,则火终究被水彻底消除,而这却是不可能,否则世界就不可能如此存在。亚里士多德最终认为,柏拉图“加起来的无限”和“分起来的无限”只是在潜能而非现实的意义上才具有合理性。无限既然只在观念中存在而不在现实中存在,那么它就只能相关于“数”和“量”来讲。但是时间观念又只能放在无限中才能加以理解。因此亚里士多德就把既非实体亦非实体属性的时间也放在“数”的范畴上讲。他给时间下的定义是“时间是事物运动的数”。
岩矿石标本电性参数的测量,是为了了解矿体与围岩电性(电阻率、极化率)的差异,为矿区使用地球物理勘查手段提供前提条件,也是成果解释的物理基础。实践表明,合理的测量和利用电性参数,可以提高激电成果的解释水准和地质效果[1]。
在他看来,柏拉图的时间观作为一种生命论,将宇宙视为了一个大生命,从生命的视角来构建时间概念,并将之运用到对事物运动的理解上,而亚里士多德力学上对自由落体运动的误判正是受柏拉图这种将无机运动理解为自身消耗过程的影响。
与柏拉图不同,舍勒说笛卡尔落入了另一种机械论错误,企图从无机运动时间来构建时间概念。笛卡尔以无机运动作类比,将有机运动视为位移,从根本上遗忘了生命和死亡的问题。相较于柏拉图,笛卡尔的问题更为严重。在机械论前提下,心灵时间和心理时间都没有意义。时间究竟是存在于外部世界,还是作为事物属性存在?这一系列形而上学问题也没有意义。
社会形态的发展是合规律性的自然历史过程与合目的性的主体自觉选择过程的统一。我国现阶段主导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的社会生态化治理基本范式,也是在主客观条件共同作用下历史地形成的。
亚里士多德首先要证明时间本身不是实体。他认为实体只能是个别事物、或作为第二实体的个别事物的属和种。亚里士多德采用了反证路线来证明把时间设想为个别事物是不可能的。他先假定过去和将来是时间的存在部分,然后由此假定引出时间作为事物存在的悖论:“它的一部分已经存在过,现在已不再存在;它的另一部分有待产生,现在尚未存在。并且,无论是无限的时间的长流,还是随便挑取其中的任何一段,都是由这两部分合成的。”[2]121如果合成的时间的两个部分,一个不再存在,一个尚未存在,则时间本身自然不可能是存在的事物。因之时间本身也就不可能是实体。亚里士多德同时论证了时间也不可能是事物的属性。他指出,一个事物的属性所涉及到的必然是内在地构成该事物的元素,然而时间和空间却都是外在于事物的存在。
6.利用多种德育载体,拓宽德育教育渠道。一是加强德育网站建设,创建和丰富学校德育网站,利用网站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和网络道德教育。二是树立榜样和典型,发挥模范作用。三是加强社团建设,丰富学生校园文化生活,拓宽德育教育渠道。
舍勒处理时间问题正是从这两个间性、尤其是第一个间性出发。对于有生命的存在而言,“作为一切生命要素的重要成分,死伴随着整个生命。”[4]984任何一个时间瞬间都呈现为一个由死亡作为界限而形成的独特结构。舍勒引用生物学家鲍尔的话,将生物称为“能死的东西”[4]982。基于“死”作为界限而呈现的生命时间之瞬间结构,类似于奥古斯丁的“三重现在”[ 奥古斯丁的“三重现在”指:过去的现在、当下的现在、未来的现在。“三重现在”不存在于自然中,而是存在于人的心灵。“这三类存在于我们心中,别处找不到;过去事物的现在便是记忆,现在事物的现在便是直接感觉,将来事物的现在便是期望。”(参见[古罗马]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47页。)]。“连续的生命程序和有关这一程序的内在意识的每个任意的(逐步的)阶段的结构,包含着在此阶段中可发现的那个内容的三个独特的延展向度。”[4]975舍勒的这三个延展向度就是“直接的目前、过去和将来”[4]974。这三个向度的可变内容(XYZ)则是由意识的三种行为方式——“直接知觉”、“ 直接回忆”和“直接期待”[4]974——所给与的。舍勒使用“直接”一词来强调生命时间瞬间结构的直观性。
生命时间的这种瞬间结构还有一个功能,即显示生命变化的方向趋势,或者说在各个向度上生命之总量的分布趋势。对这一趋势的经验也被称为“死之方向的体验”。表现为生命总量在三个向度上分布的趋势是将来向度上渐少,过去向度上渐增。最后,将来向度上的生命总量之分布为零,则垂死经验就被给与。舍勒说:“我们并不走出客观时间内的一个唯一的生命瞬间,只是诞生和死亡除外。”[4]976生命瞬间在此被称为“唯一的”,当然是就其作为结构而言的,时间经验的内容流变,而瞬间结构不变。每一个瞬间,指的是“方向趋势”[4]976的变化而言的。至于诞生和死亡,诞生的时间点上是因为生命还未进入到瞬间结构之中;死亡使得生命从瞬间中走出来,其后果是什么?后果如果不是生命的终止,就只能是永生。
舍勒从生物的生命问题转到位格(Person)的永生上来。早期的神话图腾中似乎整个生物界都有位格,而基督教意义上的位格则是神和人所具有的。舍勒认为位格是人行为的统一和中心,更是人神共通的中心。人所具有的是有限的位格。而上帝则是位格的位格,即“无限的神圣位格”[4]863。
舍勒特别强调的是“精神——身体”这一序列中的位格。他的身体概念不同于平常所说的躯体或器官形,而被定义为“我们能够使之获得直接的自身被给予性的东西”。 平常谈论的身体是生理意义的躯体,舍勒的“身体”则“是一种心理物理学上无差异的现象上的被给予性”。[4]1015基督教关于“肉身复活” 的形象化理念被舍勒定义为“身体归属于位格”[4]1015。显然这个归属是不能反向的,如果相反,位格归属于身体,那肉身的死亡就必然造成了位格的终结。
身体归属于位格。精神性的位格能超越身体及身体状态的界限。这一现象被舍勒称为“飘逸”[4]1015体验。这里不仅仅是说人的精神逸出人的身体之外存在,舍勒更想指出的是,人在身体衰退、垂死之际作为位格而继续存在着。他说:“在本质序列中,位格之永生能达到多远呢?我的回答是:能够达到这种超溢,即精神对生命的超溢所能达到的程度。更多的,我就不知道了。”[4]1014-1015对于位格死后如何实存的问题,舍勒将其视为毫无敬畏感的好奇。这一态度并非基督教信徒的偏见使然,而是基于舍勒的现象学神学立场。现象学的方法决定了其表述方式不能超出意识的体验领域来讨论问题。
舍勒通过批评柏拉图以来对时间和永恒观理解的误区,将时间融入生命视野中,并引入“位格”这一人神相通的神学概念,将永恒问题放到神学的永生信仰中。这一创见悄然融汇了世俗哲学与信仰神学,也就回避了奥古斯丁以来“心灵时间”等神学时间概念是否具有世俗普遍性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柏拉图. 柏拉图全集(第三卷)[M]. 王晓朝 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2]亚里士多德. 物理学[M]. 张竹明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3]奥古斯丁. 忏悔录[M]. 周士良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4](德)舍勒. 舍勒选集[M]. 刘小枫 选编. 上海三联书店,1999.
ReligiousTimeAndPhilosophicalTime:FromPlato’sLivingUniverseTheorytoScheler’sPhenomenologicalTheology
YANG Jie-gao1,SUN Shang-cheng 2
(1.School of Politics and Law,Yulin Normal University,Yulin 537000,China;2.School of Marxism, Hunan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2,China)
Abstract: Plato’s discrimination between two types of eternity reminds two basic time horizon: one is a theological time horizon is revealed when the original eternity is regarded as a time entirety, and the other one is a philosophical time horizon which is formed by taking the time’s overall stretching as time’s present. From Plato’s continuous eternity, Aristotle raised a physical time horizon based on pure philosophy. However Augustine tried to set a psychological time to replace the physical time in order to returned to Plato’s theological view. Since Plato, both theology and philosophy, while discussing a matter of time, focus on a problem: what kind of relationship is between time and the movement of the physical world. Using eternal life and everlasting punishment , Augustine echoes two Plato’s eternal conception. However Augustine’s answer is considered to be lack of secularization. In his Phenomenological Theology, Scheler puts forward a “etenal life” of “person” ,which starts from the creature’s life, based on Augustine’s theory. On the basis of “person” which is kept by people and God together, he integrates the secular philosophy and religious theology.
Keywords: Plato; two types of eternity;Augustine;Scheler
中图分类号:B502.232,B9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7408(2019)02-0083-05
收稿日期:2018-06-13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理性宗教在乡村社会的影响研究”(15YBA09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洁高(1975- ),男,安徽安庆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历史哲学和诠释学研究。
通讯作者:孙尚诚(1976- ),女,湖南长沙人,助教,博士,瑞士巴塞尔大学博士后,主要从事宗教哲学研究。
标签:时间论文; 奥古斯丁论文; 柏拉图论文; 亚里士多德论文; 生命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哲学理论论文; 哲学流派及其研究论文; 其他哲学流派论文; 《昭通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论文; 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理性宗教在乡村社会的影响研究”(15YBA095)阶段性成果论文; 玉林师范学院政法学院论文; 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