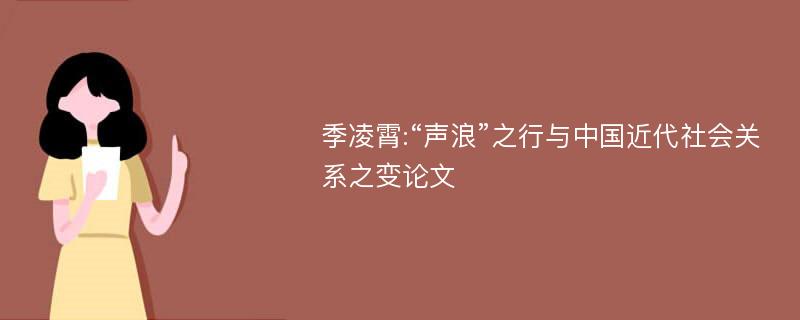
【内容摘要】以“声浪”为关键词,考察其在近代随西方声学东渐而经中译并进入大众政治语境的过程和衍生出的多重涵义,观照同时兴起的政治公共生活,后者既以“声浪”来描述,又以公共空间中实在的“声浪”为媒介,以此为线索,讨论近代中国声音知识转型与社会关系变迁之间并行、勾连的关系。“声浪”所表述或体现的公共生活,由社会的智识阶层发起,通过声音/言说得以组织,最终诉诸民众所组成的共同体。而公共生活之声音空间中秩序(因而也是关系)的建立同样以“声浪”为中介。这里的“声浪”与其声学涵义保持关联,声学新知为理解社会关系变化提供了语汇资源。这与传统中国关于声音-政治的论述和实践在在不同。
【关键词】声浪;声音;声学新知;社会关系;公共生活
1874年,江南制造局出版了英国物理学家田大里(John Tyndall)《论声音的八次讲座》OnSound:ACourseofEightLectures一书的中译本《声学》,该书由傅兰雅(John Fryer)口译、徐建寅笔述,是为将声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系统性地向中国引介西方现代声学知识之肇始。③在《声学》中,傅兰雅与徐建寅应是首次将sound wave译为“声浪”,形象地描述了声音在空气中传播、行进的样态宛如海浪。④
“空气生动传动而成声之理……人耳觉有声者,因空气之质点荡动而撞耳底之膜也……其各层空气传动之势,实同于海浪之状,故名曰声浪……声浪之传动,借空气各层之点,稍有来往,荡动成浪而前行。”①
“陶议员镕、易议员宗夔、于议员邦华皆争相起言,声浪激应,议场中立议最多者惟此数员,一时议场中之秩序为之大乱。”②
第五,碳排放强度持续下降,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十三五”期间碳强度下降率被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成为经济发展的硬性约束。2017年中国碳强度比2005年下降约46%,为实现“十三五”碳强度约束性目标和落实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奠定了基础。中国积极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等,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坚定表态中国将继续履行减排承诺,以坚定的减排决心和瞩目的减排成效逐步走向全球气候治理舞台中央。
“声浪”是西方近代声学的核心概念,它的引入意味着给中国原本的声音知识带来变革。对于声学之东渐史以及中西关于声音所持不同认知和文化立场,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之“声(声学)”一节中曾作如下评价:“早期中国人关于声的性质的思想是建立在‘气’的概念之上的。事实上,这种概念一直持续到近代,并且只有在近代物理波长理论的影响下,学术界才放弃了这种看法。”⑤李约瑟的这一论断已然受到了挑战。戴念祖在其专著《中国声学史》中细致地检索了大量论及声音的中国传统文献,他认为“振动产生声音”“声音由于空气而使人听到”等观念古已有之,例如唐代《乐书要录》已经指出“形气者,声之源”“形动气彻,声由所出”。除此之外,戴氏一并指出,传统中讨论声学时所说的“气”亦不仅仅是哲学概念上的“元气”,时而亦包含“空气”之意。⑥但这些只是零散的讨论,远非系统的知识,更没有进入一般知识人或广大民众的观念当中。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李约瑟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是成立的。至少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声音所持的一般见解与西方近现代声学知识相比,存在很大的不同。
进入20世纪,“声浪”从原本的科学读物转而进入更为大众化的文本(包括报纸与小说)中,用以描绘社会公共生活的声音方面。伴随“声浪”这段跨越语境的行旅,是“有声中国”的出现,演说日益成为“相互沟通及表达思想观念的手段”⑦,群议则是重要的甚至逐渐制度化的政治生活方式。应该说,正是由于声音之行也似“浪”,才可借此进一步想象公共空间中各人各处所发声音之汇聚、激应或是相互干扰。反过来,正是随“有声中国”之出现,“声浪”才得以成为表述它的语汇,“声浪”之语义延伸,已然体现出新的社会关系之形成。正如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关键词研究中所指出的,语言不仅“映照社会、历史过程”“一些重要的社会、历史过程是发生在语言内部,”并且“意义与关系的问题是构成这些过程的一部分。通过不同的方式,语言里出现了各种形式的新关系及对现存关系新的认知。”⑧近代不断拓展的公共生活通过“声浪”而体现,其逐渐秩序化的要求亦通过对“声浪”的关切而得以表达。
本文即对“声浪”作关键词式的考察,追溯它在晚清民初不同文本中的踪迹,梳理其使用语境与意义的变化,并以此为线索,尝试理解中国近代声音知识转型与社会关系变化之间的并行与勾连。实际上,不仅“声浪”,这一时期还有不少自西文译出的科学词汇跨越语境、延展了原有的语义。例如,谢弗(Ingo Schäfer)分析了谭嗣同是如何借用“以太(ether)”这个概念来发展其后期哲学的。阿梅龙(Iwo Amelung)则探讨了晚清中国对西方力学的接受过程,包括术语的翻译、寻找力学之“中源”的努力,以及力学词汇是如何进入哲学与政治论说的。⑨与“以太”或“力”等概念不同的是,“声浪”是更为具体形象的词汇,它没有被过多地牵涉进哲学层面的推演或是较抽象的政治论述,“声浪”就构成切实可感的公共生活之声音空间。因此,本文要考察的“声浪之行”,不仅是声音新知自西徂东、“声浪”一词跨越语境,也是公共空间中的声浪如何散播、如何被感受到。我们不仅能够借由新知的接受、意义的衍变来理解近代兴起的政治公共生活,后者本身亦有微妙的变化,体现在对“声浪”的关切中。
一、晚清声学东渐与“声浪”的译出
地质工程中,由于节理和地质分割等构成了结构面,这使得地质项目工程的风险具有较为明显的多变性和复杂性。另外,该风险不仅与地质本身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也与人为的不规范操作有关。同时,外部因素也会对项目工程产生负面影响,进而阻碍工程建设的正常进行。
“古人闻牛鸣窌中而知宫,离群羊而知商,听雉登木鸣而知角,见豕负而骇而知微,听鸣鸟在树而知羽,五音之妙,能以耳力得之。自黄帝命伶伦象凤鸣而造律吕,每三分而损益,隔八位以相生,而度量权衡规矩准绳皆出于黄钟之管。且律吕可以候天地自然之气,由是播诸八音,以宣八风,听之者可以知兴亡治乱善恶灾祥之故,微妙至于如此。”
那么,声音在空气中传播的样态究竟如何?1874年出版的《声学》以“浪”来描述之,“各层空气传动之势,实同于海浪之状,故名曰声浪。”有趣的是,《声学》不仅将sound wave译为“声浪”,又以排列推动的小球与孩童为例,辅以图像来说明声音是如何经空气“传动”最终及至耳膜的(见图1):
图1《声学》插图
“以甲乙丙丁戊五童鱼贯成列,各童之手伸直而搭于前童之肩。设有人忽推甲童之背,甲童必推乙童,乙童推丙童,丙童推丁童,丁童推戊童,戊童因前无所推,必向前而仆。设前有大鼓,其手必击动鼓面而作声,虽有百童,亦必如此,声过空气而动耳内之膜,与此同理……其传而复退即同于气点传声时之状。气点因有凸凸力,声浪经过之时空气各层向前击其邻层,经过之后仍自后退,气点之凸凸力愈大,荡动愈速,传声亦愈速。”
在启蒙事业中,声浪的作用在于带来思想与情感的震动,最终达成民族的觉醒——“百余载之睡狮,公等以最平最稳之声浪唤醒之。”
《声学》是关于现代声音知识的专门译书,且其影响很大。李莉在对晚清介绍声学的各类出版物进行比较之后认为,跟《声学》比起来,其他或失于零散,或更为简略浅显。“直到20世纪初,在中国传播的近代声学知识,基本上没有超出《声学》一书的范围。”
马拉松的发展离不开赛事推广与营销,世界马拉松大满贯赛事在赛事推广方面都会利用慈善赛提升赛事美誉度和可信赖度。其次,在赞助商方面各赛事都会寻求媒体伙伴,通过宣传扩大赛事影响力。例如柏林马拉松的媒体伙伴为7家,芝加哥马拉松7家,纽约马拉松4家,波士顿马拉松更是不愁媒体合作,合作的媒体有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美国WBZ有线电视台、美国福克斯广播公司、英国广播公司、欧洲新闻电视台及世界知名媒体[6]。
1893年,晚清另一本重要的声学译著《声学揭要》刊行,该书由美国传教士赫士(W.M.Hayes)口译、朱葆琛笔述、周文源校订而成,由登州文会馆刊出版。《声学揭要》基于法国加诺(Adolph Ganot)所著《初等物理学》(Elementary Treatise on Physics)之英译本第14版,并略去了原书中难度较大的章节,因而是较为初级的读物。需要指出的是,《初等物理学》的英文译本在法文原版的基础上,辅以田大里的讲座内容为补充,因而《声学揭要》与《声学》很多内容是重合的。《声学揭要》同样介绍了“声浪”这一概念,说明“扬声”过程在空气中形成圈层状的“气浪”,其中发生了各层空气之间的碰撞。
“声浪”作为一种新知,在晚清最后几年的教育改革中,进入了高等小学理科教科书:
“空气传声,自发声处之周围,因其颤动,触击空气。空气之质点,即递紧递松,回环成浪,而波及于远,是谓声浪。”
可见,在“声浪”译出之后的短短30年时间内,至少在接受一般学校教育者那里,它已成为必须要了解的基本科学知识。
实际上,声音在空气中传播是空气“质点”的纵向运动。《声学》已经指出,“声浪之传动,藉空气各层之点,稍有来往荡动成浪而前行,并非直透各层而过也。”1898年《时务通考》出版时,对此有所解释:“其层层传动之势,实同海浪传行之状,浪行而水不行,声往而空气亦未往,不过质点往复荡动而已。故声之行动亦以浪名,谓之声浪。”1900年翻译出版的《物理学》进一步指出声光传递过程中的“浪”,“非其运动之实质,自己进移,乃实质之各小分之震动传播。”(见图2)
图2高等小学理科教科书(卷四)插图
对于19世纪晚期的一般知识人来说,要理解分子(质点)运动也许仍有一定难度。但“声浪”作为一种对“空气扬声”过程的形象描述,更新了国人对于声音何以能够从其源头传出并及至听觉者的理解,从此即可借“浪”这一具象来想象声音的传递。
在一轮历史复习中,笔者还想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复习开始前一定要制定一份可行性强的复习安排,挑选好的参考资料有助于学生的复习。另外,还需要清楚课本和参考资料的关系,记忆和训练的关系。通过有效的复习措施,在高三最后一年中也可以有一个惊人的突破。
二、晚清知识人对声学新知的接受
1.传统声音-政治话语和实践与近代中西声学的对接
对于晚清读书人来说,“声浪”是一种新知,在不同于其所接受传统教育中关于声音的“旧见”。那么,他们如何接受、又在何种程度上理解西方声学?下面我将围绕《格致书院课艺》等材料对此问题展开讨论。1886年至1894年间,致力于西学译介与传播的格致书院将学子之课艺佳作辑刊为《格致书院课艺》(以下简称《课艺》)。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窗口,以了解清末乐于接受新学的一般读书人所建构起来的知识图景。在提交给格致书院的课艺论文中,晚清学人在中西科学、哲学、社会与政治思想以及时务等等方面一抒所见,其中亦零散地论及声学。从这些有限的议论中我们能够了解到,声音波动等知识在何种程度上对读书人来说是可(或不可)理解的。而我将首先占用一些篇幅,借助《课艺》的一段材料来展示中国关于声音的传统认知,以及它如何被嵌入到人-自然以及政治秩序的整体之中。由此我们可以反过来理解,为何近代政治形态——即社会关系形态——之变化,需要一种替代性的关于声音的话语。这段材料首先出现在长沙学生彭瑞熙答1887年春季课题“格致之学中西异同论”的论文中:
在产后42天,顺产的女性生殖系统逐渐恢复到孕前状态,而剖宫产的女性可能在产后8周恢复。不管剖宫产还是自然分娩,喂奶充分的产妇,恢复排卵的时间晚,雌激素水平稍低,阴道黏膜层较薄,宫颈分泌的黏液较少,产后第一次性生活时,有人感觉干涩或者疼痛,以后逐渐恢复正常,大部分夫妻感觉性生活质量与孕前无变化。
这段材料先是追溯了古人以不同的听觉方式积累声音知识的三个阶段,首先,是通过微妙的耳之听觉获得“五音”,后者原本均为自然流露、鸣响之声;其次,是通过模仿凤鸣创制律管;最后,则是以律吕候察自然之气。实际上,上述均为以听觉沟通自然的方式。继而,彭瑞熙引入了“风”和“气”这两个古代声音知识体系的核心概念。王小盾将“风”解为“在天地之间流动的气体”,“气”则更为抽象,是“有生机的元素,联系于呼吸及其节律”,两者均是听觉的重要对象。以耳听风和以律察气作为古代重要的听觉实践,其对象不止于具体实在的声音,本质上是天、地、人之“气”,包括节气、气象、物候、地理方位、人世秩序等等。同时,上述听觉活动同时也是仪礼的构成部分,意在感知、交通、应和自然之气。这就不难理解律、历共生,律原为历法制度,“以耳齐声”“鸟声校正”“管器定律”正是中国历律学的建立过程。可见听觉实践在古代祭祀神明、指导农事与人事等方面(或进言之,在社会生产活动安排与社群治理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声音知识从一开始就与政治有关。
既然听觉的对象不止于实在的声音,听觉能力就不能单凭耳力(或者说物理的听觉范围)来定义。王小盾援引《庄子》区分了三种听:“听之以耳”,是“仅接触事物表面的愚人之听”;“听之以心”,是“可接触事物本质的聪人之听”;“听之以气”,即“掌握天地万物之数理”的圣人之听。另外,他还追溯了“圣”之原义指通达天意和耳聪目明,这是一种“抽象方式的听”,原属巫的德性。
以超凡的耳力洞觉与顺应天、地、人之气是统治者应当具备的品质,其中也包括民风(民之声),这落实在先秦的采诗制度当中。《礼记·王制》言,“天子……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郑玄指出“陈诗”是“采其诗而视之,”孔颖达疏曰,“此谓王巡守见诸侯毕,乃命其方诸侯大师是掌乐之官,各陈其国风之诗乃观其政令之善恶。”王弼将《论语·泰伯》中“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解为,“夫喜惧哀乐,民之自然,应感而动,则发乎声歌,所以陈诗采谣以知民志风。既见其风,则损益基焉,故因俗立制以达其礼也。矫俗检刑,民心未化,故又感其声乐,以和神也。”可见,诗之兴同样出于自然的感应,采诗实是礼乐制度的一部分,它是声音性的,且乐在政教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至此,我们不妨反观在包含了声音的一套政治话语-实践当中,声音(尤其是其媒介特性)究竟如何。首先,声音有其抽象的性质,声音是自然之中运动的“气”的表征,实在发出的声音仅是它的一个层面。与之相应地,听觉同样可以是抽象的,尤其是“圣人之听”。再次,无论发声或听觉,都强调是与自然的感应。既是感应,那便没有时间性,即不强调声音发出与传递的过程,也削弱了声音作为一种主体表达的媒介。最后,声音在政治制度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礼乐承担了教化的功能,采诗听风则是统治者洞察民风与政令的方式。但或许正因为这一“圣人之听”并非实在的听,声音本身作为媒介便可能被替代。根据阎步克的研究,秦代创立御史监郡制度,御史负责接收和保管文件(史主书主法),是国君的“耳目”,实际上对地方或民间情形的知晓已转而以文字为主要媒介。而即便是在采诗制度当中,亦需经乐官的收集、整理,采诗绝非民众以声音直陈天听。读者会发现,本文在回顾中国声音-政治话语与实践的传统时,隐约以西方声学以及声音在民主政制中的角色为参照。由此,我们可以反过来理解,何以近代政治生活方式、社会关系发生变革时,无法从原有的关于声音-政治的论述中得到支撑,转而要挪用西方声学的语汇。
再回到《课艺》的答卷,针对前文所引的这段材料,彭瑞熙和宁波学生王辅才分别对中西声学作了比较:
“彼西人《声学》一书,未必能出其范围也。”
19世纪下半叶,声学知识作为“声光化电”之学/西学中重要的方面被引介到中国,在《声学》译出以前,已散见于一些科学出版物中。1855年,上海墨海书馆出版了英国传教士合信(B.Hobson)编辑的《博物新编》,以图说明置于无气的玻璃罩中之钟“无声”,指出传声需要空气。⑩1859年,李善兰所译《重学》介绍了声音在空气中传播的速度值。1866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著《格物入门》;又经1889年、1899年两次修订而成《增订格物入门》和《重增格物入门》,其中亦涉及声音知识,归入第二卷“气学”中。其中说明了人能够听到声音是因为“外物相触,天气动荡,扬至耳内而成声”,并且无“天气”则虽“极大声音断难达于星月之际。”1872年至1875年间,由丁韪良、艾约瑟(Joseph Edkins)主编的期刊《中西闻见录》ThePekingMagazine中,曾连载有《论音学》一文,定义“音学乃考验各种之音、发音之理、传音之据也。”介绍了发声与传声的原理,“无论何音,皆由颤动而生;”“音之传扬,当由有体质之物发出。”这些零星刊载的声学新知,将声音的传播当作需要考察的过程来看,指出声音由振动产生、声音的传播需要介质——常常是空气。
“声浪”是启蒙的媒介。进入20世纪,宣讲、演说甚至改良戏剧等有声的口头传播方式日益成为启蒙的重要手段,“启蒙的声浪在城市、街头、寺院、戏园、茶馆、山野乃至村落,此起彼落。”借助于言说的启蒙是一种单向的、有目的的、功能性的(因此是需要“听清”的)传递信息与号召社群的事业,是先觉者的声音及其信息传向被启蒙者的线性过程。这与“声浪”强调声音的传播过程是相契合的。
有趣的是,根据戴念祖等人的研究,我们已经知道,在近代以前关于声音这一物理现象,中国已经积累了丰富的(且有分异的)知识和具体应用。然而,彭、王二人在追溯中国“声学”时,仍然回到早期,这颇堪玩味。也许如王小盾所言,上古时期人之生存格外依赖听觉,将耳朵看作同神灵交通的器官,其听觉能力达到极其高超微妙的地步,这种能力在后来的历史中已然丧失了。因此,这一时期既是听觉知识的滥觞,亦是其发展的一个高峰,对后世来说甚至略带神秘色彩。故此,彭氏才说西方声学“未必能出其范围”。
与此同时,我们或能将前引《课艺》所述视作一直持续到近代的关于声音的正统论述,它确立了声音在人-自然及政治秩序当中的作用,特别是将顺应自然之气、将超常的听觉能力留存在“圣人”身上,实则从声音的角度固定了一套关于政治合法性的话语。这种正统论述与儒学在中国无与伦比的地位有关。正如阎步克指出的,“儒”很有可能就起源于古代乐师。尽管后来儒生学者与音乐或声音的关系弱化了,但关于声音的正统叙述保留下来。这是一套关于人世与自然秩序整体的说法,故而王辅才意识到中国之言声是“务其大者远者”;而西方声学的成就在于“法”,在于对实在的、作为传播过程的“声浪”进行细致的测量与推定。
彭、王两人的回答,都试图将西方声学纳入到关于声音的传统话语体系当中。其中既显示出晚清一般读书人对西方声学新知的理解尚且有限、中西声音知识体系之间存在隔阂。这一接受情况实则体现出传统话语的根深蒂固——无法抛弃的正是这套话语中以声音为中介的政治秩序。而另一种声音知识体系的进入,将声音从原有秩序之中解开,将之作为客观的物理对象来探究。相应地,后面我们将会看到,“声浪”和与之相关的近代政治公共生活是多么不同。
2.人声如浪:吴趼人的理解
从《课艺》的讨论来看,晚清知识人基本接受了“声浪”这一概念,提到声学总会言及“声浪”,并了解到“声浪”有其行速、可以测量。但由于缺乏系统的基本物理学教育支撑,对“声浪”等新知的理解不免失之浅表。前文已经说明,中西声学在知识上无法建立衔接。因此,对“声浪”及其知识的接受常常依赖于日常生活的经验。最直截的方式,是以水浪来参详声浪,如描述声音在空气中传播“与海浪同”“与浪因风激相同”等。有趣的是,晚清小说家、报人吴趼人起初对“声浪”却存有疑问:
“声学家之言声也,曰:‘声有浪。’闻者咸疑焉。又曰:‘声之为浪也,如以石投水然,石所投处,即声所发处。视石下水时,水之涌而成浪,散为圆旋,渐远渐微,至不可见乃已;声之传浪亦若是云。’吾初不之信也。迩者入市,市人嘈杂若鼎沸,闻声而不能辨音。于是恍然悟,声浪错杂之不能辨音,犹之水浪错杂之不能辨纹也。继而更有所悟焉。夫水之为浪,平行而已;若夫声则合东西南朔上下,皆得而闻之。是则声浪之发状,其如球乎?惜乎声之为物,无形无质,不可得而见耳。”
购物网站为互联网用户提供了分享和表达他们对已购买的商品兴趣和观点的平台。每天,数百万用户在购物网站上发表大量的评分和评论,反映他们对不同物品的喜好程度。手动分析这些意见并进行推荐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因此,挖掘评论数据并通过算法进行个性化推荐应用十分广泛。但是推荐的算法研究仍然有空间,诸如数据稀疏[1]、适用范围狭隘[2]、冷启动[3]、推荐的实时性[4]等问题仍然没有完全解决,在个性化推荐方面的研究空间充足,仍然需要众多学者不断加深这方面算法的研究。
根据吴趼人的叙述,他开始无法想象声音是海浪状的,直到进入市集、置身于鼎沸的人声之中,才由“声浪错杂之不能辨音”联想到“水浪错杂不能辨纹”,并借此进一步来理解声浪发出之样态,是朝向所有方向的一个空间。换言之,他是经由切实地身处人声的场域之中来理解声浪这一概念的。值得注意的是,“声浪”一词在这里转变为“声有浪”和“声之为浪”,“浪”成为“声”所蕴含或制造的宾语。尽管吴趼人的理解方式未必具有代表性或逻辑性,这里特意提及,是因为这种理解方式在作为西方声学概念的“声浪”与公共生活之声音环境之间建立了连接。用以理解“声浪”的日常经验除了“水浪”,还有对公共生活声音嘈杂的体验。我认为这种连接并非偶然。浪与市声早已有之,正是在近代声音知识发生更替的转折点上,“浪”这一隐喻才被带入了公共生活的声音空间。
三、近代公共生活中的“声浪”
进入20世纪,“声浪”成为大众文本当中的常用词,常常直作“声音”解。例如,“此自鸣钟之声浪,直达于美芬之耳鼓中。”这说明“声音”一词之常见,它不再是新鲜的、有待普及的声学知识,并且开始容纳其他意义,尤其是政治的。文章的这一部分将对“声浪”作关键词式的梳理,并借遗存纸上的记录观照现实的声音及其所中介的新的社会关系。
王东杰论及“近代言语文化的兴起”,认为其重要因素是“以‘国民’为核心的一系列政治理论的广泛传播,以及围绕这一概念组织起来的新兴政治行为和机构的出现。”“民众不仅经由‘声教’被启蒙,他们还是现代政治的广泛参与者、在理论上是政治权力的最终来源。”这一论述道出了以声音或言说为媒介的近代公共生活(以及相伴发生的社会关系变化),其中重要的两个方面,一是以声音/言说传播思想、启蒙民众,二是民众同样能够发声。这两个方面皆有“声浪”的介入,既在隐喻层面,也在现实层面,既在意义层面,也在声音层面。
“其实中国之言声,不过务其大者远者,且亦徒存其理,法则早已沦亡。西人则无论物之微者,事之细者,苟与声学相关,即不殚缕晰条分,以笔之于书,以传于世。此西人测音之法所以反能日异月新也。夫总而言之,则曰声,分而言之,则又有传声回声之殊。行声透声之别。声之传也,全赖空气,而其传动之势,与海浪同,故又名曰声浪。声之回也,回折数次,每次渐淡,故曲折峰峦内,回音必大,继则渐小,以至于无。声行则与光行之理相同,声透则与光透之理无异,并可以同法试验。至若弦音管音及一切钟鼓之音,明其质点,详其功用,西人亦推阐入微,所以声学出而寻常之器之用几穷也。其测音之法虽繁,然亦无非凭籍乎器也。有一种测音器,无论何音皆可一测而知其大小多寡。”
情况 2.1 B2中至少有一个子集是Y中顶点的色集合,不妨设为{1,2,3}。由{1,2,3}是Y中顶点的色集合,可得:1,C(ui), i=1,2,…,10,则每个C(ui)只能是以下集合之一:{1,2},{1,2,3},{1,2,4},{1,2,5},{1,2,3,4},{1,2,3,5},{1,2,4,5},{1,2,3,4,5},得出矛盾。
“声浪”描述了启蒙既借助于声音,同时也表达出它所带来的冲击、震撼力量。晚清“科学小说”《新法螺先生谭》中,觉醒的法螺先生欲以一己之声浪唤起“宵梦方酣”“善根性被侵蚀”的四万万国人:
“唤醒国民,其余之责;虽然,我灵魂仅存四分之一,虽欲发声,则声浪必微,吾同胞国民,既散处在八千万方里面积之亚洲上,又乌能一一振聩觉聋,而醒其痴梦耶……将以求我灵魂之身,而炼成一不可思议之发声器。”
《声学》将耳膜比作鼓,声音从发声者开始,层层推动中介物质的“质点”,最后敲击耳鼓使人听到。根据这种理解,声音传递是点到点的、有介质的、波浪状的线性过程,且这一过程在形象上呈现为推动力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言说或声音为媒介的启蒙事业中,除了以言语传递意义之外,声音同样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克莱默尔(Sybille Krämer)正是以声音为例提出了媒介的“轨迹(Spur)”概念,她说:“声音制造了陈述,但是它也诠释了被陈述的内容。它用它的整个……身体性意指了那种在言语中说出的东西……声音与言说的关系就类似于无意中使用的轨迹与有意识使用的符号之间的关系。”克莱默尔是想表达媒介本身(这里是声音)在媒介活动(言说表达)之中留下的痕迹,这提醒我们将注意力转向“声浪”本身。
1903年4月,俄国拒不执行《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拒绝从东北撤兵。为表抗议,4月27日开始,爱国人士在上海张园安垲第举行集议。在30日的集议中,“蔡君民友登台演说开会大意,次马君君武演说,次诵《爱国歌》前二章。千人同声,音节甚壮。既而争先题名,中国万岁之声震屋壁。”这里,声音不只是爱国演说中传递信息之载体——正是“千人同声”的音量与雄壮声气使身处其间者深受震动。“中国万岁之声震屋壁”明确地表达了声音本身的力量,对其感受是触觉性的,惟其身处这一声音空间之中才得体验。应该说,在张园拒俄集议的个案中,“声浪”的力量是声音的物理层面(千人同声、音节甚壮)与意义层面(拒俄、爱国)在具体场景当中的重合。众人一齐高呼的“声浪震荡不已”,叫人无法充耳不闻。
20世纪20年代,清华大学由于“在大视觉听讲演时,后面坐者,常听不清楚”,故“请叶企孙博士研究大礼堂之声浪,及其改良方法。”到20世纪30年代,西方现代建筑声学通过一些专业建筑杂志译介到我国,细致地考察了声浪在建筑物中的传递、吸收、折回、相互干扰等等原理,并针对电影院、广播无线电放送室、会场及音乐厅、静室等不同场合,给出相应的声学建议。同一时期,随着有声电影的流行,电影院的广告中也开始强调在有声机、正音纸板等声音设备方面的投入,“为求声浪的更完美,更清晰”或是“发音纯粹,绝无杂声……声浪普及”。
一旦报刊成为集群的手段,“声浪”亦能以抽去声音的方式存在于印刷媒体当中,例如有“报纸之声浪”等语。报刊甚至走得更远,它能克服物理距离将散落的声音集中、组织起来:
“今日幸与诸父老昆弟情话一室中,不敢自闭,辄发表一二。诸君如表同情,或认招股份,或认任撰述,群策群力,聚室以谋。俾成此五千年来吾皖人之出版物,上之可附陈诗之遗,下之即为乡土之史,而前途所最绝特之潜力,则能使流寓他省与游历外洋之同乡,声浪相切,电力相吸,组成一有机体之大群,此其希望尤为无穷也。”
这则材料颇为有趣,作者(演说者)既借助于一室之内的言说呼吁同乡杂志的出版,又将演说辞刊登在《申报》上。作者立足于地方,将同乡出版物与“陈诗”与“乡史”联系起来,即同时与声音表达和文字记录联系起来——如果说声音是一室之内、一乡之间表情和结群的媒介,报刊则是其在更广阔地理范围内的一种延伸。报刊能汇集“声浪”,它扮演乐官或史官的职能,对采集的声音进行组织与修整,如此才能“组成一有机体之大群”,其中已留下印刷媒介的“轨迹”。
现实公共生活中的“声浪”同样可能是嘈杂与混乱的,故而内含着对声音作为启蒙或群治之媒介的破坏性。梁启超在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描写了上海张园集议演说“众声喧哗”的场景:
“却是座中这些人……那坐得远一点儿的,却都是交头接耳,卿卿哝哝,把那声浪搅得稀乱……他们那拍掌是很没有价值的,随便就拍起来。那坐得远的人,只顾谈天,并没听讲。他听见前面的人拍掌,便都跟着拼命的乱拍,闹到后来,差不多讲一句便拍一句,甚至一句还未讲完也拍起来,真个是虎啸龙吟,山崩地裂。”
遇此嘈杂混乱的场景,座中便有“新式人物”来维持议事的秩序:
“只见一个扮外国装的,忽的一声,跳上台去,扬着手中的木杆儿,大声说道:‘今日在这里是议事,不是谈笑!奉劝你们静点,不要在这个文明会场上,做出那野蛮举动出来。’”
王今认为,许多集议演说的旁听者,亦是张园其他各类娱乐演出的参与者,“他们很大程度上延续的是在传统的戏楼、茶园里听戏和听说书时的模式”,而演说属西方传统,其中的听觉模式是舶来的。站在启蒙者的立场,他们焦切地希望启蒙的对象能够留心听讲,而非像在茶园中那样注意力分散,他们试图确立启蒙“声浪”之绝对主导的地位,但散漫的听众却同样用发出声音的方式将之“搅乱”了。“声浪嘈杂”使“演词半未明了,”破坏议程。甚至在新开国会中,乱发“声浪”是议员扰乱议会的方式。
因此,亟待在公共生活空间中建立起“声音的秩序”,这一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智识阶层所倡导的。在启蒙或议事的场景中,应确保发言者的声音被听清,消极的喧哗应当被取消,但在适当的时候,民众亦可齐声应和,共同组成集体的声浪以表达“民意”。
公共生活“声音秩序”的重整恰是从戏剧演出场所开始。以1908年开业、取鉴欧洲与日本剧场格局的新舞台为首,改良剧场讲求“声浪洞达”“视线、声浪、空气三致意”,采用舞台与联排座椅的形式,实行卖票制以取代传统的案目制,一改传统茶园中散漫喧闹的观剧/听剧方式,还“取消了在剧场内抛手巾、泡茶、要小帐等种种老式茶园剧场的旧习”,“净化”了原本更为喧杂的声音环境,除此之外,改良新剧亦更多采用念白,以期戏剧启蒙的社会功能。“听清”的要求愈益增长。应该说,戏曲改良与剧场物理空间的改造是同步的。
“声音秩序”的建立着力于两个方面,一是在公共场所中人之行为(发声或沉默)的规训,二是从建筑空间设计入手,关切声音(特别是有“意义”的声音)在建筑之中传送的效果。后者作为建筑声学的问题,愈益受到重视:
“会场建筑曾聚多数部员悉心讨论始定办,法该场之顶棚系为人字形,愈上愈锐,迨告成后,试验演说时则发言声辩论声以至步履唾吐之声无不为锐尖顶槅所摄,于是声浪嘈杂,虽有师旷之聪亦莫能辩。旋又觅请工师设法改良。据工师云非改建平顶万难合用。后由各部员竭其平日研究物理之种种心得,始购得白布百余匹,将议场顶堋幔成平面式,然布匹不能隔绝声浪,故至今每至开议时秩序稍乱,则发言之声仍令人莫能分辩。”
因此,在政治公共生活当中,一人之声无以成浪,“声浪”是群体意愿的表达,“声浪”所蕴含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正是在于“民众作为权力来源”。民国初年,有评论者发现,“同胞二字已流行多年矣,光复以后几成为一般人士之口头禅。会场之上、募饷之地,必有无数同胞;同胞之声浪接触于耳鼓,甚至公举一人、攻击一人,亦必曰为同胞。”“同胞”已从启蒙的对象变为政治诉求的旨归。
至此,“听清”成为越来越多场合的律令。原本被批评过于散漫嘈杂的启蒙对象,许多人转而成为主动沉默倾听的、同质化的声音消费者。听觉秩序的建立不仅仅依靠对“文明”行为的倡导,亦经由物理空间的设计而对听众/发声者的身体进行摆置,或是对声音进行加工,这同样能够微妙地改变人与声音、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有趣的是,伴随这一过程、在对上述场合的声音方面进行表述时,“声浪”又恢复为单纯的声学概念,惟其如此,才能对其进行测算与处理。这里,作为纯粹声学概念的“声浪”,已然包含一种对“听觉秩序”——因而是人之关系——的诉求。
四、结语
至此,我们已梳理了20世纪早期大众文本中“声浪”的多种涵义。兴起的群体公共生活以言说为中心,“声浪”则描绘了(同时也构成)公共生活开展之空间的声音状况——言说者的声音在场所中之传递或被扰乱;大众声音之杂乱稀散或是汇聚震荡;公共生活之声音秩序也愈益通过对场所中物理声音的测算与增减而建立。与此同时,“声浪”也是抽象的,它能够召唤与凝聚共同体(同乡,同胞,睡狮等等),并进而形成共同体的意志表达,这既作为一种常见的表述,在现实中同样能够诉诸报纸这一媒介来达成。
尽管看上去,本文所列举文本中的“声浪”若以“声音”代替也可读通,但两者之间仍有细微差别。一是“声浪”更强调声音的传递过程,它突出作为表达意义之媒介的声音本身是否能够清晰达致,以及声音之间干扰或激应的关系。二是通过“浪”之比拟,将群体力量带入了对“声浪”的想象之中。这同样有其科学依据,比如声音的共振可以具有摧毁性的力量。《课艺》就说,“且声有浪,因气激荡成浪,如水因风激一般。若巨声之浪,有破纸窗坠屋瓦之能。”相较而言,“声音”一词没有这样的色彩。这两点差别实则与“声浪”之科学涵义有所关联。这足以说明,正是“声浪”若隐若现的科学意涵,才使之可能与近代转变的社会关系之间建立复杂的并行关系。
“声浪”所表征或体现的是一种兴起的公共生活,它由社会的智识阶层发起,常常通过声音/言说得以组织,但最终诉诸民众所组成的共同体。民众不仅是“声浪”的启蒙对象,更是“声浪”力量的来源。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是在这一社会关系的框架之中,“声浪”或者更进一步说由不同媒介所中介的“声浪”,同样体现出社会关系的微妙差别。我已经说明,在启蒙和群议的场所中,都试图建立有秩序的听觉空间,而这一秩序是以大部分参与者的沉默为代价的,并且听觉者未必能转换位置成为发声者,在多数情况下只是被要求在“适当”的时刻组成“声浪”的一分而已。在20世纪10年代以后,场所中听觉秩序越发以一种隐性的方式来维持,即基于对“声浪”传布进行测算与设计的建筑声学。而当“声浪”借助于印刷媒介“发出”时,同样不能忽视报刊的组织、整合作用。不同的媒介在“声浪”发出与散播之中留下“轨迹”,折射出不同的社会关系。
声音总是沟通人与其所在之世界(人与他人他物、人与环境)的重要通道。实际上,无论中西,关于声音原理的论述都没有停留于这一自然现象本身,实则亦在表述由声音中介的人与世界的关系,包括人在自然及政治秩序中所处的位置,或是人如何探究和处理自然界及其物理对象等等。在中国关于声音的传统论述与政治实践当中,缺乏直陈的声音空间,听觉实践有其抽象的层面皆最终指向“圣人”,民众的声音经由官员的整理与组织,在秦汉以后更多地依赖文书之中介,物理的声音本身似乎始终没有一个清晰的存在。因此,在近代会关系发生变化时,需要新的语汇资源来对之进行理解,反过来,用以想象社会关系或描述公共生活的声音观念/词汇的更替(其中亦有承接),在根本上则意味着关系的变化。两者之间并非因果的关系,而是发生于近代的一种同步关联的转折。
综上,教堂广场区域作为中心区的广场空间处于视线聚集性较低的区域,空间吸引到达的交通潜力较小.而实际调研结果也明显反应出:虽然天主教堂特殊的文化底蕴吸引游客前来游览,但当游客来到教堂广场区域时,视线集中于教堂之上,在拍照参观之后一般选择离开广场,或在教堂东部的树荫下休憩.位于中心区域的广场却常常被人忽视,空间利用率较低.
最后要指出的是,“声浪”之涵义也好,近代发生变化的社会关系也好,同样无法斩断与历史的关联。举例来说,1927年刊于《商业杂志》“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声浪中的洋商” 的漫画(见图3),将“声浪”表征为海浪,而受此“浪”裹挟的、挤在一只小船上的洋商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以此来表达民众意志的不可违逆。这既将“声音”与“浪”直接联系起来,同样也可读解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传统思想,即民意对于有权势者具有颠覆性的力量。由此看来,作为一个理解近代社会关系与公共生活转变的关键词,“声浪”之中蕴含着混杂的多重意义,其意义来源也绝非单一清晰的。这既是其时各种观念、知识并陈杂错的结果,也折射出清末民初公共生活中的种种状况。与此同时,亦须仔细辨析“声浪”之中种种媒介之轨迹。毋宁说,这幅漫画中的“声浪”是以报刊为其媒介,因而“声浪”在这里实是抽象并经整合与转化的。由此亦能理解,近代报刊似乎更能与以文字为中心的信息沟通传统衔接,甚至以“太史陈风”来表述自身合法性——原本掌声音的乐官摇身变为主文字的史官——尽管“声浪”也是报刊中常用的词汇。这在在说明,也许正是“声浪”在公共生活空间中实存的那一面,与关切物理声音之新知有更密切的联系。
图3“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声浪中的洋商”漫画
注释:
① [英]田大里:《声学》,[英]傅兰雅口译,徐建寅 笔述,上海江南制造局1876年版,卷一,第2b页。文中着重号均为本文作者所加。
赵锡田把铅笔在一八八团阵地上画了个圈,此刻,外面的炮声早已停息,他知道,肉搏战已经展开。坚守了三天三夜,一八八团早已被打残,绝对应付不了这场屠杀式的肉搏战。
② 《初八日资政院纷扰情形北京》,《申报》,1910年11月17日,第4版。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往往扮演指导者和监督者的角色,尤其是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建设中,教师更应懂得适当放手,把课堂还给学生。比如笔者在教学中,除了讲授教材知识外,还引导学生每周举办一次英语阅读比赛,比赛名次不是最终目的,而是激发每个学生的分享意识,把自己喜欢的英语短文或故事讲给其他同学听。但在内容选择上,笔者鼓励学生们选择那些故事情节比较强的文章,这样的内容丰富,语句相对比较简单,不仅便于分享的人表达,更便于倾听的人聆听,让学生在欢乐的分享气氛中掌握了单词、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③ 《声学》的英文原作初版于1867年,由田大里所作的八次声学讲座辑录而成;随后分别于1869年、1875年、1883年重版。《声学》的中译本以1869年的英文版本为基础。田大里,今译丁铎尔、丁达尔,还有译作廷德尔,英国物理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本文一致使用“田大里”这一译名。参见李莉:《晚清译著〈声学〉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王锦光、徐华焜:《丁铎尔及其物理学著作传入中国》,《物理》,1989年第4期。
④ 关于近代声学与物理学其他各门的名词翻译及演变,参见王冰:《我国早期物理学名词的翻译及演变》,《自然科学史研究》,1995年第3期。
⑤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物理学及相关技术”第一分册“物理学”,其中(h)声(声学)一节,与[英]鲁宾逊(Kenneth Robinson)合著,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33页。
⑥ 戴念祖:《中国声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6-58、33-36页。
做足主题性报道重在挖掘特色主题,拓展延伸主题内容。当前正在开展的教育实践活动,同样要求采编人员坚持群众路线、践行“四民”要旨。因此,采编人员应该多深入基层、深入一线,与广大群众交心谈心。
⑦ 陈平原:《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代中国文章变革》,王汎森编:《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383-428页。
⑧ [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37页。
⑨ [德]谢弗:《谭嗣同思想中的自然哲学、物理学与形而上学——关于“气”与“以太”的概念》;[德]阿梅龙:《重与力:晚清中国对西方力学的接纳》。两篇文章均收入[德]郎宓榭、[德]阿梅龙、[德]顾有信编著:《新词语新概念:西学译介与晚清汉语词汇之变迁》,赵兴胜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年版,分别见第267-280、202-239页。
(1) 南端采用大锅底形土方开挖(见图8)方法,不符合设计要求的分段、分层开挖的要求,导致土方开挖过程中基坑及周边环境急剧变形。
⑩ [英]合信:《博物新编》,和刻本,出版时间不详。
这七绝逍遥阵由侠客岛北斗七星阵变动而来,方乾在侠客岛穷海之边,夜参北斗,由星辰运转之中,悟出内力变化,得七七四十九变,可由七人、十四人、二十一人,一百四十七人,直至七百人形成大中小北斗七星阵,以门客家丁席卷来攻侠客岛的敌人,实是侠客岛第一防守奇阵。
“气学”分“论天气”“论蒸汽”“论音声”三章,可见这里的“气”是一个较为粗泛的物理概念。“天气”即空气。不知将声学知识编入“气学”中,是否有将之与中国传统声音知识对接的考虑。
[美]丁韪良:《格物入门》,京都同文馆,1868年,第2卷,第47a页。
[法]法国师克勤:《论音学》,《中西闻见录》,1874年4月第21号,第10-12页。
[英]田大里:《声学》,[英]傅兰雅口译,徐建寅笔述,上海江南制造局1876年版,第1b-2a页。
李莉:《晚清译著〈声学〉研究》,第62页。
王冰:《中外物理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79页。《声学》出版之后,傅兰雅又择《声学》之要点,编为更具普及性质的《声学须知》,于1887年出版。此后《声学须知》又收入傅兰雅辑译的丛书《格致须知》中。参见李莉:《晚清译著〈声学〉研究》,第52页;戴念祖:《中国声学史》,第521-528页。
1899年,《初等物理学》法文版另由李杕译出,即《形性学要》,由徐家汇汇报印书馆初刊。参见李莉:《晚清译著〈声学〉研究》,第59页;包晶晶,咏梅:《晚清物理这译著〈形性学要〉初步研究》,《内蒙古师大学报(自然汉文版)》,2017年第3期。《声学揭要》亦一再重版,包括1898年美华书馆、1898年益智书会、1902年鸿宝书局等版本。
[美]赫士译:《声学揭要》,上海益智书会,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版。
王季烈:《高等小学理科教科书(卷四)》,上海文明书局,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版,第38、39页。
[英]田大里:《声学》,[英]傅兰雅 口译,徐建寅 笔述,上海江南制造局1876年版,第2a页。
杞庐主人:《时务通考》,上海点石斋石印本,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第1b页。
《物理学》由藤田丰八译、王季烈重译,其中编有关于声学的内容。参见王士平、刘树勇、李艳平:《中国物理学史·近现代卷》,广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68页。
熊月之:《导论》,上海市图书馆:《格致书院课艺(一)》,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86页。
彭瑞熙:《格致书院课艺(一)》,第165页。
王小盾:《上古中国的用耳之道——兼论若干音乐学概论和哲学概念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
王小盾:《上古中国的用耳之道——兼论若干音乐学概论和哲学概念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第166、152-153页。需指出的是,这一研究对于声音知识的梳理,在历史维度上似乎还不够细致。例如,余英时提出先秦时期的“轴心突破”,其中重要的方面,正是不同的思想流派在“气化宇宙论”的基础上发展出“天人合一”的观点,以突破以礼乐交通天人的巫文化传统。其间,与“天”交通也从作为巫的特殊能力转变为依赖个人的修养。因此,“气”这一概念应晚于“风”,并且,从商周至秦汉,“天”“风”等概念均有变化与分异。参见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
[汉]郑玄 注:[唐]孔颖达 疏:《礼记疏》,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重刊本十三经注疏本,卷十一,第40a-b页。
[三国]何晏 集解:[南北朝]皇侃 义疏:《论语集解义疏》,清知不足斋丛书本。
阎步克:《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70-71页。
王辅才:《格致书院课艺(二)》,第398页。
阎步克:《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
杨毓煇:《格致书院课艺(二)》,第356页。
吴趼人:《趼艺外编》,吴趼人:《吴趼人全集(第八卷)》,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103页。
《哀情小说情海波澜记(九)》,《申报》,1908年2月14日,第8版。
王东杰:《历史·声音·学问:近代中国文化的脉延与异变》,东方出版社2018年版,第116-117页。
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6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引见第141页。有趣的是,在这本写于20世纪末的著作里,也使用了“声浪”一词。
昭文东海觉我(徐念慈):《新法螺先生谭》,《小说林》,1905年,第19-20页。这段材料以及前文所引《趼呓外编》的段落,由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段书晓博士提醒我注意,在此向她致以谢意。
《安徽歙县南卿程慈心来函》,《申报》,1906年7月6日,第10版。
[德]西皮尔·克莱默尔:《作为轨迹和作为装置的传媒》,收入其编著:《传媒、计算机、实在性——真实性表象和新传媒》,孙和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4-85页,引见第70页。
杨天石、王学庄编:《拒俄运动1901-190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7页。引文录自1903年5月1日之《苏报》。
东埜:《拟众议院进步党议员李国珍上如来佛书》,《申报》,1913年5月24日,第13版。
我:《清谈》,《申报》,1912年3月30日,第3版。
《梁任公别有会心》,《申报》,1912年11月22日,第3版。
胡郁文:《安徽旅沪同乡恳亲会演说词》,《申报》,1907年6月10日,第2版。
王今:《张园的演说:清末民初上海公共空间的听觉文化研究》,《热风学术(网刊)》,2017年9月总第6期。本文所引《新中国未来记》见第五回“奔丧阴船两观怪象,对病论药独契微言”,《新小说》,1903年7月15日,第7期,亦转引自王今此文。
《国民筹还国债大会记事》,《申报》,1910年1月5日,第10版。
默:《杂评一》,《申报》,1913年5月19日,第3版。
《改良新戏(趣剧)真假夫妻(正剧)(张诚)奇情新剧感人实深》,《申报》,1913年10月20日,第12版。
《开明公司新舞台甲寅元旦开幕广告》,《申报》,1914年1月16日,第1版。
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上海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上海卷》,中国ISBN中心1996年版,第637-639页。
《中央教育会之怪状》,《申报》,1911年8月3日,第5版。
《研究大礼堂声浪》,《清华周刊》,1926年第1期。
Dr.A.H.Davis氏著,倪庆穰 译:《建筑物与声浪之关系》,《工程译报》,1931年第3期。另有F.R.Watson原著,唐璞 译:《房屋声学》,连载于1933至1934年的《中国建筑》杂志上。这里,唐璞已将sound wave译作“声波”。
《丽都大戏院素描》,《申报》,1935年1月31日本埠增刊,第9版。
《大光明大戏院不日开幕》,《申报》1933年6月8日本埠增刊,第6版。
葛道殷:《格致之学中西异同论》,《格致书院课艺(一)》,第173页。
《邸报别于新报论》,《申报》,清同治壬申六月初八,第1页。参见黄旦:《耳目喉舌:旧知识与新交往——基于戊戌变法前后报刊的考察》,《学术月刊》,2012年第11期。尽管“大师”“大史”一字之差,其职责在先秦则是分殊多过重合。基于对古籍的检索,这一混用可能始于唐代,即便可能是讹用,这一现象仍然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王敦庆:《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声浪中的洋商》漫画,《商业杂志》,1927年第2期。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费资助项目“声音技术、感官文化与中国听觉现代性”(项目编号:531118010255)的研究成果。
(作者系湖南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学院助理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毓强】
标签:声浪论文; 声音论文; 声学论文; 这一论文; 中国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年第7期论文;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费资助项目“声音技术; 感官文化与中国听觉现代性”(项目编号:531118010255)的研究成果论文; 湖南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学院论文;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