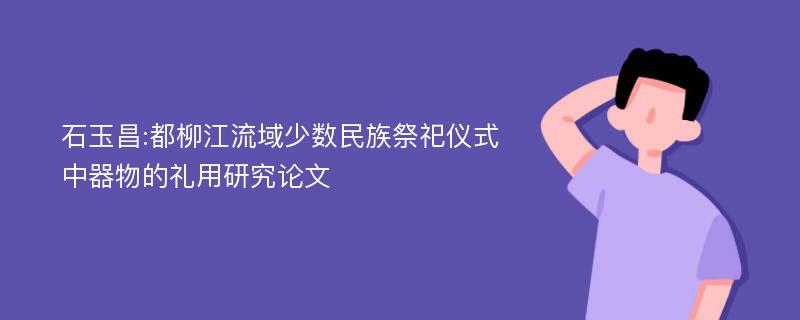
摘要:鼓、香禾糯米、生产工具等器物在都柳江流域少数民族祭祀仪式中的礼用,反映出少数民族在适应独特天地系统中的农耕禁忌和万物有灵的文化基因。透过祭祀仪式中器物的礼用,可发现器物已超越了其工具性而上升为神性、可以推断出有关人类活动的各种时间和空间信息,可探见少数民族社会结构与文化心理结构。
关键词:祭祀仪式;器物;礼用
都柳江发源于贵州省独山,流经三都、榕江、从江、黎平等县,入广西三江寻江口,最后汇入柳江干流融江段。流域面积11326平方公里,全长310公里。生活着以苗族、侗族为主的,以山地稻作为主要经济类型的农耕民族。因该流域生存的天地系统山高林密,资源丰富,人们生活所需要的一切皆来自于自然,人们的信仰、器物、技术都与当地的天地系统有着密切的联系。独特的物质文化映射出少数民族进化过程中与当地独特生态系统的互动,尤其在自然崇拜的图腾下,少数民族生活中的器物已超越了其工具性而上升为神性,这在传统祭祀仪式中有最为集中的体现。
一、从指涉到顺延:祭祀仪式中器物的文化意象
农耕民族祭祀仪式最明显的特点即是万物有灵,自然世界与人是有秩序的非连贯的集合,自然万物从其独特的角度构成了自然世界与人文世界的秩序整体。自然平等促成了人们对待所有事物的态度,通过祭祀仪式这一命名行为对神性意向进行指涉性话语阐释。器物在祭祀仪式中的礼用是将不确定的神性通过器物的“存在”方式保证了确定性,通过祭祀仪式这一活动使自然界神的非存在渲染上了深深的形而上学的、有神秘色彩的玄想,由此促使了人们对非常在的神附着于物的敬畏和崇拜。
(一)仪式的文化构建:礼的文化基因
仪式承载着整个民族、社会的核心要素。著名仪式研究学者莫尼卡.威尔逊认为:“仪式能够在最深层次揭示价值之所在……人们在仪式中所表达出来的,是他们最为之感动的东西,而正是因为表达囿于传统形式,所以仪式所提示的实际上是一个群体的价值。”[1]礼是仪式的根基,是人类进行文化构建的一种文化形态。在人类的发展进程中,礼的特性逐步融入到各种仪式和礼俗当中,成为该族群文化结构的内在逻辑,这种逻辑又反过来成为仪式的现象。后现代时代的到来,推进了人们对礼的有关传统与现代的质疑,他们认为礼是一个集族群、权力、意识形态、制度、经济等在内的多元叙事问题。
仪式传递着一个民族文化的“意”的形态,仪式中器物的使用则是使意识形态在仪式中的礼有了确定的位置和指向。从仪式外显形式看,仪式行为看似毫无意义,但经器物的点缀,一切礼的脉络就有了识别的标志,这使得一个民族的精神有了结构和秩序。正是通过以器物为载体的确定系统结构,少数民族才有了文化阐释的基础,才能构造文化的意义。仪式的文化构建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少数民族个体文化认同提供一种表达的形式;二是对少数民族个体文化情感的形成进行规范和塑造。个体生命是基于应对自然和社会基础之上产生与形成,其礼与文化的形成和表达都必须在有形的客观世界中得来,物质性是有形世界最明显的标志,社会规范与个体行为的认可需要借助器物进行认定。神话、信仰等超社会形态均是以某种物质、文化为原形,仪式过程是通过器物的超工具性呈现将抽象的自然观具象化,由此仪式的理念就有了传播的渠道。
(二)文化记忆与习性:仪式的审美功能
器物与文化一样,都具有传承性,从文化的传承中可发现文明的发展规律。同样,器物也是在与自然、人类、时间信息进行多种交流碰撞后所遵循的一种从低到高、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透过器物,也能发现人类进化的阶段与脉络。以器物为主要媒介的文化记忆,对民族主体性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器物这种类似于集体文化习性的集合体,经过仪式这一过程的外化,二者的互动塑造了一个民族整体的习性与文化记忆。
都柳江流域以山地稻作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在农耕生产活动下,一直保持着连续性、地域性。人们以大山为美、以水为美,以万物有灵的生态社会为美。尽管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审美的取向并不完全固化,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总在不断地融合新的元素,但以自然生态、万物有灵的审美习性与审美记忆一直占据着整个流域少数民族的文化轴心。尤其是该流域以血缘为纽带群居的社会结构,有力地塑造了人们的认知心理结构。族群内部严格的等级与生态位,使得每一个人的行为与习性都固定在稳定的生态位上,人的生命形态在自然面前,如何与自然互动、交流,这有效约束了人们对于自然无限度的索取,于是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文化形态,并通过仪式和器物呈现出来。
1.2.2 党参总皂苷含量测定。人参皂甙Re标准品用甲醇溶解,配制1.2 mg/mL标准品母液。移取标准品母液30、60、90、120、150 μL于具塞试管中,60 ℃水浴中蒸干,经香草醛-高氯酸-冰醋酸显色反应后,以试剂空白(随行处理的甲醇)为参比溶液,分光光度计测定吸光度,绘制标准曲线[11]。
从审美的角度看,都柳江少数民族的审美情趣与道教极为相似,他们普遍认为人类的超越是回归自然,是将个体的精神放逐到自然中去。农耕民族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在族群内部行使的是族内宗教的治理功能。传统的审美习性必然保留在道德审美的结构之中,通过仪式的文化记忆表达出了审美的无限性和多样性。正是这种无限性和多样性使得人们在创造器物选材时有了无限性,如木器、藤器、篾器、石器、草器等等。从器物的功能上则划分出了生产器具、生活器具,每一个类别下又有多个种类,如生活器物中的囿、簋、箕、篓、碗、觚、瓢等等。这些器物经由人为制成,其外形、功能、礼用无一不是在人们特定生态审美之下的创造。
(三)作为宗教制度的仪式
祭祀作为一种制度化的仪式,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和分工。在身份、角色、性别、年龄上都有严格的规定。这种仪式是一种具有个体精神的活动,也是一种自律性的活动。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内部祭祀,遵循着双重的组织制度,一是血缘的代际结构,二是社会文化角色的结构。制度具有两个特点:“首先,制度不是无目的的建构,而是源于人类本原性需要,以及由此派生的需要。其次,社会中存在的种种制度是一个整体,各种制度之间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并不是决然对立的。”[2]
都柳江流域祭祀仪式包含物质层面的意义和精神层面的意义,这两个层面都蕴含了制度体系中潜在的一套规则和禁忌。在物质层面上,透过仪式中的器物,可探见文化体系中个体成员物质需要的具体形式,即制度文化对来源于自然界的器物的选择和限定,包括物质与社会环境下的仪式创造的技术手段和历史上形成的集体记忆所持的接受态度;同时仪式在精神层面上产生了宗教内部个体的文化需要和能力限制。宗教与生态伦理有着密切联系,少数民族宗教包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具有明显的生态保护功能。少数民族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人造物崇拜仪式中蕴含着尊重自然、敬畏生命、关爱生命等生态伦理思想[3]。少数民族仪式中的宗教生态伦理对于丰富生态伦理思想体系,维护地区良好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从行为到意义:祭祀仪式中器物的礼用
都柳江少数民族祭祀仪式是当地社会的一个缩影,虽关涉的器物广泛,象征指向却相对集中。爱德化·泰勒对比研究了古代和现代土著部落的神化和仪式,分析了看似荒谬、野蛮的仪式背后动物、植物以及其他器物的象征意义,得出了“一切崇拜活动都源于万物有灵”的结论。都柳江祭祀仪式中器物的礼用,皆是对自然崇拜的指涉和象征。
国企集团公司间形成的内部资本市场资本配置对隶属于企业集团的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可以通过对以下几个理论的分析得到。
(一) 鼓的礼用
1. 作为工具的鼓
“功能性食品”是一门食品科学与预防医学、营养科学等相关内容相互融合的学科,是食品营养与检测等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该课程不仅要开展理论教学,还要有一定的实践教学,让学生对各种功能性食品的生产有直观的了解,熟悉具体的操作步骤。然而,课堂中教师对各种功能性食品开发的讲解,比较抽象枯燥,学生不容易理解和学习,特别是对生产技术及设备缺乏感性认知。从目前的教学效果上看,仅局限于课堂中的教学是远远不够的。而教学内容的重组对于课程知识的补充和丰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教学效果的改善也十分明显。
农耕工具是一种固定的形态,在祭祀仪式中的礼用变化不大,它不似鼓和香禾糯一样,可以多种形态呈现。工具类型的使用取决于祭祀、祈求的对象,如在水稻等两春作物的祭祀中,会使用犁、耙、锄等工具;营林祭祀会使用斧、锛等工具;捕渔祭祀会应用网、篼、竹帘等等。
鼓是祭祀中的礼器,也是生活中的乐器,苗族人喜好跳鼓,很多舞蹈均是以鼓为主要乐器,如驰名中外的反排木鼓舞。铜鼓主要用于祭祀,其声音低沉,回音重,为了增强鼓声的沉重感,在敲打鼓时,在鼓的另一面由一个人用铁皮桶随敲击合、放,以此制造铜鼓更沉的回音,增强鼓声的厚重感,更显仪式的庄重。铜鼓鼓点的节奏相对平缓,轻重变化的频率不高,跳鼓的人随鼓点踏步时,表情、动作幅度不大。木鼓不单是一种祭祀用鼓,还是节庆、交往时的主要乐器。木鼓声音脆响,短促,这样的鼓点最大的好处就是容易激发人们的情绪,将人群带到一种欢愉的状态。所以,当人群在踩鼓时,往往动作幅度大,节奏明快,跳的过程中还伴有“呜~~~~呜~~~”的欢呼声。
鼓的工具性除了表现在它的“用”之上外,还有向心性的功能。在跳鼓时,鼓置于中央位置,人们环鼓而成圈,以鼓为中心开展的祭祀、欢庆活动,体现了文化认同与心理归属,更重要的是将一个族群更紧密地集合在一起,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
2. 作为象征的鼓
鼓在各种仪式中的礼用,在中国古代很早就有记录,由于鼓声音洪亮深沉,人们将其声与雷声等同起来,以此尊鼓为通天的神器。《易·系辞》有载:“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周礼》亦载:“凡国祈年于田祖,吹豳雅,击土鼓,以东田钧。国祭蜡则吹豳颂,击土鼓,以息老物。”鼓在祭祀中主要用于祈雨、祈丰收之用。
苗族鼓在祭祀中的礼用是将祈年和祭祖合为一体。“吃鼓藏”是苗族最为隆重的祭祀活动,苗语称“努姜略”或“弄钮”。人们将鼓视为祖先的化身,将其埋在人迹罕至的地底下。“吃鼓藏”根据地区和苗族支系的不同分3年、5年、9年、12年一祭不等,以12年最为普遍,祭祀的形式、内容大体相同,一般分“醒鼓”、“祭鼓”、“送鼓”三个程序,分三年进行,原则上寅年“醒鼓”,卯年“祭鼓”,辰年 “送鼓”。“醒鼓”是将埋于地下的鼓取出来的仪式,通常不能见光,由鼓藏头看吉时,由村寨内德高望众的几位祭师主持,全村男丁合力取出。“祭鼓”是“吃鼓”的最高潮,一般在卯年农历十一月第一个或者第二个辰日进行,“吃鼓”分黑鼓和白鼓两种,黑鼓的祭牲是水牯牛,白鼓则用的是猪,由村寨内户主为男性的儿孙辈准备,以宴请来参加吃鼓的各方来客。在此之前,每家每户要通知所有亲戚一起参加“弄纽”,包括外嫁出去的女儿,在外工作的亲戚以及其他村的表亲、朋友等等。
“祭鼓”仪式包括“牛旋塘”、“吃簸箕饭”、杀牛等活动,因鼓藏中的重要祭牲为牛,牛又称牯,所以人们也常将此认为是“牯藏”,将牛作为核心的图腾。“牛旋塘”是由鼓藏头或祭师带领,在男扮女装的芦笙队的簇拥下将祭牲用的牛牵到指定的“旋牛塘”顺时针方向旋转三圈,以示时运通达,吉祥平安。“吃簸箕饭”是通过吃祭祀所用的食物,实现自然力量的获取过程。通常是每家每户要准备一甑子五彩糯米饭、猪肉、米酒放到公共划定的区域,供外来的宾客食用。“牛旋塘”和“吃簸箕饭”仪式后,所有人参加踩鼓、跳芦笙等活动,人们围绕鼓形成很多圈,由鼓藏头打鼓,最内圈为祭师或寨老,中圈为男丁,接着是妇女,最外圈为外来宾客。杀牛是“吃鼓”活动的高潮,有着严格的规则。杀牛、剖牛等一应事务由户主的舅舅们执行,其他人一律回避。同样,杀牛过程也不能见光,通常是在半夜进行,待牛杀妥后,再将牛肉分食给房族内部,用牛肉和内脏煮熟待客,所以“吃鼓藏”的宗教意义源于“吃牯脏”的图腾祭祀行为。这一活动连续举办三年,三年过后,人们会举行“送鼓”的仪式,将鼓重新埋于地下。
“送鼓”的仪式相对较简单,在辰年农历三月左右进行,由祭师或鼓藏头主持,在简单的参拜祖鼓仪式后将鼓送到原来的地方,保存起来,再经过3年、5年、7年、9年期限不等,才会再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吃鼓”活动。
(二)香禾糯米的礼用
都柳江流域百越民族的族源和族性决定了其生存的天地系统与水有密切联系,其生栖的独特自然生态环境决定了其稻作生计方式的文化生态模式,围绕生产方式所创造出的一切形而上的“意”和形而下的“器”都与水文化和稻作文化有密切的关系。人们爱水敬水、习水便舟、自然崇拜、火耕水薅、饭稻羹鱼,干栏式房屋等都是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4]。香禾糯作为都柳江流域少数民族社会中的特需品,发挥着“器”与“意”的双重作用,具体表现为香禾糯的工具性和文化性。从“器”的功能上看,香禾糯的生长所需的气候、环境与都柳江流域的自然环境相契合,且其营养元素和口感符合当地少数民族的体质需求;其次,少数民族独特天地系统中的生产技术和生态智慧有利于香禾糯的生长。从“意”的角度看,都柳江流域农耕民族的特性和围绕生物生长的时令而创造的与时、节相顺应的文化习俗,以及香禾糯作为一种“礼器”在祭祀、婚、丧、诞等礼俗中的应用,已超越了工具性而上升为神性,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当地人对其都有着较强的依赖性。
1. 作为食用的糯米
采用氧化镁半熔法处理样品、热水浸提时发现,因氧化镁颗粒较细且带有电荷,其在水中不易凝聚,形成的沉淀体积较大,对高铼酸根有一定的吸附作用,故试验尝试采用加入凝聚剂的方式来凝聚沉淀以减少其对铼的吸附。选取2g氧化镁和铼标准溶液为试验对象,按照实验方法,分别以氨水、硝酸铵、聚乙烯醇和氢氧化钠为凝聚剂进行试验,以铼的测定值除以理论值计算铼回收率,结果见表2。
仪式,有学者将其界定为“基本的社会行为”[6];也有人认为“仪式是关于重大性事务的形态,而不是人类社会劳动的平常形态”根据仪式的功能、场域、认同、仪礼,有学者将仪式梳理出这样的意义:(1)作为动物进化进程中的组成部分;(2)作为限定的、有边界范围的社会关系组合形成的结构框架;(3)作为象征符号和社会价值的话语系统;(4)作为表演行为和过程的活动方式;(5)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经历和经验表述[7]。农耕民族的祭祀,包含了仪式的所有意义,在仪式的表达上更具指向性,它集中体现了人与自然的互动和以生态文化作为结构的文化认同。
侗族以鼓楼为中心群居,每一个鼓楼都是一个血缘家族,故每一次祭祀都是一个房族、村寨的集体性活动,每一个人从精神上都希望获得庇佑,但是从责任上,每一个人都应该为祭祀活动出资出力。因此,祭祀所用的吃食,皆中来自于各家各户集资。人们以糯米为祭祀的礼器,以糯食为集体享用的主食。一方面,祭祀中的糯食,在人们的认同上它本身已高于物质本身,成为人的精神依靠,能够在来年的丰收和人畜平安方面发挥超自然的力,人们通过吃糯食的这一行为,实现人与神性之天的沟通。另一方面,无论是参与祭祀的个体还是集体,在祭祀中的表现都赋有一种力,能够在祭祀过程中自发地抑制他们的行为,通过这种行为的自律,呈现出他们对自然、对神的尊崇。所以,吃糯米饭不完全是身体需要,而是个体对祭祀所形成的观念中的物质力量的追随。
平儿完全赤身,他走了很远。他去扯衣襟拭汗,衣襟没有了,在腿上扒了一下,于是才发现自己的身影落在地面和光身的孩子一般。
2. 作为象征的糯米
农耕民族祭祀,在祈求作物丰收的同时还包含对人口繁衍的美好愿望。人与自然界万物共生,自然是生命的本原,农耕民族的祭祀仪式,在赋予人类心灵以活力的同时催生植物生长,人口繁衍。人们通过种香禾糯——吃糯食——用糯米祭祀、交往,形成了以黔东南为核心的“糯食文化圈”。祭祀仪式通常选在种小春和种大春的时节,少数民族有关婚嫁交往为目的的礼俗活动也会在这期间举行,所以人们会将糯米制成多种形式的食物,如乌米饭、黄花饭、扁米、糍粑、粽子等作为精神与愿望的物化形态,在文化交往、祭祀仪式以及各种礼俗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系统需要控制4个步进电机的运动,步进电机的型号为JK57HS56,相应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型号为TB6600。由于4个步进电机不需要同时运动,本文选择复用开发板GPIO7作为方向控制端,GPIO8-11分别作为4个步进电机的脉冲发出端,使用共阳接法将驱动器与开发板连接到一起。
原米的礼用:未经烹煮的糯米为原米,是祭祀仪式中必不可少的礼器,与原米一同使用的还有盛米的器具,通常是升、碗。原米在祭祀中有两种形式的用途,一种是用升、碗装满用来插香烛之用,作为一整年的供奉;另一种是在祭祀前以及在整个祭祀场域内播撒,一为驱邪,二为神性覆盖。用作供奉的米,由祭师奉献,通常是经全手工脱粒、去皮的新米,祭师将米放在祭坛之上,点烧香烛,待香烛烧尽,升里的米不能倒掉、不能给人或牲口食用,而是由祭师拿到鼓楼里或者祠堂里长期供奉起来,直到下一次再进行祭祀时,才会将旧米换掉,换掉的旧米也不会随意扔,而是要撒在鼓楼周围和村寨的每一个角落,以示神旨无处不在。用作驱邪的米是在祭祀队伍游寨时用。在整个队伍到齐后,祭师会有一个简单的祭祀活动,往往是画符水,说吉利话。他们会用囿篓装上米,一路走一路撒,用米开路,以示保村寨、人口平安,保作物繁盛。
工具的“文化反哺”是农耕祭祀仪式引发的变迁维度上对工具的器物“用”的层面的天人关系的颠覆或倒置,仪式过程中所发生的场域精神由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文化影响。在仪式主题、仪式精神,器物礼用中突出表现为器物选择过程的中代际倾斜、去中心化和象征[5]。随着文化交流不断深入,工具在仪式中的象征文明传承过程中会出现的代际颠覆现象,记录着社会变迁带给人的心理体验的痕迹,它能在精神层面上赋予仪式以完整的价值和意义。
“乌米饭”是都柳江流域四月初八这一天普遍食用的特制的糯米饭。四月八侗族称为“牛王节”,也叫“开秧门”。因都柳江流域农耕民族在山高林密的自然地理环境中,无法用现代机器进行耕种,只能依靠牛为动力,所以牛不止是少数民族的祖先化身,还是人们进行生产的必要工具。四月初八一过,打田栽秧就开始,牛就要开始进行繁重的劳动。所以,在这一天,牛不会进行任何劳动,而是由人赶到水草最丰盛的地方,任牛自由活动。开秧门这一天吃乌米饭有两种功能:一是自这一天后,打田栽秧时候到了,吃香喷喷的乌米饭,既可以防蚊虫,祛风解毒,又可强身健体、百病不生。乌米饭是一种紫黑色的糯米饭,是采集野生植物乌饭树的叶子舂碎泡水,在色素全部融于水后再将糯米泡入水中,九小时后捞出放入木甑里蒸熟而成,所用材料均为自然生长,因此在这天吃“乌米饭”也意味着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三)生产工具的礼用
都柳江流域山高林密,梯田层层,为适应特殊的地理和自然气候条件,各民族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和使用了包括生产、生活以及手工艺等方面具有浓郁地方特点和民族特点的技术文化,并根据资源与功能的不同,创造并使用了独具地方特色的生产生活工具。这些工具不止满足人们使用的需求,在祭祀、礼俗仪式中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少数民族对生产生活工具的保存与维护方面做得特别谨慎,而且对工具的神性崇拜也尤为虔诚。
1. 作为生产的工具
2. 作为象征的工具
此外,都柳江流域相对湿度大,不利于农作物的保存,所以人们只能将农作物腌制起来,故食酸成了一种普遍的饮食习惯,每当作物收获后,都会腌制成酸食或放太阳底下暴晒,脱水保存。故腌制用的木桶会妥善保护,常换篾箍,并保持木桶整洁光滑。
与都柳江独特生态环境相适应的生产工具其材质主要以木器和铁器为主,为方便使用,往往是木器与铁器的结合,如犁、耙、锄、镰,锯,还有作物存储、加工的工具,如谷桶、腌桶、木捶、碓、箕、囿等等。都柳江一年种两季,分别为大春和小春,因为作物不一样,所用的工具也不一样,每在一季作物种下后,人们都会把工具洗干净,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保存,小孩不允许拿生产工具随便把玩,更不能把污秽之物抹到工具上,甚至有些安放工具的地方被认为有神灵守护,每逢特殊的节日,还要敬香供奉。如放碓的地方不允许孩子去玩,更不能骑到碓杆上,也不能将垃圾堆放在旁边,家里的牲畜也要避免到碓周边活动。
由于架构的变化,一些现有软件不适用新的架构体系,需要重新设计编程,完善、扩展软件功能。有些软件目前还没有国内产品,需要在新架构下自主研发解决没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问题。
在脱贫攻坚后期,顽固贫困问题突出。2017年底,隆化县贫困人口中低保、五保户占30.7%,因病致贫占37.22%,60岁以上老人占29.2%,贫困人口致贫原因复杂,贫困程度较深。且大部分贫困户属初中以下文化程度,思想观念陈旧,视优惠贷款为生活救济,将借贷资金用于日常生活开支,缺乏将其转化成生产性投入的意识。多数贫困户对农业保险缺乏基本认知,对保险缴费存在抵触心理。高龄贫困人口风险厌恶程度高,贷款意愿低。现存贫困人口综合能力较弱,金融素养较低的客观情况,降低了金融机构的整体扶贫效用。
加工好的糯食:苗族姊妹节是一种民俗、婚恋、社交方式,其背后蕴含人们在崇敬自然的前提下进行了一种人口繁衍的交往,“姊妹饭”是礼俗活动的一个重要载体。每年农历三月十三,苗族适婚的姑娘们都要上山去采南烛木叶等植物染料,制成黑、红、黄、蓝、白五色糯米饭。按本地人的说法,吃了姊妹饭,防止蛀虫叮咬。姊妹饭既是姑娘们送给情侣表达情意的信物,又是自然崇拜重要载体,以饭的颜色来表达不同的愿望:绿色象征家乡美丽如都柳江,红色象征寨子发达昌盛,黄色象征五谷丰登,紫蓝色象征富裕殷实,白色象征纯洁的爱情。
Research on Configuration Optimization of Escalator Assembly Profiles based on SAP System
工具的核心功能突出在“用”上,祭祀仪式中农耕工具的礼用,象征人、器、天地的“三位一体”,也就是三者的“和”与共生。当地在描述工具是否好用时用“顺手”一词,意思是工具制造与人体工学相符,在应用到生产时,便于操作。因此祭祀仪式时在祭坛上或旁边摆上犁、耙或者镰、斧之类工具,意寓生产顺利,风调雨顺、万物生长。
苗族鼓按材质分木鼓和铜鼓两类,根据地区和习惯的不同,人们使用的鼓也会不同。铜鼓又称太阳鼓,因其鼓面上刻有太阳纹案而得名;木鼓有两种制作方法,一种是取大树密度最大的一截,直接将内心掏空,另一种是用杉木板拼合而成呈圆筒形鼓框,两端细中腰略粗,两端蒙以牛皮为面,皮面四周边缘用竹钉固定,故也称“牛皮鼓”。
三、祭祀仪式的符号意识形态:天地、时令与他性
中国是世界上水稻品种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其驯化和栽培的历史,至少已有 7000 年。《礼记·月令》记载,“乃命大酋,秫稻必齐,曲蘖必时。”秫稻也就是都柳江流域普遍种植的糯稻,香禾糯是当地少数民族社会中不可或缺的物品。都柳江流域山高林密,资源丰富。也正是因为气温均衡,湿度大,梯田土壤含肥量不高的生态条件,尤适香禾糯的生长。都柳江流域少数民族喜糯食,香禾糯口感松软、香味浓郁、冷饭不回生、耐饥饿,尤适合当地少数民族体质所需,在生理上人们对香禾糯有较强的依赖。
(一)祭祀仪式中器物符号的多元对话
仪式是一种带有古典神话进化特点的人类活动,其演变和发展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整个仪式中带有明显的神性色彩,仪式过程、内容、形式都反映出了人与神之间、人与天地系统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互文(context)、互疏(interpretation)、互动(interaction),在社会总体结构和社会组织中具有指示性功能。
都柳江流域少数民族祭祀仪式是通过仪式的象征功能来释放农耕民族这一知识系统的符码。卡西尔(Cassirer.E.)认为,语言和象征作为人类文化的基本特征,可大致定位于人类作为动物性方面的语用符号与物质能力指示[8]。人作为仪式中的行为主体,其行动被仪式中的场域、氛围、程序、规则所影响,与此同时其行为方式也附着了特定民族、特定情境中的符号意义。从符号功能指涉分析,都柳江祭祀仪式具有如下功能:
1. 制度性交流与对话。像“四月八”、“开秧门”一类的农耕祭祀,包括祭师、器物、成员在内的人群,他们在农耕祭祀中的行为、祭祀中器物的使用、仪式过程都是预先设定的。祭词、附和词等交流、呼应的预设规定都赋予了仪式一种新的条件,人们以一种全新的状态和身份在享受着仪式的过程,个体的仪式行为也构建出了一个完整的结构叙事,在仪式背后的少数民族社会发挥着能动的作用。
例如:许多数学概念需要用数学符号来表示.如dy表示函数y的微分.各种数学符号也是表达不同数学概念的独特方式,有助于学生更加容易理解和形成数学概念,数学符号的表达使得学生对数学概念的理解更加简洁明了.为了增强数学的科学性,很大一部分数学概念的定义都是用各种各样的符号来标识的.许多数学概念还需要用图形来表示.有些图形也是数学概念的一种,比如圆形,正方形,三角形,梯形等.有些数学概念可以用图形来表示,比如y=x+1的图象.像函数的微分dy,就具有几何意义.
2. 祈求性对话。祭祀中的器物作为一种礼器,其工具性功能与神性功能呼应,除了在祭祀过程中要进行展现外,还传递着为了获得某种神祇、精神、权力、庇佑、或者圣灵等集合的信息。人们通过器物的呈现,经人的引领对话,使人与神的交流集合到物上,以此获得神性。
3. 常规性交流。祭祀仪式中的礼器作为一种社会精神高度集中的载体,它集中凝聚了社会价值、群体信念、道德语码等等,并将生命的理解与传说的“生命圈”循环地在生产、生活、技术改进、工具升级等行为中加以呈现。
(2) 提出了一种新的机械液压混合蓄能悬挂系统设计方案,与传统蓄能悬挂系统相比,在综合考虑悬挂适应范围、安全可靠性、零件加工工艺性及维护方便性等方面均有明显优势.
(二)祭祀仪式中的器物与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是当代所有民族文化构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它关乎一个国家、民族、部落是否拥有共同的信仰、习俗、道德、审美、艺术。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约翰·汤姆林森指出:“文化认同这一概念无疑位于当代文化想象的核心地位。”[9]文化认同是通过行为和符号来发挥作用,农耕民族的仪式以其祭祀过程的神圣性彰显了本民族共同的象征符号,除祭祀仪式的行为外,符号是承载文化认同的核心要素。
水侧调节通过调节暖风器中凝结水水量来调节空气预热器空气入口金属壁温。水调节的是疏水,比容较蒸汽大大减小,容积通流量就减小很多,阀门开关行程就很小,调节精度会有所降低。但由于暖风器中的蒸汽压力始终是供汽压力,所以饱和温度不变,有利于选择更低压力的蒸汽汽源,进一步提高汽轮机抽汽回热的效率。为避免暖风器中的凝结水滞留在暖风器内引发的锈蚀、水击、振动等问题,暖风器疏水不能采用热静力型自动疏水器,宜采用机械疏水器,而且其出力要留一定的裕量[4]。水侧调节暖风器去扩容器的系统图如图3所示。
祭祀仪式通过行为与器物传递少数民族宗教信仰与文化价值。仪式中的行为与器物发源于该民族的文化信仰,同时又反作用于文化信仰。人们通过祭祀仪式传达了人们对自然的畏与和。器物在仪式中的存在是一种应然状态,通过人们的祭祀行为,将器物引入了一种超然的状态中,即人们通过对器物的应用和摆布,尽可能地展现器物的始源,通过仪式过程“用”的行为,将器物的呈现意义上升到少数民族个体与自然交流的“畏”的层面,以个体经验来规避“一定场所来的、在近处临近的、有害的存在者。”[10]这种存在是少数民族集体的记忆,存在于社会生活中吃、穿、住、用的各个层面,附着在所用、所吃、所接触的一切器物之上,再通过祭祀仪式这一塑造的行为,来构建族群内部以器物为载体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认同。“正是通过他们的群体身份——尤其是亲属、宗教的阶级的归属,个人得以获取定位和回塑他们的记忆。”[11]
祭祀仪式在同一群体的人、物关联上建立了共同性,在族群内部起到了一种引领和凝聚的作用,通过仪式中器物的使用塑造并承载了传统,使得仪式中象征的符号——器物成为了文化认同的标志。祭祀仪式久远的传承历史和丰厚的文化积淀,以及祭祀意识的超越性、自由性等特征与审美意识保持着本质上的一致性,渗透着丰富的美学意蕴。审美思维保留的大量原始思维、神话思维因子,使得少数民族祭祀仪式的审美思维具有了文化上的母体意义,也由此演绎出少数民族丰富而独特的审美文化现象,并成为祭祀仪式所表达的审美意识、审美形态的基础。
通过器物建立的信仰、神话、宗教的联系,赋予了人类活动的意义。少数民族祭祀仪式中器物的礼用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保留了许多独特的文化内涵。都柳江流域农耕民族祭祀是物质展示与神性意象密切联系的仪式化现象,与生产生活中的器物相比,仪式中器物的礼用增添了仪式的神性,使得器物更具价值。透过器物回望农耕民族的发展,能激发当地少数民族重新发现一种更好的生存方式。探讨少数民族祭祀仪式中器物的礼用,是对少数民族原始的宇宙观、生命观、价值观,回归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存在境界,对人类的精神危机、环境危机、传承危机肯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 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M].黄剑波,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 张从良.从行为到意义——仪式的审美人类学阐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3] 龙正荣. 黔东南苗族宗教生态伦理及其现实意义[J]. 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2).
[4] 吴军.活水之源——侗族传统技术传承研究[M].南宁:广西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
[5] 吴一文. 仪式与表演中的文化传承——苗族古歌演述的民俗背景[J]. 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
[6] Rappaport. R. A. Ecology. MeaningandReligion.Richmond[M].Calif: North Atlantic Books,1977.
[7] 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研究评述[J].民族研究. 2002.(2).
[8] Cassirer. E. W T AnEssayonman[M]. New York : New York Books,1944.
[9] 约翰.汤姆林森. 全球化与文化认同[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0]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社,2014.
[11] 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 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A Study on the Etiquette Use of Utensils in Sacrificial Ceremonies among the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n the Duliujiang River Basin
Shi Yuchang
Abstract: The etiquette use of drums, glutinous rice, production tools and other things in the sacrificial ceremonies among the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Qingshuijiang River Basin reflects their farming taboos that emerged to enable them to adapt to the unique geographic system and their culture in which all things are thought to have life. It unveils the switch from practical tools to divine objects, information about the time and space of human activities, and the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structures of the ethnic minorities living here.
Keywords: sacrificial ceremonies; utensils; etiquette use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1707(2019)02-0076-0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都柳江流域少数民族传统技术变迁研究”(17FMZ002)。
作者简介:石玉昌,女,侗族,贵州民族大学副教授,民族教育学博士。(贵州贵阳 550025)
[责任编辑:骆近丹]
标签:仪式论文; 祭祀论文; 器物论文; 柳江论文; 文化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神话与原始宗教论文; 原始宗教论文; 《阿坝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都柳江流域少数民族传统技术变迁研究”(17FMZ002)论文; 贵州民族大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