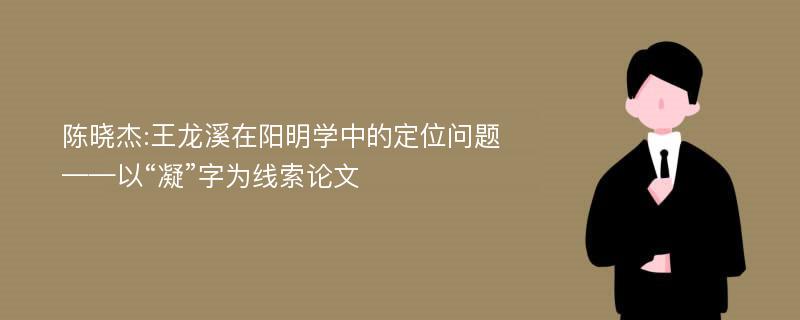
[摘 要]王龙溪历来被认为是阳明后学“良知现成派”的代表人物,但在他的著作中却有很多阳明后学“良知修证派”的代表性论述,如“凝”等。对于王龙溪思想的研究,就有必要跳出常规性的对比图式,深入到其文本内部。在王龙溪思想中,“凝”主要属于工夫论范畴,是以体悟本体为前提下所做的先天工夫,与此同时,他关于“凝”、“收摄”工夫论的表述也隐含了道教色彩。在成圣的阶段论上,王龙溪吸收了禅宗的顿悟渐修等理论思想,而从有关他对“外缘”以及“家事”的负面评价来看,他在思想上则偏离了阳明学的万物一体精神。
[关键词]王龙溪;阳明学;凝;顿悟渐修
一、引言
王龙溪(1498—1583,字汝中,名畿)是明代阳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后人提及阳明学时,王龙溪也一直是无法绕过的对象。基于本文的立场是要重新探讨与检视龙溪在阳明学中的位置,因而有必要简单回顾先行的研究是如何把握龙溪与阳明学之间关系的,这大致可分为三个层面。
首先,作为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对龙溪本人思想的考察自然是重点所在。龙溪通常被视为“良知现成派”,在后世则与王心斋(世称“二王”)等被一并归入“激进派”或者“王学左派”①参见嵇文甫《左派王学》,上海三联书店2014 年版。。但近年来的研究已经不再满足于笼统地判别其流派或者路数,而是深入到其文本内部进行挖掘,出现了不少针对具体问题的研究②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例如上田弘毅的《王龍渓における悟と修》(《中哲文学会報》第8 号,1983 年)、彭国翔的《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明的阳明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年版)、佐藤錬太郎的《王畿の『易』解釈について》(《陽明学》第10号,1998 年)、伊香賀隆的《王龍渓の「顏子」論》(《日本中國学會報》第62 号,2010 年)等。。
在当前社会经济不断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各个行业都在积极发展,虽然对我国国民经济增长而言,具有一定的影响和作用。但是生态环境问题却一直被忽视,甚至有很多领域在发展时,对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影响。甚至有很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将牺牲环境作为自己发展的代价。由此可以看出,在当前我国现代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和发展的背景下,虽然经济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对环境的破坏也越来越严重。
其次,关于龙溪与佛道的关系问题。先行研究大多认为,龙溪积极地吸收佛教以及道教的思想,其“三教观”也基本秉承王阳明的“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吾之用”[1]1289的兼容并包之态度,“良知两字,范围三教之宗”[2]154。例如吴震在《阳明后学研究》中,以“调息法”为切入点,讨论了龙溪对于道教养生之术的关心以及背后所涉及到的问题[3]314~315。虽然龙溪对佛道思想多有吸收,但大多数学者并不认为其由此就已经偏离了儒家之立场。
第三,儒学本身不是为了思辨而思辨之纯粹学问,即便明代心学长于理论,儒者在现实世界中的实践与价值观也值得重视。宋明儒学通常被概括为“内圣外王”,并且“内圣”应当是与“外王”互为表里的。从王阳明开始,就高举“万物一体之仁”的自不容已精神,很多阳明后学的士人不仅有制定乡约等移风易俗的切实行动,还试图干涉政治,实现经世理想。如果说目前学界在上述两个问题(龙溪的思想史研究以及其与佛道关系)上并没有本质上的分歧,那对龙溪的实践立场以及判定,则存在着一定分歧。例如岛田虔次在《王龙溪先生谈话录以及解说》中,虚拟自己为龙溪身边之人,并记录下龙溪之所言,把龙溪描绘为一个热情洋溢、有“冲决网罗”之气概的阳明学传人[4]。荒木见悟则在《明代思想研究》中指出,龙溪在出示同志的《严约规》中明令禁止议论朝政:“其官司得失、他人是非,一切不置诸口,违者罚。”[5]107与王心斋相比,龙溪既无“素王思想”,对于当时崛起的商人阶层以及社会问题也缺乏关心①之后荒木见悟还分析了龙溪撰写的《中鉴录》,认为龙溪对宦官制度本身并无反省(这点与黄宗羲等后世儒者的激烈批判与反省相比,就更加明显),坚信只要致良知就能解决一切问题。荒木见悟指出,本心之发挥必然会受到社会以及历史的诸多制约,更何况本以处理内廷之杂物为本职的宦官,一旦掌握政治实权,又怎能是诉诸良知一念就能轻易解决的问题,而这正暴露出龙溪思想的观念性的幼稚(参见荒木見悟《中国思想史の諸相》,中国書店1989 年版,第213、215 页)。。
2)技术手段。为实现大型仪器设备面向全社会的开放共享,需要整合仪器设备,使之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建设功能完善的信息平台[7]。其主要技术手段包括:运用数字化技术建立设备信息档案;运用数据库技术实现设备使用时间分配管理;运用互联网技术实现设备的远程预约申请;运用多媒体可视化技术实现设备操作的高效培训。这些现代化技术的运用以及信息平台的建设,支撑设备从申请预约到实验操作整个流程,并提供统计、汇总、导出等功能,实现仪器设备全生命周期的信息化、数字化管理。
吴震还指出,虽然龙溪表面依据孟子,作出“性命合一”的解释,实则依循道教脉络。道教内丹思想非常注重“性命”二字,内丹学的理解也与儒家有所不同:“‘性’有精神意识之意,而‘命’字则主要理解为气或生命的意思。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性命双修’等工夫主张。”[3]339他并且认为,龙溪的此等主张与他用“亥子之间”来解释“向晦宴息”一样,都是用道教的思想来解释儒家的思想[3]339。那么,这里的“气”,以及“发散”、“翕聚”带有道教的特征与实践性,也应该没有什么疑问了。由此,我们再来看下面这段提及“收摄”的材料:
另一方面,即便是认为龙溪对于现实世界缺乏关心的荒木见悟,在前两个问题(龙溪的思想及其与佛道关系)上也没有提出根本的异议。然而,如果龙溪确实如荒木见悟所分析的那样,对于当时的政治以及民生的关心极其有限,那么我们必须追问:为什么龙溪所主张的“现成良知”,本可以“自生道义,自存名节”[2]79,具备无限创造规矩条理的能力,在现实世界中却自我限制,也并没有对种种既成现实规范与成见(“典要格套”)进行积极的检视与再创造?更明确地说,如果龙溪的思想与实践是前后一贯的话,就不应该出现第三点有关他的现实实践的评价分歧问题。
如前所述,龙溪所主张的“凝”、“收摄”工夫必然是在良知初步呈现或者对良知有所领悟的基础上才能做(即“先天之学”),如果我们套用汉传佛教的术语(明代儒者无论迎佛还是排佛,几乎也都会援用此套话语体系)“悟修论”,那似乎“凝”就可以归入“修”的范畴。但对良知本体的领悟与建立在本体意义上的“凝”之修证,其关系究竟如何?换句话说,通过“凝”之修证,是否人就能彻底达到最终的圣人境界?除了“凝”以外,对于成圣之目标而言,还是否有其他重要的工夫?在此过程中,是否还会有新的体悟?是否会有反复甚至后退与挫折?要回答这一系列问题,仅依靠前文的关键词式检索与分析显然是不够的,因此,本部分将把视野放宽到龙溪的“悟修论”以及相关内容上。
二、“凝”的工夫与道教倾向
不管是明代阳明学内部的争论,还是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大体上都喜欢将龙溪与阳明学“稳健派”或者“良知修证派”进行对比性的思考。典型的就是如下图式(schema):
先天——后天;四无——四有;现成——修证
原来,两栖飞机在水面上滑行时,要想改变水中航向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而配备四台发动机的“鲲龙”AG-600想要在水里灵活转弯,只需要改变一侧发动机的推力即可轻松实现。同时,多台发动机的设计还可以提高它在风急浪高恶劣环境下起飞或者降落时的安全系数。
这种通过对比来强化对立双方观点上的差异性,确实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龙溪在与聂双江、罗念庵等人的论辩中,也给人以“激进派”或者“现成良知派”的印象。然而,对立化图式的思考并非无弊,它往往使问题简单化和片面化,而忽略了研究对象本身可能具有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对作为王龙溪“对立面”之一、所谓“良知修证派”的钱绪山的研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吴震在《阳明后学研究》中就指出钱绪山与龙溪的思想实质上存在着诸多共通之处,用对立性的“四有说”去概括钱绪山,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3]117~156。对于龙溪思想的理解与把握,其实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但未受到学界充分的重视。
此外,有些场合下“凝”字与其说是工夫论的范畴,毋宁说与君子的气象联系了起来:
通过中国知网,南京体育学院图书馆及网络搜索查阅了有关定向运动、高校运动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文献、书籍及文件,基本掌握了普通高校开展定向运动的现状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特征,为本课题研究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基础。
我们以龙溪的“凝”字以及近义词用例,作为问题的切入点。“凝”字,《说文》曰:“水坚也。本从冰。”所以“凝”本来是水坚固的形态亦即“冰”,又有“成,定也”(《增韵》)之义。而与“凝”相关的词,例如“凝聚”,似乎应该是与“发散”相对立的,然而从龙溪著作中的相关使用来看却并非如此。一方面,从下面这两则材料来看,“凝聚”(或者“收敛”)和“发散”确实是对立性的概念:“先师有云:‘道德言动威仪,以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若强于就喧而不知节,习于多事而不知省,未免伤于所恃,毕竟非凝翕之道”[2]119;“夫良知灵明,原是无物不照,以其变化不可捉摸,故亦易于随物。古人谓之凝道,谓之凝命,亦是苦心话头。盖良知即道即命,若不知凝聚,则道终不为我有,命终不为我立。吾人但知良知之灵明脱洒,而倏忽存亡,不知所以养……夫养深则化自显,机忘则乐自生”[2]456。
然而,也有材料显示:“真机透露即是凝。若真机透露前,有个凝的工夫,便是沉空守寂。”[2]61如果要作出一致性解释的话,根据所列举的材料来看,大概只能是这样的:“凝”字本身有两种含义,一是相对于“发散”而言的“凝聚”的内敛工夫;二是达到一定境界后的“凝”,此时“凝”就只是一个描述语,所以可说良知之透露,发散即凝聚。龙溪论“几”[2]58以及与聂双江辩“寂感”问题时候,都采取了这种思路:寂感不二,反对将“寂/感”、“已发/未发”理解为经验层面的时间先后关系。
一般认为,强调工夫上的“收敛”或者“收摄保聚”是“良知修证派”的特点。例如主张涵养未发之心体、体立而用自生的聂双江,以及与龙溪反复论辩、思想有过多重转折的罗念庵。作为他们对立面的龙溪,在黄宗羲看来是“悬崖撒手”[6]226②“悬崖撒手”本为禅宗的话头,例如《无门关》第三十二则《外道问佛·颂》云:“不涉阶梯,悬崖撒手。”这意味着提倡顿悟,主张在某种瞬间当下的时刻领悟到真理本身,而不是循序渐进的修行与磨练。式的人物,但在他的著作中却有很多提及“凝”、“收敛”、“缉熙保任”等话头,这确实给人一种违和感。
教材中安排了学生自己动手来完成青霉和匍枝根霉的培养和观察,使学生掌握真菌的主要特征。然而,在课堂教学实践中,学生按照教材的操作提示能看到馒头和橘皮发霉,但由于混有杂菌,学生难以观察到典型的青霉和匍枝根霉的形态结构。且青霉分生孢子梗上成串的孢子容易碰落,菌丝容易断裂,盖盖玻片时要特别小心,既缓慢又不能移动位置,给教学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本文尝试制作青霉与匍枝根霉模型,可以让学生观察到清晰、完整的青霉和匍枝根霉的形态,不仅能很好地诠释教学难点,还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2.2 基于K-means算法的优秀班集体评选方法首先将真实数据集按年级进行划分,分别得到2015级、2016级和2017级各班级的参评数据,然后从3个年级的数据集当中分别选取所有属性取值较平均的班级(均衡发展班级)、若干属性取值较大的班级(偏离发展班级)和大多数属性取值较小的班级(最差发展班级)作为初始聚类的中心,按K-means聚类算法的执行过程,将各年级的数据集分别聚为3类,最后将均衡发展的类内的班级作为本年级的优秀班集体。具体的实现过程如下。
或问:“学者用功,病于拘检,不能洒乐,才少纵逸,又病于不严肃,如何则可?”先生曰:“不严肃则道不凝,不洒乐则机不活。致良知工夫不拘不纵,自有天则,自无二者之病,非意象所能加减,所谓并行不相悖也。”[2]152气象的凝重或者威严,在龙溪看来未必就意味着拘谨死板,君子会随着外界的感应而随机应变。
早在先秦的孟子心学思想中,就有“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上》)的说法,强调先天绝对之本心会因为后天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而为“外物”所牵引,从而丧失本己。龙溪也曾提到:
在对龙溪所说的作为工夫的“凝”依然是“先天之学”这一点有了初步的确认之后,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凝”以及与之相反的“发散”究竟意味着什么。“发散”与“发用”,在宋明儒学的讨论框架内(更常用的是“发用”),一般意味着“本体”在“感”之后的“应”,因而是经验层面的概念。这个“本体”或者是“天理”,或者是“良知”,但不会是诸如汉儒的“气”之类的范畴。而“凝聚、收敛”则侧重于工夫的层面,强调对于本体的保养和不随外缘物欲所动,这当然是聂双江、罗念庵思想的核心概念。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龙溪曾在“气”的背景下提到了“发散”与“翕聚”、“凝”。例如他说:“天地之道,阴阳而已矣。不专一则不能直遂,不翕聚则不能发散,易简所以配至德也。日月者,阴阳之聚也,其行有常度,故能得天而久照,君子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吾人精神易于发泄,气象易于浮动,只是不密,密即所谓凝也。”[2]117这里以阴阳二气论天地日月,气凝聚之后才能发散,人心也是如此。还有另一段相关的材料,则从“身心”的角度进行阐述:“自今言之,乾属心,坤属身;心是神,身是气。身心两事,即火即药。元神元气,谓之药物;神气往来,谓之火候。神专一则自能直遂,性宗也;气翕聚则自能发散,命宗也。”[2]85既然说“气翕聚则自能发散”,那么先来看龙溪对于“气”的用法。对此吴震已经作了详尽的分析,他认为,一般情况下,“气=充塞于天地之实体(万物根源)”[3]333,这是很传统的观点。而在龙溪的《东游会语》一文中,可以归纳出如下图式:
为什么在对龙溪思想以及三教问题的理解并不存在原则性分歧的情况下,对于龙溪的实践以及评价问题,学界研究却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别?事实上,岛田虔次等学者依据龙溪本人所主张的“经世济民”说法,认定其实践也必定是积极入世的。荒木见悟同样也依据龙溪本人的文献,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在这里其实已经牵涉到思想史研究的基本方法问题,我们通常认定文献所记载的思想家的言说必然与其所思所行具有一致性,否则思想史研究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都将遭受根本的质疑。但是,上述一致性的假设只是研究的起点,如果根据相关文本,思想家的实践与其自身的主张存在不一致甚至自相矛盾的情况,那么像岛田虔次那样从“思想”直接推导出“实践”与“行动”,就很值得商榷。
大抵我师良知两字,万劫不坏之元神,范围三教大总持。良知是性之灵体,一切命宗作用只是收摄此件,令其坚固,弗使漏泄消散了,便是长生久视之道。古人以日月为药物,日魂之光便是良知,月魄便是收摄日光真法象,所谓偃月炉也,其几只在晦朔之交。不得先天真气为种子,皆后天渣滓也。[2]202
武术对外教材翻译杂乱,令海外武术习练者无法理解内容语义。访谈得知,对于仅有的外语武术教材,海外习练者普遍表示教材中语言翻译难以理解,无法进行自学。造成此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文化差异,中国武术具有浓厚的东方文化色彩,在世界观和认识论方面拥有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与西方文化产生强烈的对比,给翻译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例如太极拳中的“野马分鬃”、“白鹤亮翅”等形象生动的动作名称,对于外语翻译而言,是一件棘手的事情,需要翻译人员在进行外文翻译的过程中,具备很强的业务能力,既要通晓中国文化,又要熟练掌握该国语言。
既然所谓的“命宗”如上文所说,与身、气相联,“一切命宗作用只是收摄此件,令其坚固,弗使漏泄消散了,便是长生久视之道”的说法便显然是在捏合阳明学与道教了。
龙溪又以“日魂”来配“良知”,尽管在阳明学中,经常有将“良知”本体比喻为“太阳”的说法,但是在此语境下恐怕也是出自于道教的概念,原因有两点:第一,“日魂”与“月魄”对举,且使用了“晦朔之交”的道教典故;第二,学界很少注意到,龙溪曾经使用“离明”来比喻“良知”的说法,“凝目睛,始能善万物之色;凝耳韵,始能善万物之声,天聪明也。良知者,离明之体,天聪明之尽”[2]480。这里龙溪依据的是道教内丹思想的“坎离造化论”。以上两点均可用五代末彭晓的《周易参同契鼎器歌明镜图》中的一段材料来加以说明:“日者阳也,日中有鸟,阳含阴也。月者阴也,月中有兔,阴含阳也。此天地显垂真象,令达者则之,可谓真阴阳也。”吾妻重二解释道:“也就是说,阳中含阴的离卦,与阴中含阳的坎卦才是‘真阴阳’。彭晓在《明镜图》解说中也说:‘阳无阴则不能自耀其魂’、‘阴无阳则不能自营其魄’。不是单纯的阴与阳,而是阴阳混合之状态,才能真正的生出诸事物。”[7]39~40而龙溪所说的“晦朔之交”,同样是道教内丹经典《周易参同契》的范畴:“晦朔之间①所谓“晦朔之间”就是“三十日半夜以前是也。丹法以时易日,则每日亥子之交,即晦朔之间也”(孟乃昌、孟庆轩编《万古丹经王〈周易参同契〉三十四家注疏集萃》,华夏出版社1993 年版,第183 页)。,合符行中。混沌鸿蒙,牝牡相从。滋液润泽,施化流通。天地神明,不可度量。”(《晦朔合符章第四十六》)
“日魂之光便是良知,月魄便是收摄日光真法象”,这样的说法依然有工夫断裂的嫌疑。因为“月魄”很显然在时间上是后于“日魂”的,然而龙溪“先天之学”主张在悟得先天之良知本体的基础上做工夫,让良知自做主宰,这样的话,工夫在逻辑上说也必然是在良知本体之后才成立的,“日魂月魄”的说法也就同样表达了“收摄”、“凝”的工夫必然是在良知初步呈现或者对良知有所领悟的基础上才能做的意思(即“先天之学”)。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评价龙溪以道教的“气”为背景的“凝”、“收摄”工夫论的叙述呢?虽然王阳明本人在后期也经常有“性气”不分、正面肯定“气”的倾向,然而这个思考本身及其转折几乎与道教无关[8]88。“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谓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谓之气”[1]62,此句可以作为总括。“‘生之谓性’,生字即是气字,犹言气即是性也……孟子性善是从本源上说,然性善之端须在气上始见得。若无气亦无可见矣。恻隐羞恶辞让是非须在气上始见得”[1]61,在此处,“性”作为“体”,其自身是不显现的,故需要“气”来得以表现,“气”即作为“用”而成为使“性”得以外在化的积极性的力量。事实上,不仅是在“性”与“气”上如此,王阳明后期论“理气”关系亦是:“理者,气之条理;气者,理之运用。无条理则不能运用,无运用则亦无以见其所谓条理者。”[1]61龙溪看似继承阳明的思想,也主张“气”的重要性,甚至多处都直接说“良知”是“灵气”(“真气”只有“不得先天真气为种子,皆后天渣滓也”中提到,却多次将“良知”与道教的“真息”放在一起说),我们固然可以依照柴田笃的做法,在儒家以及佛教中发掘此说的内涵②参见柴田篤《良知靈字考:王龍渓を中心にして》,《陽明学》第3 号,2000 年。,但由于这种道教式“气”观的渗透,龙溪的“良知”可能已经与阳明的思想存在着隔阂。
从上述分析来看,龙溪以“收摄”论良知,以“日魂”喻良知,以“弗使漏泄消散”为工夫,均与道教息息相关,其内敛与静态化之取向可以说是很难否认的。
三、“顿悟渐修”工夫与佛教价值观的渗透
(一)顿悟渐修
本文认为,龙溪对于现实社会与政治的态度以及实践上的消极性,并不能简单归结为个人的“气质”或者“时代局限”,而应当考虑与他整体思想的关系。同样,龙溪自认为是王阳明学说的正统传承人,但是他对于佛教以及道教的涉猎,真的只是某种“补充性”的东西,对于他的思想本身而言不构成任何实质性的改变?笔者对此是持怀疑态度的。本文将以龙溪著作中屡屡出现的“凝”字作为线索而展开论述,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龙溪不为人所注意(或者有意忽略)的面向,在揭示他工夫论复杂内涵的同时,对他的思想进行重新梳理与界定。
龙溪虽然因“四无说”而成为众矢之的,然而正如彭国翔所指出的,此说“仅见于天泉证道的相关记载”[9]208。相反,王龙溪更多地套用了圭峰宗密的悟修理论来进行工夫论的阐发。例如所谓“解悟”、“证悟”和“彻悟”的三悟说:
(1)是整套生产工艺及设备设施均设置在一个密封的厂房内,厂房内新型数控反击式破碎机、振动筛、清堵筛、环保节能混合破碎式制砂机均设置有与其相联的数控粉尘收除器。厂房内生产工艺被分隔为左右两部分和地下装车通道三个区域,生产工艺左右两部分之间设有空中巡查玻璃通道及位于空中巡查玻璃通道一端的操控中心。厂房室内、地下装车通道均设置有数控粉尘收除器。形成厂内主机设备及工厂室内两级负压除尘,完全没有粉尘的外扬。成品粒径可调节、粉量可控制,所以成品粒的粉量不超标、不需水洗,无污水排放,从而避免粉尘或废水污染环境,符合党的十九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精神。
君子之学,贵于得悟,悟门不开,无以征学。入悟有三:有从言而入者,有从静坐而入者,有从人情事变练习而入者。得于言者,谓之解悟……得于静坐者,谓之证悟,收摄保聚,犹有待于境……得于练习者,谓之彻悟,摩砻锻炼,左右逢源,譬之湛体冷然,本来晶莹,愈震荡愈凝寂,不可得而澄淆也。根有大小,故蔽有浅深,而学有难易,及其成功一也。[2]494①另可参见《王畿集》卷十六《留别霓川漫语》,凤凰出版社2007 年版,第466 页。可以比较一下宗密的说法:“若因悟而修,即是解悟,若因修而悟,即是顿悟。然上皆只约今生而论。若远推宿世,则唯渐无顿。今见顿者,已是多生渐熏而发现也。”(鐮田茂雄注《禅源諸詮集都序》,筑摩書房1969 年版,第191 页。)
理想的状态自然是“从人情事变练习而入”,龙溪在与他人的言谈中也反复提及,但问题是他自己能否做到“摩砻锻炼,左右逢源……愈震荡愈凝寂,不可得而澄淆”?从本文所举的资料来看,我们所能知道的是龙溪强调“凝”都不是悬空去做工夫,而必须是在对本体之良知有所领悟的基础上去做,“凝非灰心枯坐之谓,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人为天地之心,万物之宰”[2]117,“凝”似乎不应该是“有待于境”的,但是上文的“三悟”说中,却明确地说“得于静坐者,谓之证悟,收摄保聚,犹有待于境”。事实上,如果我们想到本文第二部分与“凝”相关的材料中所体现出来的浓厚道教气息,以及龙溪“亥子之交”、“日魂月魄”、并将良知比喻为“离明”的说法,均可说明,龙溪本人并未放弃过这种静态化的“有待于境”的修炼方式。
另外,龙溪有“顿悟、渐悟、顿修、渐修”的说法:“本体有顿悟,有渐悟;工夫有顿修,有渐修。万握丝头,一齐斩断,此顿法也;芽苗增长,驯至秀实,此渐法也。或悟中有修,或修中有悟,或顿中有渐,或渐中有顿,存乎根器之有利钝。及其成功一也。”[2]89这显然也是承袭了宗密的说法,在此不作详论。要之,结合上文的“三悟说”来看,龙溪是考虑到不同人由于根器等因素的影响而承认多种修行的合理性。
然而,龙溪本人可能更倾向于“顿悟渐修”的成圣之路:“理乘顿悟,事属渐修。悟以启修,修以证悟……孔子自叙十五而志学,是即所谓不逾矩之学。犹造衡即是权始,矩者良知之天则也。自志学驯至于从心,只是志到熟处,非有二也……孔子之学,自理观之,谓之顿可也,自事观之,谓之渐亦可也。”[2]500~501由此,并结合上述分析,可以作出这样的解释:龙溪坚持成圣必须“悟入”,此“悟”便是“真种子”,便是良知之自然发见处或者说“一念真机”。根据宗密的理论逻辑,我们可以合理推测,此“顿悟”尚属于“解悟”或者“证悟”(龙溪所说的“彻悟”地位相当于宗密所说的“证悟”)的范围。虽然对于良知本体有所体认,但仍然是有意为之或者“有待于境”,因而仍需要后天工夫的“渐修”。“渐修”可以有多种途径与手段,龙溪本人便毫不忌讳地使用道教以及佛教的相关概念与实践,最终理论上便能达到“彻悟”的境界,而通常学者所强调的便是龙溪对此“彻悟”之后境界的描述。说“境界”可能都并不确切,因为在龙溪看来,即便是圣人,也不是在“彻悟”之后就可以高枕无忧、不做工夫了,只是说,对于圣人而言,工夫始终是“即本体便是工夫”,是不需要人为努力或者意识层面的“勉强”。事实上,本文所分析的“凝”、“收敛”,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先天之学”,乃至我们在某些情况下,是无法区分“凝”的第一层意思(工夫)和第二层意思(描述语)的。然而那毕竟是圣人或者即便不是圣人也是上根器之人才能做的工夫。对于一般人而言,静坐,乃至道教佛教的工夫论实践中卓有成效的实践,都应当是入手处。但是,毕竟龙溪在所有相关材料中都明确主张,无论是“凝”、“收摄”还是“保任”,其对象都是本体的良知(有些时候龙溪会说“一点虚明”、“无中生有”,这当中的道教色彩就很浓厚),并非完全没有头脑地仅仅收敛身心,消除杂念与欲望,所以似乎又不能说,对于“贤人以下”而言的“凝”的工夫是“后天之学”。龙溪所说的“凝”、“收敛”虽然在层次上欠缺梳理与区分,但在某种意义上,也说明了其所包含的内容以及指涉非常丰富,在经过分析与整理之后,我们确实可以认为,龙溪在工夫论上的考量并没有忽视中下根器之人,在各种情况下虽然使用同一个概念或者有相似的说法,但只要区分清楚,这同一个概念(“凝”)就能成为是针对各种不同根器的人而进行的随机指点。对于中下根器之人而言,一方面在对良知有初步体悟的基础上,需要时时保任良知,在这个意义上,工夫虽然可能有勉强的成分,但依然可以说是“先天之学”;但另一方面,正因为根器尚浅,所以在待人接物的时候,时刻都可能为物欲等外在的东西所牵引,从而使良知受到遮蔽,因而还需要做“寡欲”的工夫,来求得良知的再次呈现。这种情形下,良知并没有成为做工夫的主体,而是其目标,所以是“后天之学”。
(二)“不变随缘”与“时时保任”
第一层含义上作为工夫的“凝”,似乎与聂双江乃至晚年之前的罗念庵很相似,但其实不然。龙溪还是强调了必须先对于“良知”有所契悟,之后方可做“收摄此件”的工夫。这是典型的阳明心学工夫论,盖“良知”既是“知是知非”的判断主体,又是将此“是非”判断后落实到行为上的最终动力,因而必然要强调一切工夫均须契合本体来做,而且在对本体的良知有初步领悟和契合的情况下所做的工夫,在龙溪乃至其他“良知现成派”士人看来,都可以说是“本体上做工夫”。结合龙溪所谓的“先天之学”(“在先天心体上立根,则意所动自无不善,一切世情嗜欲自无所容,致知功夫自然易简省力”)与“后天之学”(“在后天动意上立根,未免有世情嗜欲之杂,才落牵缠,便费斩截,致知工夫转觉繁难,欲复先天心体,便有许多费力处”)的区分[2]10,可以认为,“凝”即便在工夫论意义上也应当属于“先天之学”的范畴。如此判断的理由有两点:首先,龙溪对于“凝”的论述并没有涉及克去“世情嗜欲”的问题;其次,龙溪曾说过“真机透露前,有个凝的工夫,便是沉空守寂”[2]61,“凝”的工夫并非是要通过“凝”来使得“真机(即良知)透露”,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工夫就完全断裂为两截,这是“良知现成派”坚决否定的工夫论方法。
阳明学的“良知”有“随缘”之“用”,并且“良知”本体必须在“用”上才能呈现出来,这个呈现也必然全体是“良知”。由此就引申出阳明晚年开始提出的“因用以求其体”的思路,龙溪本人也多次强调“事上磨练”的重要性。例如他说:“若见得致知工夫下落,各各随分做去,在静处体玩也好,在事上磨察也好,譬诸草木之生,但得根株着土,遇着和风暖日,固是长养他的,遇着严霜烈日,亦是坚凝他的。”[2]87然而,禅宗思想同样也注重日常性的生活与对“境”的磨练,所谓“运水搬柴无非妙道”。由于话语的相似性以及工夫论实践上的互相渗透,使得儒佛之间的界限变得很模糊。关键点可能在于,阳明学本身就是经世之学,因此在临事之时,这个相对于行动主体而言的外境本身并不是一种负面意义的价值承载物;而作为佛教的禅宗,无论是临济宗的“无位真人”,还是荷泽宗的“知之一字,众妙之门”,都仍然是建立在传统“缘起自性空”的教义基础上,因此仍然是认“境”为“空”,不会承认其本身是具有正面价值或者宗教意义。此诚如唐君毅所言:“然禅宗肯定应许世间诸法,可非积极之肯定应许。运水担柴,固无不可见道,然运水担柴之所以可见道者,惟是因运水担柴,而心无系着、无念、无相,则运水担柴当体即空,故可见道……然即在更高之意义中,所肯定之世间法伦理政治社会之道,仍可说为求得解脱、达涅盘境界之方便:乃经一转手,以间接加以肯定。儒家则不然,其肯定世间法、则可谓之直接加以正面的肯定。自来儒者所用心,皆下求建立伦理政治社会之道必须有之理由。宋明儒之用心,自亦在是。”[10]423~424
2.1.5 精密度试验 精密吸取上述混合对照品溶液10 μL,连续进样6次,按“2.1.1”项下色谱条件测定,姜黄素、去甲氧基姜黄素、双去甲氧基姜黄素峰面积的RSD分别为1.3%、1.7%、1.9%,结果表明分析方法精密度良好。
良知虚体,不变而妙应随缘。玄玄无辙,不可执寻;净净无瑕,不可污染。一念圆明,照彻千古……惟其随缘,易于凭物,时起时灭,若存若亡。以无为有,则空里生华;以有为无,则水中捞月。临期一念有差,便堕三途恶道,皆缘应也。自其不变言之,凡即为圣;自其随缘言之,圣即为凡。[2]277龙溪在这里明显借用了《大乘起信论》的“不变随缘”理论。
(2)学习动机。学习动机是指引发和维持学生继续学习,并使之成为达到一定学习目标的一种动力倾向。成人学生通常是为满足工作、生活需要才进一步学习,即需要什么学什么,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更强的学习动机。当学习者具备较强的学动机时,在上网时能自觉浏览学习网站,进行知识或技能地学习。
回过头来看龙溪。虽然儒家一般会认为人在现实世界中因对于外在物欲的追逐而丧失自我与本心,然而即便是主张“存天理,去人欲”的朱熹,也并不认为“人欲”本身是“恶”(所以严格地说程颐、朱熹所主张的都是“去人欲之私”),更不会认为人与外物、家、国之联系有负面价值意义。但是龙溪却说:“因此勘破世间原无一物可当情,原无些子放不下。见在随缘,缘尽即空,原无留滞。虽儿女骨肉,亦无三四十年聚头,从未生已前观之,亦是假合相,况身外长物,可永保乎?”[2]207这里用了“因缘假合”与“缘尽即空”的佛教观点,并认为儿女骨肉之牵绊也只是“假合”,这无疑是滑转到“缘起自性空”的佛教立场。还有几处,龙溪一方面强调讲学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则以家事为累:“时常处家与亲朋相燕眤,与妻奴佃仆相比狎,以习心对习事,因循隐约,固有密制其命而不自觉者。才离家出游,精神意思便觉不同。与士夫交承,非此学不究……晨夕聚处,专干办此一事,非惟闲思妄念无从而生,虽世情俗态亦无从而入,精神自然专一,意思自然冲和。教学相长,欲究极自己性命”[2]120;“记闻、家役,则诚劳矣。若夫讲学,育德养身,逸之道也,何劳之有?”[2]641对于上面的材料,切不可理解为王阳明、王心斋那样的汲汲于救世的万物一体观,龙溪以讲学为己任,因而不得不舍小家而顾大家。他还明确以家事为累赘:“才离家出游,精神意思便觉不同”①这种说法在阳明后学中很常见,参见吕妙芬《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新星出版社2006 年版,第255—268 页。。并且他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妥:“予性疏慵,不善理家。安人纤于治生,拮据绸缪,终岁勤动,料理盈缩,身任其劳,而贻予以逸。节费佐急,丰约有等,家政渐裕,不致蛊败涣散,安人成之也。”[2]647既然以家为累,“修齐治平”的儒家理念又从何谈起呢?而讲学时觉得精神意思焕然一新,这本身是否也说明了他所主张的“时时保任”工夫,其实并不是“彻悟”意义上的“时时”,而恰恰是在工夫上存在着断裂与不一致的地方①这里可以对比周海门的说法:“释氏朝夕只理会此事,我辈在家在外,许多牵累,不赖师友夹持,便要沉溺。然至于日用应事,风波摇荡时,须自家做主,又靠师友不得。不靠师友亦不离师友,用自作方便。”(《东越证学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65 册》,齐鲁书社1997 年版,第487 页。)?
彭国翔认为,龙溪的“一念工夫在修齐治平的展开过程中必然指向‘以万物为一体’的经世之学”[9]143,理论上确实如此。但即便本人在某些场合下提到儒者应当以经世为志,也并不能证明,他本人实际上便是如此想,并且如此去付诸实践。阳明学成圣论的基本前提是:相信即便是陷溺于尘世之中的愚夫愚妇,也会有“良知”发见之时,这种“良知”的呈现不仅是“当下”,而且必定是“全体”之知。对此,龙溪是完全接受并且多有阐发的[2]230。然而,这种从“凡”入“圣”的绝对性的大翻转,并不就此完结。“圣”可以由“一念”而入,然而下一念若有所不慎,便可能复坠入“凡”甚至魔道。龙溪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因此一旦得“一念灵明”,便提倡“绵密凝翕”或者“收摄”。然而由于龙溪对于种种“习染情识”、后天的“知识技能”都持不信任与否定的态度,乃至以家事为累,以父子手足之情为“假合之相”,那么,他经常说的“世情”,便未必只是朱子学的“人欲之私”了。
由此,龙溪本人所实践的“事上磨练”的工夫论可能是如下这种形态:以成圣为目的,一旦体悟本体(这必须在不隔于外世的情况下悟得,禅宗也是如此),便“收敛”此真机,隔绝一切外来的“习气世情”,使之不能掺杂于其中,而“外境”是检视本人是否真正达到体悟并持续此状态的最好“道场”,久之便能让良知凝翕而不逐于物。在此,收敛真机和隔绝“世情”之间的关系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同时进行,虽然收敛以及“凝”本身也应有寡欲等效果,但是不足以“去蔽”,这样的话似是有意勉强而为之;二是收敛真机便自然能使“良知”不“缘物”,不需要另外做工夫。结合龙溪平日对于学者拘泥于外在检束做法的反感,以及他本人崇尚“自然易简”的态度来看,应当是后一种理解,这也符合前文所分析得出的“凝”为“先天之学”的结论。但这种“凝翕”工夫,由于龙溪意识上有意与“外缘”对立起来(和禅宗一样,“外缘”本身被视为负面性),最终所达到的境界或许很高妙,但仍然是一种否定意义上的“超越”。
四、结语
以上,本文以历来在龙溪思想研究中未受充分关注的“凝”、“收敛”为线索进行了讨论,得出的结论与学界通常认定的“良知现成派”领军人物的形象大相径庭:龙溪本人很重视“凝”的工夫。从材料分析来看,“凝”的内涵很丰富,既可以是体悟本体为前提下所做的工夫,又可以是工夫之“效验”。“凝”以及“收敛”等说法中,夹杂了道教色彩的概念以及工夫实践(离明、亥子之交、日魂月魄、一点虚明),龙溪本人对此的解释是,“调息”、养气等道教的工夫论只是权法。龙溪一直高调提倡的所谓“先天之学”,是“即本体便是工夫”,在良知本体上说“凝”,其本身一方面不意味着意识层面需要勉力去使得良知“凝结”,而且可以说良知是即“发散”即“收敛”,这当然是秉承了王阳明打破已发/未发、本体/工夫这些朱子学所确立的理学基本概念图式的精神,然而问题就在于,龙溪自己也并没有放弃道教的“权法”。
另一方面,龙溪倾向于对有所体悟而呈现出来的良知进行一种内敛式的维护,避免良知“感于物”而不返。然而当我们考察与此“物”相关的论述,就会发现为了避免良知被遮蔽而被否定的,并不仅仅限于宋明理学家通常所说的“人欲(之私)”,还包括了“世情”以及家事等等,所以整个外在世界对于龙溪而言,更多的是接近于佛教的“缘起自性空”,而不是程颢那样的“万物皆有春意”。龙溪认为“良知”是“不变随缘”,此完全符合阳明学之立场,但在龙溪这里,“外缘”更多地被负面化理解,这直接导致龙溪所主张的“事上磨练”工夫更多的是成圣之手段(“道场”),这在定位上显然也偏向于禅宗而非传统儒家。换个角度来看,既然“发散”、“收敛”在悟得良知本体的情况下都可以说,那为什么龙溪会更多地强调“凝”、“收敛”?主要原因就在于“随物”、“逐物”的良知容易陷于“荡越”而流入猖狂情识的危险境地。然而为了维持良知的纯粹性以维持其灵明,同样可能流入偏枯虚无或者“玩弄(良知灵明之)光景”的危险。
在成圣的阶段论上,和当时的很多“良知现成派”士人一样,龙溪认为对于良知本体之“悟”,并非一了百了,而可能是会经历多次乃至多个不同阶段的,这确实可以说是龙溪的卓见。“凝”、“收摄”可以是与“静坐”相关,也可以是“偃月炉”(日魂月魄)等等,适用于中下根器之人。通过对于时间、环境的严格选择乃至屏蔽外界的干扰,使得人能够暂时摆脱物欲与各种杂念,从而有利于体悟自己的良知,这当然“有待于境”。但同样也可以是以良知本体为对象的“凝”,在此情形下对于良知的体悟(虽然未必是“彻悟”)就是做工夫的前提条件,通过时时收敛与凝聚良知,使其不逐于物,不随境流转,这就是“无待于境”的“先天之学”。我们不能说龙溪的“凝”是“彻上彻下”,但确实对于不同根器的人,都能有所对应。对于大部分人而言,甚至是可以并用(但并非“同时”),从而呈现出这样的工夫论次第状态:通过静坐、调息等手段来“寡欲”(后天之学)→使良知呈现→良知呈现后即对其进行“凝”→工夫不得当或者逐于外物,未能致良知→良知被遮蔽,重新做“寡欲”工夫→……如果我们援引圭峰宗密的体系,那么龙溪的“悟修论”大致可以归纳如下:
龙溪本人直到晚年也并没有放弃掺杂了道教思想的诸多“有待于境”的工夫实践,可见他所达到的工夫境界应该至少是在“解悟”之后,但却未达“彻悟”的境地。并且,由于他本人在气质与实践上的偏差,如果继续走下去的话,最终所达到的“彻悟”境地恐怕也会偏向于道家式的虚静与超脱,而不是他在讲学中热烈赞颂的阳明学的万物一体之精神。
回顾开篇所提到的龙溪研究的三个方面,本文所给出的结论可以进一步总结如下:龙溪三十岁在“天泉证道”就已经提出“四无说”,但“四无说”容易产生轻视工夫的倾向而造成“荡越”之弊病。对此,龙溪本人是有清醒认识的,因此他一方面在四十余年的讲学活动中反复强调良知之先天性与“现成”(这在与“良知修证派”的聂双江、罗念庵等人的论辩中尤其如此),另一方面又很强调各种“渐修”的工夫以及对各流派思想和长处的融摄。但是仔细分析与考察其工夫论,便会发现龙溪的思想与“良知现成派”其他主要人物如王心斋等人的区别所在。龙溪重视虚静以及内敛的程度,使得我们必须重新辨析他的思想与佛道之间的异同。在这时,仅仅依据龙溪自我标榜儒家立场的言说,反而会掩盖问题所在,以为他是彻底坚持了以良知为范围三教之宗的立场。因此本文选取了诸多先行研究所不常使用的材料进行分析,并指出了龙溪的思想和气质与佛道二家的相近之处。由以上两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现实世界的实践以及评价问题上,先行研究会出现分歧的原因所在,正因为龙溪本人的思想和气质已经严重偏离了王阳明所提倡的积极入世的立场,因此在现实世界中,他对朝政很少置评,即便偶尔提及也是停留在抽象的层面而缺乏洞察力;对于当时的社会现象与问题,龙溪也缺乏关心,遑论以灵明之良知进行规范与再创造。最后,谨以罗近溪弟子杨起元对龙溪的一段评语作结:
此老乃实修之士,其修也过于其所悟,而世以遗行议之,益成此老之真修矣。何者?真修之人,岂畏人知。人有不知,正惬修者之愿,到今日为弟识破,亦此老余憾。然此老力量不能到得终古识不破地位也。何故?其悟门尚非正也。[11]329
4.1 病态行为 病态行为是一组症状群,这组症状群主要是由中枢或外周给予微生物、LPS、疫苗、促炎性细胞因子所诱导[38]。这些行为主要包括食欲与体重改变,社交、主动行为、性行为下降,快感缺乏以及睡眠结构的改变。这些行为和临床干扰素诱导的抑郁症状类似[39]。
[参 考 文 献]
[1]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 王畿.王畿集[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3] 吴震.阳明后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4] 島田虔次.王龍渓先生談話録及び解説[J].東洋史研究,1952,(2).
[5] 荒木見悟.明代思想研究[M].東京:創文社,1972.
[6] 黄宗羲.明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5.
[7] 吾妻重二.朱子学の新研究——近世士大夫の思想史的地平[M].東京:創文社,2004.
[8] 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 彭国翔.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明的阳明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10]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M].台北:学生书局,1986.
[11] 杨起元.续刻杨复所先生家藏文集八卷[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67 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中图分类号]B24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19)03-0118-08
[收稿日期]2018-05-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资助项目:17ZDA013
[作者简介]陈晓杰(1981-),男,江苏常熟人,武汉大学国学院讲师,东亚文化交涉学博士,主要从事宋明理学、江户思想史研究。
[责任编辑:黄文红]
标签:良知论文; 工夫论文; 道教论文; 思想论文; 本体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明代哲学(1368~1644年)论文;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资助项目:17ZDA013论文; 武汉大学国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