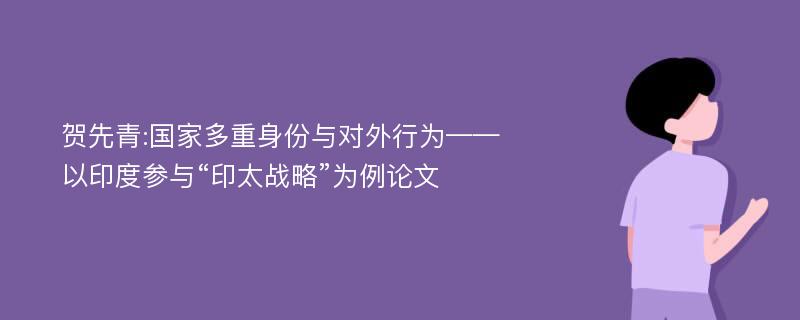
【内容提要】美国以“印太战略”来拉拢印度进而遏制中国的意图明显,而印度如何参与其中事关中国重要的利益关切。学界普遍认为印度存在积极参与、有限参与和保持平衡三种不同的对外行为方式,但他们忽视了印度对外行为的多重身份背景,这对预判印度的对外行为趋势造成了困难。鉴此,文章以“身份—行为”理论为基础,分析国家多重身份对其对外行为的影响。文章认为,国家通常根据其身份产生的驱动力施行对外行为,在多重身份背景下,国家对身份产生的行为驱动力进行排序并根据特定身份的使用场景选择主导的对外行为。印度参与“印太战略”时显示出了地区霸权国、新兴国家、民主国家的身份认知,这三种身份分别产生了追求大国地位、实现经济增长、维护民主认同的行为驱动力,印度的对外行为根据它对驱动力排序的变化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同时,在“印—美”或“印—中”关系的场景下,印度倾向于运用不同的身份来强调彼此合作的重要性,并利用中美相互制衡。
【关键词】国家身份认知;多重身份;印度外交;印度对外行为;印太战略
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印太战略”的建构基于中印同时崛起这一重要的地缘政治现实,美国利用印度遏制中国的意图十分明显。①叶海林:《“印太”概念的前景与中国的应对策略》,《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8年第2期;葛成、沈铭辉:《美印视角下的“印太战略”:政策限度及中国的应对》,《云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第 45-46 页;Sobia Harif and Muhammud, “U.S. Security Strategy for Asia Pacific and India’s Role,” Strategic Studies, Vol. 38, No.1, 2018, p.20; Balwinder Singh “India-China Relations: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in Indo-Pacific Reg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Studies,Vol. 25, Issue 2, 2018, pp.91-104; Sinderpal Singh, “The Indo-Pacific and India-U.S. Strategic Convergence: An Assessment,” Asia Policy,Vol. 26, No. 1, 2019, pp.77-94.因此,印度参与“印太战略”的方式、程度、范围等成为中国十分关心的问题。当前,学界认为在美国的主导下,印度参与“印太战略”的行为大致存在积极参与、②有学者认为印度参与“印太战略”存在一定的限度,但是他们认为印度对与美国互动保持了一种积极的态度,在中美印三边关系中,印度将继续加强与美国的关系,并明显向美国靠拢。参见叶海林:《“印太”概念的前景与中国的应对策略》,第7—8页;张洁:《美日澳印“四边对话”与亚太地区秩序重构》,《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5期,第62页;杨瑞、王世达:《印度与“印太战略”构想:介入、定位及局限》,《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1期;Sinderpal Singh, “The Indo-Pacific and India-US Strategic Convergence:An Assessment,” pp.77-94.有限参与、③部分学者认为,印度尽管参与了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但受制于内外因素,其参与的局限性十分明显,参与程度不深,范围有限。参见孟庆龙:《从美印关系看印太战略的前景》,《学术前沿》,2018年8月,第24—34页。葛成、沈铭辉:《美印视角下的“印太战略”:政策限度及中国的应对》,《云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第45—46页;王丽娜:《印度莫迪政府“印太战略”评估》,《当代亚太》,2018年第3期,第102-109页;Harsh V., Pant and Abhijnan Rej, “Is India Ready for the Indo-pacific?”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41, No. 2, 2018, pp.47-61.保持平衡④平衡说认为,印度参与“印太战略”并不一定在中美之间选边,而是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或采取“印太区域主义”的方式,加强与印太地区其它国家的互动,同时防范中美两国。参见[印]斯瓦兰·辛格:《在“印太”大辩论中定位中国:印度视角》,《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8年第3期,第29页;Balwinder Singh“India-China Relations: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in Indo-Pacific Region,” pp.91-104; Rohan Mukherjee,“Looking West, Acting East: India’s Indo-Pacific Strategy,”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No. 1, 2019, pp.44-45.三种方式。以上研究指出了印度参与“印太战略”的动机、限度甚至未来演变趋势,对于我们理解印度参与“印太战略”的行为具有重要参考意义。但以上分析视角基于不同的经验背景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这对我们预判印度的行为造成了困难。实际上,“行动在大部分时候和大部分情境中受背景性知识引导,背景性知识才是行动的主要驱动和基本逻辑”,⑤秦亚青:《行动的逻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知识转向”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第181-198页。而印度的国家身份就是这样一种背景性知识。
国家实施对外行为的过程,往往也是对“他者”身份的认知过程。这个过程包括确认其他行为体的身份并形成自我稳定的身份。换言之,国家的对外行为实际上界定了“自我”和“他者”的身份关系,①Lene Hansen, Security as Practice :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Bosnian War, London: Routledge,2006, p.6.这种身份关系反映了两国关系的状况。例如,在波斯尼亚战争中,西方国家建构了塞尔维亚“种族灭绝者”的身份,目的是为推行其军事干涉政策。②Andreas Behnke, “The Enemy Inside: The Western Involvement with Bosnia and the Problem of Securing Identities,” Alternatives: Global, Local, Political, Vol. 23, No. 3, 1998, pp.375-395.然而,现实中存在着多重身份塑造国家针对特定议题时的行为选择的问题。2018年6月,印度总理莫迪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了关于“印太战略”的演讲,他在其中建构了三组“自我—他者”的身份关系:一是印度相对于印度洋周边地区国家的领导者身份;二是印度与美国在“印太”乃至全球的朋友身份;三是中印之间合作者的身份。③莫迪在香格里拉对话的主旨演讲中论述了印度在印度洋地区的地位,主要是:印度洋对于印度的重要性以及印度在印度洋地区的领导性地位;基于民主价值观的美印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同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印之间合作的重要性。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of India, “Prime Minister’s Keynote Address at Shangri La Dialogue,” June 1, 2018, http://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29943/Prime_Minister s_Keynote_Address_at_Shangri_La_Dialogue_June_01_2018,访问日期:2018年7月15日。莫迪进一步指出,“印度不把‘印太’视为一个战略或是具有特定成员的俱乐部,‘印太’也不是一个寻求主导地位的集团,不视其为反对任何国家的某种地缘战略,印度对印太区域的看法是积极的、多元的。”④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of India, “Prime Minisrer’s Keynote Address at shangri La Dialogne,”Lune 1, 2018, http://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 htm? dtl/29943/Prime_Ministers_Keynote_Address_at_Shangri_La_Dialogue_June_01_2018,访问日期:2018年7月15日。莫迪既未否认“印太战略”存在的事实,也并不把“印太战略”视为一个排他性的地缘政治概念,似乎更愿采取一种平衡的外交行为。可以看出,国家身份这一背景性知识是影响国家对外行为的重要因素。本文拟以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身份理论为基础,针对既有研究的不足,搭建多重身份影响外交行为的分析框架,最后分析印度的多重身份和基于身份的行为驱动力对它参与“印太战略”的影响。
嘉琪对于自己的舞蹈,要求非常严格。每次要出去比赛或是要准备考试之前,嘉琪都会主动在写完作业后,对着母亲从废物回收站买回来的镜子跳上1个小时,每个周末,她还会去广州跟着老师学3个小时。即便有学业的压力,她也没有放弃过跳舞。
一、“身份—行为”关系:既有理论及不足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理论学界和外交政策研究领域掀起了身份研究的热潮,⑤Urrestarazu U.S., “‘Ident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Foreign Policy Theory,” in Hellmann G., Jørgensen K.E. eds, Theorizing Foreign Policy in a Globalized World, London: Palgrave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ries,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129.并形成了不同的分析路径。对于身份影响行为的问题,不同的分析路径尽管存在一定的分歧,但整体而言,它们基本忽视了多重身份如何影响国家的行为选择的问题。具体分析如下:
从图5可以看出,随着贮藏时间的延长,游离二氧化硫的含量持续降低,尤其是初期,下降速度很快,基本呈现线性下降。随着贮存时间延长,溶解氧逐渐将游离二氧化硫氧化消耗掉,同时结合态的二氧化硫逐渐分解形成游离态,使得游离二氧化硫呈现稳步降低。
建构主义路径。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是较早对身份进行研究的代表。他把身份与行为明确地联系起来,认为身份可以产生动机和行为特征,并借鉴哲学观念,把身份和利益当成意图和信念,两者共同作用产生行动(见图1)。温特认为,身份属于意图等式的信念部分,利益则是这个等式的意愿部分,利益概念中包含了身份的假定,而身份理论中包含了利益的假定。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对行动起作用。温特认为,“没有利益,身份就失去了动机力量。没有身份,利益就失去了方向”。①[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82页、第290—291页、第290页。
图1 温特建构主义中身份、利益和行为的关系
资料来源:[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5页、第290—291页。
第二,对身份使用的场景进行分析也可预判国家的对外行为。根据前述分析,国家在特定场景中,并不总是能够认识到它的多重身份,身份的建构根据不同的场景而具有不同的含义。①关于身份的多种建构路径,还可参见Alexandrov Maxym, “The Concept of State Ident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Journe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Vol.10, No.1, 2003, pp.34-36.进而言之,场景对身份的运用具有某种制约作用。②例如,印度参与美日澳印四方互动时,中国感到“印太战略”巨大的威胁,当习主席和莫迪在武汉会晤以及其她多边场合互动时,中印都倾向于强调彼此关系的友好,也淡化了印度参与“印太战略”对中国的影响。某种程度而言,国家对外政策关乎如何确立和处理与他国的关系,本国实力和身份乃是体现在与他国关系的基础之上。因此,对外政策需要制造出一个作为“自我”的本国身份和作为“他者”的别国身份。③刘永涛:《话语政治:符号权力和美国对外政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6页。国家所处的“自我—他者”的身份场景也预示着“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状况,这进一步暗含了国家行为选择的方向。温特从体系层次的角度,分析了三种无政府文化造就的国家间敌人、对手、朋友的身份关系。④[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13—383页。因此,把身份置放于国家对外政策的具体场景中,则可明确国家的对手、朋友、敌人是谁。
图2 身份的“价值—偏好”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Kuniko Ashizawa, “When Identity Matters: State Identity, Regional Institution-Building,and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10, No. 3, 2008, p. 579.
后实证主义分析路径。国际关系领域的后实证主义是一个庞大的理论阵营,①后实证主义的共同特点是:承认社会世界的人为建构,事实和价值不可能分离;主张对社会现实的理解而非解释;秉持反基要主义的认识论立场, 认为不存在客观中立的基础来对知识或真理进行评估。参见刘丰:《实证主义国际关系研究: 对内部与外部论争的评述》,《外交评论》2006年第5期,第99页。它们通常以语言或话语来界定真实,②刘慧:《超越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之争—批判实在论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7期,第44页。国际关系语言学转向以后,话语分析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应用越发广泛,话语成为分析身份与对外政策之间关系的重要媒介。③孙吉胜:《后结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视域下的身份与对外政策》,《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第10期,第115—126页。在话语分析中,国家身份由语言所建构,是“通过彼此叙述而产生的一种主体间认同,是社会语言建构的结果”。④孙吉胜:《语言、身份与国际秩序:后建构主义理论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5期,第26—36页。该路径最重要的启示是,身份总是显示出“自我”和“他者”的关系。
以上路径都承认身份对行为产生了影响,但它们的理论逻辑存在一定的混乱。温特的“身份—行为”解释路径具有开创性,他认为身份建构利益,利益决定行为。但该路径并未解决身份和利益在解释行为的混乱。从理论的逻辑性上来看,温特既运用反思主义的本体论作为理论基础,也运用理性主义认识论来搭建其理论框架,⑤秦亚青:《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温特及其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2—142页。进而导致在探寻行为的原因时,身份和利益都不能独自成为边界明确的变量。后实证主义试图弥合建构/理性的裂痕,即承认身份建构性含义的同时,以理性主义来构建理论框架。但有学者指出:“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者认为,利益、偏好与国家身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解释了国家的行为。但身份的概念在方法论上逐渐转向个人主义且因果关系化了,这阻碍了我们在复杂相互依赖的网络中理解行为者的身份定位以及这种身份如何持续发展”。①Bernd Bucher and Ursula Jasper, “Revisiting ‘Ident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Identity as Substance to Identifications in Ac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3, Issue 2, 2016,pp.391 - 415.“价值—偏好”的路径虽试图明确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但这以牺牲身份的多维度含义为代价。因果分析路径的困难在于,它需要概念的简化、可操作化以及可被测量。而身份作为被众多因素建构的概念,本身存在多重含义,对它进行简化和测量相对困难。②对概念测量的论述可参见:[美]格尔茨·马奥尼:《两种传承:社会科学中的定性与定量研究》,刘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50—153页。
1.金融结构通过技术创新影响产业升级的作用机制。张杰和刘志彪发现金融结构影响技术创新主要是通过影响实体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和高研发、高创新密度产业的金融资源配置来实现的,但是这种作用机制存在显著的阶段性和“门槛效应”。[10]Brown et al则通过分析欧洲高新企业R&D投入发现,金融市场主导的金融结构相对银行主导的金融结构在促进技术创新上更有优势。[11]
此外,以上分析路径忽略了多重身份对国家对外行为的影响。有学者指出,国家身份存在多种生成路径,③Alexandrov Maxym, “The Concept of State Ident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Vol. 10, No.1, 2003, pp.34-36.因此,国家在特定的对外决策中,不得不面临多重身份下如何行为的问题。温特虽然意识到了身份的多维度含义,④温特把国家身份分为团体身份、类属身份、角色身份、集体身份。具体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81—292页。但温特却简单地叙述为“除了第一种身份(团体身份),其他三种身份都可以同时在一个行为体上表现出多种形式”,⑤[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88页。并未分析这多重身份对行为产生的影响。有学者指出:“建构主义者没有解决国家如何在多重身份下做出选择的问题”。⑥Alexandrov Maxym, “The Concept of State Ident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Journe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Vol.10, No.1, 2003, pp.33-46.因果解释框架本身需要概念的高度简约,因此很难顾及身份概念的多重性。话语分析的实质是突出“话语”在分析国家行为中的核心作用,身份的多重含义被该分析框架单一化地处理了。后结构主义尽管声称“超越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建构/因果的二分法,这意味着它摒弃了一个确定性的、机械的因果关系”,⑦Urrestarazu U.S., “‘Ident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Foreign Policy Theory,” in Hellmann G., Jorgensen K.E. eds, Theorizing Foreign Policy in a Globalized World, Londen: Palgrave Studies in Internetional Relations Series, Palgrave Malmillan, 2015, p.142.然而,它并没有完全拒绝“原因”的概念而进行“构成性分析”,⑧Urrestarazu U.S., “‘Ident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Foreign Policy Theory,” in Hellmann G., Jorgensen K.E. eds, Theorizing Foreign Policy in a Globalized World, Londen: Palgrave Studies in Internetional Relations Series, Palgrave Malmillan, 2015, p.142.这难免落入因果分析的窠臼。
企业具体使用ERP的人员素质将直接决定ERP在企业会计财务管理当中应用的效果。但是,由于企业的很多财务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例如,企业的会计财务管理人员的观念比较传统,普遍没有接受过专业化的学习和培训,无法掌握最新的技术,对ERP在会计工作中的应用也不够重视,财务人员的综合素质不高这也是影响ERP的具体应用的重要因素,这就很有可能导致企业会计财务管理信息出现不及时、不完整或不真实的情况。
简言之,既有分析路径解释机制混乱,并忽视了国家存在的多重身份。鉴此,重视身份的建构性含义,准确描述身份到行为的发生过程,分析国家的多重身份认知,有助于准确预判多重身份下国家的对外行为。
最后,民主国家的身份。美国倡导的“印太战略”以寻求和具有相似价值观的民主国家合作为重要手段,而印度的民主国家身份恰好与美国形成了一种认同。印度的国家结构形式为西方式的联邦主义,政权组织形式大体沿袭了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建立的议会民主制。①孙士海、葛维钧主编:《印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40页、第142页。从意愿上看,印度一直以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而自居。在西方媒体和政治家的眼中,出于联合印度应对中国的需要,印度的“民主”常常被他们视为共同的价值观。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单独把“印太”作为一个区域专门论述,并表明“美国寻求与具有相似价值观的国家加强伙伴关系以促进自由市场经济、政治稳定与和平”,②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December 26,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 wp- content/ uploads/ 2017/12/NSS - Final-12-18-2017-0905-2.pdf,访问日期:2018年1月2日。而印度就是这样一个被美国认为拥有共同民主价值观的国家。印度的民主国家身份给印度带来了极大的自尊心的满足和集体认同感。例如,特朗普政府提出“印太战略”后,《印度斯坦时报》发表评论称:“民主力量必须联合起来免遭中国霸权的威胁。”③“Democratic Forces must Join Hands to Protect Indo-Pacific from China’s Hegemony,” The Hindustan Times, November 17,2017, https://www.hindustantimes.com/opinion/democratic-forces-mustjoin-hands-to-protect -indo-pacific-from-china-s-hegemony/story-3Juy5BnDIoaR2cApIy8IQI.html,访问日期:2019年2月26日。
二、身份认知与行为选择
“身份—行为”的三种分析路径或直接忽视了身份的多重内涵,或对多重身份影响国家对外行为的具体机制语焉不详。针对这些不足,本文分析身份到行为的发生过程,重点解决两个问题:身份如何影响行为?复杂身份背景下国家施行何种对外行为?
(一)身份、驱动力与行为
身份和特定行为并非具有必然联系,身份往往只是行为选择的必要非充分条件。但不可否认,身份影响对外行为已经成为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共识。因此,要描述身份到行为的发生过程,需要理解其中的驱动性因素。总体而言,身份影响行为的驱动性因素并不单一,大概包括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的驱动。本文把这两种驱动性因素概括为利益驱动和价值驱动。
优质护理注重在术前、术中、术后、出院后做好各项手术准备,规范手术操作,科学管理,预防不良事件的发生。术前将护理方案的确定建立在明确的病情评估基础上,且兼顾患者身心状况,努力让患者身心处于最佳状态。术中规范管理及配合,保证手术质量[6]。术后保证无菌换药、加强生活管理,以促进康复,降低并发症发生风险。出院后,继续为患者提供所需的护理服务,以保证护理的延续性,巩固护理质量,优化预后。在优质护理作用下,患者获得愉悦的医疗服务,手术质量提升,手术时间短,视力恢复好,并发症发生率低,患者的满意度高。
尽管利益作为对外行为的原因受到了批评,①主要有两种批评观点,一是认为,“利益概念受到欢迎不是因为它对权力进行了分析而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利益可以成为使用者希望成为的那种概念,”同时,“利益还因其符合常识的吸引力而受到欢迎但并非因其解释力。”二是认为,“利益概念被过分简化且是一种被错误运用的教条式概念,它只是出于平衡国内政治过程的需要而被运用于对外政策和国家行为之中。”Jutta Weldes, “Constructing National Interest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 Issue 3, 1996, pp. 275-276.但几乎所有国际政治学者都不会否认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利益依然是解释国家行为的一种语言,在外交政策的确立过程中,决定外交政策的国内语言实际上就是关于国家利益的语言,②See Jutta Weldes, “Constructing National Interest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 2, Issue 3, 1996, pp.275-276.因此用利益概念来描述国家行为的驱动力是合适的。价值是国家行为的另一驱动力。尽管国家利益对外交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但政策制定者也并未忽视基本的道德问题,③Evans Gareth, “Values and Interests in Foreign Policy Making,” Simons Papers in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No. 53, School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Vancouver, October 2016,p.5, http://www. gevans.org/opeds/SimonsWorkingPaper53ValuesInterests.pdf,访问日期:2019年3月2日。“有时政府不能利用传统的国家安全利益等概念恰切地解释它所做的承诺,那它便运用国际法律义务或更常用的价值观问题来解释这些承诺”。④Evans Gareth, “Values and Interests in Foreign Policy Making,” Simons Papers in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No. 53, School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Vancouver, October 2016,p.5, http://www. gevans.org/opeds/SimonsWorkingPaper53ValuesInterests.pdf,访问日期:2019年3月2日。有学者指出,价值对美国外交政策的驱动是明显的,尽管什么是“美国价值”存在不确定性,但这些价值已经或者应该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①Nathan Glazer, “American Value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ommentary, July 1,1976, https://www.commentarymagazine.com/articles/american-values-american-foreign-policy/,访问日期:2019年1月5日。更有美国学者直言,“如果美国外交政策没有价值观的指引,将缩小美国的利益和权力,并将牺牲一些原则和民众的利益。”②Gary Grappo, “America’s Values Should Guide its Foreign Policy,” May 23, 2017, https://www.fairobserver.com/region/north_america/rex-tillerson-us-foreign-policy-news-44139/,访问日期:2019年1月5日。
实际上,“价值是利益的反映,没有利益作为基础的价值是不存在的。价值是利益的长远判断,利益上升为精神状态就变为价值,价值的深层次却依然是物质的。”③黄仁伟:《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利益和价值重构》,《国际观察》2013年第6期,第5页。可见,价值和利益是联结起来的,利益是物质层面,价值是精神层面。进一步地,对价值的判断也需要放到行为者对利益的考量之中。美国学者在评论特朗普政府2017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时指出:“在敌手挑战美国领导地位的时代,美国对普世价值的支持,能够也应该成为美国战略的一部分,这个战略能够增强美国影响力,并能使得我们能够维持人民及其利益的安全,”“我们应该记住,美国的强大不仅仅因为美国拥有核武器,更在于我们的价值系统比我们的敌人更有吸引力。”④Daniel Twining, “Does Trump’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Have a Values Deficit?” Foreign Policy,December 18, 2017,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7/12/18/trump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has-a-valuesdeficit/访问日期:2019年1月6日。总之,利益和价值作为行为的两大驱动性因素,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分别代表了行为背后的物质驱动和精神驱动,这两者往往相互交织而影响国家行为。因此把利益和价值整合到身份影响外交行为的过程具有重要的分析意义,据此,笔者提出如下分析框架:
图3 本文分析框架⑤本文重在描述身份对行为的影响过程,因此用虚线箭头表示影响的方向。而价值与利益有时对行为共同起作用,因此,用实线双箭头表示两者之间相互影响以及联结关系。
(二)多重身份认知
在利益和价值的驱动之下,身份能够影响行为。但国家身份往往具有多重性,这迫切需要对身份的多重性认知进行分析。
国家并不总是能够或者并不总是愿意同时认知到它的多重身份。例如,与中国互动时,印度倾向于显示它作为新兴崛起国家的身份,而对其地区霸权国、民主国家的身份避而不谈。同样,印度在与美国、日本等国家互动时倾向于显示它作为民主国家的身份,而忽视它新兴国家的身份。①笔者分析了自美国提出“印太战略”以来,印度与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互动时签署的联合声明、公报以及印度领导人出访时发表的演讲等,结果显示,印度与每个国家互动时所强调的身份并不一致。在以东盟为中心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莫迪的演讲则显示了印度的三重国家身份。由此表明,国家针对同一外交议题,根据不同的对象或场景,利用了它不同的身份。通过身份认知的分析,可理解国家在对外行为中到底是何种身份(见图4)。
图4 复杂身份的认知过程
(三)驱动力排序与场景分析
国家身份的认知过程表明身份具有多重性,这些多重身份建构了众多的利益和价值取向,因此在多重身份视域下,国家不得不恰当地处理利益、价值的排序问题,以便国家在某一外交议题上采取合适的行为。此外,多重身份的认知过程也表明,国家对身份的运用需要区分特定的场景。
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发展,按照都市型农业定位,加快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培育壮大水产、畜牧、蔬菜、林果四大支柱产业;加速推进农民创业就业。完善创业带动就业的政策措施,探索建立农民创业担保体系,扶持农民创业就业。加强鄂州农业的基础地位,发展优质高产高效的科技农业和特色农业,推进农业产业化,以市场为导向,发展具有竞争优势的农副产品,提高农民收入,采用现代手段,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农业等,提高农业市场占有份额,提高农民收入。
第一,对利益和价值进行排序是分析国家对外行为的有效方法之一。但是,如何对利益或价值进行排序则出现了不同的方法。有学者认为,“理性与国家利益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理性的外交政策就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国家利益,”这意味着“寻求可能条件下利益的最大化,并选择合适的实现途径。”②宋伟:《国家利益的界定与外交政策理论的建构》,《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8期,第23页。但同样以理性为先验假定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却对利益进行了截然不同的排序,现实主义者认为追求权力、安全、生存是国家最重要的利益和目标,而自由主义者认为经济财富才是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也有学者提出客观利益和主观利益的概念,并认为客观利益总是比主观利益更加重要,因为“主观利益建立在客观利益之上”。①邢悦:《国家利益的客观性与主观性》,《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第29—33页。这种排序旨在弥合理性与非理性的裂缝,但是主观利益或客观利益内部该如何排序,研究者并未给出确定的答案。
总之,对利益或价值排序一般有两种方法,一是依据理性选择排序;二是弥合理性与非理性的裂缝,对某些利益进行理性排序,对某些利益进行主观认知的排序。②阎学通教授依据国际环境、自身实力、科技水平和主观认识水平四个维度的排序方式。虽然国家利益本身的重要性是有固定排序的,民族生存是第一位的,接下来是政治承认、经济收益、主导地位和世界贡献等,但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对于具体国家而言,这些利益的重要性、紧迫性是变动的,或者说是有排序的。参见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5—54页。实际上,身份在国家对外关系的场景中是被认知的过程,它被决策者认知并产生出特定的行为驱动力。实践中,即使同一外交政策的形成过程,国家也可能面临多重身份。要对国家对外行为选择进行准确预判,需要考察决策者如何对行为背后的驱动力因素进行排序。鉴于理性排序的缺陷,本文只论述排序的可能性,而国家往往也根据这些排序结果做出行为选择。为描述身份到行为的过程,笔者用字母D代表驱动力。在多重身份背景之下,国家往往对驱动力D进行衡量,并最终产生特定的行为倾向(见表1)。
表1 复杂身份、驱动力与行为选择
资料来源:根据身份认知过程,笔者自制。
身份认知 驱动力 行为倾向三种身份 D1、D2、D3若D1>D2>D3,则D1决定国家主导行为若D2>D1>D3,则D2决定国家主导行为若D3>D1>D2,则D3决定国家主导行为若D2=D1=D3,则国家将采取平衡的外交行为若D1>D2,则D1决定国家主导行为,D2决定国家次要行为若D2>D1,则D2决定国家主导行为,D1决定国家次要行为若D2=D1,则国家采取平衡的外交行为一种身份 D 则D决定国家行为无法认知身份 0 身份和行为关系不明确,外交行为变得不可预测两种身份 D1、D2
因果解释路径。该路径得益于实证主义者所倡导的“科学性”研究方法,在具体的研究设计上,“要求具有明确的经验问题,就此提出相应的理论假设,对其中的核心变量进行操作化,利用经验证据进行假设检验等”。②刘丰:《实证主义国际关系研究: 对内部与外部论争的评述》,《外交评论》2006年第5期,第97页。“价值—偏好”的分析路径即是其中之一。该路径认为国家身份可以产生一种特殊的价值,并决定国家的对外政策偏好,而国家将采取行为来满足这一偏好。该分析框架承认身份对行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认为“身份—利益—行为”分析模式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为“利益是一个不稳定且空洞的概念”或者说“利益概念被滥用了”。③Kuniko Ashizawa, “When Identity Matters: State Identity, Regional Institution-Building, and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0, No. 3, 2008, p.577.因此,此路径用偏好来代替利益,偏好成为身份与行为之间的中介变量。该分析框架存在两种关系,一种是因果关系,一种是目的性关系,前者被用来解释价值与偏好的因果关系,后者被用来解释偏好与对外政策行为之间的目的性关系(见图2)。
衣柜里堆成山的毛衣,究竟哪件才最适合自己呢?今天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一些毛衣穿搭攻略,快来根据自己的身形对号入座吧。
印度的多重身份植根于其国家的知识背景。在“印太战略”的背景下,印度体现出三种国家身份。首先,地区霸权国的身份。从地缘上看,“印太战略”涵盖印度视为禁脔的印度洋,印度通常以印度洋地区的领导性国家自居。从国家实力而言,印度的政治影响力、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在南亚甚至印度洋国家中都拥有绝对的主导权。从意愿来看,印度有意追求印度洋地区的领导地位。印度曾经是英国印度洋帝国的枢纽,①[澳]大卫·布鲁斯特:《印度之洋:印度谋求地区领导权的真相》,杜幼康、毛悦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页。根据这一定位,英印政府在思想上和实践上都把印度当做区域绝对的中心。印度独立以后,尼赫鲁的“有声有色的大国”②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强调:“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打动我,我也不相信中间地位是可能的。”参见[印]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度的发现》,齐文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第57页。思想贯穿在印度的外交实践中,不结盟运动是印度独立后追求大国地位的重要行为选择之一。赵干成认为,“尼赫鲁极力倡导独立外交和不结盟政策,是为了摆脱其它强权控制印度的危险,但这并不表示印度不想控制其他弱小国家”。③赵干成:《印度:大国地位与大国外交》,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8页。换言之,对印度而言,不结盟政策不仅可以摆脱两大阵营的冷战陷阱,防止大国插手其周边事务,还可实现其地区霸权目标。冷战结束以后,印度面临的地缘环境发生了变化,印度认为,其本身的强大实力使其不得不做区域霸权国。④Madhavi, Bhasin “India’s Role in South Asia-Perceived Hegemony or Reluctant Leadership?”,Indian Foreign Affairs Journal, 2008, pp.1-25.实际上,印度精英或多或少地认为,印度有成为大国的“天命”,第一步便是使印度洋成为印度之洋。⑤[澳]大卫·布鲁斯特:《印度之洋:印度谋求地区领导权的真相》,杜幼康、毛悦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77页。2012年,印度智库政策研究中心(CPR)发布的《不结盟2.0》报告认为,印度应该保持战略自主(strategic autonomy)的外交政策,以便印度能够从多元的伙伴关系和经济机遇中促进国内发展,这也将促进印度大国地位的提升。⑥“Non-Alignment 2.0: A Foreign and Strategic Policy for India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CPR India, February 29, 2012, http://www.cprindia.org/research/reports/nonalignment-20-foreign-and-strategicpolicy -india-twenty-first-century,访问日期:2019年1月10日。因此,印度的大国梦想根深蒂固,这在冷战后印度洋的地缘政治图景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即任何大国进入印度洋都可能被印度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
三、印度参与“印太战略”的行为选择分析
(1)加封:集装箱出场站之前,在集装箱门上加一把电子铅封,封住集装箱门。具体过程如下:挑选一把电子铅封;将集装箱号、运载车辆号码、起点海关、终点海关输入场站计算机;将电子铅封放在加封器上;场站计算机通过加封器读出电子铅封ID号;场站计算机将集装箱号和电子铅封号传到监控中心;监控中心按加密程序返回密码;场站计算机通过加封器将密码、集装箱号码、起点、终点海关等信息写入电子铅封;用电子铅封封住集装箱门。
(一)印度的三重身份认知
综上,身份通过其产生的利益、价值等驱动性因素对国家行为产生影响。但是国家身份具有多重性,决策者对多重身份的认知过程意味着国家身份的建构与表达都具有场景特征。这造成的结果是,国家须对身份产生的行为驱动性因素进行排序,从而选择它要采取的主导行为,同时,国家也须根据场景选择利用合适身份,进而显示出自我与他者的身份关系。
其次,新兴国家的身份。新兴国家的身份是印度的主要身份认知之一,这使它和中国形成了相对友好的认同。新兴国家是一个概念模糊的定义,与之相似的还有:新兴市场、新兴经济体、新兴大国、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等。①关于新兴国家相关概念的辨析,可参见周鑫宇:《“新兴国家”研究相关概念辨析及理论启示》,《国际论坛》2013年第2期;唐辉、程又中:《新兴国家:概念演变及未来展望》,《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5年第4期。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从经济的角度使用这些词汇,他们偏重于使用新兴市场、新兴经济体、新兴工业化国家等概念。例如,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新兴国家一词在20世纪90年代初首次被提出以来,“通常是指中低收入人群,这些国家已经实施了经济发展和改革计划,并且已经开始在全球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②Richard Rousseau, “What is Meant by Emerging Countries?” April 8, 2015, https://www.diplomaticouri er.com/what-is-meant -by-emerging-countries/,访问日期:2019年2月5日。但在国际政治的实践中,新兴国家这个概念不止拥有经济含义,还是“新的时代特征下冲击国际格局体系的力量”。③唐辉、程又中:《新兴国家:概念演变及未来展望》,《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5年第4期,第36页。有学者从经济、政治、历史三个维度定义了新兴国家,认为新兴国家在经济上以快于发达国家的速度持续、稳定地增长,且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地,经济增长带动了政治权力和政治影响力的增长。此外,还应该把新兴国家置于以西方为中心的格局中进行把握。④周鑫宇:《“新兴国家”研究相关概念辨析及理论启示》,《国际论坛》2013年第2期,第69页。通过对这些维度的分析和考察,印度都属于最核心的新兴国家之一。⑤周鑫宇:《“新兴国家”研究相关概念辨析及理论启示》,《国际论坛》2013年第2期,第69页。
而上面的分析也提到过,有些时候,在现代汉语“让”字句中,动作者有时被省略。此时虽然含义上没有什么变化且在英语小句中不是很常见,但是在现代汉语的小句中还是较为常见的。例如:
印度新兴国家的身份定位是恰当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印度经济保持持续增长,根据中央统计组织(CSO)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印度已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主要经济体,预计未来10—15年将成为世界三大经济大国之一。⑥“About Indian Economy Growth Rate & Statistics”, https://www.ibef.org/economy/indian-economyoverview,访问日期:2019年1月10日。然而,尽管印度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依然面临着如何实现持续稳定发展的问题。印度学者普纳姆(Snigdha Poonam)在其2018年的新书《梦想家:印度青年人该怎样改变他们的世界》中提出,21世纪印度是否可以如普遍预测的那样的崛起,将取决于怎样解决城镇化过程中人口的教育问题以及庞大人口数量的就业问题,但是,从现实来看,印度民主法治的低效、基础设施的薄弱,都将使得这个问题的解决变得困难,巨大的人口红利或将变成灾难性的人口负担,最终结果是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⑦Milan Vaishnav, “An Indian Nightmare: Is New Delhi Read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Foreign Affairs, March 1, 2018.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reviews/review-essay/2018-03-01/indiannightmare.访问日期:2019年2月5日。关于印度的以上分析都显示了它作为新兴国家的主要特征。
多重身份及其使用场景预示了国家行为选择的倾向。印度参与“印太战略”的实质是它如何同时处理与中美两国关系的问题。印度与中、美互动所分别建构的“自我—他者”身份,产生了不同的利益和价值驱动力,对这些驱动力进行排序可预判印度的对外行为倾向。
综上所述,医院应认识到糖尿病患者健康教育的重要性,不断加强糖尿病患者健康教育管理力度,提高患者健康知识知晓率,改善患者治疗依从性,最终提高其治疗效果。
(二)印度国家身份产生的驱动力
印度参与“印太战略”的行为选择和其多重身份有关。从印度地区霸权国的身份来看,印度最主要的战略利益是维护其在印度洋地区的主导地位,同时扩大在“印太”乃至全球地区的影响力。印度新兴国家的身份则决定了它追求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并谋求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民主国家的身份决定了印度的价值认同和集体认同。
第一,为实现战略利益,印度的行为倾向是防止其它国家成为其追求地区霸权国的威胁。冷战期间,印度表现出“亲苏离美”倾向,因为印度担心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将损害印度主导南亚次大陆的能力。另外,印度认为,美国在印度洋的军事存在是持续的威胁。④[澳]大卫·布鲁斯特:《印度之洋:印度谋求地区领导权的真相》,杜幼康、毛悦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232页。苏联解体后,在印度洋乃至印度—太平洋区域,中、美、印的三角地缘博弈开始引起关注。美国学者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 Kaplan)曾预言,印度洋将是21世纪的中心舞台,同作为崛起性的大国——中国和印度的竞争或许更引人注目。①Robert D. Kaplan, “Center Stage for the 21st Century,” Foreign Affairs,March 1, 2009, https://www.foreign affairs.com /articles / east-asia/2009-03-01/center-stage-21st-century,访问日期:2019年2月26日。实际上,印太地区的战略形势远比卡普兰所预测的更为复杂,印太地区的地缘战略博弈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中美在印太地区的海上竞争;二是印度对中国海上意图的战略警觉;三是美印两国有限的海上安全合作。②季澄、宋德星:《印太视域下的中、美、印海上地缘博弈——表象与实质》,《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7年第5期,第32—47页。可见,印度的印太地缘战略中既有对中国疑虑的一面,也有对与美国加强安全合作保持谨慎的一面。有印度学者指出,在中美之间,“印度更倾向于采取一种平衡战略”。③[印]贾瓦哈拉尔:《印度—美国—中国的战略平衡:时代的呼唤》,《美国问题研究》2015年第1期。
值得警惕的是,美、日等国家企图给中印关系制造障碍。美国奥巴马政府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目的是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存在感并进而遏制中国,在与印度的互动中,也有明显拉拢印度的意图。特朗普上任以来,改亚太为印太,并直接表明欲把美日澳三边关系升级为美日澳印四方关系,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表示将加强与印度的关系,共同应付印太地区威胁,④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December 26,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wp- content/uploads/ 2017/12/NSS - Final-12-18-2017-0905-2.pdf,访问日期:2018年1月2日。并试图与印日澳联合提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剑指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⑤Harsh V. Pant, “Cornered by the Quad?” The Hindu, February 28 ,2018, https://www.thehindu.com/opinion /op-ed/cornered-by-the-quad/article22870625.ece,访问日期:2019年3月2日。印度地区霸权国身份的建构历程表明,这种身份所指向的“他者”并非一个固定不变的国家,而是根据其它国家对这种身份的威胁程度而做出的灵活判断。
第二,印度新兴国家的身份决定了印度的利益是实现快速、稳定、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莫迪能够在国大党长期执政的政治环境中当选总理,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莫迪在长期执政古吉拉特邦时采用的经济发展模式为印度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模板。莫迪上台以后,强力推动国内经济改革,相继提出“印度制造”“数字印度”等战略,推动印度朝制造业大国的方向发展。莫迪当选以来的一系列经济改革形成了以“发展”为导向的经济模式。⑥陈金英:《莫迪执政以来印度的政治经济改革》,《国际观察》2016年第2期,第113—119页。究其原因,作为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印度需要通过快速稳定的经济增长解决国内贫困和就业问题。
此外,作为新兴国家的印度,对经济增长的国际环境也保持了关注。莫迪总理2018年出席达沃斯经济论坛时发表演讲称,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遭遇三大挑战:气候变化、恐怖主义以及许多社会和国家正变得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莫迪进一步指出:“联合国、世贸组织等旧的制度体系和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在当今世界秩序下出现了巨大的鸿沟”,“全球化面临重大挫折,最典型的就是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①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of India,“Creating a Shared Future in a Fractured World,” January 23, 2018, http://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29378/Prime_Ministers_Statement_on_the_subject_Creating_a_Shared_Future_in_a_Fractured_Word_in_the_ World_Economic_Forum_January_23_2018,访问日期:2019年3月2日。所以,作为新兴国家的印度,一方面注重经济增长等发展方面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注重当前国际秩序的重构。
第三,民主国家的身份决定了印度外交行为的驱动力是国家自尊心的满足。实际上,印度民主国家的身份并不稳定,属于西方殖民政权输入的文化舶来品,并不深植于印度国家传统,因为“印度丝毫不符合‘稳定民主结构’的前提:它过去非常贫困,从某种角度看,现在依然如此,在宗教、种族、语言、阶级等方面,它又是高度分裂的,它在公众狂乱的暴力中诞生,随着不同小团体的相互争斗,公众暴力又会定期重现。”②[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 :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82页。尽管如此,印度通常以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自诩,因为民主国家的身份让印度国家自尊心得到了极大满足。正如2018年初莫迪在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中宣称:“民主、人口及其活力共同促进了印度的发展,塑造了印度的命运。”③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of India, “Prime Minister’s Keynote Address at Shangri La Dialogue,”June 1, 2018, http://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29943/Prime_Ministers_Keynote_Address_at_Shangri_La_Dialogue_June_01_2018,访问日期:2018年7月15日。莫迪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也指出了民主对于印度的意义:“将我们定义为一个国家的民主理想,也塑造了我们参与世界的方式。”④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of India, “Creating a Shared Future in a Fractured World,” January 23, 2018, http://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29378/Prime_Ministers_Statement_on_the_subject_Creating_a_Shared_Future_in_a_Fractured_Word_in_the_ World_Economic_Forum_January_23_2018,访问日期:2019年3月2日。民主国家的身份使印度具有和西方国家高度的集体认同感和价值认同感,这使得印度在对外行为中可能以价值观的大棒对其他“非民主国家”进行指责。
表2 印度参与“印太战略”的身份、驱动力与行为倾向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身份 驱动力 行为倾向地区霸权国 实现并维护大国地位 追求区域内的主导地位;排斥其它大国在区域内的影响力。新兴国家 促进经济增长 积极发展经济;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营造有利于己的发展环境。加强与具有相似价值观的国家互动,并对其他意识形态价值观国家进行指责(例如,指责南海地区的军事化危及自由开放的秩序等)。民主国家 集体认同、价值认同
(三)印度的行为选择
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把中国视为威胁性的他者,而印度参与“印太战略”的方式、程度与范围预示了中美印三边关系的演进趋势。印度地区霸权国、新兴国家、民主国家这三重身份是它处理与中、美关系的依据。
印度参与“印太战略”的主导行为将根据它对三种驱动力的排序而产生。特朗普政府提出“印太战略”以来,印度的参与行为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原因是印度对行为驱动力的排序发生变化。因2017年的洞朗对峙事件,印度一度把中国视为其追求地区主导权的最大“威胁者”,因此,美日澳印四方互动频繁。中印领导人武汉会晤以来,两国领导人通过坦诚的交流培植了双方互信,随后在上合组织青岛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约翰内斯堡峰会上进一步加深了印度对中国“良性意图”的判断,印度参与“印太战略”的意愿和强度有所减弱。直至莫迪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演讲中采取了一种平衡中美的姿态来看待“印太战略”。在武汉会晤前,印度认为,实现地区主导权的主要威胁是中国,因此它加入“民主国家俱乐部”,宣称中国在南海地区的行为是“威胁”,并对“一带一路”表示出负面态度。武汉会晤后,两国关系明显转暖,中国“威胁”的程度减弱,加之特朗普政府大打贸易战,不断恶化与伊朗的关系,印度对自身的经济增长、石油进口产生担忧,因此,印度对经济利益方面的关切上升,降低以“民主”标准污蔑中国的调门。
印度参与“印太战略”的行为还与印度所处的外交场景有关。如前所述,印度在与中国的互动中,它倾向于显示新兴崛起国家的身份,基本忽略其地区霸权国、民主国家的身份。同样,印度在与美国、日本等国家互动时倾向于显示它作为民主国家的身份,而忽视它新兴国家和地区霸权国的身份。印度知道如何利用恰当的身份传递出对特定利益的关切,进而采取特定的行为。在印美关系的场景下,印度积极参与了“美日澳印”的四方互动,在政治上、舆论上一度出现了对“印太战略”的积极态度。例如:自美国提出“印太战略”以来,印度积极参与瑞辛纳对话会构建四方关系。《印度斯坦时报》也曾发表评论认为:“民主力量必须联合起来免遭中国霸权的威胁。”①“Democratic Forces Must Join Hands to Protect Indo-Pacific from China’s Hegemony,” TheHindustan Times, November 17, 2017, https://www.hindustantimes.com/opinion/democratic-forces-mustjoin-hands-to-prot ect-indo-pacific-from-china-s-hegemony/story-3Juy5BnDIoaR2cApIy8IQI.html,访问日期:2018年2月1日。也有印度学者指出,“中国正通过‘一带一路’计划扩大在印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影响力,为了防止不利于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情况发生,各国必须联合起来形成一种全新的区域性包容框架,”因此,加强印美关系,塑造一种政治叙事来“对抗诸如‘一带一路’这样的给各国债务和环境带来负担的双边计划”非常重要。②Abhijit Singh, “The New India-U.S. Partnership in the Indo-Pacific: Peace, Prosperity and Security,”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ORF), January 19, 2018.有学者指出,在中印实力存在差距且印度把中国视为主要威胁的背景下,印度在体系之内扮演着“摇摆国家”的角色,以左右逢源的态度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达到对中国的软制衡目的,加强与美国的关系成为对中国的进行软制衡的手段之一。③胡娟:《印度对中国的‘软制衡’战略:动因、表现与局限》,《南亚研究》2018年第3期,第21—24页、第28页、第29页。
实际上,在中印关系的场景下,印度“摇摆国家”的角色也有制衡美国的一面。习近平主席与莫迪总理在武汉非正式会晤以后,印度在发表的新闻公报中说:“在当前全球不确定的情况下,印度与中国之间的和平、稳定和平衡的关系将成为稳定的积极因素,妥善管理双边关系将有利于该地区的发展和繁荣,并将为亚洲世纪创造条件。为此,他们决定以互利和可持续的方式加强更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以实现国家现代化和人民的更大繁荣。”④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of India, “India-China Informal Summit at Wuhan,” April 28, 2018,https://ww w.mea.gov.in/press-releases.htm?dtl/29853/IndiaChina_Informal_Summit_at_Wuhan,访问日期:2019年3月2日。《印度时报》报道称,“武汉峰会的目的是让两位领导人进行‘坦诚的沟通’,在未来的关系中达成谅解,通过淡化分歧,建立彼此之间的战略信任。”⑤“Modi-Xi to Chart a New Course for India-China Ties at Wuhan Summit,” Times of India, April 22,2018,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modi-xi-to-chart-a-new-course-for-india-china-ties-at-wuhansummit/articleshow/63868875.cms,访问日期:2019年3月2日。有学者指出,“印度试图重启中印关系,自然能够理解中国对‘印太战略’的关注,”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不仅冲击中美经贸关系,也限制着“印度制造”的前景,这增强了中印改善关系、加强合作的动力。①林民旺:《理顺中印关系,“印太战略”不攻自破》,《世界知识》2018年第10期,第74页。在中印领导人会晤当中,双方都表示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反对保护主义,强调坚持推进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
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具有明显的遏制中国的意图,印度如何参与其中是中国比较关心的问题。学者们指出了印度参与“印太战略”的程度、方式和演变趋势,但是他们却忽视了国家身份这一背景性知识对行为的影响。实际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表明,身份对国家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身份—行为”的既有分析路径都忽视了多重身份对国家行为的影响。针对既有理论的不足,本文解释了身份到行为的发生过程并分析了多重身份如何影响国家的对外行为。文章认为,国家往往根据身份所产生的驱动力而实行对外行为,在国家对多重身份认知的背景下,国家会对身份产生的行为驱动力进行排序并根据具体身份的使用场景选择主导行为。本文分析了印度参与“印太战略”的身份认知、驱动力以及行为选择。研究发现,印度参与“印太战略”的行为会随着它对驱动力排序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同时,在印美关系场景下,印度参与“印太战略”虽有制衡中国的意图,但是在多边场合下,印度倾向于强调“印太战略”的包容性,淡化遏制中国的意图,在中印关系的场景下,印度则强调中印友好的重要性。可见,在不同的场景中,印度利用不同的身份认同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笔者认为,印度的多重身份是既定的,但是对多重身份产生的利益/价值的排序是变化的,同时场景对印度国家身份的使用形成了限制。因此,管控中印分歧,防止边界争端影响双边关系的大局,有利于印度在追求地区领导权过程中淡化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的认知,这有助于改变印度对利益和价值的排序方式,进而改变它参与“印太战略”的行为选择。此外,加强两国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沟通、采取措施减少双边贸易逆差,也有助于加强两国在多边场合的身份认同,淡化彼此矛盾,进而削弱“印太战略”对中国的冲击。
【作者简介】 贺先青,中国南海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林勇新,中国南海研究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所所长。(海口 邮编:571100)
【DOI】10.13549/j.cnki.cn11-3959/d.2019.04.009
【中图分类号】D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55(2019)04-136-19
* 本文系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南海问题交互影响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7CGJ02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余文全博士对文章初稿提出的修改建议。此外,《国际论坛》编辑和匿名审稿专家对文章的修改也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在此一并致谢。文中错漏,由笔者自负。
【收稿日期:2019-04-12】
【责任编辑:何宗强】
标签:印度论文; 身份论文; 国家论文; 利益论文; 战略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世界政治概况论文; 《国际论坛》2019年第4期论文; 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南海问题交互影响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7CGJ02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论文; 中国南海研究院论文; 中国南海研究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