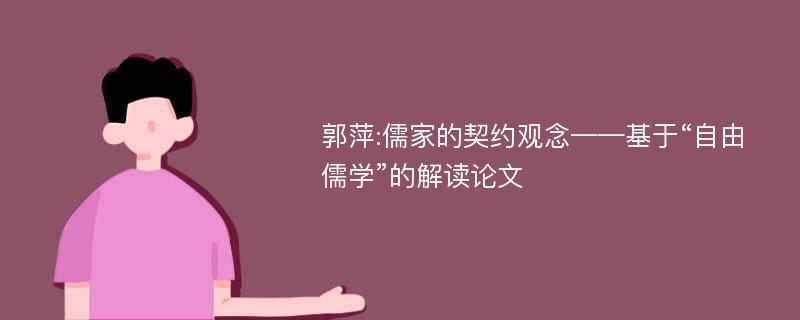
摘要:现代契约观念与现代自由的发展密切相关,因此儒家需要在回应现代自由问题过程中,对契约观念作出相应的阐释。根据汉语“契约”一词的基本涵义,可以表明儒家的契约观念具有自愿协议、责权对等的一般特质。对此,从政治哲学的层面看,契约观念作为证成自由的工具性观念,是为现实地维护社会主体的价值。“自由儒学”认为,这种关系不仅存在于西方社会,而且也贯穿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同时契约观念与自由观念一样,总是随着社会主体的转变而转变;不过,儒家契约观念始终保持着契约的一般特质,这是因为其背后依据着“诚—义—知—信”的儒学原理,揭示这一原理可以从学理上启发儒家现代契约理论的发展。
关键词:儒学原理;契约;自由儒学;自由
如果考察现代自由发展的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现代契约观念与现代自由的发展密切相关。事实上在西方,现代契约观念,包括各种契约理论,本身就是现代自由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儒家在发展现代自由的过程中,尚未对契约与自由的关系以及现代契约观念背后的哲学原理等不可回避的问题作出必要的理论回应。为此,笔者尝试基于“自由儒学”注“自由儒学”是笔者提出的一种当代儒家哲学理论构想,相关论著可参阅郭萍《自由儒学的先声》(济南:齐鲁书社,2017年),《“自由儒学”导论——面对自由问题本身的儒家哲学建构》(《孔子研究》2018年第1期)、《“自由儒学”纲要——现代自由诉求的儒家表达》(《兰州学刊》2017年第7期)、《自由何以可能——从“生活儒学”到“自由儒学”》(《齐鲁学刊》2017年第4期)、《儒家的自由观念及其人性论基础》(《国际儒学论丛》第2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年12月)等。的视角对这一问题作出一种儒学的阐释。
一、儒家语境中“契约”概念的一般涵义和基本特质
人们往往不假思索地将契约视为一个现代的、西方的概念,但诸多存世文献、儒家典籍以及相关研究成果都早已证明儒家语境下的“契约”概念既不是一个西方的舶来品,也不是一个现代社会的新名词,而是儒家自身古已有之的概念。
据此事实,我们可以作两点推断:第一,“契约”作为一个古已有之的儒家概念至今还在使用,这表明由古至今的“契约”概念都没有脱离“契”“约”二字的基本涵义。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考察汉语“契约”一词的涵义来窥探儒家“契约”概念的一般涵义和基本特质。第二,我们以汉语的“契约”与英文的“contract”对译,实际表明二者的基本内涵虽然不尽等同,但是一定有很大程度的对应性。因此,儒家“契约”概念的一般涵义和基本特质也能体现古今中西“契约”概念的根本共同性。基于这两点,我们在展开政治哲学的讨论之前,有必要先澄清一下儒家语境中“契约”概念的一般涵义和基本特质。
(一)儒家“契约”概念的一般涵义
在汉语中,作为复合名词的“契约”始见于三国魏晋时期,而在此之前,作为单音节词的“契”、“约”早已广泛存在于各类典籍中。
1、汉语“契”字释义
“契”字的本义是灼刻龟甲、兽骨的刀具。《说文·大部》曰:“契,大约也。从大从丰刀。”“丰刀”右边是“刀”,左边是一竖三横,表示用刀在一块小木条上刻下的三个记号,由此形象地反映出上古时代一种主要的记事方法——契刻记事,所以《释名·释书契》曰:“契,刻也,刻识其数也。”[1]又有《周易·系辞下》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2]这表明“契”是指在龟甲、兽骨上刀刻的记号、文字,用来记数、记事,进而人们也将刻有契文的器物本身称为“契”,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曰:“契,本以刀判契之称,因之凡以刀刻物通谓之契。”[3](P817)
武宁节度使王德用自陈所置马得于马商陈贵,契约具在。[16](P197)
由于契文深刻不易更改、损毁,所以人们便以“契”作为参验的信物,也称“符契”,通常是将刻有契文的铜牌、木牌等从中一分为二,双方各执一半,参验时两半契文相合为信。如《宋史》记载宋代政府制作的符契就是“腹背刻字而中分之……却置池槽,牙缝相合”[4](P3595),“刻篆而中分之,以左契给诸路,右契藏之”[4](P3597)。其实《礼记·曲礼上》就有记载:“献粟者执右契”,郑玄注:“契,券之要也。”孔颖达疏:“契,谓两书一札,同而别之。”[5]《周礼·质人》也载:“掌稽布之书契。”注曰:“取予市物之券也,其券之象书两札,刻其侧。”[6]可以说,“契”在古代就作为参验的信物或凭据,其功用大致相当于现代文据上的骑缝印。
两类模型虽然存在争论,但逐渐走向融合。Dehaene认为,数量近似模拟幅度表征的线性模型和对数模型在生理机能上可能是等价的。神经细胞放电形成的调谐曲线以对数刻度压缩,以保证较少神经元就可负责调谐大范围数量。在心理数量级提取过程时,心理数字线必须先经过线性拉长,匹配相应的客观值。
他明确指出订立契约的目的在于实现公民的个体自由,显然已经截然不同于儒家传统的契约观念。此外,被称为现代新儒家的张君劢也在宪法研究和制宪实践中实际运用了现代契约观念。他明确指出:
2.2.3推进有机肥替代化肥 支持长江经济带11省(市)在果菜茶优势产区、核心产区和知名品牌生产基地,全面实施有机肥替代化肥政策,集中打造一批有机肥替代化肥、绿色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园区),加快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组织方式和技术模式。
2、汉语“约”字释义
“约”字本义是绳索,义符为“纟”,指细丝,有缠束作用,因此表示缠束、环束,《说文》曰:“约,缠束也。从纟,勺声。”段注:“缠束也。束者,缚也。从纟,勺声。” 据此推知“约”有结绳之意,而这代表着一种比契刻记事更久远的记事方法——结绳记事。由此“约”引申为邀约、结盟之意,表明一种双方交往、结合的关系。如:
1.2 研究方法 A组给予埃索美拉唑(阿斯利康制药公司,国药准字:H20046379),40 mg/次,2次/d;阿莫西林(四川援健药业公司,国药准字:H21023908),1.0 g/次,2次/d;克拉霉素(江苏恒瑞制药公司,国药准字:H21033044),0.5 g/次,2次/d;枸缘酸铋钾(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国药准字:H10920098),200 mg/次,2次/d,治疗4周。B组在A组治疗方案的基础上给予枳术宽中胶囊(山西双人药业公司,国药准字:Z20020003),3粒/次,3次/d,治疗4周。
我能为君约与国。朱熹集注:“约,要结也。”[8](P345-346)
约为婚姻。[9](P398)
同时,“约”字本身有缠束之意,因此表征约束,如“约之以礼”[10]就是指以礼来约束自身的言行,另有《广韵·乐韵》直接指出:“约,约束”,《广雅·释诂三》、《玉篇·糸部》以及《集韵·效韵》也有言:“约,束也。”可见,“约”字表明主体之间相互合作且彼此束缚的关系,由此引申为双方以文字形式确定下来的共同遵守的条约或合同,例如“约法三章”即是此意,这也一直保留在现代汉语中。
3、汉语“契约”所蕴含的“契约”概念的一般涵义
由上可以看出“契”“约”二字具有相当的互释性,所以《说文解字》:“契,大约也”,《广韵·霁韵》曰:“契,契约”等,就是以“约”释“契”;而《集韵·笑韵》曰:“约,契也”,则是以“契”释“约”。这都表明“契”与“约”的字义上互有交叉,存在着某些共同或共通的内容。根据《周易·系辞传下》所言:“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2]以及孔安国在《尚书序》中所言:“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11],都可以推知“契”与“约”很可能是上古时期的记事方式,其中“约”与“结绳”相对应,“契”与“书契”相对应,由此自然引申出合同、凭据的意思。
在澄清“契约”概念的前提下,我们就可以从政治哲学层面,阐明契约与自由的一般关系。现实生活中,自由作为一种根本的价值诉求,并不是抽象的哲学概念,而总要落实为各种现实的自由权利,而“自愿协议”、“责权对价”的契约特质本身也属于一种现实的自由权利,这在现代社会中得到了更为普遍的认可,并且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自由权利被各国正式写入法律,也即契约自由,其内容主要包括缔约自由、选择契约相对人自由、确定契约内容自由和缔约方式自由等。显然,如果没有自由的价值观念和现实诉求,就不会有所谓的“契约自由”,也更不会有通过契约自由订立的实际契约。据此而言,契约存在本身就是以自由的价值观念确立为前提的,这实际表明自由观念逻辑地先行于契约观念。不仅如此,由于任何自由权利的实现都需要建构社会制度和法规才能得以保障,而“契约说”正是理论界公认的一种法的起源学说,这就意味着任何社会制度和法律规范,实质都是运用契约观念而达成的某种契约。由此可知,契约观念作为社会制度建构的方法,是一种为实现自由价值和诉求的工具性观念,而自由作为目的性、价值性的观念必然先于契约观念。在上述意义上,自由观念是契约观念存在的前提、基础和目的。
导数作为函数在某一点处的瞬时变化率刻画了函数变化趋势(上升或下降的陡峭程度),而函数的单调性也是对函数变化趋势的一种刻画,那么导数与函数的单调性有什么联系呢?(教师通过用超级画板演示曲线上点在运动的过程中,提醒学生注意观察切线的斜率符号的变化.)
事之以货宝,则宝单(殫)而交不结;约契盟誓,则约定而反无日。[12](P228)
明其约契,正其会要,定其时日,通其言语,达其情志,天下不可一日无文也。[13](P98)
而作为复合名词使用的就是“契约”,这种用法一直保留至今。如:
契约既固,未旬,综果降。[14](P332-333)
欲求契约,固合允从。[15](P1183)
由于地面IoT设备的运动,UAV的移动节能策略需要与IoT设备分簇情况联合设计,如图2所示.地面IoT设备运动导致分簇的整体位置和簇内节点数动态变化,进而影响到负责该簇通信UAV的运动.
其实作为复合名词的“契约”与单音节词的“契”、“约”涵义大致相同,都是表明主体之间就某事而进行交往合作,达成某种一致约束双方的内容并以文字确立下来作为凭据。契约的传统形态可参考郑玄的解释:“书两札,刻其侧”,这是说“书契”一式两份,在两片简牍上用文字写明有关的事项、条款,同时把两者并在一起,在相接的一侧刻上一定数量的齿,然后由当事双方各执其一,作为相互验证的凭据,这其实也是现代契约凭据的雏形。
(二)儒家语境中契约的基本特质
基于“契约”在儒家典籍中的一般涵义,以及保留下来的传统契据实物,我们可以看出,儒家语境中契约的基本特质。
其一,自愿协议。其实“协议”本身就表明缔约不能出于强制,而是双方自愿进行协商的结果,体现着双方共同的意愿。这不仅在西方有“合意成契约为法律”[17](P145)的谚语,而且在《唐律疏议》等文献所收录的传统契约中也有“两情和同”“两和立契”或者“两共对面平章”注“平章”也就是“商议”,为商量处理,重在发表意见、与人共商。等套语,金、元、明时期的契约凭据也都注明“此系两愿, 各无抑勒”、“系是二比情愿, 原非逼勒”、“系是两愿, 原非逼勒”[18](P30)等字样。相反,如果在强制、要挟之下签订契约,那就意味着契约仅代表一方的意愿,而不具合理有效性。如《史记·孔子世家》记载:
过蒲,会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蒲人惧,谓孔子曰:“苟毋适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子贡曰:“盟可负邪?” 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9](P2330)
其中“要盟”就是指要挟之下签订的契约。对此,孔子认为“神不听”,理由就在于“要盟”不是出于双方自愿而签订的契约。另如《金史》所载:
(斡里朵)为贼党江哥所执,且欲推为主盟,要以契约,斡里朵怒曰:“我受国厚恩,岂能从汝反耶?宁杀我,契约不可得也。”[19](P2002)
文中斡里朵宁死不签订契约,也是因为“要以契约”违背了自愿性。这一基本特质也贯穿至今,要知道现代社会将“契约自由”视为一种公民基本权利,就是为强调并维护契约双方协商的自愿性。
这里子驷、子展之所以理直气壮地违背契约就在于“要盟无质”,也就是说,订约时违背了自身的意愿,因而缺乏公正性。现实中,为避免当事双方偏私自身的情况,订立契约时往往需要公证人作为第三方介入进行监督。
其实汉语的“契”字即有亏欠、缺失、凹陷之意,《说文解字》曰:“刀判缺之,故曰契”,《广雅》曰:“契,缺也”[21],正是契约双方债务关系的一种隐喻。而《史记》所言:“常折券弃责”[9](P437),“贫不能与息者,取其券而烧之”[9](P2869),也是表明契券体现债务关系。当然,这种债务关系在契约订立之后才具有强制性,而在此之前,承担何种债务都是在双方协商之下自愿接受的,绝非强制的结果。因此,我们称之为“债务”或许过于消极,而应更积极地称为“责任”,但实际上,古汉语的“责”也可读作“zhai”,且与“债”字相通,《说文解字》段注:“责,引申为诛责,责任。”朱骏声《通训定声》:“责,罚也。”可以说,汉语的“责任”其实也带有某种亏欠、罪罚的意思。这一点也是中西文明的共同性,在西方不仅有“债为法锁”的说法,而且在古罗马时期,其市民法“契约”就在“协议”上加了“债务”性条款。
当然,“责权对价”意味着除了责任,还有相对等的权利,这是实现利益的代价和交换条件,而且以契约确定的权利与责任都必须是对等的,即一方如果享受到因对方兑现承诺而产生的利益,那么也就要承担与其利益相当的责任,如果逃避责任,就要受到相应的惩处,以抵偿对方没有得到相应权利的损失。因此,契约比一般性的协议的约束力要更强,双方责权的分配、权衡更具体、细致,其效用和形式都如同“律令”,其意在保障双方交易合作的平等。
二、契约观念:证成自由的工具性观念
当然,“契”“约”也常作为复合词使用,有时用作“约契”,其中“约”为动词,指约定;“契”为名词,指双方协商达成共识之后订立的凭据或文书,也就是说,“约契”是立契为凭,以防食言。如:
不过,上文也指出现实的自由权利必须要建构起社会制度才能得到保障,而契约观念正是建构一切社会制度所运用的工具性观念,这就意味着如果没有契约观念,现实的自由权利将无法得到保障和实现。所以,从自由实现的意义上看,契约观念的确立要先于具体自由权利的实现,也就是说,在实践操作层面上,契约观念是自由实现的前提和保障。
这一面相随着近现代社会契约论的提出而突显出来,特别是由“霍布斯—洛克—卢梭”形成的“自然法”进路的社会契约论对西方现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类理论无不将组成国家的基本法规视为一种“原始契约”(康德语),并且都是从现实的保障个体自由不受侵害的目的出发,来解释现代社会和国家的存在基础、存在意义以及各领域的制度建构等问题,从而根本颠覆了人们对于社会、国家存在基础和价值的传统理解。我们知道,传统国家根本上是为保障皇族的利益,皇族的最高统治权是以“君权神授”或“受命于天”思想为合法性基础,同时要通过加强臣服效忠君主的信念来维系,社会由此呈现为一种纵向的伦理等级结构;而“社会契约论”则提出以订立契约的方式组建社会和国家,公民个体乃是契约主体,由此决定了国家存在的根本目的在于确保每个公民的自由和主体价值,这实质是从社会制度建构的层面为个体自由权利的合理性提供了解释和保障。当然,订立“原始契约”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但这并不影响“社会契约论”对于发展现代自由的积极意义,事实上,现代西方社会正是由此确立了他们民主宪政的基础[22](P69)。
在当代,“社会契约论”早已超出了“原始契约”的范围而具有了更普遍的现代社会建构意义。备受关注的罗尔斯就是将“社会契约论”视为实现制度正义的充分条件,他直言自己提出“正义论”的目的“就是要概括洛克、卢梭和康德所代表的传统的社会契约理论,使之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抽象水平”[23](序言,P1)。事实上,他是把契约论作为建构正义社会制度的工具,这实际上也是指出了一种通行于社会各领域制度建构的基本方法。现实地看,契约论之所以成为解释现实自由权利的有效工具,主要是因为“像财产不可侵犯,不得滥杀无辜、救死扶伤等自然权利和义务很难找到经验上可验证的起源,求助于社会契约论却可以较好地解决其产生的理论前提问题”[24](P27),所以,在政治、法制层面广泛地被运用。
当然,针对近现代“社会契约论”的批评也很多。但需要指出的是,批评“社会契约论”并不等于否认现代契约观念对于现代自由的积极价值,恰恰相反,积极地批评者也是运用现代契约观念为个体自由权利提供制度层面的保障。要知道,功利主义者休谟虽然不认同卢梭以公意为前提的“社会契约论”,但同样坚持认为:“没有人能够怀疑,划定财产、稳定财物占有的协议,是确立人类社会的一切条件中最必要的条件。”[25](P532)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契约,其实功利主义者们无不具有契约精神,他们只是不认同卢梭的论证。此外,当代思想家哈耶克虽然也批判罗尔斯的契约论,认为罗尔斯与卢梭一样都是以理性预设的价值作为订立契约的根本出发点,其中潜伏着背离自由、通往奴役的风险。但他只是否定其订立契约的思想方法,而非契约观念本身,他所强调的是各种契约的订立都应是个体自由自发活动的结果而并无超越个体之上的人为预设,并且特别提出了“自发秩序理论”,这其实是从经验主义的进路上更彻底地贯彻了现代契约观念。
节能化,自节能惠民政策结束以后,节能家电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处于政策的真空期,处境尴尬,各企业降价抛售低能效产品,市场上甚至一度出现了“开倒车”的局面。近两年来,随着能效“领跑者”制度的退出,冰箱新能效的实施,正合时宜。从短期来看,节能高效的产品研发可能会增加企业的研发成本,但从长远角度看来,有助于使市场竞争更加公平有序,促进优势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进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2018年,家电行业的节能风暴也有望再次升级。
战国后期,士大夫之家渐渐取代宗族成为社会主体,儒家的契约观念也逐步发生了转变。如《困学纪闻·春秋》有言:
APS-C单反都可以使用同品牌全画幅单反的镜头,但反过来却不一定可以。佳能的EF-S系列镜头只能在旗下的APS-C机身上使用,而尼康的全画幅相机则可以使用DX系列镜头,但相机会自动切换到DX模式。无反相机的卡口与单反不同,但可通过转接环转接其他系统的镜头。
三、儒家契约观念与自由观念的古今之变
以上虽然是就现代社会做的分析,但从“自由儒学”的视角看,契约与自由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不是西方现代社会所特有的关系,而且也贯穿在儒家契约观念与自由观念的历史演变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儒家具有现代性的契约观念和自由观念,反而是表明儒家的契约观念与自由观念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僵死物”,而是历经古今之变,不断生成发展着的观念,它们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正是在同步的历史演变中体现出来的。
这根本是在于契约观念与自由观念都是一种主体性观念,也即都以主体的存在为逻辑前提。分而言之,自由最一般的涵义就是不受束缚、自做主宰,其实质是主体的在世状态,也就是说,自由与主体的存在相同一,现实的自由总是与其社会主体相一致。同样,契约也是基于主体才存在的,缔约的主体根本决定了契约存在的目的和价值,虽然缔约的代表往往是某一个人,但缔约主体却并非从来就是代表个体价值的个人。事实上,缔约主体也只是社会主体的一种具体存在形式。而任何主体都是由生活本身所造就,即如俗语所说“生活造就了‘我’”,但生活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总是变动不居的,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体必然随着生活方式的变迁而转变,由是自由观念和契约观念也会随着社会主体的转变而演变[26],且根本上总与其时代的社会主体价值相一致,这不仅意味着二者具有历史演变的同步性,而且意味着二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保持着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在此,笔者就儒家的契约观念与自由观念的古今之变作进一步分析。
中国社会大致先后经历了三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即宗族生活方式、家族生活方式以及当前的个体生活方式[27]。其中,在宗族和家族的生活方式下,人们以血缘宗法的宗族、家族为基本单位来组织社会生活,个体不具有独立价值,群体性的宗族或家族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体;而在个体生活方式下,社会分工的系统化、精细化,使得个体无需依附宗族、家族便可以完全获得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各种条件,非血缘的独立个体之间的交往成为现代生活的主要内容,由此形成的现代社会自然是以独立个体为核心和基础来组织社会生活的,这意味着现代社会的主体已不再是传统的宗族或家族而是个体。据此推知,在传统的宗族或家族社会中,自由乃是宗族或家族为主体的自由,契约根本是为了维护宗族或家族的价值而订立;而在现代社会,自由则是个体为主体的自由,契约也相应地为维护个体价值而订立。如下表所示:
综上所述,总之柴油机滤清器的保养,必须坚决地按使用说明书的规定时间和操作进行保养,如果作业环境出现恶劣,保养周期必须提前。拆装、检查和保养要严格按照规程操作,切不可认为各种滤清器作用不大,可有可无,否则柴油机无法保持技术状态完好,功能不能正常发挥,甚至还会大大地减少柴油机的工作寿命。
应激是动物机体为有效对抗威胁自身身体平衡和稳定的各种刺激,所作出的一系列非特异性防御反应,适当的应激反应,对增加动物机体对外界的适应能力有很大帮助,它有利于维护自身平衡和稳定。但过强或长期的应激刺激,会给机体造成严重危害。夏秋季节外界温度较高,湿度较大,牛舍温度与湿度控制不当,超过牛的承载能力,很容易导致热应激的发生。由于奶牛汗腺并不发达,一旦牛舍温度超标,牛体表的对流、辐射和蒸发散热停止,会使牛体表温度迅速升高,产生热应激。牛热应激产生后,会严重影响奶牛的生产指标。
夏商周———先秦秦汉———清民国至今生活方式宗族生活方式家族生活方式个体生活方式社会主体宗族家族个体自由类型宗族自由家族自由个体自由契约观念宗族性契约家族性契约个体性契约社会形态传统契约社会传统契约社会现代契约社会
基于历史哲学的思考,我们可以对儒家契约观念与自由观念的历史演变作具体梳理。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跨国经济合作的加强,中国与世界的接触日益频繁,英汉语言接触的频度和密度不断提高。英语作为一种全球通用语言,对汉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得汉语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出现了欧化现象[1],英汉两种语言混杂使用的现象在中国民众的日常交流中日益多见。
(一)传统儒家的契约观念与自由观念
如英国学者梅因在考察契约的早期史时所指出的: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曾经存在一种毫无契约观念的社会,只不过在最初的社会中契约是以极其原始的方式出现[28](P176)。据此而言,早在商周时期以王室为首的会盟活动就已经有了某种契约的意味,所谓“约信曰誓,涖牲曰盟”[5]。“约”和“盟”本身就是缔结盟约的方式,由此各大小宗族必须供奉周王室,而周王室也必须庇护其他宗族。这里虽然有大宗、小宗之分,但结盟的主体却都是宗族无疑,其目的也就是维护宗族的利益。此外,根据《春秋》《左传》等典籍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订立的政治和军事盟约已有200多次,所谓“君子屡盟”[29]。由于封建诸侯国实质仍是一个靠血缘宗法维系的宗族,因此这些盟约仍然是以宗族为主体缔结的,根本目的也是为了维护宗族的主体价值,这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盟约根本不同。
由上可以看出,现代契约观念与现代自由密切相关正是契约与自由之间辩证关系的体现,尤其是契约观念作为一种工具性观念,为切实保障主体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及其为实现这一切所需要的条件提供了有效的证成方法,因而是自由权利实现与否的关键。众所周知,一直被誉为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基石的英国《大宪章》,实质就是一份“大契约”,这也足见契约观念对于保障自由权利的重要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代契约观念实际地铺就了现代自由之路。
襄公三年,鸡泽之会,叔孙豹及诸侯之大夫盟,言“诸侯之大夫”。十六年溴梁之会,直曰“大夫盟”,不言“诸侯之大夫”者,鸡泽之会,诸侯始失政也。至于溴梁之会,则又甚矣。溴梁之会,政在大夫也。不言诸侯之大夫者,大夫无诸侯故也。[30](P717)
这可以说是儒家契约观念由宗族转向家族的体现。秦汉一统直至清代,遍布于政治、经济、日常人伦等各个社会领域的契约皆是以家族利益为根本目的而订立。例如,在经济契约中,最常见的止损赔偿条款都明确规定由家族全体共同承担债务,而无需征求每个家族成员个体的意愿,所以传统契据中常出现类似“若郑身东西不在,一仰妻儿及收后保人替偿”[31](P340)的内容。
其实,在前现代社会,契约对宗族或家族主体价值的维护最直接地体现在婚约的订立上,《礼记·昏义》就明确指出了传统婚约的目的,即“合二姓之好,上以祀宗庙,下以继后世也”[5]。显然,这是为了两个宗族或家族的延续和兴旺,因此传统婚约全由婚嫁双方的家长做主,而当事人只有遵循“父母之命”的资格,并无自身的意愿和利益可言。由此便知传统婚约的主体根本不是婚嫁的双方当事人,也不是双方家长,而是订约的两个宗族或家族。
需要说明的是,前现代的契约虽然通常由作为家长的父、祖、兄、伯叔或者寡母来缔结,但由于宗族或家族本身的存在先于任何社会性个体(包括家长本人),缔结契约乃是宗族或家族功能的延伸,而非个体权利,所以家长作为缔约代表乃是以宗族或家族的价值为前提和归旨,而任何成员违背契约条款也都会惩罚作为宗族或家族的代表“家长”,或者以“连坐”的方式惩处所有家族成员。总之,传统的家长自身既不是独立的权利享有者,也不是独立的责任人。这种前现代的契约观念同样存在于西方的传统社会中,例如罗马法中就存在类似中国传统家长的“家父”。所以,梅因在《古代法》一书中曾指出,在传统社会中,每个人都不是被看作一个独立个体,“而是始终被视为一个特定团体的成员”[28](P105),进而“个人并不为其自己设定任何权利,也不为其自己设定任何义务。他所应遵守的规则,首先来自他所出生的场所,其次来自他作为其中成员的户主所给他的强行命令”[28](P176)。这都表明传统社会的自由只能是宗族或家族的自由,而各种传统契约的缔结正是落实和维系这种自由的有效手段,而且无不是在传统的价值诉求下依据自愿协议、责权对价订立的结果。
(二)现代儒家的契约观念与自由观念
近代中国,生活方式再度发生了转变,由是根本导致了传统家族的解体,同时使得个体摆脱了对家族的从属性,成为独立的社会主体,相应地个体自由也成为新的价值诉求。近现代儒家在积极回应现代自由诉求的过程中推动着儒家传统的自由观念逐步转向现代,这在政治自由层面的体现最为突出。例如维新儒家谭嗣同号召“冲决君主之网罗”,康有为直接宣称“人者,天所生也,有是身体即有其权利,侵权者谓之侵天权,让权者谓之失天职”[32](P130)。而后的现代新儒家不仅提出“肯定自由,肯定民主,创造自由,证成民主”[33]的主张,而且都还从学理上努力探索了现代自由的合理性和现实路径。
达尔文有一句名言:“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识。”根据学生的年龄特征,循序渐进地对学生进行自学、观察、操作、比较、迁移、解题、归纳、总结等方法的指导与训练,发现问题及时纠正,慢慢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发展他们在自主学习、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等方面的能力。生物学科概念繁多,容易混淆,涉及面广,有经验的教师在学完一块内容后会采取适当的手段进行处理:带领学生绘制概念图,必修一用得较多;逻辑关系强的做思维导图,比如体液调节、免疫调节;层次分明但又难记住的用列表进行比较,比如不同的育种方式;涉及随机交配和自交的遗传问题利用公式模型。首先由教师指导,之后让学生针对不同内容自己确定方法并独立完成。
正是在推进现代自由发展的过程中,近现代儒家意识到了现代契约观念对维护个体自由的重要性,由此而表达出以独立个体为主体,通过自愿协议、责权对价订立契约的方式来建构现代社会制度的思想主张。例如梁启超就通过介绍《卢梭学案》宣扬了现代契约观念。他说:
人人於不识不知之间而自守之。此亦天理所必至也。…… 一夫一妻之相配,实由契於情好互相承认而成,是即契约之类也。既曰契约,则彼此之间,各有自由之义存矣。……夫以家族之亲,其赖以久相结而不解,尚必藉此契约,而况于邦国乎。
凡两人或数人欲共为一事,而彼此皆有平等之自由权,则非共立一约不能也。审如是,则一国中人人相交之际,无论欲为何事,皆当由契约之手段亦明矣。人人交际既不可不由契约,则邦国之设立,其必由契约。
要而论之,则民约云者,必人人自由,人人平等。[34](P504)
由于“符契”是双方各执一半,单凭任何一方都无法达成预期目的,这就意味着双方必须以合作的方式才能达到目的,缺一不为“契”。所以,“契”本身就体现着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不仅如此,这种合作关系一旦以“契”的方式确定下来,就成为一种无法随意变更或撤销的凭据,故而对双方具有束缚性。所以,《文心雕龙·书记》曰:“契者,结也。上古纯质,结绳执契,今羌胡征数,负贩记缗,其遗风欤!券者,束也,明白约束,以备情伪,字形‘半’、‘分’,故周称‘判书’。”[7](P146)
我国治从事制宪者,当亦知所抉择,善为国家立长治久安之基础乎!
一张文书(指宪法——引者注),所以规定政府权力如何分配于各机关,以达到保护人民安全与人民自由的目的。[35](P354)
这里张君劢强调制定宪法的目的在于保障国民安全与自由,而宪法作为根本大法,实质正是一份根本性的契约,由他草拟的“四六宪法”注1946年1月,张君劢主持起草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保留了三民主义的基本思想并贯彻政协宪草决议案内容,落实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以及内阁制之民主宪政等精神。正是这一契约的现实范本。不仅如此,他还通过《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对国家存在的意义、制定宪法的目的以及具体内容的设计等问题做了详细阐述,这都鲜明地反映出他思想中的现代契约观念。
在当代儒者中,林安梧也提出要以现代性的“社会契约”观念作为当代儒家社会制度建构的基本原则。基于传统社会解体的事实,他指出现代社会制度不再是由孝悌人伦直推出去的,而是通过个体的“契约理性”建立起来的“契约性的社会连结”。这无疑是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强调了现代契约观念对社会制度建构的意义注参阅林安梧《契约、自由与历史性思维》(台北:幼狮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儒学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哲学省察》(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年)、《后新儒学的社会哲学:契约、责任与“一体之仁”》(《原道》2003年第8辑)等。。
红芒中,构成塔壁的三千骷髅头,围着塔心的人影缓缓旋转起来。它们越转越快,从塔壁松脱,并于旋转中朝着周围分散,竟转眼将整个天葬场笼罩起来。在高速的旋转中,它们卷起黑风阵阵,风中似有鬼影浮动,头顶阴云闭月,四周飞沙走石,将云浮山巅,化作了人间的鬼狱。
纵观古今可以看出,随着社会主体的转变,儒家的契约观念与其自由观念在同步地由传统转向现代,在此过程中,不同时期的主体自由都通过相应的契约观念得到切实的保障,特别是历史上儒家传统的契约观念对于保障宗族和家族的自由权利而发挥的作用是极为突出的,同样近现代的儒家也意识到现代契约观念的重要价值,希望以此奠定现代社会制度的基石,为现代自由的发展提供切实的保障,遗憾地是他们没有从理论上提供发展儒家现代契约观念的思想方案。
四、儒家契约观念的基本原理
对此,我们并不能从儒家传统的契约观念中找到现成的内容,因为那是与传统的宗族或家族主体相匹配的观念,非但无助于现代自由的实现,而且还会对现代契约观念的发展造成阻碍。不过,我们另外发现儒家历代的契约观念虽然具体内容不尽相同,但是都未脱离“契约”概念的一般涵义和基本特质,这意味着它们背后遵循着一以贯之的儒学原理。或者可以直接说,儒家历代的契约观念都是同一套儒学原理在不同生活方式下的现实形态,这一套儒学原理可以被不同生活方式下的内容所充实,由是才形成了儒家历代的契约观念。据此可以推知,如果我们以现代性的生活内容来充实这一儒学原理,那么就可以从理论上确立起儒家现代的契约观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如果揭示了历代儒家契约观念所依据的基本原理也就找到了发展儒家现代契约观念所需要的思想方案。
其实,以往的研究已经触及到了这个问题,即认为契约观念根植于儒家的诚信思想。只不过以往的相关解释大都局限于道德维度,而这无异于将契约观念仅仅视为一个道德哲学的观念,然而从前文的论述看,契约观念的根本意义在于促成社会制度的确立,这恰恰是当前对于儒家“诚信”思想的阐释中尚未揭示的一个面向。不仅如此,“诚信”绝不是一个浑沦单一的概念,而是内在地呈现为一套思想结构。因为,在笔者看来,虽然“诚”与“信”在基本涵义上具有互释性,所谓“信,诚也”,“诚,信也”[20],但在观念层级上,“诚”与“信”并不相同,如朱子所言:“诚是个自然之实,信是个人所为之实”[36](P94),这里的“自然”并不是物质自然界(nature),而是自然而然的生活实情。据此而言,“诚”是前对象化的本源性观念,而“信”则是“形于外”的“诚”,是“诚”经验化、对象化和实证化的形态,因此“诚信”本身体现为一个由“诚”至“信”的思想过程。如果结合儒家契约观念所包含的内容做进一步思考,就会发现由“诚”至“信”也不是无中介的直接通达,而是需要以“义”与“智”为基本的中介环节,也就是说,这一过程实质展开为“诚→义→智→信”的思想结构。那么,从社会制度建构的意义上揭示这一思想结构,我们大可彰明儒家契约观念的基本原理。
(一)契约之本源:源“诚”生约
如果说一切存在者渊源于生活本身,那么,生活本身就是契约之本源。然而,生活本身并不是一潭死水,而总是生生不息的流变[37]。众所周知,儒家所理解的“生生不息”乃是天地交往化育的状态。这种源始意义上的交易流转、消息往来,作为无妄而不欺的生活实情,被原始儒家理解为“诚”,所谓“诚者,天之道也”。据此而言,“生生不息”也就是“至诚无息”[5]。
正是本源之“诚”造就了主体(“不诚无物”),同时也源始地决定了主体随时随地处于交易往来之中。因为主体作为存在者,总是有所成也有所缺,而唯有通过交易往来,互通有无,才能彼此成全,实现自身在政治、经济、道德、情感等多方面的诉求。广义地说,这无不牵扯到主体之间“利”的交换,但也正是通过这种互惠互利的交易往来才能在经验层面证成“生生不息”这一生活的实情。对此,儒家从绝对主体意义上确立起的“易道”就表明交易往来内在于主体性之中,所谓“‘易’有四义:不易也,交易也,变易也,易简也”[38](P408),《周易·系辞下传》曰“上下无常,刚柔相易”[2],就是指交易。站在儒家立场看,主体的交易就是对本源的天地交易往来(“诚”)的“明觉”,所谓“诚之者,人之道也”,由此“诚”获得主体意义,也即不欺人、不自欺作为人的主体性而得以确立,同时通过主体的交易往来,本源之“诚”才得以现实地开显,所以说“君子诚之为贵”[5]。
不过,在经验生活中,主体的交易往来常因一方“不诚无信”而失败,这无疑是对“生生不息”的生活最直接的破坏。为避免这种情况,订立契约便成为一种必要的手段。尽管儒家讲“大信不约”,而且成文的契约作为一种凭据也并不能真正超过人智;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订立契约依然具有必要性。其一,订立契约既能防范对方无信,也能表明自身诚意,因此传统契据就有“今恐人心无信,故立文契为照者”[31](P638)的字句。其二,订立契约可以“去私”、“塞怨”,通过明确双方责权可以有效地避免争讼,所谓“以质剂结信而止讼”[6],而如果“制契之不明”则往往容易导致双方纷争,所谓“凡斗讼之起,只由初时契要之过”[2]。此外,在司法审判中,契约也是的重要证据,如若不然会导致“两无中据,难定曲直” [39](P1064)。总而言之,订立契约作为一种必要的手段,乃是为了保障主体交往的通畅有序,维护主体利益不受侵害,而这在最本源的意义上都是由交易往来的生活实情所决定的注在经验生活中,交易往来的目的乃是为了维护和实现主体的利益,因此“利”是契约观念中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在此限于篇幅不作具体阐释。“利”并不单纯指物质利益,而是代表主体生活和发展的各种现实需求。原始儒家积极肯定了“利”的价值,但后世儒学往往片面强调“义”而否定“利”,偏离了原儒“利者,义之和”(《周易》)的立场。当前需要正视“利”的价值,将之纳入到儒家现代契约观念的发展中。。
(二)契约之原则:以“义”立约
“立约”包含两个层面契约的订立:一个是指根据既有的制度规范来立约(如各领域法律法规的制定),这种“立约”行为本身需要遵守某种更根本的契约,最终是以原始契约的订立为前提。还有一个则是指原始契约的订立,也即订立最根本的契约,如前文论及的“社会契约论”就是关于原始契约的理论。这种契约的订立并没有现成的制度规范作为根据或原则,而是在本源生活的基础上订立的,因而属于制度建构本身的原则问题。在这方面,黄玉顺建构的“中国正义论”提供了直接参考。他指出本源生活的道德共识就是作为基础伦理观念的“义”,事实上,这也正是原始契约订立的根本原则。我们知道,当代西方思想家罗尔斯是以契约作为证明正义的方法,但更为前提性的问题是,唯有以基础伦理的“义”为原则才能保障契约本身的正义,即如荀子所说:“不知法之义而正法之数者,虽博,临事必乱。”[40](P272)这就是说,立约本身的正义是衡量契约具体条款和执行程序是否正义的前提。在此,笔者从正当性与适宜性两方面进一步说明立约的根本原则问题注关于“中国正义论”的主要内容集中体现在黄玉顺的两部著作中:《中国正义论的重建》(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中国正义论的形成》(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年)。“正当性”和“适宜性”是黄玉顺“中国正义论”所提出的“义”的两条具体原则,笔者在此借用以说明立约正义问题,但具体的解释并不同于中国正义论。。
1、正当性
(1)“正”即“公正”,是指契约的订立不能偏私任何一方。立约要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进行协商,契约的内容一定要体现双方的合意,此谓“公正无私”。这意味着强迫或要挟其中一方而签订的契约,都不符合公正性原则,自然也就不具合理有效性。如:
楚子伐郑。子驷将及楚平,子孔、子蟜曰:“与大国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驷、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强是从’。今楚师至,晋不我救,则楚强矣。盟誓之言,岂敢背之?且要盟无质,神弗临也。”[41](P971)
其二,责权对等。从“契”“约”二字的涵义以及现实契约活动来看,契约还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协议或合同。因为契约除了体现双方的合意,还强调双方处于责权对等的约束关系中。其原因在于双方都想实现某种价值,但自身有所欠缺必须得到对方的协助,而对方提供的协助是有条件的,为此,自身也需要提供给对方某种协助作为抵偿。这就意味着契约双方处于相互的“债务关系”中。
(2)“当”即“得当”,主要是指立约双方责权对价,即任何一方享有的权利与其承担的责任应当是等价的、相当的,如若任何一方的权利大责任小,或权利小责任大,那么都是不当的。至于立约双方的具体责权比例,则是由双方协商决定,既可以双方各承担二分之一的责权,也可以是一方的责权比例大,另一方责权比例小,只要各自承担的责任与权利对等就都是得当的。
简而言之,立约之“正”在于契约以双方自愿合意为基础而订立,立约之“当”在于契约以双方责权对价为法则而订立。
2、适宜性原则
立约之“义”源于生活本身,自然不能脱离具体的时代和地域,因此唯有与时、与地相适宜才是真正的“义”,这就是适宜性原则,它主要体现为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两个方面。
所谓“因时制宜”是要求契约的订立必须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前文曾指出,由于生活的变迁导致前现代的宗族或家族主体转变为现代的个体主体,因此现代契约的订立不再是传统的宗族或家族协议的产物,而是个体之间自愿协商的结果,应体现着个体的主体价值,保障个体自由。所谓“因地制宜”是要求订立契约必须以当下的具体状况为根据,旨在强调在共时条件下,由于地域性差异或事件性差异,也会使立约双方的责权分配比例有很大不同,例如现代各民族国家对于公权力和社会责任的分配比例就各不相同,北欧福利国家政府的权力大责任大,公民的权力小责任小;相较之下,英美国家的政府权力小责任小,公民权力大责任大,因此不能一概而论。
鱼种培养与放养。结合实际的技术方案要求和业主需求,我县今年投放的鱼类品种以鲤鱼和鲫鱼为主,适当挡配少量草鱼和鲢鱼进行混养,放养标准为每尾鱼苗30克以上,每亩450尾。在具体放养时,需要做好时间控制,一般在大田秧苗移栽15天后,此时秧苗返青,开始进行鱼苗投放,投放时应尽量选择上午,并且天气晴朗时进行,做好放养育苗水温控制,鱼苗原本所处水温与稻田水温差异控制在3℃以内。放鱼前需要保证稻田肥料毒性已经消散,并进行鱼苗试水,若鱼苗状态正常,则可大范围放苗。
适宜性原则表明立约既不是一劳永逸的,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而是需要随时、随地进行损益,或者重新订立的。我们知道,西方的《圣经》也有旧约、新约之分,实际上正是随着生活的变迁,人与神重新订立契约的结果。同样,传统的儒家契约曾有效维护了宗族和家族的主体价值,促进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繁荣,但从现代价值立场来看,这恰恰是禁锢个体自由的“法锁”,然而要打开这道“法锁”就必须顺应生活的变迁和现代社会主体的诉求,从维护个体主体价值的意义上重新订立契约才符合适宜性原则,也才能体现最根本的“义”,即如孟子所说“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42]。
总之,儒家认为,订立契约的根本原则就是生活本身显发出来的交往共识和交易默契,也就是“义”,其体现为正当性与适宜性的统一。这与卢梭-罗尔斯的思路根本不同,我们知道,罗尔斯是将一种人为设计的“原初状态”作为订立契约的根本原则,认为只有在“无知之幕”的前提条件下,理性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作用,进而才能订立正义的契约,而事实上,这种脱离生活本身的人为预设,在理论上是不究竟的,在现实中也是不可能的。
(三)契约之设制:以“知”定约
契约最终要形成一套可操作性的规定,并以文书合同等形式保存下来作为凭据。因此,在以“义”立约的原则下,双方还要针对约定的内容来制定具体的条款、设计执行的程序等等,这通常体现为各种法律规范的制定需要依靠理性来完成,儒家称之为“知”或“智”。当然,儒家的“智”或“知”其实分两种:“一种是认知性的‘知’即理智、知识,处于正义原则(义)与制度规范(礼)之间;另一种则是感悟性的‘智’(以区别于知识性的‘知’)即智慧、正义感或良知,处于利益欲望与正义原则之间。”[43]对于契约具体条款和程序的制定而言,我们主要运用的是认知性的理智。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要“知礼”。这是指契约设制者应当是制礼的专家,必须要精通制度、法律、规范、礼仪等方面的专门“知识”;而且还会进行精巧的设计,懂得如何将这些“知识”合理搭配形成一个严谨有效的系统,为我所用,例如“三权分立”就是现代政治制度设计中运用理智的一个成功典范。第二,要“知人”。这是指契约设制者要具备洞察人的主体性的理智。孔子有言:“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10]另有,“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10]所谓“知人”最根本的就是要意识到当下生活方式所造就的人的主体性是什么,据此才能进一步设制出符合主体价值的条款和程序,如荀子所言:“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40](P488),“知有所合”其实就是强调理智把握的内容首先要与人的主体性相吻合。这就表明,仅仅“知礼”还是不健全的理智,只有做到“知人”才算是“明智”。现实契约活动中,唯有通过“明智”的设制才能从实际操作层面保障契约内容的正义。
(四)契约之兑现:以“信”守约
立约、定约都是为了确保双方守约,唯有守约才符合契约正义的原则,所谓“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42],“异于约则谓之不宜”[40](P496)。守约作为契约的兑现,是本源之“诚”现实地“见于事”的环节,儒家认为“见于事为信”,因此守约必以“信”。
前文已提及“信”与“诚”具有很大程度的互释性,简单说来,“信”就是“诚之实”。那么,何为“诚之实”?我们知道,《易》以“中孚”卦象征诚信,所谓“孚,卵孚也。从爪从子,一曰信也”[20],朱子进一步说:“伊川云:‘存于中为孚, 见于事为信。’说的极好。因举《字说》:孚字从爪从子,如鸟抱子之象。今之乳字一边从孚,盖中有所抱者实有物也。中间实有物,所以人自信之。”[38](P232)由此可知,“诚之实”就是要“见于事”“实有物”,这都是从兑现承诺的意义上讲的,所谓“践己所诺为信”。当然,对契约的信守,不但是要遵守自己的承诺,而且还要按照契约明确规定的内容和程序严格履行注当然,在契约实际履行中情况要复杂的多,比如现代西方提出“契约(目的)落空”原则,即出现了缔约时无法预料的情况,从而使契约目的落空或事实上不可能履行,法院可以根据案情解除契约,而不能死板地按照契约条款严格执行。。
正是由于双方是按契据规定来兑现承诺,所以契约之“信”具有两个面向:其一,由于契约条款本身是一种外在的约束,且具有法律强制力,所以契约之“信”并不是全靠双方的道德自觉来兑现承诺的。在这个意义上,契约之“信”并不等同于美德之“信”,而是带有一种“不得不”的责任义务的成分。其二,契约之“信”也不全然依靠“他律”,而根本是双方立约自愿性的延续,这意味着契约之“信”也有明显的自觉主动性的面向。毕竟,如果没有履约的自觉性,那么契约设制的再精巧、再严密也无济于事,所谓“苟信不继,盟无益也”,“君子屡盟,乱是用长。无信也”[41](P134)。不过,信守契约的自觉主动性也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源于双方为实现自身利益的功利考虑,因为唯有信守契约才能达到预期目的,这属于功利主义的道德;但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双方对自身的“忠”,所谓“尽己之谓忠,以实之谓信。发己自尽为忠,循物无违谓信,表里之义也”[44](P179),“忠信只是一事,而相为内外始终本末。有于己为忠,见于物为信。做一事说,也得;做两事说,也得”[36](P486)。“忠”与“信”不可分离,契约双方根本是因忠于己才能自觉地“践己所诺”,这不仅是信守契约最积极的动力,也是契约之“信”最值得彰显和弘扬的面向。
至此,“以信守约”与“源诚生约”首尾相应,形成了一个思想上的回环。事实上,契约之“信”不仅仅代表儒家“契约”观念的最后一个逻辑环节,而且也使得生约之“诚”,立约之“义”,定约之“智”以及契约本身作为规范制度之“礼”最终成为一个经验事实而得到了当下的直观,如程颐所说:“‘四端’不言信,既有诚心为四端,则信在其中矣!”[44](P372)因此,儒家契约观念的基本原理就可以表达为“诚—义—知—信”的思想结构,据此与现代性的价值诉求相结合将可以充实起儒家现代的契约观念。
参考文献:
[1]刘熙.释名[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孔颖达,等.周易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9.
[4]脱脱.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7.
[5]孔颖达,等.礼记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6]贾公彦,等.周礼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7]刘勰.文心雕龙[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
[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9]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4.
[10]邢昺,等.论语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1]孔颖达,等.尚书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2]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3]归有光.归震川全集[M].上海:上海中央书店,1936.
[14]魏收.魏书[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15]白居易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6]司马光.涑水记闻[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7]郑玉波.法谚[M].台北:三民书局,1988.
[18]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9]脱脱.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0]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21]张揖.广雅[M].文选楼丛书本(光绪刻).
[22]谢文郁.自由与责任[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23][美]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24]顾肃.自由主义基本理念[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25][英]休谟.人性论(下册)[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6]郭萍.中国自由观念的时代性与民族性[A].国际儒学论丛(第3辑)[C].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7.
[27]黄玉顺.论儒学的现代性[J].社会科学研究,2016,(6).
[28][英]梅因.古代法[M].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9]孔颖达,等.毛诗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0]王应麟.困学纪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31]张传玺.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 (上册)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32]康有为.大同书[M].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
[33]牟宗三.肯定自由、肯定民主[N].联合报,1979-06-02.
[34]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35]张君劢.中华民族性之养成[A].宪政之道[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36]黎靖德.朱子语类[M].长沙:岳麓书社,1997.
[37]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
[38]李光地.周易折中[M].成都:巴蜀书社,2008.
[39]袁枚.子不语(下)[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
[40]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4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42]孙奭,等.孟子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43]黄玉顺.中国正义论纲要[J].四川大学学报,2009,(5).
[44]程颢,程颐.二程遗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TheConfucianConceptofContract——AnInterpretationinViewofLiberalConfucianism
GUO Ping
(InternationalConfucianCentreofStudyandExchange,ShandongAcademyofSocialSciences,Ji’nan250002,China)
Abstract:It is an undeniable fact that the concept of modern contrac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modern freedom. Therefore, in developing modern freedom, Confucian have to interpret the concept of contract. In the light of the basic meaning of contract (“契约”) in Chinese, I can state clearly that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Confucian contract are voluntary negotiation and rights reciprocating responsibility. Then from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we can see that contract,as a proof tool of realizing freedom, actually preserve social subjective values. Based on Liberty Confucianism created by myself, I think that the concept of contract is always converted with the change of social subject in the long historical process. However, I find that the Confucian concept of contract is still holding the general meaning and basic peculiarity of contract, because it is on the basic principle of Confucianism that is“honest(诚)- justice(义)- reason(知)-faith(信)”. By uncovering this basic principle, we will get a help to create the theory of Confucian modern contract.
Keywords:the basic principle of Confucianism;contract;Liberal Confucianism;freedom
收稿日期:2018-05-24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儒家契约观念及其现代转化研究”(17CZXJ06)
作者简介:郭萍,女,哲学博士,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B222;B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19)02-0005-011
责任编辑:李观澜
标签:契约论文; 儒家论文; 自由论文; 观念论文; 宗族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先秦哲学论文; 《齐鲁学刊》2019年第2期论文; 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儒家契约观念及其现代转化研究”(17CZXJ06)论文; 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