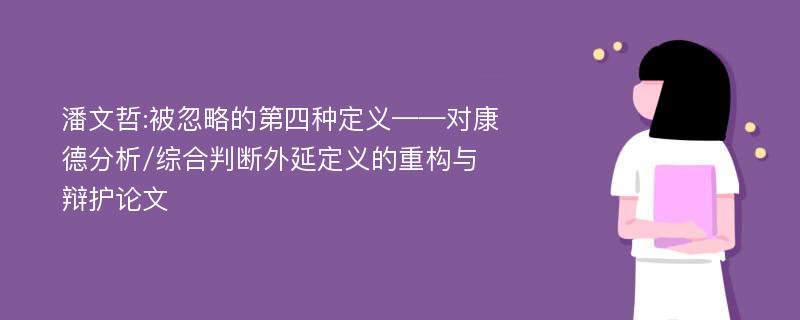
[摘 要]分析/综合判断的区分对于康德的批判体系而言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但他基于概念包含性、同一性、内容扩展性所引申出来的三种分析/综合判断定义自《纯粹理性批判》面世以来就饱受争议,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幸运的是,有一个新的角度可以为这个旧的困境提供曙光。通过对康德逻辑学讲座和相关笔记的解读与梳理,可以重构出康德对分析-综合判断的第四种定义,即一种以概念的外延,以及以对对象的归摄活动为基础的定义。而这第四种定义之所以为攻击者所长久忽略,是因为英美学界的刻板印象遮蔽了康德逻辑学的独特性所带来的革命性闪光。外延定义恰好体现了这种革命性——主要在于与康德判断本质新立场的一致性。从消极方面看,第四种定义的理论意义在于能够使一些固有反驳不攻自破;而其积极意义则在于在内容和方法上对康德理论哲学研究带来某种程度的扩展。
[关键词]分析判断;综合判断;概念包含;归摄;第四种定义
一、导言
众所周知,康德开创性地提出“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以此作为其纯粹理性的总课题[1]B19①本文根据康德研究的惯例,凡引用《纯粹理性批判》原文,以A表示第一版;B表示第二版,不再另外标注中译本页码,译文均参考邓晓芒译本。。而如果说其中的先天/后天区分在一定程度上仍保留传统形而上学的遗风,那么分析/综合的区分则纯属康德的原创②尽管康德主张这一区分的原创性,但马上遭到艾伯哈德(Eberhard)的质疑。后者主张这一区分早已存在,并且很容易被传统形而上学所解释,因此批判连同这一区分都不是新的(见J.A.Eberhard:Ueber die Unterscheidung der Urtheile in analytische und synthetische.Philosophische Magazin,1789,(1):307-332)。。因为这种区分为理性派哲学家,尤其是沃尔夫和鲍姆加登所完全忽略(尽管洛克有所暗示,却并未实际作出这种区分[2]270),因此康德不无自豪地表示:“考虑到对人类知性的批判,这一划分是必不可少的,因而在这种批判中堪称是典范的。”[2]270而分析/综合判断的区分对于康德的理性批判来说,不仅是“典范”,更是首要的。例如,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出版之后的1783年,康德在与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他的主要反对者的通信中曾向后者建议:“您可以首先考察分析和综合判断的区分是否正确。”[3]202而在给加尔弗(Garve)的信中,他同样提出理解其著作的最好顺序是先从分析/综合判断的区分开始,然后是总问题,之后才是解决方案[3]195。由此可见,分析/综合判断的区分是康德批判哲学体系是否成立的先决条件,因此拥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导言的第四节首次提出将一切判断区分为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并罗列了三种区别特征——概念的包含性、同一性、内容扩展性用以区分两者,由此可引申出分析/综合判断的三种定义[1]A6/B10。但他的这个区分和三种定义自该书1781年面世以来就饱受争议③早期针对这一区分的争议主要在于其独创性和主观性(见Maaβ:Ueber den höchsten Grundsatz der synthetischen Urtheile.Philosophisches Magazin II,1789,(2):186-231)。,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可谓影响颇深。学者汉拿(Hanna)通过对康德之后的分析哲学历史进行梳理后发现:“康德的分析理论一直是逻辑学家、语言哲学家和蒯因主义者的直接攻击目标。”[4]121并将他们的攻击总结为五个方面:1.康德的分析性标准在逻辑上是相互独立,甚至是不相容的;2.其区分太狭窄,只适用于定言判断;3.其核心概念,即包含关系意谓不明;4.分析性标准有主观的、心理学的倾向;5.康德的区分不能抵受当代分析哲学家(特别是蒯因)的攻击[4]124。这些质疑针对的都是《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的这三个定义中的一个或所有。与康德本人对这一区分的自豪相比,就连对这一区分持有最善意态度的当代解读者恐怕也很难不从康德所处的历史性出发来为其开脱。难道没有更有力的立场来支持康德对分析-综合判断的区分吗?事实上,康德还有第四种定义。而这第四种定义往往为攻击者,甚至是大部分意欲捍卫康德相关理论的学者所长久忽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这种定义散见于康德的逻辑学讲座和逻辑学笔记中,相比《纯粹理性批判》,这些文本似乎不能代表康德本人的立场。但是本文将证明,在这些文本中所体现的第四种定义是一贯的,更重要的是与第一批判中的三种定义相比,这第四种定义反而更能体现康德对判断本质的根本立场。在对第四种定义进行重构之前,本文将首先对第一批判中的三种定义进行简要分析。然后再根据康德逻辑学笔记中的论述重建他的第四种定义,并证明它的重要性——它不仅更切近康德在先验演绎部分对判断的新定义,而且也能更好地回应针对分析/综合判断区分的若干质疑。
该篇阅读材料以古埃及王国为背景,蕴含不同的宗教、历史、习俗等背景知识,若缺乏了解会导致理解偏差。为帮助学生进入阅读情境,可借助多媒体展示一些金字塔、狮身人面像的图片,通过感性认知激发学生的兴趣,接着放映Seven Wonders of Ancient Egypt等展现古希腊文明历程的纪录片实现视听说同步,使学生处于三维空间,多感官获取信息。虚拟实景可以使阅读内容故事化、情景化,学生可以是剧中人,也可是观光者或作者本人,为理解文章打下基础。
二、《纯粹理性批判》中分析/综合判断的三种定义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康德对分析与综合判断的具体区分。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导言部分,他考察了最基本的认识单元。由于概念(理性派所主张)和感觉印象(经验派所主张)孤立地看都不能是错误的,而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的判断才有对错,或真假之分。所以知识最基本的单元应该是判断。但是否所有的判断都是知识呢?答案是否定的,于是康德提出他关于分析/综合判断的区分。
为此康德提供了三个区别特征。首先是主词对谓词的包含关系——“在一切判断中,从其中主词对谓词的关系来考虑(笔者在这里只考虑肯定判断,因为随后应用在否定判断上是很容易的事),这种关系可能有两种不同的类型。要么是谓词B属于主词A,是(隐蔽地)包含在A这个概念中的东西;要么是谓词B完全外在于概念A,虽然它与概念A有连结。在前一种情况下我把这判断叫作分析的,在第二种情况下则称为综合的”[1]A6~7/B1。那么可以得出第一种分析/综合判断的定义是:主词概念包含谓词概念的判断为分析判断;主词概念不包含谓词概念的判断是综合判断。第二个区别特征是同一性。而得出的第二种定义是:“分析的(肯定性的)判断是这样的判断,在其中谓词和主词的连结是通过同一性来思考的,而其中这一连结不借同一性而被思考的那些判断,则应叫作综合的判断”[1]A7/B10。最后,第三个区别特征是内容上的——因此第三种定义就是:“前者(分析判断)也可以称为说明性的判断,后者则可以称为扩展性的判断,因为前者通过谓词并未给主词概念增加任何东西,而只是通过分析把主词概念分解为它的分概念,这些分概念在主词中已经(虽然是模糊地)被想到过了:相反,后者则在主词概念上增加了一个谓词,这谓词是在主词概念中完全不曾想到过的,是不能由对主词概念的任何分析而抽绎出来的”[1]A7/B11。
稻壳中微生物检测采用平板菌落计数法,即将样品经一系列梯度稀释后与培养基混合制成平板,经过培养进行菌落计数。
显而易见,康德似乎将这三个区别性特征都视为分析/综合判断的充分标志,因而学者通常认为康德对分析/综合判断的三种定义是各自独立的。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这三个定义中哪个才是关于分析/综合判断的基础定义?学者安德森(Anderson)认为,概念包含关系是康德分析/综合判断区分的核心。他的理由是这个定义处于三个定义之首,并且拥有最正式的表述;另外,其余两个定义也都可以还原为概念的包含关系定义,但反之则不然[5]172~176。但是,蒯因等学者质疑,康德将分析/综合判断的关系视作主谓概念之间的包含关系似乎过于狭隘[6]。并且自《纯粹理性批判》面世以来,关于分析判断的这个“概念包含关系”就饱受诟病。主要的问题是这个“包含关系”被认为是一个极不清晰的概念。为了绕开这个棘手的难题,若干康德解读者选择第二个,基于同一性的定义为主要的着眼点。这种解读有具体的文本支持,康德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的确是主要根据同一性来区分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2]270。另外,从学理上看,这个定义也显然能包括比定言判断更多的判断类型,如假言判断和选言判断。此外,该定义还与当代哲学家如弗雷格、卡尔纳普、蒯因关于逻辑真理的观念相近。因此持同情态度的英美分析学派哲学家对于康德分析判断的解读主要就是以第二个定义为基础。而阿利森出于其对《纯粹理性批判》的认识论解读,并且结合该定义的上下文,倾向于接受第三种定义。因为这种定义与内容相关——前面部分考察了知识的基本单元是判断,分析判断只能澄清已有的知识,而综合判断却能扩展知识,因此只有综合判断,而不是分析判断才是知识的最基本单元。进而引出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问题。他认为这无疑与《纯粹理性批判》的根本目的更为贴近[7]89~93。然而,这种解读的问题在于,即使承认该定义所处的论证语境是要确定认识的最基本形式不是分析判断,而是综合判断,因为前者“并未给主词概念增加任何东西”,但这个要“增加的东西”,指的仍是超出主词概念之外的概念内涵,因而始终无法绕开概念间的包含结构。
这么看来,依托于概念间的包含结构的第一种定义在三种定义中似乎更为根本。有趣的是,即使我们赞同第一种定义,即概念间包含关系的定义是基础,它实际上也与康德在之后先验分析论中关于判断本质的定义不太兼容,在那里他说:“我从来都不能对逻辑学家们关于一般判断所给予的解释感到满意:他们说,判断是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的表象。”[1]141这里的逻辑学家很可能指的是沃尔夫、迈尔等理性派的逻辑学家。以迈尔为例,他有意抽象掉事物和对象,并认为判断代表的是概念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于一个概念是否能够作为另一个概念的标记(mark)包含于后者[8]81。迈尔显然是想将判断的机能和包含的概念关系都用一个定义表示出来。但很容易发现,其定义只能囊括后来康德意义上的分析判断,而不能包含综合判断。然而,鉴于迈尔是莱布尼茨派,而莱布尼茨又主张所有真判断都在本质上是分析的,那么至少在迈尔的视域中,这个判断的定义并无不妥。康德在先验演绎中意识到判断的一般定义有必要在两个方面进一步扩充。首先,在作为命题的判断方面,以往的定义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只包含主谓判断,或定言判断,而选言判断和假言判断并没有被包含在这些定义之中。其次,在作为思维行动的判断方面,以往的定义只提到概念间的关系,康德尽管在早先的定义中将关系视作一种统一性,但这种统一性由于只涉及通过概念的比较而获得概念的从属,因此它还是分析的。分析的统一以综合的统一为前提,换言之判断的定义需要将统一这种行为的规定扩大,以包含综合统一,例如直观杂多的统一。总之,康德不再对基于概念包含关系的传统判断定义感到满意,甚至认为,就连分析判断的定义也需要被还原到更本质的层面。如此看来,导言中分析-综合判断的定义与先验演绎中判断定义的这种不一贯性,似乎印证了康普·斯密所主张的那种拼凑说(Patch-work)。但这个问题要留待最后一个部分来解答。
《纯粹理性批判》中上述三个定义实在过于简短,仿佛康德在这里只是作出规定性的定义,而没有打算提供进一步的解释。实际上,在康德的逻辑学讲座及笔记中有更多相关的论述。若将其结合起来看,它们似乎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这三个定义的第四种定义。也许我们可以从中找寻解决这些争议的线索。
三、被忽略的第四种定义
王良指出,制定新旧动能转换促进条例是贯彻落实省委重大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省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这项立法。这次立法调研,有关部门、单位、企业和人大代表等各方面结合实际提出了一些很有针对性、建设性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三件法规草案具有很好的参考作用。王良要求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和常委会法工委对有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论证,积极吸收采纳这些意见建议,把法规草案修改好完善好,确保法规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为推进全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实现高质量发展等提供良好法治保障。
但长久以来这些文本一直被大多数康德学者所忽略。其原因主要在于,它们均来自康德的逻辑学相关文本(包括不同时期的逻辑学讲义及笔记),而不是批判时期的主要文本。在英美康德研究者之中,对康德逻辑思想的关注本来就寥寥无几。造成这种忽视的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康德的逻辑学观点被认为仍未脱离“广义的亚里士多德逻辑传统”;其次,当代学者通常对康德将其先验逻辑建立在形式逻辑所提供的框架之上的做法存疑,认为不过是一种“偏执的建筑术”[9]xv-xvi。但实际上,康德在几乎贯穿其整个学术生涯的各个时期的逻辑学讲座中,不仅没有对迈尔的教科书照本宣科,反而一直采取批判性的态度。更重要的是,他时常会将其正在构思,或已经出版的批判哲学的观点融入到对传统逻辑的批判中。于是在《耶舍逻辑》中,与形式逻辑正文的内容相比,更大的篇幅被留给了导言——这部分严格意义上并不属于形式逻辑的内容。因此,康德的逻辑学文本不仅有助于澄清其批判哲学的观点,也有助于追踪其思想变化的整个过程。
对这些文本进行比对后可以发现,康德的第四种定义早在18世纪60年代就已经萌芽。康德认为:“所有分析判断教给我们的是早已在概念中,但只是模糊地想到的东西;综合判断则教给我们应当被思考为与概念结合的东西。在每个判断中,假设主词概念是a,我在对象x中想到它,而谓词在分析判断中被视作a的标记,在综合判断中被视作x的标记”[10]85。
“十一五”期间,我国原煤入洗能力从7.5亿t/a增加到17.8亿t/a左右,原煤入选量从2005年的7.03亿t增长到2010年的16.5亿t,净增9.47亿t,增长了135%。原煤入选率从长期徘徊在30%左右增长到2010年的50.9%,提高了20百分点。建成投产的选煤厂1 800多座。
在这里,康德解释了第二种定义,这个定义实际上关乎的是判断的真理性。如果判断的确定性,或真理性根据概念间的同一性即可得出,那么为分析判断,这时候同一律是作为真理的原则出现的。如果真理性不基于同一律,那么为综合判断。
康德在另一条笔记(4634,1771—1776)中以具体的例子进一步阐明了这种分析/综合判断的定义:
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等运营商的国际出口,基本设置在北京、上海、广州,其他城市均没有设置国际出口,采集如下图:
康德的第四种定义出现在他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讲义的笔记之中(例如1764—1766期间写就的笔记3127和3738,1772—1773年的4634,以及1800年经康德授权、并由耶舍所编辑出版的逻辑学讲义①这些日期是由学院版康德手稿笔记的编辑阿迪克斯(Adickes)根据特殊的方法——“自然地理学”(physical geography)来最终敲定的。但阿迪克斯的骤然离世使他未能兑现在最后一卷为其断代法提供详细论证的承诺。尽管如此,在已出版的卷次中,他仍在具体实施的层面上展现了其方法的合理性,因而为当代康德学者普遍接受(相关历史见Immanuel Kant:Notes and Fragment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xxiii-xxviii)。)。他在这些笔记中提出了一个与前三种全然不同的,以概念的外延为基础的定义。
与《纯粹理性批判》中的三种定义相比,上述第四种定义的最大差别在于:不仅综合判断,就连分析判断也是从根本上与对象x有关。尽管对象在对分析判断进行逻辑分析时可以省去,因此显得我们似乎可以仅仅通过对主谓概念的内涵关系进行辨析就能得出这个判断。但康德在上述笔记中清楚地表明,分析判断中主词和谓词的关系最终是以外延、即以包含在主词之下的对象,而不是该概念的内涵、或包含在其下的分概念为基础的。主词之所以能被包含在谓词之下,或者说谓词之所以被包含在主词之中,从根本上是因为主词所表象的对象同时构成谓词概念的外延。因此,分析与综合判断的区分就不单纯是概念之间的包含/不包含关系,而在于主词概念之下所表象的诸对象与谓词概念之下所表象的诸对象之间,或外延间的重合程度的差别。
如果我说:物体是可分的,这意味着:某物x,我在诸谓词下认识它,这些谓词共同构成物体的概念,我也通过可分性这个谓词来认识:xa是与xb等价的。现在a和b都属于x。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要么b早已在概念a之中,并构成该概念,要么b属于x而不被a包含。第一种情况下,该判断是分析的,在第二种情况下是综合的。[10]149
康德的这个外延定义反映了判断作为思维活动的本质。判断是思维的活动,而不是直观的活动,思维是通过概念进行的,而判断就是将这些概念必然地统一起来。在笔记3051中,康德将判断视作一种归摄(subordinate)的行为,它与直观的连结(coordinate)不同,前者是一直垂直的关系,后者是水平的关系[10]60。当然,归摄既可以是概念的归摄,也可以是对象的归摄,前者最典型的活动就是将低级的概念归摄到高级的概念之下,形成定言判断。同时康德也认为结果可以归摄到原因之下,形成假言判断;部分归摄到整体之下,形成选言判断。所以,归摄是判断活动的根本行为。当时的逻辑学家,如迈尔和沃尔夫显然也同意这个主张,因为在他们看来,所有概念构成一个垂直的种属等级,将低级的概念归摄到高级的概念之下就能得出所有真判断。但康德认为这种对判断的看法过于狭隘,有很多判断例如“两点之间直线最短”显然不属于这个定义,我们不能单纯通过分析两点之间直线的概念,就得到短的概念,主谓概念之间并不必然是种属关系。因此要找第三者x,这个x只能是对象,通过将对象归摄到概念之下的行为就能解释诸如后面这类判断。显然不是所有判断都能用概念的归摄解释,但所有的判断都包含将对象归摄到概念的活动,所以只有后者才是判断作为思维活动的本质。这实际上是与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核心部分中对判断的定义是一致的。在形而上学演绎中,康德将判断视作“一个对象的间接的知识”,即判断从本质上是用概念去归摄对象的认识活动,因此是知性的活动[1]A68/B93。正是基于这个定义,知性才被视为一种“作判断的能力”[1]A69/B9,范畴才能以判断形式为线索抽引出来。而在先验演绎中,判断被定义为“使给予的知识获得统觉的客观统一性的方式”[1]B141。而客观统一性也就是统觉的先验统一性使一切在直观中给予杂多结合在一个客体概念的统一性。正是这个定义使判断的形式(当判断形式用于统一直观杂多就是范畴)成为统觉所体现出来的条件,最终证明范畴的客观有效性。所以,这两个对判断本质的阐明对于康德的先验演绎而言至关重要,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康德对传统判断定义的超越,因此它们代表了康德本人对判断本质的核心思想。而只有第四种定义才与之相匹配,因为只有第四种定义才以对象的归摄为基础,前三种定义甚至没有深入到概念的归摄层面,而停留在对作为命题的判断的静态分析。
这种定义最形式化的表达见于《耶舍逻辑》(耶舍在这里显然参考了笔记3127,特别是后半部分):
其确定性基于概念(谓词与主词的概念)的同一性的命题,叫做分析命题。其真理性并不建立在概念的同一性之上的命题,必须被称为综合命题。
物体概念(a+b)应归之的一切x,广延(b)也应归之于它”,这就是分析命题的一个实例。物体概念(a+b)应归之的一切x,引力(c)也应归之它。这是综合命题的一个实例,综合命题在质料上增加知识,分析命题仅仅在形式上增加知识,前者包含这规定,后者仅仅包含逻辑谓词。[9]607
与《纯粹理性批判》中分析/综合判断的三种定义相比,这个定义最明显的区别是康德引入了变量x,它在此指代的是判断所表象的具体对象。换言之,如果一个判断的谓词概念是主词概念a的标记,那么该判断为分析判断;如果一个判断的谓词概念是主词a所表象的对象x的标记,则为综合判断。所谓的标记(mark)是传统逻辑的术语,主要是指能够在众多概念中区分出某一个概念的特征,标记在这种意义下实际上是包含在该概念之下的一个分概念。所谓一个概念包含在另一概念之下,就是指后者作为内涵在前者之中。因此,这里对分析判断的定义仍是以包含关系为基础,与第一定义是一致的。但是,标记除了有纯粹形式逻辑的含义外,康德还赋予它认识的含义——“标志是部分表象,它本身是认识的根据。它要么是直观性的(综合的部分):作为直观的一部分,要么是推论性的:作为概念的部分,此为分析的认识根据”[10]41。所以,作为对象的标记指的就是由直观所给予经验对象的属性或部分,例如手之于人,我们可以通过“拥有手的”来认识人[10]41。
接着康德分别用分析判断“物体是有广延的”和综合判断“物体是有引力的”来进一步阐明。变量abc在这里不再像上两处那样直接代表主词或谓词概念,而是代表这些概念中所表象的标记,而x仍然代表判断所表象的对象。在分析判断中,主词概念、“物体”是由(a+b)标记所构成,而x为其所表象;与此同时,谓词概念、“广延”由b标记构成,x也为其所表象。而在综合判断的例子中,主词概念、“物体”也是由(a+b)标记构成,而谓词概念、“引力”由标记c构成,x作为对象为abc标记所表象。可以说,康德在这里为分析和综合判断下了一个清晰且完整的形式定义:分析判断——概念(a+b)应归之的一切x,概念(b)也应归之于它;综合判断——概念(a+b)应归之的一切x,概念(c)也应归之它。
首先,康德在这里使用的例子是一个分析判断,“物体”作为主词概念,他用a来指代;“可分的”、或“可分性”是谓词概念,用b指代;这个句子所表象的对象依然用x来指代。在上一个笔记中,康德依然使用主谓概念的包含关系来定义分析判断,但在这里,他引入了对象x来说明分析判断中两个概念的关系。xa指的是对象x属于主词概念a,即为a所表象,而xb指该对象属于谓词概念b,被b表象,因此这个对象x在这个判断中,既被a、“物体”所表象,也被b、“可分的”所表象。但“xa是与xb等价的”这一句意谓不明,康德也许想要说的是一种同一性,即将x视作物体的同时就相当于将x视作可分的,因为可分性是物体概念的构成成分,b早已在a之中。
这代表了一种分析关系,即“b早已在概念a之中,并构成该概念”,a在b之中,作为其构成成分,实际上是说:b是a的逻辑标记,属于a的内涵。而另一种关系是综合的关系,“b属于x而不被a包含”。也就是说,谓词概念b和主词概念a都是对象x的认识标记,但它不同时是主词概念a的逻辑标记。前一种关系构成分析判断,后者构成综合判断。可以看出,尽管这个定义比上一个更加完善明晰,但其根本立场并没有改变:谓词概念是主词概念标记的那些判断是分析判断;谓词概念是主词概念所表象的对象的标记的那些判断则为综合判断。但是在这里,对象x也用来解释分析判断,而不是仅用于解释综合判断。
总而言之,第四种定义,即外延定义实际上优于《纯粹理性批判》中给出的三种定义。因为它体现了判断的本质活动,即将对象归摄到概念下的活动,也与康德对判断的定义相契合。基于此,康德能同时为分析和综合判断下积极的定义,这是上述三种定义所做不到的,它们只能给综合判断下消极的定义。另外,在康德看来,外延定义又能与内涵定义兼容,例如在分析判断中,仍可以单凭概念标记的比较,或同一性来定义,康德也试图将两者通过形式化的表达结合起来,而不是舍一取一。
四、重新考量对康德分析判断的反驳
下面我们结合康德的上述四种“定义”来重新考量上文提到的那些攻击,并尝试为其辩护。首先考虑的是关于概念的包含关系意味不明的指责。弗雷格认为康德没有能够真正说明这种包含关系,只是将其视作一种空间的隐喻关系,即“将原本放在房间里的球拿出来又放回去”[11]101。但是康德在第四种定义中清楚的指明了概念的包含关系是基于概念本身的内涵结构,即标记(康德习惯用abc来指代),而这又是以归摄到该概念之下的对象(xyz)为基础的。换言之,康德是以概念结构,包括内涵和外延的,来解释这种包含关系的。这种关系如果用空间关系来隐喻更类似于一种垂直的树形结构。概念内涵层面的包含是康德从传统逻辑中继承的,而将概念的外延引入作为更根本的结构则是康德的独创,但此举已经使他走出严格的形式逻辑,迈入一种新的、认识论的逻辑,即先验逻辑之中了。因为形式逻辑是从被给予的概念开始,它不涉及概念与对象的关系。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回答上述汉拿所总结的第五个问题。著名批评者蒯因认为康德的分析判断是“单凭意义,独立于事实为真”。而意义在他看来要么是根据定义,要么是同义性或语义规则[6]21。但正如学者汉拿所正确指出的,蒯因攻击的与其说是康德,不如说是“伊曼努尔-卡尔纳普-弗雷格”[4]172。事实上,以逻辑定义和同义性为分析性根据,此观点分属弗雷格和卡尔纳普的观点。相反,在康德看来,除了数学概念外,任何定义都只是不完全的定义,因此不可能作为基础意义出现。但是标记作为足以区分概念的工具则可以充当思维的必要手段,而之所以能获得这些标记又是以对象的给予为前提的。因此康德的包含关系不是以定义、同义性或语义规则为基础的,意义在他看来就在于概念或判断所表象的对象。所以蒯因与其说是对康德的分析性进行攻击,不如说是对弗雷格和卡尔纳普的观点进行攻击。
1 文献总体情况 共检索到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19篇,其中个例报道17篇[3-19],共18例患者,临床研究2篇[20,21]共16例患者。17篇个例报道中,中文文献3篇共3例患者,英文文献12篇、西班牙文文献2篇,共15例患者。2项临床研究均为英文文献,一项为回顾性临床研究共8例患者[20],另一项为随机对照临床试验共8例患者[21]。患者涉及15个国家,其中新西兰16例,中国3例,澳大利亚3例,美国、阿根廷、巴西、法国、韩国、加拿大、黎巴嫩、墨西哥、瑞士、土耳其、意大利、印度各1例。
其次,上文提到,蒯因和汉拿等人质疑,康德将分析/综合判断的关系视作主谓之间的包含关系似乎过于狭隘①持有这种观点的其实还包括James Van Cleve和Sun Joo Shin,当然与蒯因从其实用主义逻辑出发的批判相比,Van Cleve的批评考虑到康德对判断的一般分类,而Sun Joo Shin则根据皮尔斯的数学推理来理解康德所做的区分(见James Van Cleve:Problems from Kant,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1999,(1);Sun Joo Shin:Kant’s Syntheticity Revisited by Peirce,Synthese,1997,(1).)。。尽管康德在这里谈到的是“一切判断”,但事实上他只谈论了以主谓概念为结构的定言判断。这与传统理性派逻辑学家,如沃尔夫和迈尔对判断的定义是一致的,他们认为判断就只包含主谓结构的命题。而康德主张除了主谓结构的定言判断,基本的判断类型还包括选言和假言判断。事实上,康德在他手上的第一版《纯粹理性批判》中曾在这里批注“此论述也适用于假言和选言的综合判断以及否定的定言判断”[12]14note。那么很显然,康德之所以在这里只关注肯定的定言判断,首先是为了找出读者(例如理性派形而上学家)可以接受的前提;其次康德本人认为定言判断是基础,在这里选择定言判断为例是出于其代表性和简洁性,不能理解为康德将所有判断归结为定言判断,用主谓之间的包含关系定义一切关系。这种观点并没有出现在康德任何文本之中。相比而言,上述外延定义却能很好地推广到假言判断和选言判断中。康德本人也主张,对象的归摄可以适用于一切判断,包括假言和选言。构成假言判断前后件以及构成选言判断的选言支的都是判断,尽管在那些作为质料的判断之中的概念不是种属的包含关系,但每个质料判断都有其所表象的对象,通过比较归摄在这些判断之下对象,即外延的范围,原则上就能区分这个选言判断或假言判断是否就是分析或综合判断。另一方面,从上述第四种定义可以看出,康德并不认为他的四种定义是不相容的,于是他试图将其结合在一个形式化的表述之中。从上述分析可知,包含关系可以用概念的外延来解释,那么同一性既可以按照标记的同一性来理解例如(a+b和b),也可以根据外延是否重叠来理解;而所谓分析判断不增加知识就在于作出判断时,主词的内涵并没有改变,也没有将更多的对象包含于其下。
最后让我们来探讨关于主观心理学的指责。这个指控主要集中在第三个定义上。其中“模糊地被想到”、“不曾想到过”似乎指的是特殊认识主体的活动,或心理过程,因而不够逻辑化。与康德同时代的马斯(J.G.Maass)则认为黄金这个概念所包含的子概念对于每个人也许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多些,有些人少些,因此就此作出的判断是分析还是综合的是因人而异的,具有主观性。首先要注意的是,相比第三种定义,本文的第四种定义显然完全能够满足批评者们对抽象的逻辑定义的要求。但尽管如此,它还是基于作判断的行为——一种将对象归摄到概念之下的行为。这种行为并不是经验性的,而是属于一般思维活动的,只有经验性的活动才属于康德所反对的心理学解释,而一般思维的活动由于属于先验知识可能性的理论,因而可以与心理学区别开来。而就马斯的异议,康德的学生舒尔舍(J.G.Schulze)也提供过解答:在马斯的例子中,他们实际上是在用同一个词表示不同的概念,因此在作不同的判断。所以这并不影响理性在其本质活动,即判断,中的两种根本区分——分析和综合[13]19。
五、结论与意义
总而言之,上述分析-综合判断的第四种定义是一种以概念的外延,以及以对象的归摄活动为基础的定义。其优势在于,它更符合康德在先验演绎中所提出的全新判断定义——一种属于认识论逻辑,即先验逻辑的定义,因此可以被视作更贴近康德本人真正的观点。此外,它使得若干对康德这一区分的攻击自行失效,因为后者基本上是在概念的内涵定义的立场上展开的。
从实现创意角度来说,全画幅传感器也拥有一些优势,比如,在使用相同视角的镜头以相同的光圈拍摄时,全画幅传感器拥有更浅的景深,也就是通常说的背景会更虚。不过,现在的APS-C系统往往配备了超大光圈镜头,这让全画幅相机的优势只有在使用大光圈的定焦镜头时才会显现出来。
意象,就是客观物象经过作者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作者对外界的事物心有所感,便将之寄托给一个所选定的具象,使之融入作者自己的某种感情色彩,并制造出一个特定的艺术天地。千百年来,意象逐渐汇聚成了中国古代诗歌一道亮丽的风景。
但也许有人会质疑,既然这第四种定义才更贴合康德本人的立场,那为何不直接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导论部分直接提出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更宏观的论证结构出发去理解康德。众所周知,康德《纯批》的核心任务就是通过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重建来确立科学的形而上学,而首先要做的就是驳斥传统形而上学的那种以概念为中心,因而是以分析判断为认识结果的“逻辑-形而上学”的知识模式①这种以概念为中心的认识模式是与康德同时代的理性派哲学家核心观点,基于这个传统,沃尔夫等逻辑学家认为只有通过对无限实在概念进行分析和阐明来使其变得清晰明白,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而那些经验对象和经验命题无非是不清晰的观念,它通过分有终极实在而获得有限实在性,于是一切真理都是概念性的,因而都是分析性的。。正如邓晓芒、杨祖陶先生所言,在这一部分中,康德要重新确立“知识的构成形式、特别是最基本、最简单的知识单位的逻辑结构形式”[14]52。它既不是理性派所认为的概念,也不是经验派所主张的感觉印象,而是判断。但不是所有的判断都是知识,按照传统逻辑对判断的定义,即概念间的关系,所有的判断只是分析判断,由于其谓词包含在主词之中,因此并不增加知识内容;另外那些谓词不包含在主词概念之中的判断,即综合判断,通常是经验判断,它扩大了知识的内容,却缺乏必然性。因此,康德在这里展现了一个困局:即真正科学知识对最基本单位的要求(既要增添新的内容,又要有必然性)与传统形而上学家的工具论,即普通逻辑判断定义和分类对此的无能。进而自然地从分析判断-综合判断的区分,进入到先天综合判断的可能性问题。因而康德实际上是从传统理性派的“形而上学-逻辑”走向革命性的先验逻辑,最后反过来确立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当然康德的论证是循序渐进的,在这个开端部分,仅仅让还没从独断论的美梦中醒来的读者意识到这个困局,以及看到康德所提供的可能出路的合理性就已经足够,如果提前引入先验逻辑中那种有悖于传统的判断定义,以及相关的判断区分反而不利于整个论证的展开。
对康德分析-综合判断第四种定义的重建不仅能够很好地回应一些针对康德分析-综合判断的固有攻击,使那些以概念内涵为基础的攻击自行无效,同时还具有多方面积极意义。在内容上,它体现了康德的逻辑学,尤其在判断理论方面的革命性。康德摆脱了对命题的静态分析,深入到其背后作为思维基本活动的作判断,以及判断能力的层面。在研究方法上,对第四种定义的重建带来了一个启示,即对待康德的某个概念,要从整体的角度去理解。用康德本人的话说:“任何一种哲学的阐述都有可能在个别地方被人揪住(因为它不能像数学那样防卫严密),然而,这个体系的结构作为一个统一体来看,却并没有丝毫危险”[1]BXLIV。所以,也许一种全息性解读会更适合于康德研究。
[参 考 文 献]
[1]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M].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Immanuel Kant,Arnulf Zweig.Correspondenc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4]Robert Hanna.Kant and the Foundations of Analytic Philosophy[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5]R.Lanier Anderson.Containment Analyticity and Kant’s Problem of Synthetic Judgment[J].Graduate Faculty Philosophy Journal,2004,(25).
[6]Willard V.O.Quine.Two Dogmas of Empiricism[J].Philosophical Review,1951,(1).
[7]Henry E.Allison.Kant’s Transcendental Idealism,rev.ed[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4.
[8]Georg Friefrich Meier.Auszug Aus Der Vernunftlehre[M].Halle:Johann Justinus Gebauer,1752.
[9]Immanuel Kant.Lectures on Logic[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10]Immanuel Kant.Notes and Fragment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11]Frege.The Foundations of Arithmetic[M].trans.J.L.Austin.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53.
[12]Immanuel Kant.Critique of Pure Reason[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13]Quoted in Van Cleve.Problems from Kant[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14]杨祖陶,邓晓芒.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中图分类号]B516.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19)06-0078-07
[收稿日期]2018-12-3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资助项目:12&ZD126
[作者简介]潘文哲(1985-),男,广东韶关人,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张媛媛]
标签:康德论文; 概念论文; 定义论文; 主词论文; 谓词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欧洲哲学论文; 欧洲各国哲学论文; 德国哲学论文;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资助项目:12&ZD126论文; 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