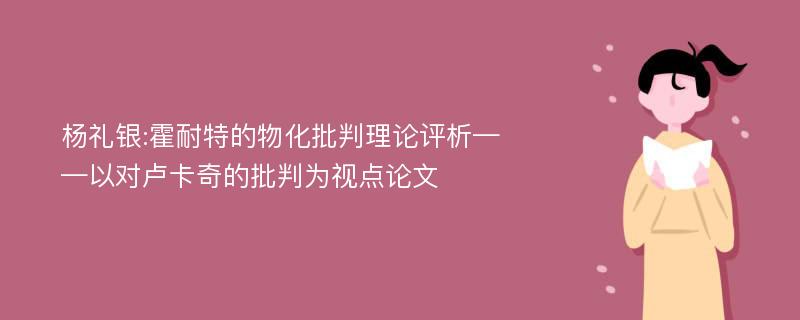
[摘 要]在承认理论的视域中,霍耐特分别从概念界定、解释策略和论证路径三个角度对卢卡奇的物化批判理论进行了深刻批评。在此基础上他以承认为基本范式,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三个方面对物化理论进行了重构,主张物化的实质是对承认的遗忘。霍耐特对卢卡奇的批判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物化批判的承认视角,在规范方面拓展了物化批判理论;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定局限性,他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向,既不能揭示物化的社会根源,也找不到克服异化的根本力量。
[关键词]霍耐特;卢卡奇;物化;承认
物化批判最早是通过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被广泛了解和认可的,之后经过法兰克福学派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20世纪社会批判的核心议题之一。当世界历史的车轮驶进21世纪,物化现象并没有消失,而是转变了形式。卢卡奇的物化批判是否还能够被用来分析当代物化现象?法兰克福学派霍耐特对此持怀疑态度。因此,他重新思考了卢卡奇提出的“物化”概念,以承认理论为分析框架,通过对卢卡奇“物化”的多方面批判,试图以一种新的方式重建物化批判理论。
一、霍耐特对卢卡奇物化批判理论的质疑
不同于卢卡奇所在的20世纪上半叶帝国主义战争与民族解放的时代,霍耐特所处的是20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全球化与利益多元化的时代。面对新的时代问题,霍耐特重新审视了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对其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剖析。主要从如下三个方面对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进行了质疑。
(一)在概念界定上批判卢卡奇将客观化等同于物化
在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思想的影响下,卢卡奇认为,随着商品生产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统治地位,“物化”现象出现并盛行开来。他将物化定义为:“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1]150虽然卢卡奇一再强调,这种物化是在商品生产成为普遍现象的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然而物化的核心要义在于对象化。因此,在他看来,只要商品生产劳动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就必然会产生与人相对立的控制人和奴役人的力量,进而造成物化。
在霍耐特看来,卢卡奇的这种界定缺乏范畴分类工具,没有对客观化和物化进行区分,导致其对物化过程的理解既不够深入也不够抽象。他指出,卢卡奇将物化现象泛化开来,即“不论在何种情况下,只要客观化地认识其他人或事理取代了承认,就发生了物化”[2]86,以至于物化已经成了人类的第二自然。不过霍耐特从正反两方面评价了卢卡奇的这种界定,认为他将物化与客观化等同起来产生了两个结果。其一,将资本主义的合理化进程等同于物化过程来进行历史哲学批判,既不将物化视为一种错误认识,也不将它视为一种错误道德,而是将它视为一种客观的错误实践。它表现为“一种仅止于旁观的行为习惯,在此状态中,不论是对自然环境、社会共同之成员、还是自身的人格潜能,主体都代之以一种疏离且情感中立的态度”[2]23。代替这种错误实践的是一种共感参与的社会实践。对此,霍耐特表示赞同。其二,这种将客观化和对象化等同于物化的观点忽略了社会实践中的承认基础,因而没有揭示出物化的真正规范基础和克服路径。借鉴西美尔在《货币哲学》中的看法,霍耐特指出,即使是在去个人化的金钱交易中,只要接受对方为交易对象,就必然会记得对方是具有各种人格特质的人,而非具有物之特性的物,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就存在着共感参与的社会实践。这样,“去人格化的社会关系预设了我们对匿名他者的根本承认”[2]128,这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不是纯粹的物化关系,并不会直接导致物化的产生。在霍耐特看来,“只有某种存在事实上并不具备事物的典型属性、却被作为事物来认识或对待时,才存在真正的物化”[3]。因此,对象化、客观化以及合理化这“三化”虽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的必要阶段,但并不是造成物化的真正原因。这“三化”是商品生产的认知形式,它们并不会直接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并不必然产生物化形式,产生物化的是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实践的具体形式。”[4]这种具体形式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承认关系。因此,霍耐特批判卢卡奇从商品生产出发对物化的分析只看到了工具理性对社会全面的控制,并没有看到物化的实质在于人与人之间承认关系的扭曲。
因此,借鉴卢卡奇的错误,霍耐特主张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探讨物化的标准。他运用了其早先提出的承认分析工具,依据承认的类别对物化作了新的界定:“此种对承认的遗忘,我们——从一个较高的层面来延续卢卡奇的初衷——可称之为‘物化’”[2]88。霍耐特认为,如果遗忘了预先存在的原初承认,则会导致主体以无感情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一切事物,周围一切在主体眼中成为某种工具化的存在,成为无感受的纯粹客体。只有承认被遗忘,物化才会产生。换句话说,正是没有运用承认这一根本范畴,所以卢卡奇的物化概念缺少立论的根本点。
(二)在解释策略上批判卢卡奇从经济的单一维度出发进行理论预设
再次是经济发展中的生产方式调整。壮拳文化作为壮人的传统身体文化,理应在壮人恋土保守的性格中得以确切传承,但经济发展中的生产方式变了。当壮拳不再是经济洪流中的“枝头俏”,也就面临着被淘汰的境遇。“爷爷教拳要是收徒弟学费,咱家早就是这条街最富的了”“没时间学,学了也不能当饭吃”[27],恪守古训、弟子五千、曾经风光无限的壮拳大师农式丰在面对当今生产方式改变的情况下也难逃扼腕垂泪、无奈孤独的命运。
在评价卢卡奇的物化批判理论过程中,霍耐特尽力将物化批判引向其承认哲学框架。沿袭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这一理论框架强调主体对他者(世界、他人与自身)预先的承认优先于主客二分的对象化认识方式和实践模式。因此,霍耐特一方面认为,卢卡奇对以对象化为核心的物化批判,是基于对非物化实践的追求。这种“真正的实践”与其所主张的基于承认的实践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一个实践主体应作为‘有机整体’,以一种‘参与其中的’、‘合作的’方式经历到外在世界。”[2]26这种实践被霍耐特称之为“共感参与的实践”。与海德格尔的“牵挂”、杜威的“互动”等概念一样,这个概念的预设对于卢卡奇批判和超越主客二分的思维框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2]37就此而言,霍耐特并不认为“卢卡奇采用主客体分析模式”[7],而是直接承认了卢卡奇对主客对立模式批判的态度。然而,霍耐特不赞成卢卡奇的是其对主客二分批判的论证框架。在他看来,卢卡奇既然预设了参与实践的基础地位,就应该将这一点贯彻到底,而不应该再回到费希特等的同一哲学框架中将人类的实践视为主体创造的客体,来追求阶级意识与历史客体的统一。因此,他说:“毫无疑问地,在今日看来,卢卡奇的同一哲学取径使他失去了以社会理论来证成其‘物化’批判的机会。”[2]27也正因为如此,在霍耐特看来,卢卡奇与真正的物化批判失之交臂,既不能揭示物化的真正内核,也不能找到克服物化的有效路径。
另一方面,霍耐特批判卢卡奇在论题上进行预设。卢卡奇认为,经济领域的物化必然会影响其他社会领域,因此商品交换所导致的物化必然会扩展至其他各领域,这样,各种物化关系都可以还原为经济关系,“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整个社会(至少按照趋势)隶属于一个统一的经济过程”[1]159。对此,霍耐特却认为,卢卡奇的这种论证实际上是先验的推理,而非具体经验的分析,后者预设了“他原先仅在资本主义市场交流中发现的物化现象,将会像疾病感染一般地,扩散到所有社会生活世界里”[2]129。而在实际情况中,卢卡奇的论证并不能合理解释非经济领域的物化,例如种族歧视、人口买卖等。在霍耐特看来,这种过度重视经济因素的视角具有片面性,以至于卢卡奇对于各种意识形态上的偏见视而不见,也无法正确看待造成物化的其他社会因素。因而,霍耐特批判卢卡奇采取经济优先性的立场对物化进行分析,他认为,这一立场导致卢卡奇从商品交换这个单一的维度出发,将经济领域的物化总体化了。
(三)在论证路径上批判卢卡奇未能完全摆脱主客二分框架的囹圄
霍耐特认为,卢卡奇早期的浪漫主义的反资本主义倾向就促使他尝试摆脱主客二分的局限,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分裂状态进行了审美维度的描述,针砭时弊地指出了文化整合的乱象,因此,卢卡奇的早期著作被他称为“批判理论的地震感应器”[6]16。在《历史与阶级意识》这本书中,卢卡奇超越了浪漫主义的视角,以历史哲学的论证路径接续了这种对主客对立的思维框架的批判,然而最终仍然没有摆脱意识哲学的囹圄,自身也充满了矛盾。
改善受端电网调峰裕度的特高压直流外送风火协调调度//崔杨,赵玉,邱丽君,王铮,仲悟之//(15):126
奏鸣曲K330的第二乐章调性以F大调为主,速度改为如歌的行板,曲式结构与第一乐章相差不大。呈示部主题优美,经过再次的反复延至展开部,主题由F大调转为同主音的f小调,跟第一乐章一样的出现了旋律上的对比,经过两次反复到达曲子的再现部,调性又改为了F大调,对比第一乐章,这一乐章更像是对人的一种诉说,这也将莫扎特音乐里细腻柔软的一面完美的展现出来。
对于物化如何成为人类的第二自然这一根本问题,霍耐特从概念范畴预设和论题预设两方面对其进行了批判。在概念范畴上,他认为卢卡奇“倾向于将不同面向的物化视为一个不可分的整体”[2]128,虽然卢卡奇尽力区分了三个不同方面的物化概念,但他未处理这三者之间的细致区别。不论是被量化的客体、被工具理性控制的人,还是只从经济利益和价值出发被看待的主体自身能力和需求,在卢卡奇看来都是“化他者为物”。基于此,卢卡奇顺理成章地进行理论预设,认为任何一种物化形式的出现都会导致另外两种物化形式的跟进。而霍耐特却认为,“不同面向的物化彼此之间不必然具有关联性”[5]77,他指出,这三种形式只有人与人之间的物化和人与客体之间的物化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内在相关性,而其他各种形式的两两组合之间都不必然相关。人与人和人与客体之间物化的相关性主要体现为,对人与人之间承认关系的遗忘会间接导致他人赋予客体的的各种意义也相应被忽略。也就是说,在人与人的物化关系中也包含着人与客体的物化。同时,对他人所赋予客体之意义的遗忘,也会导致对他人承认关系的间接遗忘。霍耐特还认为,虽然人与人和人与客体之间的物化有一定的关联性,但两者仍然存在一定差别。他指出,前者是直接物化,是我们直接遗忘了对他人的承认;而后者是间接物化,是我们遗忘了他人所赋予客体的各种意义,遗忘了他人对于客体的先行承认关系。总之,霍耐特对于这三者在概念上的区分不同于卢卡奇的笼统对待。
二、霍耐特承认视角下的“物化”内涵
在对卢卡奇物化理论进行批判的过程中,霍耐特重新界定了物化概念,形成了自己的物化批判理论。他以承认理论为框架,把对承认的遗忘作为物化的实质和关键。他指出:“物化就是预先承认的遗忘,我把它作为概念的核心。”[5]58可见,在霍耐特这里,理解物化的关键在于对承认的理解。所谓承认,“是指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共同体之间、不同的共同体之间在平等基础上的相互认可、认同 或确认”[8]3。在认知与承认的关系中,霍耐特坚持承认优先性,主张“承认先于认知”。他认为,认识活动始于对他者采取承认的态度,只有与所认知的事物保持情感上的联系,才能避免将其看作纯然的客体,才能避免物化。如果遗忘了这种态度,将会把他人视为无感情之物,采取纯然旁观式的态度对待,物化就因此产生。
霍耐特首先批判了社会交往中存在的物化现象。这种物化体现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物化,导致人与社会处于分裂的状态,“这是因为,人们之间的必要联系只是在认知上被生产出来,而不是从情感上被体会到”[6]5。也就是说,人们遗忘了先行的承认关系,采取旁观式的态度处理社会交往中与他人的关系,缺少了情感上的投入。
卢卡奇划分了三个方面的物化,即人与客体、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的物化,同时他把这三者之间的物化看作相互作用的社会过程。在卢卡奇看来,最先出现物化现象的是经济领域,也就是人与客体之间的物化,进而社会政治体制、人的思想意识领域也会受其影响,呈现出整个社会全方位的物化状况。他指出:“正像资本主义制度不断地在更高的阶段上从经济方面生产和再生产自身一样,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物化结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决定性地沉浸入人的意识里。”[1]161因此,卢卡奇也就理所当然地把经济领域中的物化推演至其他各领域,经济对政治文化的渗透必然造成社会生活全面的物化。
霍耐特从两个方面对人与人之间物化的具体成因进行了详细说明。一种是目的理性行为导致的遗忘,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过于狂热地追求某个特定目标,以至于忽略了原初的动机与目的。他以网球比赛为例作出解释,在比赛中选手只专注于胜负而忘记了对方是他的好朋友,也忘记了这场比赛基于他们的友谊关系才得以进行,内心只有赢得比赛这个单一且绝对的目标。“当认识的目的脱离了原先的脉络,认识态度便会渐趋偏狭而僵化”[2]94,这会造成情境中其他要素在视线中淡化甚至消失,导致人际交往的物化。另一种则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偏见或刻板观念造成人们对原在承认的遗忘,这种僵化的思考范式造成对事实选择性的解释,对某些重要因素的忽视。例如,性别歧视、种族歧视等,都是受长期形成的历史观念的影响而形成的思想上的偏见,是人的信念体系遭受的物化。霍耐特认为,虽然这两种情况都是对先行承认的遗忘,但两者之间也存在一定差别。第一种情况是个人内在因素表现在特定外在实践活动中的物化,而第二种情况是外在决定条件造成个人内在信仰体系的物化。可见霍耐特对卢卡奇的物化进行了拓展,卢卡奇只看到了第一种实践活动中的物化,而霍耐特则揭示了二者不同的成因,特别注意到了第二种意识形态上的偏见。
霍耐特认为,侦探主义以观察的态度建立自我关系。在侦探主义模式下,主体的内在意图呈现为先验存在,主体只需像观察客观事物一样观察自己的内心状态,主体对于自我的把握只是寻找和发现的过程。霍耐特之所以认为这种模式是自我关系物化的表现,有两方面原因。其一,这种模式将主体视作认识的器官去窥探自己的内心世界,然而这种感知自我的活动会形成相应的心灵状态,这种状态又需要更高一级的知觉活动去感知,最终导致感知能力的无限后退。其二,主体的内心状态实际上具有混杂不定、不易被掌握的特点,而侦探主义却将其视为有着固定特点和清晰轮廓的客观实体,因而造成了对自我关系的错位描述。另外一种模式是建构主义,在霍耐特看来,建构主义模式下主体的内心世界是由自我主动建构而成的,主体能够操纵控制自身内在的欲望、情感。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主体的内在心理状态实际是先验存在的,而非自我建构的,主体只能通过语言活动将其表示出来。霍耐特理清这两种自我物化关系之后,提出了介于这两种模式之间的表现主义,他认为表现主义能够恰当说明原初的自我关系。在他看来,表现主义在表达内心感受时必然认同其价值,否则就无法获得通向内心的途径。“任何一个主体若要能与自身处于一种表达的关系,她或他必须先能肯认自我,肯认自我的心理经历值得被主动认识及表达。”[2]117而一旦遗忘了这种自我肯认,就会将自我的内心世界看作纯然的客体对待,就会产生不同形式的自我物化。霍耐特认为,表现主义既没有把自我的内心状态当作僵化固定物去认知,也没有将其视为可制造之物去操控,而是以承认的方式借助语言表达了自我的心理状态。因而,表现主义能够正确描述原初的自我关系,侦探主义和建构主义则是自我关系物化的不同表现。
一方面,从卢卡奇以阶级为主体的历史哲学视角转变为以社会行动者为主体的社会理论视角,揭示了物化的规范性基础,在一定意义上回答了物化在今天为何是社会病症的问题。正如阿尼塔·查里所说,“霍耐特的物化批判基于人类与世界的承认、关心、富于感情的关系,而不纯粹是认知的、被动的态度”[11]249,这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卢卡奇未曾关注的个体情感视角。同时,霍耐特“承认先于认知”的立场补充说明了由世界观、意识形态偏见或刻板的观念造成的物化现象,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卢卡奇未能解释的人口买卖、种族灭绝、宗教歧视等问题。正如学者所言,其理论“不仅适合分析近些年来的群体差异和独特性承认的社会运动,也可以揭示近百年来的要求基于种族、民族、性别以及生理能力的社会平等的社会运动”[12]93。
在论证了人际世界存在的物化现象后,霍耐特进一步将物化批判扩展到人与自然之间。他认为,在非社会化的客观世界也存在着以中立的态度、外在的衡量标准看待客观对象的状况,这种待物方式同样是不恰当的。对于此种形式的物化,霍耐特放弃了卢卡奇的“共感参与之实践”范畴,认为卢卡奇用来证明外在自然也有可能被物化的直接取径显然不再堪用,而需要另辟蹊径,将其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物化的延伸和间接反映。他指出,“对他人的先在承认同时包含着尊重他人所赋予客体之各种意义面向”[2]98,即遗忘了与他人承认关系的同时也会相应地遗忘他人赋予客体的意义。在此,霍耐特引用了阿多诺的相关论述证明他的观点。阿多诺认为,幼儿对其所爱之人的情感认同是其认知的前提,这种情感认同还会使其所爱之人对于客观对象的观点长久地留在他的记忆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人赋予对象物的意义会通过幼儿的模仿活动被再次赋予客体。霍耐特借此说明物化自然是对物化他人的转借,而对人之外的客体的承认源于他人对于客体的立场和态度。由此,他把物化自然定义为“我们在认识对象物的过程中不再注意到该物所具有的、源自具体他人观点之种种意义面向”[2]99。这种物化将客观事物看作无生命之物,未看到它们与周遭之人的联系以及所具有的多元意义,遗忘了他人赋予客观事物的先行承认关系。所以,霍耐特把物化自然作为人际世界物化的延伸,通过主体间的承认优位间接论证客体对象的物化。
机构/区域临床试验伦理委员会建设与发展的探讨…………………………………………………… 温珠明等(13):1738
总之,霍耐特认为,物化他人、物化自然以及自我物化这三者形成的具体原因和表现形式虽然存在差异,但究其根本都归结于遗忘了先行的承认关系,采取旁观中立的态度而非共感参与的情感认同态度来看待所面对的对象。由此,我们可以确定他的物化理论建立在承认优位基础之上,离开承认优先性就无法谈物化的生发过程。物化的直接后果是社会冲突模式的变化,即从基于承认的斗争转变为妥协或阴谋。霍耐特不无忧虑地指出:“因此,我们应当注意到,社会冲突变得越来越野蛮,多元承认已经行不通了,其内在的对尊严的保护原则已经荡然无存;人们越来越被迫地使用妥协或非公开斗争的方式来获取生存的尊严,但这种仅存的主体间的承认也越来越少有人能够做到。因此,当今的社会冲突变得野蛮化了,其原因就在于为承认而斗争的道德根基在过去几十年内已经遭到严重摧毁,以至于这种斗争愈演愈烈地成为徒有其表的争论。”[9]
三、对霍耐特物化批判理论的评价
由上可知,霍耐特的物化批判理论源于对卢卡奇物化理论的批判,这些批判从主体间相互承认的视角上既拓展了物化批判的社会理论视野,又深化了其规范性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于其理论贡献,学界已有所认识,[10]在此作两点补充。
霍耐特认为,内心世界是物化的第三个场所,主体与自我之间原初的共感态度会被纯然旁观的态度取代,导致主体与自我关系分裂而无法正确认识自己。他使用反向论证的方法,先解释了侦探主义和建构主义所描述的两种错误的自我关系,在此基础上指出表现主义才是自我关系的正常状态,通过正反两种情况的对比证明了自我物化这种有误的偏差状态是存在的。
另一方面,霍耐特的物化批判理论拓展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雏形,对于后期的法兰克福学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霍耐特在对卢卡奇物化理论的批判中,展示出他对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进一步改造和深化。从卢卡奇到哈贝马斯再到霍耐特,批判理论的发展脉络实际上表现为由生产范式到交往范式再到承认范式的转化过程。哈贝马斯虽然超越了生产范式,指出了社会的交往面向,并以交往范式构建起新的社会考察维度,但他停留在话语交往层面,仍然用语言来解释社会主体间的规范性。而霍耐特则超越了语言理论框架,他将交往理性转化为主体间的承认,“从而将哈贝马斯所没有实现的社会批判理论立场和日常道德经验连接起来”[13]306,从社会病理学的角度为批判理论探索新的规范基础,推动了批判理论的新发展。同时,无论是卢卡奇还是法兰克福学派,受韦伯合理性思想影响,都停留在工具主义的解释层面。他们从工具理性的视角对时代作出批判性诊断,而霍耐特以承认的优先性基础为依据,从本体论意义上解释物化,他指出,“在我看来,与人类的本性相关的承认是一个社会本体论事实”[14]353。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会批判理论的解释传统,为批判理论提供了新的方法论维度。
双氧水脱硫处理电解烟气并制备硫酸铝并利用铝灰生产硫酸铝的综合利用技术,在技术上可行、在设备上和实际应用上成熟,在运行费用和经济效益上也有一定优势,与电解铝生产实际和危险废物处置需求非常贴合,具有开发利用价值。
尽管如此,霍耐特的物化批判理论并非无懈可击,我们不能过度拔高它的价值,对此已有学者对他进行过深刻批判。我们以为,这一理论在如下两方面是不当的。
一方面,由于过度批判了卢卡奇的历史哲学论证路径,霍耐特专注于物化的情感投入方面,以至于忽视了其社会物质基础和相应的社会历史条件。他在批判卢卡奇从生产范式出发进行预设时,过于强调文化、心理等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将一切社会不和谐都归结为主体间没有形成相互认同的情感状态。他对卢卡奇过分专注于经济物化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方向,而过度诉诸文化和心理的体验。正如克里斯汀·洛兹所说:“霍耐特物化概念向心理学和规范性基础的转向,使它不可能发现物化的物质基础,更值得可信的是霍耐特无法为现代性内在的社会病理的经济学解释留下空间。”[15]184-200因而,霍耐特所说的物化更多的是心理化的物化,他抛弃了对物化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分析,抛弃了社会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剥削的本质。
另一方面,霍耐特以社会病理学方法代替了卢卡奇的阶级分析方法,从所谓本体论角度进行批判也使得他很难解释预先存在的、先验的承认为什么会被忘却。虽然霍耐特提出,主体持续参与某种单边性实践时会迫使他们把人的“定性”辨别特征撇开不管,而此时主体就会忘记甚至钝化基础承认关系。但他也指出:“即使是今天, 我也不能完全确信这种方法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合适途径。但同时, 我也找不出别的方法来解释把他人视为同类这种根深蒂固的基础认同是怎样被取消的。”[3]因此,从本体论出发,他很难从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找到真正物化的事例,“只有在例外情况下, 当社会达到零点时, 我们才能谈及这些基础承认被取消的情况”[3]。这使他虽然列举过一些例子进行说明,但大都限制在人口贩卖、性交易等极端事例中。同时,他也将卢卡奇所认为的从普遍商品交换出发而产生的物化排除在真正的物化之外,“被卢卡奇视为物化态度主要来源的商品交换, 似乎并不构成忘记基础认同的真实案例”[3]。霍耐特认为,商品交换中的人仍然是被法律所承认的人,享有着最低限度的尊敬,因此不构成真实的物化,而未能看清这最低限度的尊敬是源于资本增殖的需要。他对卢卡奇阶级分析法的抛弃必然使他看不到,在当今新帝国主义条件下,克服异化的根本路径不在于个人行动对承认的再现,而在于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其根本依靠力量不在于单个的个人,而正在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觉醒与联合。
孕妇激素水平的增高,致使静脉中的血流量增加,同时由于妊娠子宫压迫盆腔静脉,影响下肢静脉回流所致。持久站立位工作,妊娠晚期腹内压力的增加,都促使症状加重。当然,这种现象会随孕期的消失而消失。
[参 考 文 献]
[1] [匈牙利]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 [德]阿克塞尔·霍耐特.物化:承认理论探析[M].罗名珍,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3] [德]霍耐特.对物化、认知、承认的几点误解[J].胡云峰,译.世界哲学,2012,(5):114-121.
[4] [美]延森·苏瑟.物化与扬弃——对话阿克塞尔·霍耐特[J].杜敏,李泉,译.国外理论动态,2014,(6):1-4.
[5] Axel Honneth. Reification: A New Look at an Old Idea[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6] [德]阿克塞尔·霍耐特.分裂的社会世界:社会哲学文集[M].王晓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7] 刘光斌.论霍耐特对物化批判的承认理论范式[J].南京社会科学,2016,(3).
[8] [美]南茜·弗雷泽,[德]阿克塞尔·霍耐特.再分配,还是承认?——一个政治哲学对话[M].周穗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9] [德]霍耐特.社会冲突的野蛮化———21世纪初的承认斗争[J].翁少龙,译.学习与探索,2014,(9):8-14.
[10] 徐苗苗.物化: 作为“预先承认”的遗忘———试论霍耐特的物化观[J].学术交流,2013,(5):20-23.
[11] 衣俊卿.新马克思主义评论:超越物化的狂欢[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12] Christopher F Zurn.Recognition ,Redistribution ,and Democrary : Dilemmas of Honneth’s Critical Social Theory[J]. Europe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13 : 1 , April 2005.
[13] 胡云峰.规范的重建:关于霍耐特的承认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14] Bert van den Brink,David Owen,eds.Recognition and Power: Axel Honneth and the Tradition of Critical Social Theory[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15] Christian Lotz. Reification through Commodity Form or Technology? From Honneth back to Heidegger and Marx ,Rethinking Marxism[J].A Journal of Economics,Culture&Society,2013,25(2).
[中图分类号]B5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9)08-0029-08
[收稿日期]2019-01-30
[作者简介]杨礼银(1977-),女,重庆大足人,副教授,博士,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责任编辑:杜 娟〕
标签:理论论文; 社会论文; 客体论文; 关系论文; 主体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欧洲哲学论文; 欧洲各国哲学论文; 德国哲学论文; 《学术交流》2019年第8期论文;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