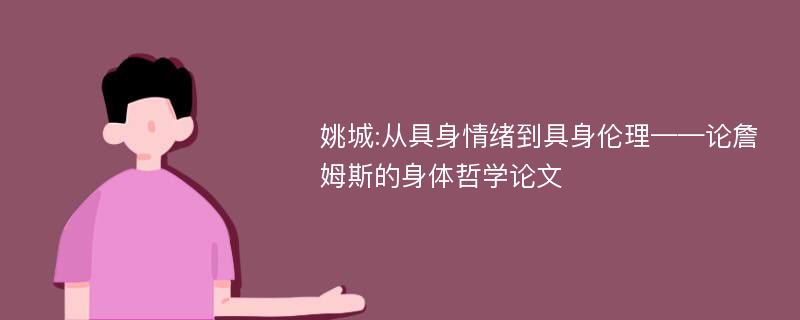
摘 要:詹姆斯认为情绪反应是由身体引起的,这个理论从问世起就面临着质疑与批判。然而,如果把詹姆斯的情绪理论放到他的整个哲学框架中进行考察,即会发现情绪理论涉及詹姆斯对身体的独特思考,是通往詹姆斯身体哲学的道路。身体被詹姆斯设想为一个超越了心理—物理二元论的本源经验场,拥有和意识流/意识场相同的结构,具身的情绪是身体与周遭环境打交道的方式。詹姆斯同时认为伦理行为是一种高级的情绪性反应,他的具身情绪蕴含具身伦理的可能性,通过对其伦理行为的身体维度的研究将有助于加深对伦理行为本性的理解。
关键词:詹姆斯;具身情绪;具身伦理;身体哲学
詹姆斯曾提出过一种独特的情绪理论,我们不妨设想一个日常生活中的场景来刻画詹姆斯理论的特点:一个小孩在花园里尽情嬉戏,心情惬意,突然一条大蛇从她面前窜出,小孩受到惊吓,心跳加速,脸色发白,身体发汗,然后拔腿就跑。在这种情形中,我们一般会认为小孩先受到对象——蛇的刺激,然后产生了恐惧的情绪,恐惧的情绪继而让她产生上述种种身体上的反应。而詹姆斯的观点恰恰相反,在他看来,小孩面对蛇的刺激时先是产生了身体上的种种反应,继而才产生了恐惧感。他说道:“我的理论是,由事实产生刺激时,身体方面先直接发生变化,变化发生时,我们感觉到有这样的变化,就谓之情绪。”[注]威廉·詹姆斯:《心理学原理》下,方双虎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881页。身体变化导致情绪变化的观点挑战了当时流行的看法,詹姆斯对身体反应的强调也遭到诸多诟病,有人攻击他的这一观点是极端的还原主义[注] Cf. Howard Feinstein, William James on the Emotions, JournaloftheHistoryofIdeas, vol. 31, no. 1(1970), pp. 133-142.。但是,随着对詹姆斯哲学的深入研究,学者们发现对其情绪理论的解读可以建构出一套身体哲学,这一解读不仅避免了对詹姆斯的还原论指控,还能从中发掘詹姆斯哲学的新面相。本文的目的即依据詹姆斯的情绪理论来探索他的身体哲学,并依据其文本,将他的身体哲学拓展至伦理领域,由此刻画詹姆斯身体哲学的理论起源及其理论效应。
一、从情绪到身体
如上文中的引文所说的,詹姆斯认为身体变化引起了情绪变化,他采取了下面的论证策略:“如果我们设想某种强烈的情绪,然后再试着把对它的身体症状的所有感觉从我们对这一情绪的知觉中抽离出来,我们就会发现没有什么遗留下来,没有组成情绪的‘心理要素’。没有身体上的变化,情绪所剩下的只是一种冷静的、中性的、理智上的感知状态罢了……恐惧这种情绪,如果没有急促的心跳、粗短的呼吸、颤抖的嘴唇、发抖的四肢,也没有起鸡皮疙瘩,没有内脏机能的紊乱,那还剩下些什么呢,我完全想象不出来。”[注]威廉·詹姆斯:《心理学原理》下,第883页。按照这个策略,如果减去情绪经验中沾染着的身体反应,就只剩下一些没有实质内容的空洞名词,仅通过这些名词我们无法理解何为情绪。詹姆斯把身体的生理反应视作情绪的根源,他的这种想法常常被误解为将一切情绪还原为生理过程的极端还原主义,并被认为是一种根本无法得到实验结果支持的臆想[注] Cf. Howard Feinstein, William James on the Emotions, JournaloftheHistoryofIdeas, vol.31, no. 1(1970), pp. 133-142.。确实,詹姆斯将情绪完全看作生理机制的反应,看上去的确像是一位极端的还原主义者,然而,他却明确地否定了这种质疑,他认为自己的理论不同于那些将情绪等同于神经过程的理论。但是在面临批评时,他又始终坚持情绪必须经由身体而被引起[注] William James, The Physical Basis of Emotion, PsychologicalReview, vol. 101, no. 2(1994), pp. 205-210.。
这种明显的冲突表现出詹姆斯理论的内在张力,实际上,在詹姆斯的著作中,类似的冲突并不少见,其根源在于詹姆斯在研究意识时经常在两套概念系统之间来回跳跃,如费恩斯坦(Feinstein)指出的那样,詹姆斯的理论中存在着唯物论方法与其本人的形而上学和宗教倾向间的内在张力[注] Howard Feinstein, William James on the Emotions, JournaloftheHistoryofIdeas, vol. 31, no. 1(1970), pp. 133-142.。林斯霍滕(Linschoten)也持同样的看法[注] Hans Linschoten, OntheWayTowardaPhenomenologicalPsychology:ThePsychologyofWilliamJames,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22-25.。于是詹姆斯的研究方法是双重的:一方面是从第一人称出发,通过对内意识领域的现象学考察获得心理状态的内经验;另一方面是第三人称的,以生理学为标杆研究行为、心理状态的物理条件[注] Hans Linschoten, OntheWayTowardaPhenomenologicalPsychology:ThePsychologyofWilliamJames, p. 37.。可见,那些批判詹姆斯的理论是极端还原主义的人是有依据的,詹姆斯确实在说明情绪的过程中使用了大量第三人称的视角,将对情绪的生理机制的描述作为对情绪本质的说明。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詹姆斯哲学中与还原论分离的另外一面,即他也强调情绪经验只有通过内省的方式才能被呈现,“詹姆斯坚持情绪是不可还原为其物理基础的内在经验,因此对其研究也应该是通过内省的方式才能够精准”[注] Richard Shusterman, BodyConsciousness:APhilosophyofMindfulnessandSomaesthe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48.。这样一来,他通过对心理状态的肯定保证了内经验领域的合法性,也就是说,情绪是完全在内经验领域被体验到的,这就能避免认为詹姆斯忽略了情绪所具有的作为一种独立经验的地位[注] Howard Feinstein, William James on the Emotions, JournaloftheHistoryofIdeas, vol. 31, no. 1(1970), pp. 133-142.。
按照上文中的论述,如果从第三人称视角出发,身体引起情绪的过程完全可以用生理学语言刻画,这就会导向还原论,而如果承认情绪作为一种非身体性的实体来引起身体反应,又会导致笛卡尔式的身心二元论难题。而詹姆斯试图拒绝使用笛卡尔的框架来解决由此导致的身心问题[注] Hans Linschoten, OntheWayTowardaPhenomenologicalPsychology:ThePsychologyofWilliamJames, p. 50.,为了避免两难的困境,我们必须发掘詹姆斯身体概念的多重含义,并在此基础上重构他对情绪—身体关系的说明。首先,詹姆斯早期仍使用了笛卡尔式的框架,根据心理—物理两种实体的划分,他认为身体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纯物理的对象,身体诸要素的组合和运作可由生理学语言进行刻画和定义,这样一来,詹姆斯的情绪理论是还原论的。然而在其后期著作中,詹姆斯又将身体看作超出单纯物理对象并克服了心物二元论的源初意义发生场,他说道:“我们的身体本身是模棱两可性的最出色例子。有时我把我的身体视为纯粹是外部自然界的一部分。有时我又认为它是‘我的’,我把它归到‘我’一类里,于是在它里边一些局部变化和规定性就当作精神性的事件了。它的呼吸就是我的‘思想’,它的感觉的调整就是我的‘注意’,它的肌肉感觉的变更就是我的‘努力’,它的内脏的慌乱就是我的‘情绪’。”[注] 威廉·詹姆士:《彻底的经验主义》,庞景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2页。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这种对身体的理解并非是詹姆斯后期哲学中提出的全新观点,其《心理学原理》一书中的相关的论述已经为这种身体观的出现做好了准备。Cf. Richard Shusterman, BodyConsciousness:APhilosophyofMindfulnessandSomaesthetics, p. 139; Hans Linschoten, OntheWayTowardaPhenomenologicalPsychology:ThePsychologyofWilliamJames, p. 50, p. 53, p. 301.在“模棱两可”的意义上,詹姆斯认为情绪与身体无法按照主体—客体、内在—外在的框架割裂开来,情绪和身体之间不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实体的交互性或主宰性的关系,而应该是身体变化时,情绪作为变化的显现同时生起。
《组织学与胚胎学》由《组织学》和《胚胎学》两门科学组成,是紧随《系统解剖学》之后,医学生需要学习的一门医学入门课。
上面的论述让我们看到了身体在詹姆斯哲学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它可以满足詹姆斯的某些哲学愿望,比如捍卫人的经验的多样性以及避免还原主义等。除此之外,它对于刻画人在世界中的行动模式亦有裨益。将詹姆斯这套具身化情绪的理论推进到伦理[注]某些哲学家区分了道德和伦理两个概念的用法,例如威廉斯认为道德一词源于拉丁语,关注的是社会对个体的期待,而伦理一词源于希腊语,关注的是个人的品格。威廉斯同时指出在现代语境下,道德是一个更狭窄的系统,是伦理的一种特殊的发展和形态。参见B.威廉斯《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陈嘉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1~12页。本文不区分伦理和道德两个概念的用法,二者可互换使用。缘由是:在詹姆斯的语境中,无论是社会期待还是个人品格,都旨在说明一种对具体行动者的要求,他不关心这种要求的内容是什么,而关注这些要求得以实现的条件。领域,可以为理解人类伦理实践提供独特的视角与方法。
孤岛采油厂加强“班组舆情疏导员”的培训和管理,不断提升他们的心理学应用、人际沟通技巧、形势政策解读等综合素质能力,确保他们能够找准切入点,把握着力点,抓好落脚点,确保自我教育法的作用得到有效发挥。
通过上文的解释,我们希望可以初步勾勒詹姆斯身体哲学的基本方面,并回应对詹姆斯情绪理论的还原论指责。如上文所言,在詹姆斯的思考中,身体被看作是一个超越了主—客、内—外之分裂的场所,心—身之间的划分也不是本体论上的区分,而只是功能性的区分;而身体经验有一个“边缘”结构,这一“模模糊糊”的“边缘”早已为身体经验与周遭情境的相互引发做好了准备,正如林斯霍滕所言:“身体在我能想象所有可能出现的事情之前就已经准备好了。在‘我’将世界向自身表象之前,身体就已经知道世界了。”[注] Hans Linschoten, OntheWayTowardaPhenomenologicalPsychology:ThePsychologyofWilliamJames, p. 299.这样一来,对“我”在世界之中与被给予的情境打交道的理解,便不能再诉诸有机体如何适应环境、如何对刺激做出反应这样的简单模式。下文我们将看到,伦理作为一种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同样也涉及具身化的情绪运作,如此,伦理其实就是一种具身化的伦理。
二、具身情绪的结构
为了说明具身情绪的内在结构,我们有必要先回顾詹姆斯的意识流学说,因为在詹姆斯那里,经验、思想、意识三个概念可以互换使用[注] 尚新建:《经验概念是威廉·詹姆斯哲学的基石》,赵敦华主编:《外国哲学》第28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19页。这里的经验早已超出了近代哲学对经验的理解,经验不再只是提供给心灵的认知材料或单纯的感觉表象,而是一种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是一种亲身投入(赵敦华主编:《外国哲学》第28辑,第108页)。林斯霍滕在谈到詹姆斯的意识流理论时,也直接将其理解为经验流。Cf. Hans Linschoten, OntheWayTowardaPhenomenologicalPsychology:ThePsychologyofWilliamJames, p. 62.。经验与思想都是具身的经验和思想,如同詹姆斯反复强调的那样,身体状态所生成的经验就是“我”的思想、“我”的意识,“情绪是对我们身体中被唤起的事件的共鸣的经验”[注] Hans Linschoten, OntheWayTowardaPhenomenologicalPsychology:ThePsychologyofWilliamJames, p. 279.。传统哲学,特别是英国经验主义认为意识状态是由基本的意识元素或意识单子组合、加总而成,詹姆斯对这种思路很不满:“没有人经历过一个自身就很简单的感觉。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天起,意识就是关于各种对象和关系的复合体,而我们称之为简单感觉的东西,只是我们的注意力常常厚此薄彼而产生的结果。”[注]威廉·詹姆斯:《心理学原理》上,方双虎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74页。从詹姆斯的视角来看,所谓组成意识状态的基本元素本就是理性反思的结果,由于反思者设定的概念框架不同,产生了各式各样的所谓的构成意识状态的基本元素,这些理论彼此间争论不休且无定论。但是,如果将这些概念框架悬置起来,不要预先设定它们的有效性,在前反思的状态中直接面对意识体验,就会发现它是河流状的[注]陈亚军:《哲学的改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06~107页。。用詹姆斯自己的话来说:“意识不是衔接起来的,而是流动的。形容意识最贴切的描述就是将其比喻为‘河’或‘流’。”[注] 威廉·詹姆斯:《心理学原理》上,第185页。在有些地方,詹姆斯也把意识流称作意识场,这个说法强调的是“整个意识波或者任一时刻展现给思想的对象场”(威廉·詹姆斯:《宗教经验种种》,尚新建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 第172页)。林斯霍滕不刻意区分意识流与经验流的做法也让他直接把意识场称作经验场。Cf. Hans Linschoten, OntheWayTowardaPhenomenologicalPsychology:ThePsychologyofWilliamJames, p. 251.下文中将身体的意识流和经验流称作身体的经验场也是出于这个缘由。意识是一条河流蕴含这样一个观点:我们所能知道的“某物”并非是孤立的,而是与河流中的其他“某物”处于一种相互纠缠的关系之中。詹姆斯说道:“我们简单地根据思想产生的对象来为我们的思想命名,就好像每一个思想都只知道它自己所指的事物,对其他事物一无所知。实际上,每一个思想除了知道被命名的那个事物以外还模模糊糊地知道许多其他的事物。”意识或思想中总有一个核心的部分,这个部分是被意识抓住并“点亮”的部分;然而这个“点亮”的部分周围环绕着一个“晕轮”“地平线”或“边缘”(fringes)。这些比喻非常贴切,晕轮或边缘指那些我们意识中围绕着显要意识的部分。边缘构成了不同意识状态之间隐秘的连接部分,两个看似无关的意识内容通过它联系在一起。从另一个视角看,这个边缘“模模糊糊”却渗透着已然逝去的意识和将要到来的意识,它不仅为当下的意识保留着部分逝去意识的残留,同时也为即将到来的意识经验指明趋势并做好了准备,这就是意识流内在包含着的时间结构,用詹姆斯的话来说:“旧事物缓慢消失,新事物接踵而至,这便是记忆和期望的胚芽,是时间知觉的回顾(retrospective)和预期(prospective)。新旧事物使我们的意识川流不息,具有连续性。如果没有这个连续性,意识就不能称作意识流了。”[注]威廉·詹姆斯:《心理学原理》上,第186页、207页、195页、478页。意识流的连续性必然意味着它是在一个回顾—当下—预期的时间结构中进行的。
从上述的引文可以发现,詹姆斯区分了两种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一种是知识,另一种是体验。在另外的地方,詹姆斯将其区分为相识的知识(knowledge of acquaintance)和相知的知识(knowledge-about),与前者关联的是感受与情绪等,与后者关联的是判断和概念等[注]威廉·詹姆斯:《心理学原理》上,第170~172页。。实际上区分为体验和认知更为清晰:对世界的认知设定了一个外在于认知者的对象,认知被认为是一种超越了个体的普遍官能,通过知识的方式对对象进行精确的把握;而另一种方式则是切身的体验,切身的体验是一种尚未概念化的、前反思的亲身介入。詹姆斯举过这样的例子:“当我看见蓝颜色时,我知道这是蓝色;当我吃梨时,我知道这就是梨的味道……但是我却说不出任何关于这些事实的内在特性以及什么使这些事实形成现在的性质。我不能将这些事情的知识告诉给任何不曾熟悉这些事情的人。我不能描述它们,不能让一个盲人猜测蓝色是什么样子的”[注]威廉·詹姆斯:《心理学原理》上,第171页。。认知方式与体验方式之间的差别一目了然。基于此,詹姆斯区分了两类对道德的理解。第一种是知识性的:我们通过反思从经验中抓取一些内容,经过概念系统的分拣之后将其归到“道德”或“伦理”及其更精细的范畴名称下。例如,老师向学生教授道:“8月8日晚8点,张三在玄武湖畔勇斗歹徒。这就是一个勇敢和正义的行为。”按上述詹姆斯的观点看来,这仅仅是为一种外在于个人经验的行为命名,它构成一种关于“正义”和“勇敢”行为的知识。第二种则可被称为实际的道德经验,即当面对着道德的场景(如“正义的事件”)时,身体上生起情绪变化,这就进入了一个与道德相关联的情绪状态。根据上面的引文,詹姆斯认为后者,即有关道德的切身经验更能够揭示道德行为的深层根源[注] 针对这一点,舒斯特曼就曾指出詹姆斯所患有的种种疾病对其身体的摧残,直接影响了他的心理状态和道德状态,正是这种切身的人生经验让詹姆斯对具身的情绪与道德间的关联有着深刻的洞察。Cf. Richard Shusterman, BodyConsciousness:APhilosophyofMindfulnessandSomaesthetics, pp. 136-137.。也就是说,在真实的道德行动中,具备关于道德原则的知识并不一定意味着具备道德行动的能力。道德行动的触发并不是依赖于对道德知识的掌握,而是依赖于具身情绪与具体的道德情景之间的相互引发和构成。
当然,这种“推进”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在詹姆斯论述情绪的时候,他就考虑到了一些“精细情绪”的构成,它们包括道德感、理智感和美感[注]威廉·詹姆斯:《心理学原理》下,第894页。。詹姆斯仍旧把这几种“高级”情绪的产生“归功”于身体:“在理智的激动或道德的感化的一切情况中,我们不难发现……如果没有因正义的事件而激动,没有因慷慨激昂的行为而兴奋;那么我们的心理状态根本就不能被称为情绪的状态。事实上,它仅仅是一种对于事物应该怎样称呼的,一种对于事物的精妙、公正、慷慨等性质的理性知觉。这种评判性的心理状态应该纳入真理认识中去;它完全是一种认知行为。然而,道德和理性的认知几乎是不可能如此单独存在的。细致的内省表明,我们的‘共鸣器’一直在运转,它的作用程度超乎我们的想象。”[注]威廉·詹姆斯:《心理学原理》下,第895页。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詹姆斯在这里所谈论的道德感特指一种能激发道德行动的情绪,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关心的是如何刻画情绪在道德行动中的触发性以及其与独特情境的关联性作用,而不是要从具身情绪出发去建构一套规范伦理学。
当然,仅仅把情绪看作是构建詹姆斯身体哲学的起点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追问:一种身体化了的情绪——具身情绪具有怎样的内在结构?它又如何与周遭的情境打交道?
三、迈向一种具身伦理
正是在这一点上,有学者发现了基于詹姆斯的情绪理论来建构其身体哲学的可能性:“詹姆斯在情绪理论中所表达的身体观是一种整体性的观点……身体不是肌肉、血液、腺体、神经等组织的集合,身体在这一大堆组织的共同协作下涌现出一个超越物质层面的现象层面。身体就是自身携带着意义和价值的,表达了一种姿态和意愿,是活的身体,不是一副复杂精细但仍然只是机械地对环境进行反应的装置。”[注]董雪:《詹姆斯情绪理论新释》,《学术探索》2015年第1期。肉身本就是意义化的,因此它才超出了单纯的物理对象的范畴,而成为活的、有机的身体[注] Hans Linschoten, OntheWayTowardaPhenomenologicalPsychology:ThePsychologyofWilliamJames, p. 123.对活的身体的论述亦可见John Wild, TheRadicalEmpiricismofWilliamJames,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1969, pp. 3-7, pp. 375-378.。舒斯特曼评论詹姆斯的“身体”时所举的例子也较好地诠释了这一点:“身体作为一座桥梁,连接了内在自我和外在自然这两个空间,同时也连接了物理事件和心理事件。身体把我们经验中的这些领域之间的界限消除了。我可以把我正在流血的手指看作一个等待被包扎的外在物体,我也能体验到它是我绞痛着的一部分。”[注] Richard Shusterman, BodyConsciousness:APhilosophyofMindfulnessandSomaesthetics, p. 145.身体本身是意义化的身体,身体的动作并非是单纯的物理位移,同时也是意义的表达。
詹姆斯更进一步,把自我与身体也紧密联系起来:“我认为只有个体化了的自我才是真正被叫作自我的东西,这种自我是所有经验的世界的一部分内容。所经验的世界(另外也叫作‘意识场’)永远是同我们的身体一起出现,把我们的身体作为它的中心——观察中心,行为中心,兴趣中心……身体是集中点,是坐标的原点,是整个经验系列中的常住的重点位置。一切事物都环绕在它周围,并且从它的观点被感觉。”[注]威廉·詹姆士:《彻底的经验主义》,第92页,脚注。这样一来,我的情绪是身体对周遭的情境做出应答的方式,用流行的概念来说,情绪是具身的(embodied)情绪,是一种独特的身体状态[注]董晶晶、姚本先:《威廉·詹姆斯与具身认知心理学》,《心理学探新》2017年第3期。。如林斯霍滕所言:“让身体产生变化的那些刺激作为情绪被经验到了,这不是简单的触发事件,而是一种情境的作用。情绪是对事物意义之共鸣的观察,意义则取决于它们显现的情境。”[注] Hans Linschoten, OntheWayTowardaPhenomenologicalPsychology:ThePsychologyofWilliamJames, p. 283.这样一来,具身化的情绪与其周遭世界的打交道便是一个意义构成的过程。当情绪出场的时候,并非是一个脱离了身体的自我操纵着物理意义上的身体进入某个情境,再按照一系列刺激—反应的清单来对种种外部刺激做出反应,更不是某个事物先刺激到一个叫“情绪”的机制或官能,进而“情绪”再发出指令让身体产生相应的反应。上述过程可按如下的形式来刻画:自我进入到一个具体的情境之中,这个情境是整体化的,所谓的整体化就是个体将其周遭的情境整个地经验到了,在这个整体化的情境之中,身体同样是作为一个整体与情境纠缠在一起,并产生各式各样对情境的意义关联。在身体经验中,精神性的“自我”和物理性的“身体”都是反思后经由理性概念构造的产物,在这二者生成之前的身体经验场更为本源。
综上所述,将舒适护理应用在手术室护理工作中,能够在缓解患者焦虑情绪的同时,降低患者手术后发生并发症的几率,从而能够有效提升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
身体意识或身体经验也具有这样一个结构[注] 林斯霍滕在论述詹姆斯的身体意识(经验)时,认为身体意识(经验)是自发性的,是身体本身所具有的,其自身也可以按经验流的方式得到理解。不过他是直接用胡塞尔的术语来解释詹姆斯的理论。尽管胡塞尔的理论和詹姆斯的理论有相似性,但本文不认同这种做法,为了将二者区分开,保持詹姆斯思想的独立性,本文将用詹姆斯自己的概念来解释他的想法。Cf. Hans Linschoten, OntheWayTowardaPhenomenologicalPsychology:ThePsychologyofWilliamJames, pp. 296-297.。身体经验同样是一条河流,而不是由基本元素组合加总而来,而情绪作为身体经验的一种样态,也包含着上述结构。当身体变化作为情绪经验出现时,这一具身情绪周围也有这样一个晕轮或边缘,与周遭情境中的事件相互牵连,与此同时它也具有一个内在的时间结构。作为经验场的身体在情境中的经验活动不但自然保留着之前的经验,还将自身的意识投射到将要发生的事物中去,使得我们具有一个做出反应的预期。设想一个场景,在漆黑的夜晚,我不得不穿过一片坟地回家,周围刮着冷风,我不禁打了个冷战;但我不得不硬着头皮向前走,在经过一座坟墓的时候,只见一个东西从坟头上窜出,这时我双腿一软,呼吸急促,心跳加快并大叫了出来。这是一个恐惧场景,在这个场景中,有意识的身体被其周遭情境整体笼罩了,身体迅速生起恐惧情绪。我们不能说到底是坟、风,还是窜出的东西构成了使我恐惧的决定性要素,只能说是这个情境整体地进入到我的经验场中,我的身体在这个环绕着我的情境中现身,身体的诸通道都向情境敞开了。在以整体性的方式与情境打交道的过程中,冷风、坟地、漆黑的夜等要素并不单纯只是一些物理事件,它们在独特的文化背景中共同构成了一种包含着“恐惧”意义的关联体;而进入此一情境的人,他的身体本身承载着其生活历史的积淀和习性,一旦情境与身体之间构成了意义共鸣的构造关系,情境中所渗透的“恐惧”的意义便和身体中的“恐惧”情绪形成了相互引发与相互构成的经验。这一引发和构成的发生同样是在具身情绪的时间结构中发生的,因为当恐惧的情绪被经验到时,“前恐惧”的经验已然为此经验做好了准备,此经验也为身体如何做出反应提供了引导。按照詹姆斯对时间意识的分析,我恐惧的那一瞬间已然包含着“回顾”和“预期”在里面了。在与情境打交道的过程中,情境与“我”的情绪之间构成一种情绪活动—情绪相关项的意向结构,它不同于刺激—反应的因果性模式,只能认为是一种周遭情境与有意识的身体之间的相互引发与构成。
福克斯错误地理解了马克思的生产性劳动理论,认为互联网用户活动是一种无意识的劳动生产行为,可以通过劳动为资本创造价值。用户上传到网络上的个人信息、社交网络中的行为、个人兴趣偏好、浏览网页记录都会作为商品以一定的价格出售给广告商[注]Fuchs, Christian,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p.90.。这种观点乍一看似乎符合马克思对生产性劳动的定义,但实际上他错误地理解马克思对生产性劳动的定义。
因此,我们可以说詹姆斯提倡一种具身的伦理学[注] 具身伦理(embodied ethics)这一概念并不主流,但也有学者零星地做出过阐发,比如麦克拉伦(Kym Maclaren)曾借用梅洛-庞蒂的身体哲学构建一种具身伦理学,用来解决美德伦理学与义务论伦理学间的冲突。Cf. Kym Maclaren, Merleau-Ponty’s Embodied Ethics: Rethinking Traditional Ethics, ExistentialistThinkersandEthics, ed. by Christine Daigle, Montreal & King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42-165.,其从身体的维度出发来刻画我们的伦理行为的动机关联结构。从西方哲学的传统来看,身体在道德理解中一直是被驱逐、被鄙夷的对象[注] Thomas Blake, Affective Aversion, Ethics, and Fiction, ThePalgraveHandbookofAffectStudiesandTextualCriticism, eds. by Donald Wehrs and Thomas Blak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 208.。如在康德这样的哲学家看来,身体处于自然因果性的领域,身体只体现自然的必然性,而无法体现作为理性的人的自由,而情绪这种自病理学刺激而来的要素更是不可能成为触发道德行为的动机。如此,道德是非身体性的。这构成了一种对伦理的独特想象,伦理活动必须超越由身体带来的特殊性和任意性,或可借用查尔斯·泰勒评论现代伦理学的说法:“我们必须克服并超越自身的狭隘和偏见,获得一种所有地点、所有人的信念,类似于自然科学努力占领的‘不取立场的视点’”[注]查尔斯·泰勒:《世俗时代》,张容南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第415页。。于是,许多伦理理论依赖于发现或发明抽象的道德原则,由于这一抽象的道德原则来源于“不取立场的视点”,因此它们被设想为公正且普遍适用的。当然,以道德原则为核心的伦理学并非毫无意义,它建构了人类实践所需遵循的公共规则。但在詹姆斯这里,问题从“什么是一个可被辩护的伦理原则”转变为“实现伦理需要哪些条件”。在他看来,只寻找抽象原则是不够的,因为如此人们拥有的只是有关道德的知识,但仍缺乏将道德现实化的条件,用布雷克的话来说,它尚不是人类对活的经验的知觉(perception of lived experience)[注] Thomas Blake, Affective Aversion, Ethics, and Fiction, ThePalgraveHandbookofAffectStudiesandTextualCriticism, eds. by Donald Wehrs and Thomas Blake, p. 207.。从詹姆斯的视角来看,光有道德原则是不够的,掌握很多关于道德原则的“死”知识并不意味着能够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道德原则必须要进一步成为具身的情绪经验,它才能“活”起来。只关注抽象的道德原则和道德知识容易流于伪善。詹姆斯举过一个著名的例子:一位贵妇人为剧中人的遭遇落泪,却对她的马车夫在门外受冻毫无感觉。詹姆斯认为这些人“只能以单纯和抽象的方法去识别善性,这是多么悲哀啊!”[注]威廉·詹姆斯:《心理学原理》上,第94页。贵妇人只知从某些符号或意象中“识别善性”,也就是把善或道德当作某种外在于自身的知识和抽象原则,而当进入真实的场景时,她却缺乏体验到善性并行动的能力。这种情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见,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人在口头上宣扬各种道德观念,而当需要亲身实践那些道德观念时,他们就显得很无力了。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无法在自己实际的切身经验中为这些抽象的道德观念找到一个位置。当宣扬这些观念的时候,人们常不自觉地把自己放置到一个脱离了身体的、“不取立场的视点”之上;而当需要亲身实践这些观念时,人们才发现那些道德观念难以激起他身体的情绪经验,他根本不知道在一个真实的伦理场景中该如何行动,进而也就无法对那个具体的情境做出恰当的回应。按照我们上文中对具身情绪的结构的分析,单个被抽象出来的事件与从经验中被判断和概念捡取出来的道德知识之间并无法形成真正的意义关联体。情境中的事件与具身的情绪需要在一个相互引发的经验场中才能发生关联,因为没有了经验场的边缘、晕圈,事件和情绪便失去了相互构成的可能性,只剩下抽象的原则与个别事件之间刺激—反应式的单薄关联。正因如此,詹姆斯向来反对把伦理行为建基于抽象的原则和知识之上[注]万俊人、陈亚军编:《詹姆斯文选》,万俊人、陈亚军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348~349页。,实际上,这和詹姆斯整体的哲学气质是一致的,即他反对一种用整体反对部分的理性主义倾向,“他反对的理性主义是绝对主义和独断论的”[注]周骐睿:《实用主义也是一种理性主义?——舍斯托夫诠释下的威廉·詹姆士》,《江淮论坛》2018年第1期。。詹姆斯的伦理思考也一样反对从整体到部分的独断论原则,其强调的是对具体情境的亲身介入。他认为即便是同亲人聊天或在马车上给人让座这样的小事都很重要[注]威廉·詹姆斯:《心理学原理》上,第95页。,这些事件看似微不足道,然而它们要求有身体的行动者亲身介入具体场景,因而使得行动者可以培养在道德场景中恰当行事所依赖的情绪,并且随着情绪与情境形成意义的关联体,人们就会逐渐获得在具体的道德场景中恰当行事的能力。正如布雷克所言,我们对自身经验的具身情绪化应对是道德发展的动力[注] Thomas Blake, Affective Aversion, Ethics, and Fiction, ThePalgraveHandbookofAffectStudiesandTextualCriticism, eds. by Donald R. Wehrs and Thomas Blake, p. 218. 布雷克坚持了休谟式的宣称:道德判断与行为被情绪和激情所引导。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詹姆斯的理论比休谟式的观点多出的一个维度就是身体的维度,因为情绪是具身化的,因此当情绪推动道德判断时意味着身体与周遭情境已相互纠缠构成了一个伦理维度。从詹姆斯的理论中可以合理地推出伦理行为是在场的、直接的和情境化的。这也是不能将詹姆斯与形形色色的情感主义者相混淆的缘由。。缺乏这种通过具身化情绪对特定情境进行回应的能力,那些抽象的道德观念就没有获得展现的机会。
综上,身体在伦理行为中的作用意味着在场性的出现,也就是说伦理意味着某种在我周遭与我直接遭遇的场景。与抽象的玄思不同,这种具身伦理要求将道德原则放到具体场景中具体行动的维度上,相比为某一道德原则做精妙的辩护,詹姆斯更关心如何在一个具体的伦理情境中做出恰当的应对。如马切蒂所言,詹姆斯关心的伦理问题是抽象的道德原则与实际的个人生活之间如何连接的问题[注] Sarin Marchetti, EthicsandPhilosophicalCritiqueinWilliamJam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 70.,而一种可能的方式就在于反思,并不断拓展自己的道德感受性[注] Sarin Marchetti, EthicsandPhilosophicalCritiqueinWilliamJames, p. 58.。从本文的角度来说,那便是将有身体的自我置于一个又一个具体的情境中,使其直面纷繁复杂的生活之流并领受其意义,以便能恰当而又体面地回应被给予的情境。
讲这些话是需要勇气的,尤其第六条的说法,许多人就因为类似意见而且说得远比潘天寿缓和也在不久后成了右派(被上纲成反苏)。其实当时中苏尽管表面上十分友好,却不乏内在分岐与矛盾,此种政治局面如何影响了毛泽东对中国画问题上不同意见的判决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在南下杭州,听取浙江省委相关汇报后作出的反应,是所有人都想不到的。
四、小 结
行文至此暂可告一段落。本文一开始从詹姆斯对情绪的论述入手,顺着这条线索发掘其中的身体维度。在这里,情绪不再是脱离身体的情绪,而身体亦不再是物理意义上的身体。身体被视为一个本源的经验场,一个具有意识的有机组织,身体自身包含着经验的结构。这样一来,具身情绪也同样要按照身体意识或身体经验的内在结构展开,正是在这种结构中,具身情绪与周遭情境有了相互引发和相互构成的关联形式。在此基础上,詹姆斯又将道德感视为情绪的一种,这一线索将身体与伦理行为联系在了一起,在具身情绪与道德情景的相互引发中,可以看到伦理行为对情境、对面对面的相遇等维度的依赖。詹姆斯的伦理思考与主流的伦理学展现出了两条路线的差异:前者是身体化的情境伦理学,强调情绪与体验;而后者是无身体的普遍伦理学,强调抽象规则与原理。不过这两条路线并非对立,詹姆斯只是更关注抽象规则和原理之实现所需要的条件,在他看来,抽象的伦理原则如若不能现实化,就会沦为空洞的说教。从这一点看,詹姆斯不仅没有反对主流的伦理学,反而是对主流伦理学进行了补充。而从具身伦理的思想出发将有助于继续探索人类伦理行为的结构的本质,同时也为理解人性提供一种独特的视角。
DOI:10.13796/j.cnki.1001-5019.2019.04.004
中图分类号:B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9)04-0027-0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实用主义研究”(14ZDB022)
作者简介:姚城,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博士研究生(江苏 南京 210023);陈亚军,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 杭州 310007)。
责任编校:余 沉
标签:詹姆斯论文; 身体论文; 情绪论文; 经验论文; 情境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美洲哲学论文; 北美洲哲学论文; 美国哲学论文;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实用主义研究"; (14ZDB022)论文; 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论文; 浙江大学哲学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