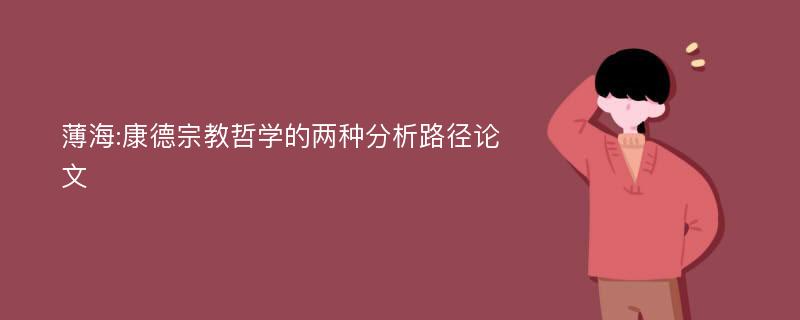
摘要:康德的道德宗教建立在对传统宗教分析的批判上,通过对宗教神学的本体论、宇宙论尤其是自然神论的批判,将神性的宗教和人性的道德联结在一起。宗教与道德的统一并不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客观世界中,而是在人们认知理性的逻辑中。通过对人的日常“经验”和人的“先验”的认知逻辑的分析,康德把宗教神学中“上帝”的功能悬置了起来,以“灵魂”为中介统一了此岸世界的道德实践与彼岸世界的幸福。康德既证明了“上帝”存在的必要性,又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上帝”对自然世界的影响,其目的就在于让具有纯粹理性功能的宗教道德指引人们主动地、创造性地开展社会实践,履行自身的道德义务。
关键词:宗教哲学;纯粹理性;自然神论;道德
康德的宗教理论和神学理论都是带有思辨性质的,这种思维逻辑突破了传统宗教神学的研究思路,所要研究的对象已经不再是客观世界中人与物质的变化。康德通过对传统神学理论的批判塑造了以“感性”、“知性”、“理性”为中心的认识论体系,联结了宗教的信仰和人的德行,最终在认识论层面统一了神学理性与人的社会实践。
2.3.2 对粗脂肪含量的影响 在氮、磷、钾肥单施处理下,与对照相比较,北林202粗脂肪含量增加不显著,粗脂肪含量最高时,仅为2.53 %。氮、磷、钾交互配施,不含氮处理(N0),在高磷、高钾配施处理下,N0P60K100,N0P60K150,N0P180K50和N0P180K100粗脂肪含量显著高于其他处理;含氮处理(N30),各氮、磷、钾交互配施的处理粗脂肪含量均显著高于对照N0P0K0,粗脂肪增幅8.44%~31.65%,其中N30P180K50粗脂肪含量最高,达3.12%(表4)。
一、重塑自然神论中的神学理性
1.从“经验”与“先验”的比较中抽象出神学理性的思维逻辑
在《纯粹理性批判》和《宗教哲学讲义》两部著作中,康德将自然神论中的上帝描述成一个不具备生命特性的宇宙本源。他认为倡导自然主义的学者们总是在批判各种超自然的现象以及这些现象所带来的灵感和启示,而与之相反的理性主义学者们却并不反对超自然现象所带来的启示,他们只是尽可能地反对人对超自然现象和超自然信仰的膜拜,更反对将这些信仰构建成为某种形式的宗教。康德的宗教思想与他的哲学思想一样都充满了严谨性,他没有将所有的论证都限制于对基督教启示的研究上,而是在批判这种宗教启示可能性的基础上揭示了自然神论的核心内容。康德认为,上帝的存在具有必然性,这是宗教发展的传统所规定的。人们在认识宇宙、参与社会活动的过程中将整个世界的运转规律寄托在某种永恒不变的“实体”上,虽然不同的人在各自的认知过程中形成了形式各异的知识与体悟,但是在这些知识和体悟之外的尚未明确的社会经验与认知感觉等都被归纳在“物自体”的范畴中。“绝对的必然”虽然强调了上帝的存在,但是这种存在的形式并不能被人完全理解。
康德对上帝存在的证明是多方面的,他批判了传统宗教哲学中关于上帝存在论证的理论的同时又为宗教哲学与人的现实生活进行了理论上的联结,这就为宗教哲学奠定了道德实践的基础。在分析传统宗教遗留的命题时,康德总结了各种关于上帝的论证。他发现欧洲16、17世纪的宗教冲突导致了宗教内部不同派系的斗争与屠杀,虽然宗教战争最终以各方面的妥协为结局,但是这种宗教的内部矛盾从来没有被取消过。在整个欧洲传统宗教斗争的过程中,无论是罗马天主教,还是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都坚持唯有自己代表了真理,没有任何一方主张宽容地对待矛盾。康德认为,传统的宗教哲学在“上帝存在”的证明中形成了三个主流的逻辑模式,一种模式是本体论的证明模式,一种模式是宇宙论的证明模式,而最后一种模式则是康德集中精力所要研究的自然神学的证明模式。康德认为,在他之前的安瑟伦、阿奎那、笛卡尔、莱布尼兹等人着重地采用了前两种宗教哲学的论证逻辑,中世纪以来的神学认知都围绕经验性质的认识论和先验性质的认识论而展开。“我们为了这一目的所可能选择的所有的途径,要么是从确定的经验及由这经验所认识到的我们感官世界的特殊性状开始,并由此按照因果规律一直上升到世界之外的最高原因;要么最后抽掉一切经验,并完全先天地从单纯概念中推出一个最高原因的存有”。〔1〕康德认为,自然神论的证明逻辑虽然不是最完美的神学推论逻辑,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自然神论的推导逻辑在前两者的基础上做了一个综合性的判断。神学本体论的分析逻辑是宇宙论和自然神论分析逻辑的基础,在叙述方式上,本体论的逻辑与宇宙论的逻辑又存在一定的矛盾性和排斥性,当前两者的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时,自然神论便成为了新的神学批判逻辑。
在康德的理论中,自然神论发展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寻找解决宗教纠纷的逻辑,因为从整个宗教的斗争史来看,暴力和战争已经不能解决现实社会的问题,而教会的内部矛盾使得罗马教会失去权威。新教提出的“唯有圣经”的理念虽然表面很符合神与圣徒之间的价值评判,但对圣经本身的不同理解使得每个宗教团体都在争夺话语权。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认识到了具有普遍性的理性主义的发展是人们解决宗教矛盾的最有力的武器。在这一问题的影响下,康德以自然神论之父赫伯特勋爵与洛克所提出的神学理性的原则为例,分析了“上帝存在”与“人的德行”之间的关系。人虽然对具有罪恶的事情怀有批判甚至仇恨的态度,但是不论历史如何发展,人的批判永远无法确保人自身能够从社会的罪恶中剥离出来,人的社会活动总是被好与坏、善与恶所包围。对于康德来说,这种现象的产生并不是宇宙发展的真实过程,而只是人作为具有意识的存在对社会实践的片面性的反应。赫伯特勋爵所强调的“人总是憎恨罪恶,并且为自己的罪过忏悔”是一种经验层面的假设,这种经验性的判断在受到历史知识的控制外还受到了宗教信仰和神学理性的影响,也就是说这种经验层面的推理判断将会在时间的发展中走向一种先验的逻辑判断。康德认为,这种转变就蕴藏于赫伯特勋爵所提出的第四个宗教原则和第五个宗教原则之间的转换中。如果说人对“罪恶”的憎恨源于后天的“经验”,那么“人死后有好报也有惩罚”则是来源于“先验”的认知。康德认为,不论是赫伯特勋爵还是洛克对宗教教义所规定的原则,都继承了宗教历史的神秘性,这种神秘性为宇宙间绝对必然的存在者和现实的存在者之间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关联。康德认为,从传统宗教原则发展的过程来看,神学家们一直努力让宗教信仰与人在“经验”中所获得的理性相融合。为了这一目的,神学家们倡导把具体事物的相关概念更加具体化和形象化,他们认为在范畴上对研究对象的区分是消解理论分歧和信仰分歧的重要方法。就像洛克所提出的宗教原则那样,希望将人的认知的能力与事物发展的趋势或者说与事物发展的可能性联结在一起。康德认为,传统宗教原则与宗教意识的发展都具有一个宗旨,也就是自然神论的宗旨,这一宗旨即是去除宗教中与理性相悖的,乃至超越理性的内容,把信仰仅仅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
康德认为,自己所需要的上帝必须是全知的,不仅知道世间万物的发展过程,也知道每一个个体人的思想过程。这样一来,上帝便会了解每一个个体人的行为动机,知道每个人的行为是出于道德的目的还是非道德的目的。从表面上来看,凡是出于道德目的的行为都被规定为一种符合于“善”的德行,而出于非道德目的的行为都被人们认为是一种“恶”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在对自然神论理论的分析中,康德认为善与恶的问题是自然神论学者们所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这些学者始终没有在目的论上将善与恶统一起来考察。他们所要研究的合目的性的神学已经附属于人的认知能力,“他们就引进了目的因的概念论,因为他们把一大堆合目的的结合着的实体如此困难地取得的统一性从对一个实体的因果依赖关系转变成了在一个实体中的依存性的因果依赖关系;……(他们)都既没有解决自然和目的性的最初根据问题,反而把这一问题宣布为无意义的了,……所以按照理性运用的那些单纯理论原则是永远得不出对于我们有关自然的目的论评判是充分的神的概念的”。〔8〕康德认为,人们所需要的上帝必须是一种全善的、公正的上帝,上帝的全善可以把上帝本身作为道德的制高点,从而让人们产生信仰与膜拜,而上帝的公正性则可以完美地把福报配发给每一个个体人,使得每一个个体人不会因为担心自己得不到利益而未实施道德的行为。而为了确保所有的一切与“善”有关的意志都能够无限时间地持续下去,人们对上帝的另一个希望也就是康德心中上帝的另一个属性便油然而生,这种属性强调上帝是永恒的而且是无处不在的。
2.在批判传统自然神学的基础上突出理性的信仰问题
笔者认为,刑事立法政策作为刑事政策学科的一部分,它是在对犯罪行为的认识与分析的基础上做出的有关刑事立法的方针、政策的总和,是刑事立法的依据。因此,刑事立法政策作为政策的一种,其在制定需有民意的考量;作为刑事法科学的一部分,其过程也必须存在公民监督。
可以看出,康德认为传统的自然神论忽略了人在社会实践中所获得的经验性的意识,而人的这种经验性的意识就是人类宗教信仰的根源。不论是传统的宇宙论、本体论和自然神论,与之相关的学者们都在“上帝存在”的论证中假设了一个最高的实体,认为人的现实生活就是在自发、自觉地履行这个最高实体为我们安排的计划。虽然自然神论者们在批判了宇宙论和本体论的虚无性后自己也陷入了社会实践与自我认知的矛盾中,但通过对这种传统的自然神论观点的重构,康德呈现了从宗教虚无到神学理性的转化过程。“只能设想以某种最高理智者为前提的,因而假定这个最高理智者的存有是与我们的义务的意识结合在一起的,尽管这种假定本身是属于理论理性的,不过,就理论理性而言,这种假定作为解释的根据来看可以称之为假设,但在与一个毕竟是由道德律提交给我们的客体(至善)的可理解性发生关系时,因而在与一种实践意图中的需要的可理解性发生关系时,就可以称之为信仰,而且是纯粹的理性信仰,因为只有纯粹理性(既按照其理论运用又按照其实践运用)才是这种信仰产生出来的源泉。”〔4〕从此角度看,康德继承了经验派的认知理论,但与此同时,康德又重视人的先天认知的能力,通过先天的认知来规定后天经验的感知与发展。休谟否定了因果关系,但康德确立因果性的地位,并认为它是人们先天的认识形式,人们通过先天的、因果性的认知来规定和限制自我在后天经验感知领域的不同层次。但是因果性只适用于可能经验的范围。康德认为,宇宙论的神学立场完全出自人类自身对自身的证明,世间之物都可能是自然存在的也可能都是偶然存在的,但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有生有灭。如果人们在理性的推理中无法证明任何一个事物存在的第一因或者说是根本原因,根本推动力,那么任何一个找不出第一因的事物可能在理论上来说都是不存在的。在人类的经验和感知系统内,这些事物可以归类为幻想。其实康德所做的所有工作,目的并不是为了消灭上帝在世间存在的理由,而是为了阻止知识侵入到人类信仰的领域。康德认为,所有证明上帝存在的方式不仅没有办法增加人们对上帝信仰的信心,反而败坏了上帝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人们无法认识上帝的存在,也无法认识到上帝的不存在;在一切与“上帝存有”有关的证明中,理性永远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而在把知识从对上帝信仰的领域中驱逐出去之后,康德的下一个目的就是要用人的道德来填补理性与知识的空缺。
康德曾经总结了自然神学的证明逻辑:“既然不论是一般物的概念还是关于任何一个一般存有的经验都不能达到我们所要求的东西,那么剩余下来的一个办法就是尝试一下,看看某种一定的经验,因而对当前这个世界的诸物的经验;他的性状和秩序,是否适合于充当一个能够可靠地帮助我们去确信一个最高存在者的存有的证明根据。一个这样的证明我们将称之为自然神学的证明。”〔2〕康德虽然认为启蒙运动后的神学理性将建立在传统的自然神学理论的基础上,但康德并没有不加批判地接受传统自然神学的所有逻辑,而是对这种传统的推导逻辑进行了重构。他认为,最初的自然神论的基础问题就是对上帝存在的肯定与规信,而在之后的神学理论的发展中,这条基本的原则也被摆放在多种矛盾冲突的夹缝中。这种矛盾的根源,或者说最主要的源头就是休谟所提出的怀疑论哲学理论。休谟认为,一切知识来源于感觉;感觉之外不可知;所有的因果关系只是人们习惯性的联想,与原因结果没有直接的联系;通过这些理论的推演,休谟对上帝存在的假设进行了种种批判,最后导致上帝在休谟的理论中成为了一种不可知的外在物,从而迫使整体的自然神论的理论大厦面临崩溃与坍塌。就这样,康德在怀疑派所统领的知识标准的背景下提出了著名的论点:“我必须扬弃知识,以便为信仰留地盘。”〔3〕在他看来,传统自然神学将“感觉”作为人类认知世界的唯一方式,“感觉”和“认知”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同样的事物或者说是人的具有相同功能属性的能力;这种同一性的思维逻辑逐渐削弱了“经验”的功能性作用。传统的自然神论总是将人的“感觉”能力看成一种特殊的经验模式,以至于磨灭了真正的社会实践所带来的真正的“经验”,在这种思维模式的影响下,自然神论的倡导者们认为可以将单凭“感觉”所捕获的知识与现实世界的运行秩序相统一,即把具有神性的上帝及对上帝的信仰和现实的物质世界的发展规律融合起来。
二、构建宗教哲学中的道德基础
1.“德”与“福”在人对世界的认知过程中获得统一
机械加工车间能量消耗大是企业面临的关键问题,在生产过程中,调度作为一种降低车间能耗的有效方式受到了广泛关注,合理的调度方案可有效减少车间的能量消耗[1]。然而,如何在不牺牲完工时间、延期成本等传统目标的同时,实现车间节能优化调度,是绿色制造背景下亟待研究的问题。
康德发现一方面,有德性的人本应该是最高的善,另一方面有德性的人也本应该是享受幸福的人,但是他也意识到按照正比例让有德性的人享受到同等的福是一个复杂而又艰难的过程,所以他对如何让“德”与“福”能完美地结合也做了详细的讨论。康德认为,二者的结合推演不能通过分析的方式来获得,因为分析的方式是从原有的命题中找出本身自由的子命题,是没有新知识可以获得的逻辑方法。他认为幸福和道德是至善的两个在种类上完全不同的要素,因而它们不可能通过分析的方法而认识到。为了将“福”与“德”完美地统一在一起,康德将日常生活中的人作为了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他认为,哲学视域中所要讨论的“人”的概念并非传统宗教神学中所涉及的人类学概念,人的发展过程虽然是经验性的过程,但是对人的研究并不能仅仅束缚在他的日常的现实性上,而从“先验”的角度来研究人的认知能力和认知方式将会为解释人类宗教的道德属性问题带来新的思维模式。康德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将“先验”的感觉(知识)与人的后天的实践经验联结到一起,他对“福”的理解可以看成是一种先验知识领域的信仰。现实生活中的人对知、情、意的获得过程从某种程度来看就是人按照先验的感知而参与自我意识的建设过程,因为这种实践的行为的发生直接与人的意识成长相关,康德认为在这种意识的领域中统一“福”与“德”将会是一个纯粹性的、理性的实践。在康德的理论中,人类的知识只是反映了现象界的某些现象,只有尽可能地将所有人的所有知识综合起来,才能抽象出最贴近“自在之物”的知识。可以看出,康德所指的幸福本质上是一种物理意义上的幸福,也就是人们通过掌握理性以改造物理世界的形式来满足自身需要后所产生出来的一种幸福。从这种角度来看,人是不能在世界上通过一丝不苟地遵守道德法则来希望达成幸福与德性的任何一种必然的和足以达到至善的联结的。所以康德认为,“德”产生“福”在现象界的推演是不可能成立的。康德的思维并没有到此就被现象界的限制给打断,在康德看来,这种“德”与“福”的联结是可以超越物理世界的界限而完成的。由此康德从此岸世界转到了彼岸世界,在没有宗教的道德领地中,康德通过上帝把“德”与“福”联结在了一起。
康德伦理学的本质就是一种意志的自律,他所要探讨的是一种普遍的道德法则,可以让每一个人都利用这种法则而不是理性知识来让自己对真理充满信心。“人作为一个理性存在者,由于其理性而必须把自己视为理智,不是视为属于感官世界的,而是视为属于知性世界的,因此,人具有两个立场,可以从两个立场观察自己,首先就它属于感官世界而言,它服从自然法则(他律),其次就它属于理智世界而言,它服从不依赖于自然的、并非经验性的、而是仅仅基于理性的法则。”〔5〕在康德的宗教理论中,自然法则和理性法则都是影响人类社会实践的重要因素,通过理性的认知,人能够为自己构建一套行为规范,当这些行为规范成为了人类的习惯和传统后,凡是继承了这些传统形式的人便被评价为理智的和聪明的人,凡是与这种传统意识相违背的人便遭到了排挤和压抑。康德认为,自律并不是一种束缚,而是一种自由,是理性为自身立法的一种自由。人的行为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自己约束着自己,自己为自己立法,自己成为自己的规定性,自我不仅可以履行道德的义务,也可以对道德进行评价,道德的根本不是理性知识,而是自我与自律。在康德的推理中,既然道德是人的自我的规划与自律,那么道德就可以不需要宗教的理论来支持,也就是说在康德眼中,道德与宗教是没有关系的,道德可以不需要宗教。如果一种道德是外在物,或者说是一种至高者附加在人身上的,那么康德便会认为人们对这种道德法则的尊重并不是一种纯粹的道德活动,所以康德总结道:“道德为了自身起见(无论在客观上就意愿而言,还是在主观上就能够而言),绝对不需要宗教。”〔6〕
道德为了自身起见,也就是说道德为了道德自己的发展是不需要上帝的。但如果道德不是为了道德自身的发展,反而是为了别的什么原因可能就需要一种宗教,一种上帝来为它完成非道德性但却充满着信仰的目的性。康德认为,任何一个人在做任何一个事情之前,自己的心中都不需要有任何担心疑虑来约束自己。倘若每个人都这样做,那么康德的那个最著名的问题就会被行为的实施者提问出来,那就是“我可以希望什么?”康德认为,所有的希望归根结底都是指向幸福,而幸福就是对我们一切偏好的满足。康德对幸福和道德的关系也作了分析,认为幸福与道德不是决然对立,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两种事物。在康德看来,幸福和道德是一种和谐的关系,虽然不对等,但是有着一致性;对幸福的谋求本身是一种自我道德发展的路径;甚至从终极角度来看,幸福就是自我道德完善的前提条件,也是道德自我完善的至高点;但幸福不应该是自我道德发展的目的,因为在康德看来,道德的履行是纯粹的,不掺杂任何目的性与偏好的行为,否则这些道德行为都是不真实、有杂念的希望。因为人是一种理性的动物,所以通过理性的推演,人们在履行道德的过程中可以预见到自己的道德将会达到的结果,意志规定一旦转化为道德行为,就会必然在现象界产生自己的结果。而人的希望都是指向幸福的,所以人的道德行为的预期与自身的幸福具有趋同性。康德认为,惟有有德性的人享有幸福,才是完美的善,也即是至善,它本质上就是一种“德”与“福”的结合。康德在进行分析时既考虑了宗教神学为人所规定的先天的义务,同时又考虑了具有自然属性的人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人性。从神性角度来看,“福”就是放置在人性彼岸的某种奖励,凡是遵守道德规则的人都将有机会获得他们所向往的幸福;而从人性角度来看,“德”就是摆在人性此岸的一种规训,每一个社会生活的实践者都有义务将道德作为自己人生的责任。如果说幸福是人对自我生活方式的评价标准,那么道德则是人类评价自我的客观条例。康德的分析逻辑就是在不断从主观上和客观上统一人的自我发展的认知过程,通过自我认知,人不断地肯定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消解日常工作生活中因自我评价和他人评价不同所造成的矛盾。“对康德来说,人的道德仅仅在于他具有把‘humanity’作为客观性目的来对待的能力,但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必须要把他人的主观性目的作为他自己的主观性目的——只要这些主观性目的和客观性目的不冲突。因为大部分主观性目的关心的是个人的幸福,所以康德的道义论一定是可以兼容功利考量的。”〔7〕
2.由“上帝”到“灵魂”,统筹道德的“善”与宗教的“福”
“三分栽,七分管”,发展核桃产业没有一支过硬的技术队伍不行。一要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核桃技术服务队伍,加强科技培训,提高管护水平。经过技术培训,落实技术承包责任,让他们充分发挥专业技术人员在核桃产业发展中的作用。二是加强对农村乡土技术人才的培训,每村要有3-5个技术员,每户要有一个懂技术、会管理的明白人,不断强化核桃产业发展的技术支撑。
在康德的理论中,由“恶”向“善”的转变过程就是道德目的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把上帝看作“至善”的最高属性,将自我的“善”的概念认定为生命中理所应当要去履行的目的和责任。当“善”被认为是理所应当、自然而然地存在并发展时,与之相匹配的人的社会行为便具有了合目的性的功能。在人、道德、上帝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康德把上帝看成是一种必要性的设想,将上帝看作神圣的立法者和创造者,但同时康德又直白地告诫所有人,上帝的这种功能完全出自于理性的分析,上帝的存在并不是经验生活中所证明的理论,在经验生活中,在理性的帮助下,对上帝的认识仍然是不可企及的。对于康德来说,上帝所要发挥的最大作用就是彻底地把道德转变为人类生活的终极目的。通过宗教的发展,上帝的意志被呈现在了教义的规则中,通过不断细化,这些教义规则直接涉及人类道德实践的具体环节和对社会行为效果的最终评价。对于那些认为宗教为目的论核心的理论家们,康德则充满了严肃的批判的态度,他认为不论是人性向善的问题还是人性向恶的问题从本质上来看都不是先验的宗教问题,而是日常生活中人的自我认知的问题。上帝在人与人的道德之间起到了引导性的作用,这种作用并不是必然需要借助宗教的力量才能实现的。宗教目的论对于康德来说类似于一个虚假的命题,虽然在理论论述中并不符合人的理性认知的一般规律,但将上帝作为价值评价的标准,可以将道德目的论与宗教目的论统一起来,消除宗教发展中关于上帝意志与人的自由发展之间的矛盾。对于康德而言,在很多情况下,上帝与人的灵魂有着共同的属性和功能,上帝的存在本身是为了满足人们的一种自我道德发展的要求,是人们自己塑造了一种能够满足自我需求的上帝。同时,康德也同样关注与人自身相关的灵魂,人的道德灵魂直接与人的先验知觉产生关联,在认识论的意义上,不论是“德”还是“福”,是“恶”还是“善”,人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和重构都能在人的“灵魂”的层面获得最广泛的认同。
可以看出,康德在研究人性本质的过程中,并没有生搬硬套地将人与宗教嵌入上帝的理念所能覆盖的场域中,而是巧妙地引入了“灵魂”的概念,如同预设上帝与“至善”的关系一样,康德也赋予人的灵魂以一种道德的禀赋,“在我们的灵魂中有一样东西,我们如果恰如其分地将它收入眼底,就禁不住要以极大的惊赞看待它。此时,惊赞是正当的,同时亦是振奋人心的。而这种东西就是我们一般的原初道德禀赋”。〔9〕康德认为,人的灵魂与人的认知能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灵魂在人类的认知系统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调节性作用。就人的理性认知的能力而言,灵魂连接了道德与宗教,使得道德的评价标准在宗教的教义中得到了充分的彰显。与此同时,“恶”的倾向性与“善”的倾向性在“灵魂不朽”的场域中获得了统一。康德对“恶”与“善”、宗教与道德的统一虽然引进了“灵魂”这一范畴,但是康德的宗教理性与神学理性最终并未走向不可知论或者一种认知意义上的玄学。康德虽然认为包括“自在之物”在内的某些现象是不能被人类的理性认知把握的,但这些不能被人类认知和掌控的东西必定不是人类社会实践的出发点,更不是人类道德发展的终极目标。“灵魂不朽”在康德的哲学逻辑中可被解释成一种具有连续性的历史现象,是人的历史性的思维逻辑与认知能力。在宗教建设的过程中,人的“灵魂不朽”已经不再是独立存在的单一性人格,而是在历史上前后继承的意识集合,人的灵魂存在于这种历史性的意识集合中,而这种意识的集合就是人在历史发展中所习得的经验与感知。人类宗教的建设和人类道德实践的开展对于康德来说是同一个社会实践的两个不同的写照,不论最终评价的结果是“恶”还是“善”,康德始终相信人类最原始的意图是受到某种自然意识的影响。伴随着人们不断思考自己的发展模式,不断选择和更换自己的生活方式,人们最后会发现自己选择的必定是自己最愿意接受的现实。人按照自然的意图来规划自己的社会活动,缓解了“恶”与“善”的对抗性矛盾,同时又将道德实践与宗教理性或者说神学理性统一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
三、总结
康德的宗教哲学具有跨时代的意义,面对中世纪宗教哲学的解体和启蒙运动后新的宗教哲学的缺失,康德开始以理性的角度分析宗教的发展模式。在研究中,康德将属人性的道德与属神性的宗教联结在一起,认为在上帝神性的规制下,道德的发展能够更加真实和纯粹。“经验”和“先验”是康德分析道德与宗教问题的两个维度,“经验”的分析所指向的就是人的道德行为,“先验”的分析所指向的则是人类所希望获得的幸福。不论是“经验”层面还是“先验”层面,康德的理论推导都不是神秘主义或玄学意义上的,而是建立在一种理性思辨的逻辑上。自然神论是康德重点分析的对象,他发现人在感知整个世界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了宇宙的完美和人类社会的合目的性,人将不由自主地认为在这一切的背后有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在发挥着作用,但并不能因为这个原因,人对上帝的信仰就变得毫无批判以至于让人自身的生活失去了主动性和创造性。对于自然神论康德继承得最多的思想就是对宗教本体论的反思,他希望能够通过更加理性的认知方式来理解自然界的发展规律以及人类社会的演变过程。康德所要关注的不仅仅是彼岸世界的神,他更加关注此岸世界的伦理道德,在很多分析中,上帝被人的理性悬置了起来,人的道德行为与人对幸福的希望成为了康德理论中的重要议题。对“善”与“恶”、“德”与“福”之间的统一问题的研究是康德批判并超越自然神论的突出表现,与人相关的道德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体系,但宗教的发展必定关注人的道德,道德的发展逐渐成为了康德宗教理论的基础和立足点。人通过信仰将自己的德行与上帝的意志相关联,但是康德理论中的信仰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我暗示,而是一种经过纯粹理性批判之后形成的宗教信心与信念。在理性的批判之后,康德消解了“经验”在神学中的基础地位,而只保留了人的宗教信仰,他把宗教逐渐叙述成为人类道德发展的最终结果,从而避免了人因现实生活的困惑所产生的不可知论。通过纯粹理性的批判,康德最终完成了历史性神学信仰向理性宗教信仰的转变,而人类社会的宗教信仰问题也最终被转化成为人类的道德问题,有限的人的社会实践与无限的道德价值在人的认知领域获得了最终的一致性。
参考文献:
[1][2][3]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71、490-491、22.
[4]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72-173.
[5]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M].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460.
[6]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5.
[7]翟振明.康德伦理学如何可以接纳对功利的考量[J].哲学研究,2005(5).
[8]康德.判断力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96.
[9]康德.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M].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38.
Two Ways of Kant's Religious Philosophy Logic
Bo Hai,Hou Guangxin
Abstract:Kant’s moral religion is based on his criticism of the analytical logic of traditional religions.Through his criticism of the ontological cosmology of religious theology,especially the deism of nature,Kant connected the religious god with the moral of human nature.The unity of religious and moral is not in the objective world of people’s daily life,but lies in the logic field for people to understand the reason.Based on people’ s daily experience and the transcendental cognition logic and analysis,Kant put the religious theology God function mount up to this side of the unified soul as intermediary world of moral practice and the shore of the world of happiness.Kant proves the necessity of the existence of god,and to some extent weaken the influence of god in the field of natural world,so the seeming contradictions of logic in nature is not contradiction in essence,Kant’s purpose is to let a purely rational function of religious morality to guide people to carry out social practice actively creative their moral obligations.
Key words:religious philosophy,pure reason,deism,morality
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547(2019)07-0031-08
基金项目:本文系辽宁省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L18BZX006)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薄海,辽宁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博士;
侯广信,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哲文教研部讲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哲学博士。
责任编辑:阿 莽
标签:康德论文; 道德论文; 宗教论文; 上帝论文; 理性论文; 哲学论文; 欧洲哲学论文; 欧洲各国哲学论文; 德国哲学论文; 《理论界》2019年第7期论文; 辽宁省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L18BZX006)阶段性研究成果论文; 辽宁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哲文教研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