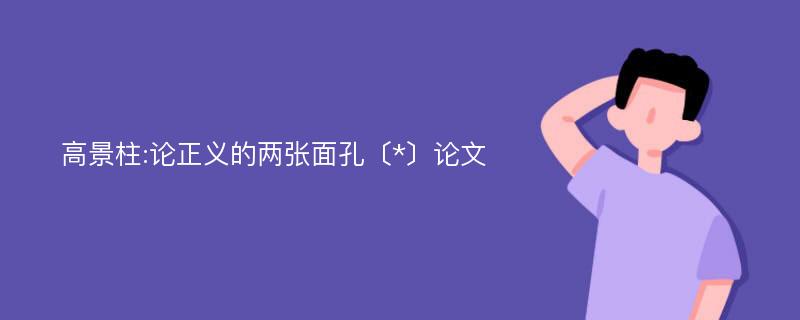
〔摘 要〕作为当代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中的重要理论之一,正义的基本含义是给予每个人以其所应得。正义具有两张面孔,一是从共时性维度出发,那种关注同一世代之内的人们之间关系的“代内正义理论”,二是从历时性维度出发,那种关注不同世代之间的正义问题的“代际正义理论”。相较于人们给予代内正义的极大关注而言,代际正义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就这两种正义之间的关联性而言,代内正义的实现是解决代际正义问题的前提,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代际正义只能从属于代内正义,相反,代际正义的实现也反过来有助于解决代内正义问题。
〔关键词〕正义;代内正义;代际正义;约翰·罗尔斯
在当代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中,正义无疑已经成为一个核心概念。作为一种道德理论和政治理论,正义必须有着明确的适用范围,即人们关注的是“谁之正义”。戴维·海德(David Heyd)在探讨一般的道德理论和政治理论时曾言,“康德认为道德原则适用于所有理性的人。边沁认为它们适用于所有的众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把政治道德的范围限制在城邦的自由公民身上。基督教神学关注以上帝的形象所创造的人类的灵魂。每种道德理论和政治理论都是根据其基本规范原则来确定其主体的适用范围:康德关注的是理性,边沁关注的是快乐的最大化,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注的是美德的培养,基督教关注的是灵魂的救赎。”〔1〕那么,如何确定正义的适用范围呢?休谟曾经强调正义是用于调控个人之间的合作关系的,认为虽然自然赋予了人类无穷的欲望和需要,但是自然并没有给予人类满足这些欲望和需要的丰富手段,为了生存下去,“人只有依赖社会,才能弥补他的缺陷,才可以和其他动物势均力敌,甚至对其他动物取得优势。社会使个人的这些弱点都得到了补偿;在社会状态中,他的欲望虽然时刻在增多,可是他的才能却也更加增长,使他在各个方面都比他在野蛮和孤立状态中所能达到的境地更加满意、更加幸福。”〔2〕在休谟那里,人类并不是生活在诗人们所谓的“黄金世代”中,人类脱离自然状态而进入社会状态以后,为了能够生存下去,正义也就出现了。由于在19世纪以前,人类的科技发展水平是极为有限的,人类当时的种种行为对未来世代所产生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再加上休谟等人之观点的影响力,当时的正义理论基本上只是关注同一世代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没有涉及到未来世代的处境问题。
后来,情况发生了改观,未来世代的处境问题逐渐进入了正义理论的视野,正如约尔格·特雷梅尔(Joerg Tremmel)曾言,“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关于非重叠的世代之间的正义的系统概念和理论已经首次得到了发展,这是在同时代的人之间的正义理论被阐明2600年之后。这种拖延可以用当时和现在人类行动范围的不同影响来加以解释。”〔3〕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社会手中所握有的力量在日益增长(如核武器的巨大威力是过去世代的人无法想象的),这种力量足以使得生态系统失衡,倘若此种情况真的出现,不仅当今世代的成员要受到影响,而且未来世代的成员亦会受到影响,此时正义理论也开始关注当今世代与过去世代、未来世代之间的关系以及未来世代的处境问题。如果我们认为早先那种用于处理同一世代之内的正义理论体现了正义的“共时性维度”,那么此处我们所言说的那种涉及到未来世代之处境的正义理论就体现了正义的“历时性维度”。也就是说,正义除了具有关注同一世代中的成员之间关系的一面,还有关注当今世代与过去世代、未来世代之间关系的另一面。前一种正义理论可以被称为“代内正义理论”(intragenerational justice),后一种正义理论可以被称为“代际正义理论”(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例如,有G1和G2两个世代,那种用于处理世代G1内部或世代G2内部关系的正义理论是代内正义理论,而那种用于处理世代G1和世代G2之间关系的正义理论就是代际正义理论。这也是本文所言说的“正义的两张面孔”的主要所指。那么,正义的两张面孔所指向的两种正义理论的具体内涵以及关注的问题是什么?它们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关联性?这也是本文将关注的主要问题。基于此,为了较为全面地展现正义的两张面孔,本文将首先关注正义的内涵及其范围,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分别探讨代内正义理论和代际正义理论的主要意涵及其关注的核心问题,最后探讨正义的这两张面孔之间的关联性。
该类进口远程脉冲水表采购周期长且费用高,当设备损坏需要维修或更换时,会因采购周期长严重影响生产的持续运行,且因费用高导致性价比低。
一、正义的内涵及其范围
什么是正义?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虽然正义的概念变化多端,但是其基本含义都是一样的,即给予每个人以其所应得,应得是正义的最基本的内涵。譬如,柏拉图认为,“正义就是给每个人以适如其分的报答”。〔4〕在柏拉图那里,正义存在于灵魂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或社会有机体的各个部分之间的和谐秩序之中,每个公民应当做与其本性相适应的事情,否则,正义并没有得以凸显。在查士丁尼《民法大全》中,古罗马法学家乌尔庇安曾给正义下了一个著名的定义:“正义乃是使每个人获得其所应得的东西的永恒不变的意志。”〔5〕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正义是政治共同体的最高道德,而且是统摄其他道德的最高道德。他曾将正义分为“矫正正义”和“分配正义”,并且也是这两个概念的首创者。亚里士多德强调正义的真实意义主要在于平等,分配正义在于成比例,“人们都同意,分配的正义要基于某种配得,尽管他们所要(摆在第一位)的并不是同一种东西。民主制依据的是自由身份,寡头制依据的是财富,有时也依据高贵的出身,贵族制则依据德性。”〔6〕可见,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正义在于给予人们所应得的东西,在于按照某种标准将东西分配给人们,相等的东西给予相等的人,不相等的东西给予不相等的人。
当然,应得也是一个极具争议的概念,应得的基础是什么呢?应得的核心思想是每个人应当得到其所应得的份额,正如麦金太尔所言,“正义是给每个人——包括给予者本人——应得的本分。”〔7〕然而,我们应当如何确定应得的基础呢?也就说,我们应当参照什么来判断人们是应得的,还是不应得的呢?如果我们不能明晰应得的基础,那么我们将不能确定应当依照何种标准来确定人们应得与否。关于应得的基础主要有下述几种观点:第一,道德是应得的基础,这是一种“道德应得观”。依照道德应得观,为了决定谁应得什么,必须决定哪些道德值得赞赏和奖励,倘若某个人的行为显现了某种良善的道德品质,这个人应该得到赞赏或奖励。良善的道德品质理应受到人们的称赞,然而,倘若严格依照道德应得观来判断某种行为是否应当得到赞赏,有时会得到一些不恰当的结果。例如,A和B看到有两个小孩失足掉进了水里,A毫不犹豫地跳进水里,将一个小孩救了上来,他做此事并不是为了获得任何回报。假如B也跳进水里去救了另外一个小孩,但是他做此事的动机是为了获得孩子父母的奖赏。显然A救孩子这一行为背后的动机要比B救孩子的动机要高尚一点,但是难道我们可以说B的行为不应得获得赞赏吗?如果严格依照道德应得观来进行判断,B救人行为背后的功利性太强,并没有体现一种无私奉献的道德品质,因此不应该获得称赞。显然,这种观点有违道德直觉,因为无论B救人行为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他的行为都应该获得赞赏;第二,应得的基础在于努力,这是人们通常所言说的“努力应得观”。譬如,C有在一天内生产6件衣服的能力,D在一天内只能生产3件衣服。然而,由于C做事散漫,并没有完全发挥自己的能力,他在一天内仅仅生产了3件衣服。D做事勤奋,但由于能力较为有限,一天内也只生产了3件衣服。依照努力应得观,虽然C和D的产量是一样的,但是由于D较为努力,他就应得更多的奖赏。显而易见,以努力的多寡来判断人们是否应得更多的奖赏,这是不合理的:一方面,人们难以测度努力的多少及其程度;另一方面,当有人非常努力,但是其所取得的成就甚少时,人们应当如何判断其应得多少呢?比如E在生产衣服的能力上弱于C和D,即使他比D还要勤奋许多,在一天内也仅仅只能生产2件衣服,此时人们也很难说他比C或D应得更多的奖励。因此,人们并不能仅仅依靠努力的程度来决定谁应得更多;第三,应得的基础是贡献,正义要求人们因对社会的贡献或者努力的结果而得到奖励。在人们有关应得基础的讨论中,以贡献作为应得的基础较少具有争议性,“我们要对社会所创造的财富和可利用的资源进行分配,必须考虑到与业绩相关的超过平等财富分配的要求。直觉上看这是很清楚的,并且也符合道德共识,就是我们应理解并赞成那些在共同财富的创造过程中付出了更多的努力或作出了更大贡献的人,在财富分配中获得更多的一部分。”〔8〕依照贡献应得观,贡献是人们所得的源泉和依据,人与人之间的分配是否公平,可以将其所得与其贡献进行比较,当一个人的所得与其贡献相符时,分配正义就实现了,反之,就背离了分配正义。
在现代社会,当人们讨论正义时,通常指向的是“分配正义”或“社会正义”,虽然分配正义一词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出现,社会正义则迟至19世纪时才出现,但是分配正义和社会正义这两个词也经常被通用。分配正义是一个含义丰富、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内涵的概念,在塞缪尔·弗莱施哈克尔(Samuel Fleischacker)看来,虽然在现代社会,人们通常将整个社会的资源分配问题视为正义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现代意义上的“分配正义”要求政府保证每个人都能获得一定程度的物质财富,但是这种分配正义概念只有两百年的历史。譬如,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认为分配正义指的是确保那些应得回报的人按照他们的美德获得其应当获得的利益的原则,易言之,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美德是分配正义的标准,分配正义并不关注物质财富的分配问题。只是到了18世纪以后,在斯密、卢梭、康德、马克思和罗尔斯等人的不懈努力下,分配正义的关注对象才开始转向穷人的生活处境,以及如何通过对物质财富的再分配从而改变穷人的处境等问题。〔9〕
我们在探讨正义理论时除了关注正义的内涵以外,另一个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是我们关注的是“谁之正义”,易言之,谁应当以及能够被纳入正义的范围?这也是我们在判定正义有哪两张面孔时的核心根据之一。针对这一问题,通常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主张认为应该关注同一世代的人们之间的正义问题,另一种主张则认为除了关注某一世代的人们之间的正义问题以外,还应该关注不同世代的人们之间的正义。世代所涵盖的范围是较为广泛的,除了我们刚才提及的“当今世代”和“未来世代”以外,还有“过去世代”。就这三种世代的内涵而言,当今世代通常是指目前活着的、在场的人,未来世代指的是那些尚未出生的、尚未出场的人,过去世代通常是指已经死去的、退场的人。倘若某种正义理论只关注某一世代之内的人们之间的关系,该正义理论就属于代内正义理论的范畴。倘若某种正义理论关注的是过去世代、当今世代和未来世代之间的关系,该正义理论就是代际正义理论。
二、共时性正义
如上所述,正义既包括共时性维度,又包括历时性维度,与这两个维度密切相关的是,正义可以被分为两部分,即“共时性正义(synchronic justice)和历时性正义(diachronic justice)。共时性正义是当代人之间的正义,或者是那些完全参与社会的政治关系的当代人之间的正义。历时性正义需要处理当代人与未来公民之间的关系。”〔10〕我们在此部分所探讨的那些关注正义的共时性维度的代内正义理论,即“共时性正义”,而下一部分将探讨那些关注正义的历时性维度的代际正义理论,即“历时性正义”。
代内正义理论主要关注某一个世代之内的人们之间的正义关系问题,这一正义理论大体上也可以被分为两部分,一是关注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正义问题,二是关注群体与群体之间的正义问题。人们在关注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正义问题时,往往将侧重点置于某一民族国家的成员之间的正义关系。很多思想家在探讨正义理论时,通常不自觉地接受了该理念,大体上只有斯多亚派的哲学家等少数学者曾经质疑过该立场。然而,现如今有些学者已经开始进一步延续斯多亚派的立场,主张扩展正义的适用范围,譬如查尔斯·贝兹(Charles Beitz)和涛慕思·博格(Thomas Pogge)等世界主义者已经强调,在全球化时代,如果正义理论的适用范围仅限于诸如民族国家这样的共同体之内,那么其吸引力将会大打折扣。一方面,很多学者主要关注民族国家范围内的个体与个体的分配正义问题。当代的许多平等主义者仍然将国家视为正义共同体的边界,如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就大体上认同该立场。虽然罗尔斯在《正义论》的第58节中曾依照其秉承的契约主义方法偶尔提及了国际正义,但是当他在探讨正义理论时主要还是将讨论的范围限于民族国家之内。他曾强调正义原则主要与社会的基本结构有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的影响十分深刻并自始至终。在此直觉的概念是:这种基本结构包含着不同的社会地位,生于不同地位的人们有着不同的生活前景,这些前景部分是由政治体制和经济、社会条件决定的。这样,社会制度就使人们的某些出发点比另一些出发点更为有利。这类不平等是一种特别深刻的不平等。”〔11〕在罗尔斯那里,社会被设定为一个拥有封闭结构的共同体,其正义原则就适用于调节该共同体的成员之间的关系,与其他共同体的成员之间的关系并不在其调节范围之列。
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开始超越民族国家等共同体的界限,以世界主义为分析视角,建构了各种全球正义(global Justice)理论。例如,在贝兹和博格等世界主义者那里,倘若在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时代,正义理论和平等理论的适用对象仍然像某些共同体主义者所不断申述的那样,仅限于民族国家等共同体的成员,其视野就未免太狭隘了。贝兹曾在1975年发表的《正义与国际关系》一文以及在1979年出版的《政治理论与国际关系》一书中,较早地深入探讨了富裕国家及其公民是否有一种正义的义务以便帮助贫困国家及其民众,并与其分享他们的财富这一问题。为此,贝兹将罗尔斯《正义论》中的契约主义方法用于分析全球贫困、全球不平等和全球自然资源的分布不均等问题,坚持罗尔斯的国内正义理论可以在全球层面上适用,提出了全球差别原则和资源再分配原则。〔12〕在贝兹那里,鉴于国际社会的制度与国内制度之间的相似性,只要人们在国内原初状态中不拒斥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在国际原初状态中人们也将不得不接受全球差别原则。博格批判了罗尔斯后期在1993年的《万民法》一文中以及在1999年出版的《万民法》一书中所构建的国际正义理论,认为罗尔斯的国际正义理论与其所秉承的国内正义理论之间存在着张力。譬如,博格批判了罗尔斯的名为“万民法”的国际正义理论,认为罗尔斯漠视了全球背景的不正义问题,武断地拒斥世界主义而没有将世界上的所有人作为道德关怀的终极对象,其万民法并不是一种平等主义的万民法。博格秉承世界主义这一基本立场,并试图建构一种全球正义理论来化解这种张力。作为一个世界主义者,博格认为一个人不论其国籍、财富、性别、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等因素是什么,都拥有平等的道德地位,都应该被作为平等者来对待。博格强调一些发达国家曾经在历史上奴役过他国人民,以及在当今世界上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共处于同一个合作体系之中,发达国家对全球贫困者负有某些援助责任。为了解决目前日益严峻的全球贫困和全球不平等问题,博格设想通过“全球资源红利方案”(global resources tax)来加以调节,该方案认为“虽然一国人民拥有和完全控制其领土上的所有资源,但该国人民必须对它选择开采的任何资源支付红利”〔13〕。依博格之见,某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在开采自然资源并出售以后,无论该资源的售卖国还是该资源的购买国,都必须为此支付一定的红利,这种红利可以被用于解决全球贫困和全球不平等问题。
代内正义还包括群体与群体之间的正义,譬如,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正义问题,以及一国公民与他国公民之间的正义问题等等,这两种正义理论都与罗尔斯的立场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一,我们可以将男女之间的正义问题称为“性别正义”问题。罗尔斯的《正义论》出版以后,面临着很多批判,其中一些女性主义者提出了自己的异议,并在此基础之上阐述了性别正义理论。苏珊·奥金(Susan Moller Okin)曾言,“罗尔斯自己忽略了性别,尽管他在理论初期有过把家庭放在基本结构中的论述,但没有考虑在正义制度中家庭是否存身其中、以何种形式存在。……因为他有关性别的假设,他不能把正义原则适用于人类抚育这一领域,一个对成就正义、维持正义至关重要的领域。”〔14〕在以奥金等人为代表的女性主义者那里,罗尔斯等人的自由主义正义观既没有关注女性的正义诉求,又没有试图矫正女性在父权制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中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为了真正实现性别正义,奥金等女性主义者强调应该超越自由主义传统内部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二分法(即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二分法),认为这种二分法漠视了家庭等私人领域中所存在的非正义现象,并致使某些学者只将正义理论适用于公共领域;其二,国际正义主要关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正义问题。如前所述,罗尔斯在1993年的《万民法》一文及1999年出版的《万民法》中阐发了其国际正义理念。与构建国内正义理论一样,罗尔斯在证成其国际正义理论时同样也采取了契约主义方法,认为在他所设想的国际原初状态中,各国人民(peoples)的代表将会接受他从国际关系的规范中所总结出来的下述八条原则:“1.各人民是自由且独立的,并且它们的自由独立将得到其他人民的尊重。2.各人民要遵守协议和承诺。3.各人民是平等的,它们必须是那些约束它们的协议的订约方。4.各人民要遵守互不干涉的义务。5.各人民有自卫权,但无基于自卫之外的理由发动战争的权利。6.各人民都要尊重人权。7.各人民在战争中要遵守对战争行为设立的特定限制。8.各人民对那些生活在不利状况下、因此无法拥有一个正义或正派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其他人民负有一种援助的责任。”〔15〕当然,上述八条原则并不是他的万民法的全部内容,罗尔斯还曾强调,倘若人们在思考国际正义问题时觉得有必要,还可以适当增添其他原则。
三、历时性正义
〔1〕David Heyd,“A Value or an Obligation?Rawls on Justice to Future Generations”,in Axel Gosseries (ed.),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167.
代际正义由“世代”和“正义”两个词构成。世代的内涵较为丰富,尤金妮亚·斯卡比尼(Eugenia Scabini)和埃琳娜·玛尔塔(Elena Marta)认为“世代也许被定义为群组(cohort)、与消费方式相关的生活阶段、家谱的传承(genealogical lineage)或者经历过类似历史事件的一群人。”〔18〕斯卡比尼等人随后一一介绍了世代的四种含义。根据第一种定义,世代被理解为群组,这是关于世代的人口定义,指的是基于出生年份或者年龄的分析单位。时间周期可以是1年、10年或者一个人出生到随后生下自己孩子之间的平均间隔,这个间隔通常是25年或者30年;第二个定义是关于世代的经济定义,涉及到消费方式或者消费者的类别,一些人因年龄相同而在消费方面有着相似的偏好,或者与生产系统有着相同的关系。根据这种定义,我们至少可以确定三代人同时存在,即青年人、成年人或老年人;第三个定义是关于世代的家谱定义,它将世代定义为一种特定类型的家庭关系,而不是从属于某一年龄组或者经历过同一历史时期的事实来看;第四个定义是关于世代的历史主义定义。该定义是建立在共同的社会历史经验的基础之上的,强调了特殊的历史事件的重要性,从文化和社会的角度来界定世代。根据这种观点,一个人一生中只属于一个世代,比如“1960年代的一代”指的是那些生活在1960年代的青少年。
不仅如此,如上所言,世代所包含的范围也较为广泛,大体上包括过去世代、当今世代和未来世代。虽然未来世代从表面上而言指的是那些尚未出生的、尚未出场的人,但是人们对当今世代和未来世代之间是否存在“重叠”这一问题,通常有两种看法,一是“非世代重叠”,二是存在“世代重叠”。克莱顿·胡宾(Clayton Hubin)和威尔弗雷德·贝克曼(Wilfred Beckerman)等人采取的是前一种用法,胡宾是较早地关注罗尔斯的代际正义理论的学者之一,他曾言,“当我在谈到未来世代时,我是指这些世代与我们所处的世代没有重叠。……我在此感兴趣的是,当今世代被要求在非功利主义的基础上,对未来的、非重叠的世代在道德上被要求做什么。”〔19〕贝克曼在通过质疑未来世代是否拥有权利从而试图批判代际正义理论时,也曾言“我将讨论尚未出生的未来世代,并不存在世代重叠的情况。于是,我并不关注因情感的关系我们倾向于关心我们的孩子或他们的后代,也不关心因同样的原因我们对他们负有责任。”〔20〕特雷梅尔在其研究代际正义理论的重要著作《代际正义论》中认为“非世代重叠只是一种建构。那种普遍适用的代际正义理论应该包括所有可能的世代之间的比较,也就是说,它必须包括不重叠的世代,但是不限于这些世代。排除世代重叠的代际正义理论并不是完备性的。”〔21〕可见,特雷梅尔采取的“世代重叠”的概念。
在小山坡的山腰僻静处,范峥峥转身偎依到贾鹏飞的怀里,两人紧紧地搂抱在一起。日夜的思念,今天居然在山野团圆,真的,说农民工建设了城市,可是这小城却没有我们夫妻的一张床啊。喘着粗气的贾鹏飞边说边转过范峥峥的身子,让她抱住一棵大树,然后从后面褪下范峥峥的百褶裙子……
根据代际正义理论是否涵盖过去世代、当今世代和未来世代等世代之间的关系以及是否包括世代重叠,我们可以将代际正义理论分为“广义的代际正义理论”和“狭义的代际正义理论”。广义的代际正义理论既是一种处理当今世代、过去世代和未来世代之间关系的代际正义理论,又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处理老年人、中年人和青年人之间关系的代际正义理论。广义的代际正义理论不仅要着重探讨当今世代对未来世代负有何种道德义务,而且也要处理当今世代对过去世代的行为负有何种道德义务。历史上存在很多非正义的行为,譬如奴隶制和种族灭绝等等,都是过去世代中的某些人对某些人所犯下的罪行,对于这些历史上的非正义现象,有很多问题值得深思,正如邓肯·艾维森(Duncan Ivison)曾言,“在讨论我们彼此亏欠什么时,我们应该给予过去多少规范的权重?哪些历史上的非正义是重要的,为什么?应该赔偿谁?谁应该给予赔偿?什么形式的赔偿?最后,在捍卫(或批判)赔偿时,需要考虑什么样的审慎的和政治的考量?”〔22〕其中的很多问题都与代际正义理论有关,例如,当今世代对过去世代中的受害者的后代(如黑奴的后代、被屠杀之人的后代)负有何种义务?由于如何矫正历史上的非正义现象,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因篇幅所限,我们在此并不展开,实际上,很多代际正义理论往往并不涉及到如何处理当今世代与过去世代之间的关系问题。
零价铁还原-芬顿氧化工艺已广泛应用于各类化工废水的预处理工段,其中零价铁还原技术的处理效果比较稳定,而芬顿氧化技术需投加大量的双氧水药剂,导致药剂用量大、运行成本较高。
〔11〕〔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7页。
四、代内正义与代际正义之间的关联性
代际正义与代内正义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为什么我们需要单独讨论代际正义理论,而不是将其与代内正义理论一起探讨呢?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代内正义理论和代际正义理论的问题域的差异有着很大的关联性。代内正义理论和代际正义理论所关注的问题显然是不同的。如前所述,代内正义理论关注的是同一个世代之内人们之间的正义问题,譬如,一个国家内部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正义问题,罗尔斯在《正义论》所构建的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就主要关注此类问题,还有国际正义理论、全球正义理论以及性别正义理论等等都属于代内正义理论的范畴。然而,代际正义理论主要关注是不同世代的人们之间的正义问题,并不关注国家之内的正义问题、国际正义和性别正义等内容,当今世代和非重叠的未来世代之间的正义问题,就属于代际正义理论的范畴。从理论层面来说,代际正义理论主要关注如何理解代际关系?怎样证成代际正义理论?未来世代拥有权利吗?倘若有的话,这些权利的根基是什么?利益和负担怎样在各代之间进行较为公平的分配?当今世代对未来世代负有道德义务以及负有何种道德义务?如果我们将道德义务分为消极义务和积极义务,那么我们对未来世代负有禁止对其施加痛苦的消极义务,还是负有主动促进去福祉的积极义务呢?消极义务和积极义务在有些情况下可以显而易见地区分开来,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很难被区分开来。另外,倘若当今世代对“亲近的未来世代”的义务与“遥远的未来世代”的义务之间出现了冲突,那么哪个义务更加具有优先性呢?从实践层面而言,代际正义关注的问题是多种多样的,如环境问题和人口问题等,就是代际正义理论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实际上,环境问题、经济问题和人口问题都与可持续发展有一定的关联性,它们分别关注经济方面的可持续性、环境方面的可持续和人口方面的可持续性。在构建代际正义理论的过程中,人们通常假定当今世代与未来世代是不会碰面的,正是因为当今世代在做出能够影响到未来世代的环境政策、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等决策的过程中,未来世代是不在场的,这才需要我们认真思考怎样才能公平地对待未来世代,怎样才能获得一种自洽的代际正义理论。
代内正义与代际正义之间的关联性,大体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代内正义的实现是解决代际正义问题的前提。对于代内正义与代际正义之间的关系而言,廖小平曾言,“不论是在不同国家之间、不同地区之间,还是在不同群体之间、不同个人之间,代内的严重不公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甚至还在不断地加重。如果代内公平作为一个问题还不能解决,代际公平又如何能够实现?大谈代际公平不显得有点尴尬吗?因此,虽然代际公平在价值上具有优先性,但要解决代际公平问题,必须首先立足于代内公平的实现。”〔23〕倘若一个世代内的分配正义、性别正义、国际正义和全球正义等诸代内正义的内容得不到实现,那么那种致力于实现代际正义的努力往往变成一种空谈和奢望。也就是说,从事实考量的角度出发,人们需要优先解决代内正义问题,尤其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形中更应该如此,然而,此时人们仍然需要考量当今世代所采取的政策可能对未来世代的影响。人们之所以要如此,在很大程度上与代际之间权力的不平等性和非对称性有关。当今世代既可以为未来世代做贡献和进行储存,也可以伤害未来世代,不为未来世代进行任何储存而大量消耗很多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例如,当今世代对核废料的处理措施是否妥当,可以对未来世代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倘若当今世代采取一种不负责任的环境政策,未来世代就很难拥有干净的水源、清洁的空气和不受污染的土壤,而未来世代不得不接受这一切。这与代际关系所具有的非平等性和非对称性密切相关,简言之,当今世代可以伤害未来世代,而未来世代对此是无能为力的,同时,未来世代的偏好乃至其是否能够存在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受到当今世代的影响。〔24〕如果当今世代不采取审慎的行动(如采取那种会产生大量污染的环境政策、大肆向外借债),那么当代内正义实现之后,代际正义并不是自然而然就可以实现的。
应改传统的“冬剪为主”为“四季修剪”。改形的重心在冬剪,而保证改形成功的关键则在于生长季修剪。所以要把全年70%~80%的修剪工作量放在生长季节进行,特别是抓住夏剪这一重要环节,采用刻、抹、扭、拉、摘、切、疏等综合手法,多动手、少动剪、不动锯,达到树体生长和成花结果的有机统一。否则,施入的肥料先长成条子再成为冬剪下来的柴火,何苦呢?
另一方面,代际正义的实现也反过来有助于解决代内正义问题。与人们对代内正义理论的密切关注相比,人们对代际正义理论倾注的精力是较少的,即使在对代际正义理论的有限研究中,人们往往认为代际正义只是处于从属地位而已,正如扬纳·汤普森(Janna Thompson)曾言,“在现代政治哲学中,代际正义理论通常被视为共时性正义理论的附属物。”〔25〕实际上,代际正义应该与代内正义处于同样的位置,不能只处于从属地位。虽然我们在以上强调代内正义的实现是解决代际正义问题的前提,这一观点意味着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人们要优先解决代内正义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代际正义只能从属于代内正义,更不意味着代际正义处于一种可有可无的地位。人们在致力于实现代际正义的过程中所采取的诸多举措,往往也有益于代内正义的实现,譬如,代际正义理论强调在发展的过程中,可持续性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倘若当今世代秉承这一发展原则,强调采取各种保护环境的政策,那么当代人所处的环境也会逐渐得到改善,也会拥有清新的空气、干净的饮用水和没有污染的土地以及食物。倘若当今世代采取相反的发展举措,毫无顾忌地向自然索取并不顾及这种行为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那么环境的恶化不仅影响到未来世代,也影响到了当今世代,这种情形肯定也不是当今世代希望看到的。
式中,M为FFT点数,l=Round(2NMvΔfTr/c),继续对s(i)作FFT后归一化取模,可得
注释:
代际正义主要涉及到正义的历时性维度。虽然代际正义从表面上来看是一个明白易懂的概念,关注的是世代与世代之间的正义问题,但是由于“正义”和“世代”这两个概念本身内涵的丰富性以及代际正义必须要着重处理的代际关系的独特性,代际正义的含义也变得较为模糊。我们首先看一下,代际正义在英文中有几种表述方式。实际上,在英文中,代际正义有多种表达方式,较为常见的表达方式有“justice between generations”“justice across generations”“generational justice”和“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等方式。当罗尔斯在探讨代际正义理论时,他所使用的是“justice between generations”,布莱恩·巴里(Brian Barry)在提及代际正义理论时,曾经既使用了“justice between generations”,又使用了“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16〕,并以后者为主。与其他用法相较而言,“justice across generations”的使用频率较低,特雷梅尔在其主编的《代际正义手册》的“导论”中曾言,“‘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和‘generational justice’这两个词是同义词。正如‘性别正义’这个词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性别之间(而不是在一个性别群体内部)的正义一样,代际正义也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世代之间(而不是某一世代内部)的正义。因此,前缀‘inter’是可有可无的。”〔17〕目前,当人们在研究代际正义理论的过程中,越来越倾向于使用“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这种表述方式,这种表述方式也愈发具有影响力,我们也采取这种表述方式。
〔5〕〔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77页。
〔2〕〔英〕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525-526页。
〔3〕〔21〕Joerg Chet Tremmel, A Theory of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London,Earthscan,2009,pp.1,25.
〔8〕〔德〕威尔福莱德·亨氏:《被证明的不平等》,倪道钧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57页。
现场调查发现,近几年施工企业中标合同额有较快增长,其中一些铁路和高速公路施工项目不仅顺利完成,还与业主、当地政府和群众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为企业创造了良好的口碑。遗憾的是,这些项目完工后,由于没有在该地区获取新的项目,只能进行常规的人员遣散、设备异地调遣的处理。这样做,不仅撤场直接成本高,而且企业在该地区获得的市场认可也无法延续。一段时间后,企业再来该地域投标项目或中标后进行施工时,市场认可、市场信息、与当地政府及业主等相关方建立沟通协调等工作还要从零起步。总的来看,企业缺少长期的市场开发规划和重点市场培养意识,也未能发挥优势项目的带动作用。
素养考查分析:该题从实际问题出发,考查了组合学科知识,需要考生掌握一定的组合题解题技能.有些考生能够将这个实际问题抽象成一个组合数学问题,并写出解答过程:.但是有些考生会遇到不同程度的障碍,例如问题的数学抽象过程中有困难、组合运算出错等.这个题目其实是以“选人问题”为背景,考查学生在真实情境中将具体问题抽象成数学概念、数学关系的能力,即对数学抽象素养的考查,同时对数学建模、数学运算等素养也提出不同程度的要求.
〔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35页。
对于海峡两岸学者而言,推动跨文化交际理论的发展是其难以回避的使命。近年来,我国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发展的新趋势之一是融合其他学科的最新理论对原有交际理论进行修正和补充。跨文化交际学的“修辞转向”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新发展。
〔7〕〔美〕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万俊人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第56页。
〔4〕〔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页。
〔9〕〔美〕塞缪尔·弗莱施哈克尔:《分配正义简史》,吴万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2-19页。
〔10〕〔25〕Janna Thompson,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in an Intergenerational Polity,Routledge,2009,pp.2,3.
狭义的代际正义理论并不涉及当今世代对过去世代的行为负有什么样的道德义务,而主要涉及到当今世代与未来世代之间的关系,此时也会关涉到我们刚刚提及的是否存在着世代重叠的问题。那种采取世代重叠概念的狭义代际正义理论同样也要处理老年人、中年人和青年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例如,它涉及到家庭中的代际关系。虽然特雷梅尔偏爱世代重叠并强调非世代重叠只是一种建构,但是当人们在探讨当今世代与未来世代之间的关系时,非世代重叠的假定往往是一种主流的设定,人们通常关注的是当今世代对那种与当今世代并不存在重叠的未来世代(以下简称“非重叠的未来世代”)负有哪些道德义务。对于探讨代际正义理论而言,人为“构建”的非世代重叠情况同样是有用的。在那种采取非世代重叠的狭义的代际正义理论中,未来世代是指在目前地球人的所有人去世以后将会存在的人,换言之,这些人目前尚未出场,未来世代也可以被分为“较近的未来世代”和“遥远的未来世代”。倘若我们采取这种关于未来世代的界定方式,刚才我们提及的老年人、中年人和青年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应该属于我们上面提到的“代内正义理论”需要解决的问题。总之,大部分关于代际正义理论的研究,倾向于假定在不存在世代重叠的情况下探讨狭义的代际正义理论,即如何处理当今世代与非重叠的未来世代之间的关系。
(5) 辅助服务市场化。电能交易市场化后,更应建立并强化辅助服务市场,用市场价格体现辅助服务的价值。预计未来辅助服务的价格会大幅提升。
〔12〕Charles R.Beitz,“Just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Vol.4,No.4,1975,pp.360-389.
(3)If Michael had spent more time with his fathere,he would not have lost him with so much sorrow.
〔13〕Thomas W.Pogge,“An Egalitarian Law of Peoples,”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Vol.23,No.3,1994,pp.200-201.
〔14〕〔美〕苏珊·奥金:《正义、社会性别与家庭》,王新宇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51-152页。
〔15〕〔美〕约翰·罗尔斯:《万民法》,陈肖生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3年,第79页。
〔16〕参见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284;Brian Barry,“Justice between Generations”,in Law,Morality and Society.Essays in Honor of H.L.A.Hart,P.M.S.Hacker and Joseph Raz (eds),Oxford,Clarendon Press,1977,pp.268-284;Brian Barry,“Sustainability and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in Fairness and Futurity.Essays on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Andrew Dobson (e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93-117.
〔17〕Joerg Tremmel(ed.), Handbook of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Cheltenham,Edward Elgar,2006,p.19.
〔18〕Eugenia Scabini and Elena Marta,“Changing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European Review,Vol.14,No.1,2006,pp.81-82.
婆婆是个干净利落的人,要强了一辈子。来到欣欣家,也发挥了她一辈子的特长。没几天,婆婆就摸到了他们俩的作息和生活规律,连连叹气说这不行,这样身体就都完了,还历数老亮从小的好习惯,言下之意,如今的“败家”和“不务正业”都是欣欣给带坏的。她强迫老亮每天早晨必须吃早饭,没直接说欣欣,但是眼神已经很有杀伤力地说明,她这个媳妇儿太不合格了;又责令他们必须回家吃晚饭,不可以叫外卖;不过年不过节的,不能乱买东西。这基本就是含沙射影地指责欣欣了,因为每天的快递拆开,基本都是欣欣的……
〔19〕Clayton Hubin,“Justice and Future Generations”,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Vol.6,No.1,1976,p.70.
〔20〕Wilfred Beckerman,“The impossibility of a theory of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in Joerg Tremmel (ed.,) Handbook of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Cheltenham,Edward Elgar,2006,p.54.
〔22〕Duncan Ivison,“Historical Justice”,in John S.Dryzek, Bonnie Honig and Anne Phillips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Theo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508.
〔23〕廖小平:《伦理的代际之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9页。廖小平此时所提及的“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即本文所说的“代内正义”和“代际正义”。
〔24〕参见高景柱:《论正义与代际关系》,《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作者简介:高景柱,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西方政治思想史、当代西方政治哲学。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西方国别政治思想史”(项目编号:13&ZD149)的阶段性成果。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9.03.002
〔责任编辑:汪家耀〕
标签:正义论文; 世代论文; 理论论文; 未来论文; 的是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学术界》2019年第3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西方国别政治思想史”(项目编号:13&ZD149)论文;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