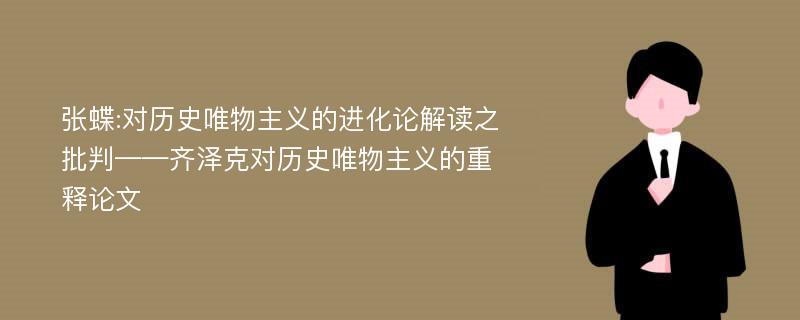
内容提要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一书中,齐泽克在批判历史唯物主义进化论解读的基础上,重新解释了历史唯物主义。齐氏一反进化论解读对生产力的重视,致力于提高生产关系的优先地位。从精神分析理论的视域出发,齐氏展示了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作为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动力这一悖论的逻辑。齐泽克将资本主义悖论的逻辑与剩余快感的逻辑进行互文性理解,提出了资本主义悖论具有建构性的观点。在历史观问题上,齐泽克一方面颠覆了进化论解读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连续性的强调,凸显了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断裂性,从而为革命敞开了可能性空间;另一方面,通过施行成分的提法,更好地展现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能动性作用。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 生产关系 资本主义悖论 革命
齐泽克通过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的进化论解读,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重释。齐泽克重释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进化论解读主要有三大方面的根本差别:第一,在分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时,齐泽克不仅重视生产关系的重要性,而且还为生产关系奠定了优先地位。第二,齐泽克通过剩余价值与剩余快感的互文性理解,剖析了资本主义悖论在资本生产过程中的显现方式,反对进化论解读将其看作资本主义最终走向灭亡的根据,相反,认为这一形式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具有建构性作用。第三,在史学观方面,齐泽克主要着力解决历史本质和历史主体的认知这两个核心问题。在历史本质问题上,齐泽克否定了进化论史学将历史看成是封闭发展的连续体的观点,强调了历史唯物主义固定历史流动,切断连续历史的重要性,凸显了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革命性因素;在历史主体认知问题上,齐氏延续了卢卡奇重视阶级意识的传统,提出了施行成分的说法,更好地展示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能动性。
生产关系的优先性
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论述,通常被表述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一般叙事模式:“最初使生产力迅速发展成为可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成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生产力超出了生产关系的框架,因而需要建立新形式的社会关系。”①齐泽克将这一理解斥为“寻常的历史主义—进化主义解读”②。他批评这样的进化论解读过于简单化,并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相去甚远。齐氏认为,进化主义解读只是大致借鉴了“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的范式,并将之称为“蛇的隐喻”,“蛇皮一旦撑得太紧,就会蜕皮”③。对此,齐泽克还提出了一个就这一解读而言无法解答的诘问,即“如何严格确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的那一顷刻——尽管这一顷刻只是理想性的?”④这一质询找到了进化论解读的阿克琉斯之踵。
不同于这种简单化的进化论解读,齐泽克肯定了马克思本人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思想是具有多层次性的。他通过分析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的一段话,阐发了他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辩证运动的全新理解。
马克思的原话如下: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以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为前提;这种生产方式连同它的方法、手段和条件本身,最初是在劳动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的基础上自发地产生和发展的。劳动对资本的这种形式上的从属,又让位于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⑤
齐泽克的解读如下:
马克思论述了资本控制下的生产过程中的形式吸纳和真实吸纳之间的关系:形式吸纳先于真实吸纳;也就是说,资本首先吸纳生产过程,只是到了后来,才逐步地变革生产力,使生产力与生产过程相一致。与上面提到的过分简单的观念相反,是生产关系的形式驱动着生产力发展,即驱动生产关系的“内容”发展。⑥
在这里我们首先必须厘清两个使用不一致但至关重要的概念。马克思所使用的“从属”一词,《资本论》的英译本用的是subjection,而在齐泽克的解读中则使用了subsumption(《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的中译本译为“吸纳”)。这两个概念都关涉劳动和资本的行动,只不过表示了两种相反的行动方向。用L表示“劳动”,C表示“资本”,将“从属”(subjection)的行动方向表示为“→”,那么,“吸纳”(subsumption)的行动方向就表示为“←”。于是,“从属”(subjection)所表示的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就可以化约为公式:L→C;而“吸纳”(subsumption)所表示的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就是C←L。这样,我们就能一目了然地看到,L→C和C←L这两个公式所表示的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劳动“从属”(subjection)于资本和资本“吸纳”(subsumption)劳动,表示着同样的含义。所以,齐泽克的形式吸纳和真实吸纳就是马克思的形式上的从属和实际上的从属。齐氏的矫情,大抵是用“从属”与“吸纳”这两个新的概念,去表达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矛盾运动,一个是主动意义上的,一个是被动意义上的。
厘清了这两个概念之后,我们进一步对比马克思的原话和齐泽克的解读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的这段话提示了以下三个关键信息:第一,生产方式是生产的前提;第二,关于劳动对于资本的从属,区分出了形式上的从属和实际上的从属;第三,在逻辑顺序上,劳动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先于生产方式的产生与发展。从这些信息中,我们可以看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远不是进化主义解读的范式所能涵括的。资本的目的虽然是通过扩大生产无限增殖,但是,以何种生产方式进行生产这是在进行生产前已经预先设定了的。生产方式的产生与发展基于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生产关系是生产的前提。
齐泽克的着眼点在于对马克思所区分的两种从属关系的含义及其顺序做重新阐明。齐泽克把“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理解为生产关系,“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理解为生产力。因此,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让位于“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的这一过程就变成了:首先是资本吸纳生产的过程,即先是变革生产关系,然后再是变革生产力,使生产力与生产过程相一致。齐泽克的解读与进化论解读正好相反,是形式驱动内容,形式建构内容。生产总是在某一特定的生产关系中展开的,因此,生产力也总是某一特定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力,没有脱离生产关系的自在自为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作为生产力的前提存在,建构并驱动着生产力的变革与发展。这也正反映了齐泽克对形式的重视是一以贯之的,在齐泽克的理论体系中,形式都具有建构性意义。通过批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进化论解读,齐泽克凸显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优先性地位。
资本主义悖论的建构性
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的分析,马克思阐发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就“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⑦进行了说明:
关键并不在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时候,生产关系的框架就会开始限制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关键在于,正是这一固有的限制,这一“内在的矛盾”,驱使着资本主义的永恒发展。资本主义的“常态”就是对它自身的生产条件进行永恒的革命:刚一降生,资本主义就“腐烂”了,它充满了严重的矛盾和不一致,对平衡充满了内心的渴望:这正是永不停息地变革和发展的原因。对于它来说,要想反复消解它自身的根本性的、构成性的不平衡(“矛盾”),要想与它自身的根本性、构成性的不平衡(“矛盾”)达成妥协,唯一的方式就是永不停息地发展。它的局限不是它的限制,而是它发展的动力。⑨
2.道路绿化覆盖率低,道路绿化带窄小,部分已形成的道路没有植树绿化。行道树树种单一,没有形成立体空间的和谐,与点的结合还不够,城市的防护林体系没有形成,预防灾害能力不高。
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而资本的增殖是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困化为代价换来的。因此,资本要想保持持续增殖,就必须使自身的增殖限制在广大生产者仍可被剥夺的范围之内。而这种限制与资本无限增加生产,无条件地发展生产力的目的相矛盾。资本的目的在于无限增殖,而其增殖的方式却必须建立在有限的条件之下,所以,马克思认为资本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
第一,完善师资队伍保障。其一,优化师资结构,构建适用于专业技术人才培养的师资团队。其二,加强教师培训力度。高校在鼓励教师继续深造方面,不应一味追求学术造诣,要将提高教师实践技能提上日程。高校要积极组织教师深入企业生产一线进行实践,鼓励教师参加企业交流会,全面深刻了解企业文化。这对指导大学生的实践教学十分重要。与此同时,高校还应当聘请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共同参与大学生实践教学的指导,高校教师可以同企业人员交流互动,从而在实践教学方面收获更多的经验。其三,改善教师教学方式。高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教师除了选择传统讲授的教学方式外,要重视启发式和行动导向式的教学方法。
一是要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利益冲突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源和基础。基层警务工作要依靠依法照章办事,切实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7]基层警务机关要按照“发现得早、控制得住、处置得好”的总体要求,根据有关信息,及时了解当前社会的核心问题并且及时处理。高度关注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地区的动向,健全和完善维护稳定的预警工作机制。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基层警务工作者应该主动配合有关部门进行问题调查,根据调查情况进行针对性的行动,协调人民群众通过正常渠道反映问题,指导群众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通过源头上即基层方面的控制来保证社会的稳定。
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以广大生产者的被剥夺和贫困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⑧
李青海在谈及自己违纪违法心态时说,对自己的行为已经严重违纪违法也心知肚明,但当时贪婪和侥幸已经在心里占了上风,完全将党纪国法抛诸脑后。正如他在忏悔书中自讽,在法院工作时,取得的法律专业研究生证书,是为了职务升迁增添含金量混来的文凭,学过法但只是作为晋升之用,在工作中依然是个“法盲”。而且在他看来,很多事都是私下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只要对方不说谁也不会知道。
资本生产是以广大生产者的被剥夺作为增加生产的前提条件的,它只能限制在这一条件允许的范围内,但这与无条件地发展社会生产力相矛盾,这正是齐泽克所说到的资本主义从一降生就存在的“严重的矛盾和不一致”,是资本主义自身“根本性的、构成性的不平衡(‘矛盾’)”。为了消除这种不一致,资本主义只能不断扩大生产条件所允许的范围,“对它自身的生产条件进行永恒的革命”。而发展其自身的生产条件的方式就是不断扩张生产。在齐泽克这里,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正是驱使资本主义永恒发展的动力所在,这就是齐泽克发现的资本主义特有的悖论:“资本主义能够把它的局限,把它的无能为力,转化为它的力量之源:它越是‘腐烂’,它的内在矛盾越是趋于恶化,它就越要为了生存进行内部革命。”⑩齐泽克致力于挖掘资本主义悖论的建构作用。
(3)依托水土资源发展水产林果经济。大力发展特色水产业,走常规和特色水产品养殖与深加工之路。自主研发适销对路的系列水产品,在荆门及周边地区开设漳河水产品直销店和专营连锁店。同时适应市场变化,积极调整经营思路,加强对外销售合作,漳河水产品远销北京、新疆等十多个省市。林果品结合旅游,发展生态观光农业和特色采摘销售,延长产业链,提高经济效益。漳河“李集岛”蜜橘和水产品“脱脂大白刁”品牌逐步建立。
传统意义上,我们这样理解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不一致表现为社会生产方式和私人占有方式之间的矛盾,并且这一矛盾已经渗入资本主义的骨髓,成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而齐泽克显然并不满足于此,将资本主义悖论从解构性因素变为建构性因素才是他的真正意图。齐氏就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一段话展开了进一步的解读:
关于资本主义悖论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运作方式,齐泽克从精神分析理论的角度予以了解说。齐泽克找到了剩余价值这一理论突破口,用充斥着大量精神分析理论术语的语言对剩余价值的逻辑与剩余快感的逻辑进行了互文性理解:
虽然齐泽克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比庸俗进化主义深刻的地方就在于马克思发现了剩余价值,以此展示了资本主义悖论,为实在界之残余保留了位置。但是,齐泽克同样对马克思提出了批评,认为马克思没能处理这种悖论。他认为,最具代表性的例证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对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描述,即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关系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这一矛盾吁求着社会革命,革命的功能在于建立新的适应生产力发展需求的生产关系,于是,生产力继续高速发展。这完全就是庸俗进化主义的辩证法。但是,齐泽克本人也同样未对资本主义悖论做出合适的处理。不过,齐泽克提到了资本主义悖论的建构性作用,这是过去关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悖论的论述中常被忽略的内容。那被齐泽克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之动力的资本主义悖论,普遍被认为是将资本主义推向灭亡的真正原因。如法比奥·维吉(Fabio Vighi)就认为,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始终站在黑格尔主义的立场上,断言资本主义最终走向灭亡是其自身造成的,并不是作为主体的无产阶级的胜利。齐泽克通过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作为切入点,提出了资本主义悖论的建构性作用。通过精神分析理论对剩余价值的重新解释,资本主义悖论的建构性作用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不一致性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是如何运作的这一过程体现出来。
剩余快感的逻辑是这样展开的:剩余快感并不是原初快感的剩余,相反,剩余快感中的快感只能依附于剩余而存在。同样,剩余价值的逻辑如是展开: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剩余价值是资本扩大生产的目的,即资本保持自身增殖,同时,又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起点,所以,剩余价值并不是价值的剩余,相反,资本价值的存在必须依附于剩余价值,没有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生产也就无以为继。因此,齐泽克说剩余价值是“启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成因’”,这同源于剩余快感作为欲望的客体—成因(object-cause of desire)。从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出发,在齐泽克看来,“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有效地凸显出拉康的作为剩余快感之化身的小客体的逻辑”。
关联理论的核心就是寻求最佳关联性原则,即人类的交际行为都会产生一个最佳相关性的期待,接受者要确定交际者的交际意图,就必须在交际双方共知的认知环境中找到对方话语和语境之间的最佳关联,通过推理推断出语境的暗含意义,从而获取语境效果,达到交际的目的。
十月革命重复了法国大革命,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是一种误认,毕竟十月革命并不是法国大革命。但是,正是通过十月革命这一误认,我们认出了法国大革命的精神,十月革命回溯性地建构了法国大革命的意义,使我们触及了法国大革命。齐泽克在革命问题上的激进之处在于断裂为重复所敞开的可能性空间,而齐泽克的革命正处于这个激进的断裂点上。齐泽克通过区分两种时间观,进一步区分了基于这两种时间观之上的历史观。连续性的官方史学扼杀了重复之可能性,作为对立面的历史唯物主义为重复的对象——那些被获胜的历史所抛弃的失败事件——打开了大门。
那个晚报记者林超我却是见到过的。那夜出事以后,我整天就龟缩在学校里,哪里也不敢去,整天在小说中打发惶恐,麻醉自己。渐渐的我也开始涂抹一些文字,两年后居然在校内声名鹊起,两年间长长短短发表了30余篇小说和随笔,那篇《我是衰哥我无敌》在社会上还引起了一点轰动。林超就来采访我了。
剩余快感不是使自己简单依附于某种“正常”的、根本的快感的剩余。这么说,是因为剩余快感中的“快感”只能出现在这种“剩余”中,因为剩余快感是构成性的“过度”。减去剩余,就会失去快感。这与资本主义无异:资本主义只有对其自身的物质条件不断进行革命,才能死里逃生,倘若“保持不变”,倘若达成了内部平衡,它必死无疑。因此,剩余价值与剩余快感存在着同源关系:剩余价值是启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成因”,剩余快感是欲望的客体—成因。
女人在巡视完自己分管的病房之后,给她一个要好的女友打了电话,说约她明晚去家里吃拌面。两个人都是河南籍,又是小学同学,为求职都来到了外省这座陌生的城市里,自然很亲近。好友也刚好跳出了婚姻这个大鸟笼,打自由那天起就跟女人说,她再也不会去碰婚姻那张网了,免得又得鱼死网破。
本项目使用的混凝土平仓推土机有两类,分别为D31p-18A和D65P-8,二者均产自日本;所使用的仓面碾压设备有三类,包括BW200、BW202AD和BW75S,三者均产自德国。检测设备有DN-40中子仪和TS-600VC值测量仪。
2012年1月至2014年11月收住我院ICU进行亚低温治疗行脉搏指数连续心输出量(PICCO)监测的颅脑损伤患者60例,GCS评分 3~7分,符合重度颅脑损伤诊断标准,排除既往有心肺疾病者。所有患者均行亚低温治疗,治疗时间72 h。将60例患者随机分为咪达唑仑复合芬太尼组(A组)和冬眠合剂组(B组),每组30例。两组病例数、年龄、性别、GCS评分、SOFA评分等比较,差异无显著性,具有可比性。
革命的可能性
关于历史观的论述,有两个先后相继的问题是绕不开的,一个是关于历史本质的问题,另一个是关于历史主体的认知问题。齐泽克围绕着这两个问题展开了对作为历史观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进化论解读的批判。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史学观,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历史本质为何的问题,并且对历史本质的回答也将决定这一史学观的性质与定位。齐泽克将历史唯物主义定位在进化论史学的对立面,这种判断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进化论史学所分别对应的不同的时间观而做出的。对于时间观的区分,齐泽克借鉴了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里关于时间的论述,明确提出了两种时间模式:一种是空洞的、同质的连续时间;另一种是被填充的非连续时间。前者对应的是进化论史学,后者则界定了历史唯物主义。基于对时间模式的这种区分,拥有同质的、线性的连续时间观的官方史学就被齐泽克认为是一种进化论史学。在这种进化论历史观的视域之下,历史被视为封闭发展的连续体。相反,历史唯物主义由于基于被填充的非连续的时间观之上,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下,历史就成了由失败事件的重复,被回溯性地建构。
齐泽克将历史唯物主义放在了官方史学的对立位置上,二者的对立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视角方面,官方史学是胜利者的凝视,而历史唯物主义则是从被压迫者的视角出发的;其次,在历史内容方面,官方史学撰写的是胜利者的伟大成就与文化宝藏,而历史唯物主义除了观照伟大人物的成就外,还关注默默无闻者的劳作以及失败的被压迫阶级的行动。最后,在对待时间的问题上,官方史学面向未来,而历史唯物主义则面向过去。
齐泽克对官方史学的理论样态的概述如下:官方史学从获胜者的视角出发,通过将获胜者的伟大成就确立为写入历史的连续性事件,从而屏蔽了失败之物,即将被压迫阶级的行动,将同时代默默无闻者的劳作排除在历史书写之外,由官方确认的“实际发生过的事件”构成了连续性的“实证”的历史。官方史学并没有给被压迫者留下位置,用齐泽克的话来说,他们的失败成了被窒息的过去,也就是齐泽克所谓的经历了符号性死亡。由于被压迫者在官方史学中找不到任何可以归诸自己的东西,他们只能把被窒息的过去归诸自身。
与此相反,在精神分析理论中,历史作为符号网络,是可以被不断书写的。根据这一逻辑,“过去”是依赖于能指网络而存在的,也就是说,过去被纳入能指的共时网,在符号秩序中,以历史传统的形式呈现,并随着能指网络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如是展开:当新的主人能指出现,关于过去的叙事就会以一种新的方式被重构,使过去仍然保持可读性,并回溯性地改变了整个传统的意义。基于这样的“过去”概念,“重写历史”就被齐泽克做了如下阐释:“把某些因素纳入新的肌理,进而赋予这些因素以符号性分量。”基于从未来返回的时间观和以符号能指为核心的叙述主义历史观,齐泽克把历史视为是不断地被重写的,因为无意识总是在未来的意义呈现之中被纳入现实的能指共识网中,每一次新的因素重新整合进入符号系统之中,就意味着历史被重新书写。
我无意中参与了一场巷战,被路过的老师扭送到校长室。校长看着我劣迹斑斑的违规记录,摆摆手说:“你回家去吧,以后,也不必再来了。”
基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齐泽克对革命持积极态度,并将每一次失败的革命都纳入到当前革命的胜利之中。“革命行动通过重复,回溯性地拯救过去。”因为官方史学将历史视为封闭的发展连续体,这一连续体是以获胜者或者说当权者的视角去看待的,所以,过去那些失败之物便无法进入胜利者的视野,无法进入符号系统。而这些被窒息的过去就成了被压迫阶级拯救自身,在符号秩序中重生的唯一希望。因为过去以失败之物的形式包含着未来的向度。齐泽克就此对革命进行了分析:“当前革命形势把自己视为对过去失败了的形势的重复,视为通过对其自身的成功开发而获得的回溯性‘救赎’。”换言之,现实革命的命运同时也决定了过去失败了的革命的命运。现实革命还肩负着过去革命在其之中重复自身的使命。
在《无器官的身体:论德勒兹和连续性》中,齐泽克举了十月革命重复法国大革命的例子,认为十月革命对法国大革命的重复,是对法国大革命失败的一种回溯性的补偿,给予了法国大革命以前所未有的崇高意义,这正是革命的创生性所在。革命作为历史的断裂点,为新历史的出现敞开了可能性。法国大革命作为失败的事件被官方史学排除在外,而作为一种重复,十月革命的胜利打断了历史的进程,回溯性地赋予法国大革命以重要的意义。十月革命胜利后将法国大革命纳入了历史进程中,纳入了重写的历史之中,历史在十月革命这里形成了断裂。
基于对剩余价值所做的精神分析的处理,齐泽克为资本主义悖论打开了精神分析的维度:“资本的运动,根本性的阻塞,通过狂热的活动、过度的力量消解和再生产自身。”“根本性的阻塞”(fundamental blockage)即无限发展生产力与生产条件的限制之间的矛盾,也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不一致性,“狂热的活动”和“过度的力量”描述的是生产过程的特征:生产盲目地为资本而生产,资本无限制地增加生产。资本将自身投入到这样的生产活动之中,消解了自身,并产生了剩余价值,达到了自身增殖的目的,对自身进行了再生产。根据资本主义悖论的逻辑,齐泽克进一步指出,这种“狂热的活动”和“过度的力量”是根本性无能(fundamental impotence)的表象形式。具体而言,无限发展生产力与生产条件的限制之间的矛盾,推动着资本的生产活动,而这一矛盾也正是通过资本的生产活动才显现自身。
通过对历史本质的重新定义,齐泽克为革命打开了可能性空间。在对历史主体的认知问题的探讨中,齐泽克进一步提出了施行(performative)成分的说法,用以解释革命主体的阶级意识对于主体本身的建构性作用。
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样态就被如此表述:对过去失败了的革命的重复,回溯性地完成了自我救赎,新的历史形成,过去的失败被纳入了符号秩序之中。在被压迫者对过去之维的执念之引导下,历史的发展就不能是连续流动的,换句话说,为了让过去从历史中被分割出来,作为事件进程连续体的历史就必须被割断。齐泽克看到了历史唯物主义割断连续流动的历史发展的能力。齐氏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在于:“它有能力阻止、固定历史的移动,有能力把细节从历史整体中隔离出来。”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过去,是用当下填补过的过去,它并不存在于官方史学中,不构成官方史学中历史发展的连续进程,所以说,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框架中的时间是非连续性的,是被填充的。齐泽克突显了历史唯物主义固定时间、切割连续历史的能力,为历史的重写与重复开辟了道路。重复必然要涉及“过去”,但是,在齐泽克对“过去”的描述中,并没有历时性的影子。“过去”是被压抑的过去,是被排斥在官方史学之外的过去,也就是被获胜历史建立起来的连续性所排挤出来的过去,是重复之所在。历史唯物主义为革命打开了可能性空间。
在关于历史认知的问题上,齐泽克在《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做的》(齐泽克视该书为对《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一书的补充说明)一书中论述道:
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对历史进程的一个模糊的“客观认识”,因为它是一个历史主体的自我认识的行为;它包含无产阶级的主体性立场。换句话说,历史唯物主义固有的“认识”是自我指涉的,它改变其“客体”——只有通过认识行为,该客体才变成自己确实“是”(is)的事物。
齐泽克挖掘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施行成分,不将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历史进程的客观认识,而是将其看成一个施行过程,即“历史主体的自我认识的行为”。历史唯物主义是这样一种施行活动:它最终指向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但是,无产阶级必须通过一个自我认识的行为才能成为历史主体,而无产阶级认识的对象就是其自身的历史使命。所以,历史唯物主义固有的“认识”是无产阶级认识其自身,认识自身的革命使命,而当无产阶级认识了自身之后,就成了具有革命的主体性立场的无产阶级了,无产阶级就这样通过认识行为改变了自身,使自身成为革命主体。即此而论,历史唯物主义表明了这样一种施行活动:无产阶级通过认识并接受自身的历史使命,改变了自身,使自身变成历史主体。齐泽克施行成分的提法延续了自卢卡奇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视阶级意识的能动性作用的传统。
诚然,齐泽克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解读与传统意义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大相径庭,被称为“非正统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但是,齐泽克坚决反对莫伊什·普殊同(Moishe Postone)等人试图建构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的做法。与莫伊什·普殊同不同,齐泽克通过在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的进化论解读的过程中,用精神分析理论、黑格尔辩证法等思想资源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进行了新的阐释,力证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仍然对当今社会具有解释力,尽管为获得这种解释力,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在齐泽克那里被部分地消解了。同时,在理论旨趣上,齐泽克也坚定地跟随马克思的步伐。那些资本主义批评家们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目的只是为了更好地巩固资本主义的现有地位,维持资本主义的长久存在,为其查漏补缺。而齐泽克与马克思一样,站在彻底反对资本主义的立场上,而不仅仅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某项政策或某个经济模式,如凯恩斯主义;或某个政治制度,如民主制度。齐泽克接过了马克思的终极理论目标,通过对资本主义现状的反思与批判,来达到最终消除资本主义的目标。更为重要的一点是,齐泽克对革命仍保有积极的态度,虽然齐泽克至今仍未能为其理论找到合适的革命主体,但是,齐泽克反对进化论解读的目的始终是为革命争取话语权,即便这只是理论中的而非现实性的。
①②③④⑥⑨⑩[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53、53、53、54、53~54、54~55、55、55、53、55、173、66、174、173、174~175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83页。
⑦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8、278~279页。
齐泽克继承了拉康提出的欲望和欲望表达的区分以及对索绪尔所指/能指理论的改造,认为欲望是通过语言符号表达出来的,原初快感就通过语言被纳入到了符号系统之中。但是,受到能指的歪曲,语言永远无法充分表达欲望,总有一些快感溢出符号界,成为遗漏与剩余,这便是剩余快感。这些剩余快感驱动着剩余欲望,是欲望的成因。而能指并没有相对应的所指,能指指向另一个能指,因此,欲望的客体就是匮乏的,就是缺失。剩余快感不得不被转归为欲望客体。齐泽克用“欲望的客体—成因”这样的表达方式,是为了凸显剩余快感既作为欲望的客体,同时也正是欲望的成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2~413页。
Fabio Vighi, MourningorMelancholia?CollapseofCapitalismandDelusionalAttachments, Repeating Žižek, Agon Hamza(ed.),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184.
CT及MRI增强扫描上,SPT均表现为轻度延迟强化,其病理基础是肿瘤实性成分和假乳头状成分的过渡区内肿瘤细胞围绕血管排列形成类似血窦改变;在动态增强MRI上其时间信号曲线呈流入型,具有一定的特征性,因此实性或实性成分较多的SPT的时间信号曲线有一定的诊断价值,而对于囊性或囊性成分为主的SPT,需要结合T2WI压脂及DWI序列进一步作出正确的诊断。
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中对“时间”的论述大致可以做这样的区分:一种时间是“雷同的、空泛的”,是“同质而空洞的”;另一种时间是“被此时此刻的存在所充满的”,“静止而停顿的”。参见[德] 本雅明《启迪:本雅明文选》,[美]汉娜·阿伦特编,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73~275页。
历史哲学的理论范型主要有三种,即思辨的历史哲学、分析的历史哲学、叙述主义历史哲学。分别对应着本体论、认识论和语言论。叙述主义历史观,打通历史与叙述/阐释的严格界限,或者说,将叙述/阐释的地位从历史的解释功能提升到了叙述/阐释之于史学的本质的重要性地位。齐泽克的历史观就是典型的叙述主义历史观,他致力于从阐释中反过来为历史赋予结构与意义。
Slavoj Zizek, OrganswithoutBodies:OnDeleuzeandConsequenc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11.
而且整个餐饮行业每年在以70%的比例洗牌,结构性过剩,门槛低,跟风严重,消费者喜好千变万化,一家店能存活三年就是胜利!
在语言学领域,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区分了Performatives和Constatives这两种言语行为。Performatives被译为“施行式”,Constatives被译为“记述式”。施行式:表达有所作为,目的是以言行事、以言施事;记述式:表达有所述之言,目的在于以言指事、以言叙事。(参见[英] 奥斯汀《如何以言行事》,杨玉成、赵京超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在社会学领域,布尔迪厄将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中的Performative作为其社会学理论的核心议题,但布尔迪厄主要强调命名的“performative”力量,通过言说将言说的东西变为现实,因此,布尔迪厄理论中的Performative译为“述行”更为恰当。(参见Pierre Bourdieu, What Makes a Social Class? On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xistence of Groups, BerkeleyJournalofSociology, Vol.32, 1987; Pierre Bourdieu, LanguageandSymbolicPower, John B. Thompson(ed.), Gino Raymond and Matthew Adamson(tra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performative”被翻译为“述行”。但是,齐泽克所强调的仍然是言语的行为功效,侧重点在于行为,而不在于言说,因此,本文将使用“施行”这一译法。
在《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政治因素的享乐》一书的导言中,齐泽克表示,该书“通过明确表述一些理论体系,力图对《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的分析做一些补充”。参见[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政治因素的享乐》,郭英剑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政治因素的享乐》,郭英剑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9页。
Kelsey Wood, Žižek, AReader’sGuide,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2012, p.286.
作者简介:张蝶,1986年生,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责任编辑:赵 涛〕
标签:资本主义论文; 历史唯物主义论文; 马克思论文; 生产关系论文; 历史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哲学理论论文; 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论文; 《江海学刊》2019年第3期论文; 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流动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