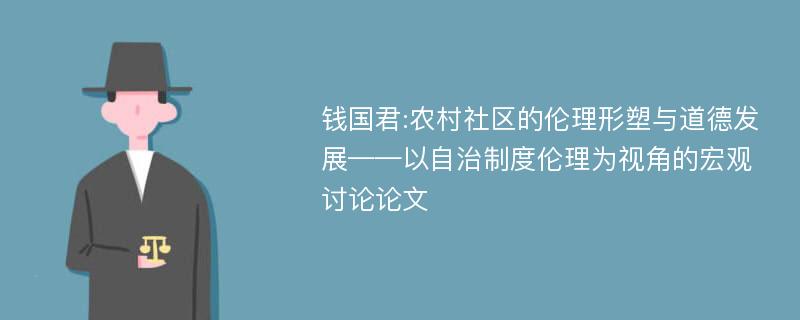
摘 要:从制度伦理到社区伦理秩序再到个体道德进步,是基于自治视角考察农村社区伦理道德发展应当遵循的基本逻辑。针对当前农村社区面临的“情面”逻辑愈发式微、“家园感”空前失落、“权威真空”“价值空场”等典型问题,应当通过自治制度伦理扬弃农村熟人社会伦理,建构“依系的主人翁式的”社区人伦秩序。而在实践中,需要审慎对待社区伦理道德的“本土资源”,明晰自治制度实体规定的根本“善”与基本“善”,并且重视程序的“善”——这也是现实中最容易被忽略的方面。
关键词:农村社区;自治;制度伦理;人伦秩序;道德
农村社区是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出现的新型乡村聚落形态注这里所说的社区特指城乡一体化体征较为明显的一种农村社会结构,相较于社会学泛指的社区,也可称为农村新型社区。其形成的地缘总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人口规模小、人口密度大或较为分散的若干行政村合并而建;另一类是依托中心村镇,由原有人口规模较大的一个行政村建设而成。其社会结构主要特征可概括为:因地制宜的产业支撑,较完善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以及一定规模的居住人口。,相对于自然村落,其“现实生活过程”发生了深刻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从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出发,“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因此,道德……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1]524-525。生产生活方式的显著变迁势必会导致农村社区面临前所未有的道德发展问题,这不仅影响乡风文明程度的提高,更关涉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注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保障。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2/04/c_1122366449.htm。以下简称“中央一号文件”。,因此,有必要务实而审慎地对这一问题加以考察。
一、研究视角的重要性——基于概念关联的扼要说明
我们关于问题的讨论之所以从制度伦理的视角展开,首先是缘于“伦理” “制度伦理”“道德”三者的逻辑联系。
(一)“伦理”是“道德”的“承担者和基础”
有词源考证提出,“伦”本义指人际关系次序,“理”本义是“治玉”,当名词使用时引申为纹理等,“伦理”意指人与人的关系次序之理[2];“道”的本义是人行走所循之道路,后引申为“做人之道”,“德”与“得”相通,言指使他人获益的同时自身获得了品格觉悟,道德即是个体内生于心外化于行的“人之为人”的品质遵循[3]。朱贻庭教授进一步提出,中国传统语境中的“伦理”与“人伦”相通,意指人与人的关系及其秩序——“宗法等级关系的实体存在”,“道德”是基于“伦理实体”的话语,即“伦理”中的个体德性,例如,“父慈子孝”中的“慈”与“孝”是父子关系的“伦理”规定,“道德”则是个体如何“慈”、如何“孝”的品格,“伦理”与“道德”的这种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突出特点。抛开宗法等级的消极面,其中亟待重视的思想资源在于:“‘伦理’正则‘道德’兴,‘伦理’乱则‘道德’衰。……提倡一种以至任何一种道德规范,如果不明确或根本没有其‘承担者和基础’的‘伦理’,那就不具现实性,是不可行的,如同虚假的‘广告语’一般”[4]。
建功新时代,扬帆新征程。当前,苏州正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自觉用新思想定向领航,以新思想对标找差,从新思想寻策问道,按照省委决策部署和对苏州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实施十二项“三年行动计划”,为再创新辉煌夯实坚固基础、注入强劲活力、再添秀美气质、绘就艳丽华章。
以“伦理”即人的关系的“规定性存在”为基础审视道德问题,在方法论上与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是根本一致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我们拒绝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作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伦理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一切无理要求,……我们断定,……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5]99。由此可以发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伦理”与“道德”也是有区别的:“伦理”指向的是社会关系——“历史”的而非一成不变的存在,而“道德”则以社会关系的发展状况为基础。
强调农村社区治理以“自治为基”,无疑是要凸显社区中个体的主人翁地位。而按照上述逻辑,社区自治的制度伦理对道德发展的贡献取决于个体的自治“身份”成为事实的程度,同时取决于自治制度所期待的社区伦理秩序对个体生活如何重要。前一个条件意味着个体对社区自治的切身参与是全面的、实质性的,而非形式化的、名实分离的;后一个条件表明,个体道德精神的真正确立依赖于个体对自治制度伦理与自身生活意义之间关联程度的深切体察。就社区共同体而言,前一个条件是达成道德价值共识的必要条件,后一个条件是实现共识向“共同行动”提升的主观要件。由此可以推定,自治制度伦理达致农村社区伦理道德理想图景的基本遵循是:社区个体的共同体“身份”在场,个体生活对于制度伦理的“意义”信任在场。对社区自治的制度伦理的实现逻辑(即制度应当彰显哪些伦理价值以及如何彰显这些价值)的考察,都需要在这种双重“在场”的理论框架下进行。
两组患者在下肢手术后均给予常规抗生素预防性抗感染、消肿止痛对症支持治疗,其中对照组给予低分子肝素进行治疗,1次/d,5000 u/次,连续服用15天;研究组给予益气通脉汤,具体药方为:黄芪18 g、水蛭8 g、地龙10 g、红花10 g、三七10 g、柴胡10 g、丹参10 g、泽兰10 g等以上各药均为道地药材,200 ml/剂,2次/d,术后6小时后服用一次,早晚分2次于饭后服用,术后连续服用15天。所有的操作、治疗及数据统计均有同一组技术成熟的治疗组医生完成。
(二)“制度伦理”集中彰显“社会伦理”
对于“制度伦理”的理解,首先应该以区别“伦理”与“道德”为前提,否则就会陷入道德制度化或制度道德化的倾向——众所周知,这是中国传统社会为维护等级礼法秩序而呈现出的典型特点,其必然导致“个体的丧失”,这也是有学者质疑“制度伦理”概念的重要原因[6]。其次,应当明确概念间的层次。“伦理”言指社会关系和秩序,所以“伦理”也可谓“社会伦理”。“伦理”或“社会伦理”在逻辑上是上位概念,“制度伦理”范畴则是在“社会伦理”如何达成的意义上使用的——意在表述制度运行(订立和实施的各个环节)如何彰显社会伦理,这便涉及制度的价值问题,亦如高兆明教授认为的,制度伦理指称制度的“善”,关注“制度的伦理特质、伦理属性,其主旨在于指向并揭示‘什么是好的制度’‘一个好的制度应当是怎样的’‘一个好的制度何以可能’。……其指向的真实内容应当是:对于制度的价值审视”[7]40-43。这也言明了“制度”与“伦理”为何可以连用而成为一个学理范畴。
习近平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8]。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最重要方式是制度治理,“政通人和”的现代要义是制度运行切实而通畅,从而达致社会关系的融洽和道德进步。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乡村治理要坚持自治为基础。所以,通过自治的制度伦理表达和实现社区伦理,继而促进个体的道德品质,是探讨农村社区伦理道德如何发展的基本脉络[注]对这种逻辑重要性的强调,并非是要否认德育的重要性。关于社会伦理、制度伦理、德育、道德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将另撰文阐述。。
二、农村社区伦理道德问题的典型图像
(一)“情面”逻辑愈加式微
苏力教授曾以电影《秋菊打官司》中“秋菊的困惑”为例生动描述了正式制度所遭遇的尴尬——其在定纷止争的同时损害了乡村社会长期有效且仍将依赖的社会伦理关系网络[16]。如果说成文制度是现代的,非成文制度(民间礼俗习惯等)则是“活着的历史”,这种伦理道德知识在乡村社会具有稳固的心理基础。社区自治制度权威性的确立有必要重视社区诸群体的礼俗习惯和潜移默化的价值观念,这是个体对制度伦理产生“意义”信任的前提,也是重构“家园感”的前提,否则“制度供给的产品不对路”在所难免。
例4:“I did notice you never brought friends home from school,” Mrs. Ellis said.(感知)
“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5]99农村经济转型以来,集体耕作的“同质性”生产方式总体上转变为家庭式、个人式的多样化市场化行为,邻里间的互帮互助不再像以前那样重要,稳固伦理道德的“情面”纽带也随之松动。而市场化的日盛又使得农村个体逐利观念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正面意义”,当这种意义被偏颇推崇时,“富”便在价值排序中获得了相较于德性的优先地位[10]190-195,这在导致“情面”逻辑趋向式微的同时也侵蚀着传统的义利观。与自然村落相比,这一状况在农村社区更为凸显。在我们的调查中[注]调查在四川雅安3个乡镇所辖的8个农村社区展开,采取以自填式问卷(共26个问题,发放问卷800份)调查为主辅之以访谈的方法,并在对有效数据采用SPSS17.0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除特别说明外,文中提及的调查均指我们对四川雅安社区的调查。,当被问及“相对以前生活的农村,社区人际关系的变化”时,76.9%的样本选择了“变化大,不如以前亲近了”。与此相关的原因选项中,53.3%的样本认为“更关注赚钱,不太留意这一问题”;42.6%的认为“社区中有不少外村人,与他们之间缺乏信任”;30.4%的认为“人情味越来越淡,不愿互帮互助特别是不愿挪借钱物的现象比以前多了”;当被问及社区舆论对道德的约束程度时,37.2%的样本认为“现在的人不太在乎别人的评价”,甚至有11.3%的认为“有钱了,别人自然会对你热情”。
(二)“家园感”进一步失落
费孝通先生称谓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是“长老统治”,即“教化性的权力”,文化性的强制都含有这种权力——“凡是被社会不成问题地加以接受的规范,是文化性的……文化的基础是同意的,但文化对于社会的新分子是强制的,是一种教化过程”[13]82-83。道德教化过程自然也是道德权威确立的过程,这种权威既存在于长幼尊卑关系中,也存在于官民之间,且一并陶冶出“经营群体生活的分子”。倘若失去普遍同意的价值基石,道德权威的丧失便不可避免了。
“家园感”曾经是农村的一种典型存在。固定的职业身份、安分淳朴的生活方式、基于地缘血缘的人际依赖等要素合力铸就了安身立命的“家园”体验。而肇始于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多样化转变,“农民”不再意味着安于泥土囿于家乡,行业职业多元使“农民的终结”成为一种现象。曾经生于斯、长于斯、安于斯的村落在精神层面成了“陌生的家乡”,“家园”共同感逐渐被消解。随之而来的,是熟人社会“相互密切的认识”和伦理的“默认一致”渐行渐远。有调查表明,“对村庄共同体的留恋与乡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呈现出一定的负相关关系”[10]。依此推断,更趋近城镇化的农村社区群体“家园感”失落的广度和程度势必是空前的。借鉴樊浩教授的表述,“家园感”空前失落引发的伦理问题是:“我”进一步成为“原子式”的“我”而非“我们”中的“我”,私人生活不断吞噬公共生活,精神同一性更加孱弱。“在‘伦理精神’中,‘伦’始终是出发点和归宿,它不仅预设了‘家园’,而且具有回归家园的能力,这就是‘精神’。”[12]伦理精神与“家园感”是辩证的“共在”,一损皆损。“家园感”的断裂,如果不续之以新的精神联系,农村社区必然是“低度关联”的、仅仅为居而聚的“无伦理”形态,个体在相当程度上是“没有社会规定性的自我”,缺乏“我们如何生活在一起”的道德能力[注]有田野调查表明,一般而言,低度社会关联型的村庄,村民缺乏一致的行动能力,公共事业难以组织,地痞骚扰村庄十分普遍,老人受到虐待时有所闻。详见贺雪峰:《新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75-281页。。
(三)“权威真空”与“价值空场”
按照黑格尔的描述,“家园感”源于“所珍视、所认识、所爱好”的“自己的东西”——它们是身心安顿的依托,是文化“畅适自足”的根基,更是共同精神的“栖聚地”[11]。“家园”和“家园感”也由此具有了浓重的伦理意义。
文化多元、道德价值多元是社会转型过程的真实写照。农村社区群体是经济转型的受益者,却又是文化心理和价值冲突更加显著的亲历者。相较于自然村落,他们更加远离了传统的道德文化,尊长的教化权威在物质追求冲动和“我的地盘我做主”的价值倾向中不断遭到否定,而以权谋私和腐败现象又导致对社区官德缺乏整体性信任。谁是令人心悦诚服的道德教化者?社区“权威真空”已然成为需要深刻检省的实践难题。另一方面,生产生活的城镇化取向并不意味着与公共性、现代化休戚相关的价值意识的进展,交往的无序化即是这方面的突出体现——遇到关乎自身利益的问题时去社区“两委”吵闹的现象屡见不鲜,甚至演变为极端性事件。而且,我们在与社区干部的访谈中发现,价值观模糊甚至无意识的现象并非罕见:一些人“我行我素”,对扰民、破坏公共环境觉得“无所谓”;一些人游手好闲,对诚实劳动和敬业不以为然;一些子女觉得“啃老”不关乎道德。另外,关于“你对乡风文明的理解”和“你对平等公正的理解”两个问题,分别有13.1%和19.7%的样本选择了“说不清”,甚至有7.3%和10.2%选择了“没怎么想过”。
三、自治制度伦理何以“在场”:基于“价值依系”的理论分析
所谓实体规定的“善”,主要指向的是关涉权利—权力关系和权利—义务关系的实质性内容(相对于程序性内容而言)。“权利—权力”关系配置的“善”在制度伦理中具有根本性,是根本性的“善”;而权利—义务关系配置涉及的是制度伦理的基本价值,是基本的“善”。 根本与基本层次划分的法理依据在于:“在权利确认、实现和保障的各个环节,权利—权力关系决定权利—义务关系”[20]。
降水从6月25日21时(世界时,下同)开始至29日06时结束,主要降水集中在26—27日。26日00时—28日00时累计降水(图1)表明,雨带呈东西带状,大于100 mm的降水横跨河南东南部、安徽中部和江苏南部,3个降水中心分别在安徽霍邱(224 mm)、江苏金坛(307 mm)以及安徽南部的枞阳(241 mm)。苏南沿江降水大于200 mm,张家港和南京处于250 mm雨量线的东西两侧,降水量分别为248 mm和259 mm。
为了开展锁合随动式限幅机构地面系统级验证试验,根据该限幅机构的工作原理和结构组成,研制了限幅机构试验件,如图9所示。
按照这种“价值依系”的逻辑,昂格尔上述关于现代社会制度“最重要政治任务”的话语就可以转换为:制度伦理所显示的价值标准真正成为道德遵循的充分理由需要满足两种预设,其一,个体的共同体身份的“所有方面”是实践中的“事实”;其二,道德发展状况首要地取决于个体生活对制度伦理的价值证成。
综上所述,对于道德发展的考察,应当遵循从伦理到道德的逻辑,这是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和坚持唯物史观的必然结论。
四、自治制度伦理促进社区伦理道德发展的实践框架
(一)前提性问题:审慎对待“本土资源”
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乡村社会的特质是“伦理本位”,其“所求无非彼此感情之融合,他心与我心之相顺。此和与顺,强力求之则势益乖;巧思求之则情益离”[9]。“情面”对维系农村熟人社会伦理起着核心作用,“情面”逻辑的机理是人际间的信任,继而促成义利兼顾甚至重义轻利的普遍一致的道德观念,“情面”逻辑的社会心理意义还在于:熟人社会的“舆论场”会对个体道德选择产生驱动效应。另外,梁先生还提出,“伦理本位”遭到破坏的始因是滥觞于西方的个人本位[注]详见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68-73页。由此推断,计划经济时期以国家和集体利益至上为主导的道德文化建设并未真正打破农村社会的伦理格局。[9]。
采用下沉式绿化带,可以降低地表径流流速,减小径流流量,从而起到调蓄洪峰流量的作用。此外,通过下沉式绿地,土壤能够将雨水径流中的多数悬浮颗粒污染物和部分溶解态污染物去除。
避免农村社区自治制度“水土不服”的首要步骤,无疑是制度订立过程的最广泛参与,未经广泛参与订立的制度从一开始便在事实上否定了未参与者的共同体“身份”。有报告显示,乡村自治中民主选举发展快,而决策、管理、监督的自治制度滞后问题比较突出,主要原因在于农村居民对于制度订立的参与不足[17]。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社区“两委”职能在很大程度上从上级部门的“协助者”演变为指令执行者,自治制度被淡化,进而导致自治制度的订立遭到冷遇。问题的背后,反映出的“是政府角色的越位、错位,是载体行政职能与自治职能高度重叠导致的私域——公域关系的纠缠不清”[18]。为此,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特别强调要维护村委会的特别法人地位。其次,需要在制度运行的精神交往过程中推进“价值共享”的启蒙。“精神发育的公共性,在于经由‘思’而表达出实践性”[19],价值共享意在表达通过放弃“意气用事”(这一点尤其重要)并在理性思量的基础上有序协商达成价值的“共享性意见”,并由此完成对熟人社会“情面”逻辑的扬弃。社区群体职业、地缘、与社区生活紧密程度的多样性以及受教育程度的参差不齐,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价值分歧,所以有必要通过“互主体性”的精神交往,即包容的、对话的、多维的商谈克服从“自我”出发的“原子式”观念,进而最大程度地达成彼此间的伦理道德共识,这是对社区伦理精神的启蒙——一种循序渐进的“关系理性”启蒙[注]贺来教授认为,现代性深层的“二律背反”是“主观理性”与“共同感”的分裂,克服这一困境的哲学出路在于寻求新的理性形态即“关系理性”——在超越单子化个人的社会关系中理解个体生命意义根据的理性,这种“价值眷注”是中哲与马哲融合的重要生长点。贺来:《“关系理性”与真实的“共同体”》,《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第22-44页。。再次,应推进伦理道德评价自治组织建设。这种建设期待与“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大力培育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农村社会组织的宗旨高度一致。这种组织不是“两委”解决纠纷职能的简单化的“改头换面”,而应当是社区党组织领导的(鉴于其是公益性组织,所以党组织的领导应当是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向性领导,而非事无巨细地“把关”,但可以有一定比例的党组织成员进入该自治组织)、人员构成多元(需要综合考虑民族、阶层、职业、年龄、性别、乡贤等)的一种通过确证个体行为是否契合社区伦理继而督促其道德发展的“自组织”类型[注]有文从某一角度对此作了探讨,参见施敏峰、胡世明:《“无主体熟人社会”中农民道德主体性重塑的自组织范式——以“道德评议会”为个案》,《长白学刊》,2014年第1期,第112-117页。。另外,应当重视通过自治制度激励社区志愿者组织的发育。“志愿”本身就是一种精神品格,而且,志愿者组织连接着个体与社区,是增强个人与社区关联度的重要载体。
结果显示,死亡凸显组中,高自尊者在职业认同及其职业行为、职业期望两个维度上均显著高于低自尊者,二者在职业承诺、职业价值观、职业情感、职业认知四个维度上无显著差异,详见表 9。
(二)厘清自治制度实体规定“善”的层次
“社会生活中一种自然的、潜在的秩序的意义必须与重新创造社会制度的能力协调一致。实现这种调和,并因此而为普遍意义的社会共同体而努力,也就成为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的政治任务。”[14]昂格尔此语的要义在于:制度解决现代社会伦理秩序危机的能力取决于其对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超验性批评”(可理解为意识评判)与“内在性秩序的意义”(即伦理统一性的意义)的调和力。英国学者约瑟夫·拉兹在对“意义”作哲学分析时引入了“依系”的概念,并提出,“意义主要依赖于我们所依系的对象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其他事物”[15]。进一步说,一般而言,我们相信依系关系的价值是源于对象的恰当性,之所以追求依系关系是因为它(们)的价值是我们所相信的,因此,个人在公共领域的道德节制的首要理由并非是不偏不倚的。而依系关系指涉的“非个人价值”(即公共价值)之所以能够超越对依系对象的价值以及依系关系自身的认识,是因为这些“非个人价值”与我们生活的成败相关。例如,个人可能认识到参与公共生活的意义,但只有切身实践参与具体的公共生活从而在“事实上支持这些善”,才使公共参与对个人生活的“成功”变得重要。因此,依系并非是有关我们自身的事实,而是“一种由我们担保的态度”。而且,在依系关系场域中,当且仅当一个人的“身份”(人是依系关系中的人而非“单子式”的个体)的“所有方面”(可理解为社会结构各领域活动过程的依系身份)被接受时,这种身份才能成为个体生活中积极的力量,这是生活意义的来源,也是道德责任的来源,换言之,“我们必须真实地面对我们是谁”。
习近平强调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21]313。“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要深入挖掘农耕文化的优秀思想资源,发挥其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的重要作用,引导农民向上向善。什么是社区治理最应当继承发展的传统文化?我们认为,非 “为政以德”莫属。在儒家政治伦理思想中,“‘为政以德’的政是教化性的”[9]83。教化者权力的合法性源于其德性,所谓“正人先正己”,这是为政者教化权威确立的必要条件——道德教化的成效取决于被教化者对教化内容的生活“意义”的信任程度,而这种信任首先是源于对教化者的道德信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21]105“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加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发挥其战斗堡垒作用,而且在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五个方面的表述中将“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置于首位,并进一步提出推动村书记通过选举担任村主任。对基层党组织地位和作用的强调旨在凸显其凝聚人心的伦理意义,社区基层党组织是思想道德教育的最重要主体,因此,切实继承“为政以德”的优秀思想资源,进一步创设和细化增强社区党组织成员党性修养(特别是“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这一观念)的制度规定,是提升社区个体对基层党组织信任度从而提升思想道德教育实效性的重要步骤。
拉兹对依系与价值之间关系的论证旨在驳斥价值的抽象普遍性(即价值的运用不顾虑任何时间、地点或任何特定的个体),并进一步说明:道德价值必须通过依赖于社会条件的方式证实自身,并依赖于个体对“非个人价值”的实践确证方能被接受。显然,这种观点与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的立场是并行不悖的。
1987年日本明尼苏达大学的Kazerooni等人设计了一种直驱式主动柔顺末端操作器,由直流无刷电机带动连杆机构实现平面内二自由度的运动,并通过末端力传感器进行力闭环控制,被动RCC弹簧结构使气动研磨头实现竖直方向的柔顺补偿,如图29所示。为进一步提升末端操作器的柔顺性,Kazerooni联合麻省理工学院开发了被动可调柔顺装置PVCEE(passive variable compliance end-effector),如图30所示[42]。
另一方面,“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网络的每一个结附着一种道德要素,因之,……所有的价值标准也不能超脱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了”[13]35-42。亦即是说,道德行为因对象与自身关系远近亲疏的不同而有程度上的伸缩,但如果将这一价值标准的惯性影响(如为亲朋好友谋利)蔓延至社区“两委”,其履行自治职能的后果很可能是其成员疏于约束,甚至沦为以权谋私和腐败的“村霸”[注]这方面的现实境遇,可参阅网络新闻“在村民自治的架构下规范农村公务接待”,网易,http:// news.163.com/16/0107/14/BCO03OEN00014AED.html。 ,社区其他群体的共同体“身份”随之演变为“被治理”身份,继而在“权利—权力”配置关系中成为丧失了主体性的存在。所以,自治权利禁止公权力滥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是社区自治制度“善”的根本要义。“中央一号文件”将“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原则之一,即是这种伦理意义的凝练表达。
权利—义务关系实质上是利益获得的对价关系,即利益如何正当(包括过程和结果)。“正确理解的利益是全部道德的原则”[1]335,利益从来不是“一己私利”,而是“彼此恰当”,沿用美国法律经济学家科斯的观点,即“权利的相互性”[22]。社区自治制度伦理的基本意蕴,在于平等公正地调节关涉不同个体利益方面的权利义务,也就是说,共同体成员在社区结构中的权利义务需要“获得来自伦理实体系统结构方面的具体规定”[7]289。制度实体规定的“善”直接地体现为诸种利益关系中权利义务的平等公正安排,即关于权利义务的设定既符合社区公共生活和公共利益愿景,又能胜任个体对正当利益的诉求,这是制度伦理对于促成社区伦理和个体道德发展应当作出的贡献。相比具体问题具体处理的“个案的方式”,其更能够普适性地给予利益相关者确定的权利义务预期,正因为如此,“最大效益的权利配置,……是指社会的制度化权利配置”[16]。
(三)充分重视程序的“善”
制度的程序规定直接关涉实体性权利—权力关系以及权利—义务关系配置的实现问题。在法治条件下,制度实体规定“善”的实现程度,首要地取决于程序规定是否能够为其提供足够的支撑。概言之,程序“善”指向的是权利—权力关系以及权利—义务关系配置的“规则化运作”。
社区群体对自治制度伦理实体规定“善”的判断、体认乃至期盼,无疑需要实现这种“善”的程序技术的系统性支持,周严、自洽、公开、可操作等,都是程序“善”的关键词。缺少了它们,权力的防控、权利义务的落实极有可能变得虚妄,正如有学者对浙江温岭民主恳谈的自治实践进行翔实调查后所感受到的:“对乡村民主来说,民主技术的优化和改进更具直接的现实意义和突出价值”[23]。我们调查发现,由于缺乏相应的程序规则,社区自治中决策的随机化、随意化问题颇为突出。例如,某一社区的居民公约规定:“违反本社区居民公约的,居民委员会可以取消其享受或暂缓享受社区的福利优惠待遇”,但对决策程序却只字未提,通过何种程序判定取消享受和暂缓享受的情形?当事人是否具有质辩的权利?经过几轮质辩?具体的质辩步骤是怎样的?质辩权利的行使期限多长?等等,诸如此类的程序设计在其他居民公约中也几乎是空白。访谈中,一些居委会干部表示,如果遇到这种情形,一般都采取“和稀泥”的处理方式,以居民不闹事为原则。按照法理,这属于典型的“自由裁量权”滥用。程序会增加治理成本,但程序更是伴随实体正义实现全过程的“形式正义”,由此可见,程序表面上是“繁文缛节”,但事实上却是一种需要高度重视的“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应当坚持法治为本,所以农村社区自治只能是“法治乡村”前提下的自治。众所周知,实体规定和程序规定是法的两大组成部分,不可偏废,但从农村社区的现实境遇来看,自治制度伦理的程序“善”仍是一项“远未完成的设计”。
五、结语
借用美国学者吉尔兹的说法[24],自治尤其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费孝通先生更加简明地提出:“联系着各个社会制度的是人们的生活,人们的生活有时空的坐落,这就是社区。每一个社区有它一套社会结构,各制度配合的方式。”[14]116-117生产方式差异、地域差异、文化差异、生活背景差异,意味着新时代农村社区自治不可能有普适的实践模式,自治制度伦理的社区实践自然也不可能有标准化套路。因此,我们的探讨毋宁说是“画面并不完全”的、粗略的。然而,“对道德发展的宏观考察表明,道德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后,将重新成为一切个体自我肯定和相互肯定,自我发展和共同创造的必要表现形式”[25]。这是伦理道德的辩证法,也是我们进行上述讨论的立场和态度。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王冬桦.为伦理与道德的概念及其关系正本清源[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121-122.
[3]邹渝.厘清伦理与道德的关系[J].道德与文明,2004(5):16-17.
[4]朱贻庭.“伦理”与“道德”之辨——关于“再写中国伦理学”的一点思考[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6.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鲁鹏.关于制度伦理若干问题辨析[J].天津社会科学,2012(2):57-58.
[7]高兆明.制度伦理研究——一种宪政正义的理解[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8]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05.
[9]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42.
[10]王露璐.新乡土伦理——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乡村伦理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9.
[1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M].贺麟,王太庆,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174-175.
[12]樊浩,等.中国伦理道德报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3.
[13]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14]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M].吴玉章,周汉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223.
[15]拉兹.价值、尊重和依系[M].蔡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5.
[16]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17]魏后凯,等.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16[R].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423-425.
[18]钱国君.政治理性及其场域:缘于基层依法自治的考察[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10):194.
[19]许章润.置身邦国,如何安顿我们的身心——从德国历史学家迈内克的“欢欣雀跃”论及邦国情思、政治理性、公民理性与国家理性[J].政法论坛,2013(1):12.
[20]公丕祥,等.法理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201.
[2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105.
[22]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M].盛洪,陈郁,译校.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142.
[23]陈朋.国家与社会合力互动下的乡村协商民主实践——温岭案例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360.
[24]吉尔兹.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M]//邓正来,译,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73-171.
[25]辜堪生.试论改革的道德与道德的改革[J].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7(4):81.
EthicBuildingandMoralDevelopmentinRuralCommunity:Macro-discussionBasedonthePerspectiveofAutonomousInstitutionalEthics
QIAN Guo-jun1,WU Yan-xia2
(1.SchoolofMarxism,ChengduInformationEngineeringUniversity,Chengdu610225,China; 2.SchoolofCultureandBusiness,SichuanCulturalIndustryVocationalCollege,SichuanChengdu610213,China)
Abstract:Institutional ethic→community ethic and order→individual moral progress is the followed basic logic for examining how rural community ethic and morality develop based on autonomous perspective.According to the typical problems in rural community such as more and more serious “human emotion” logic,unprecedented decline of “home feeling”,“authority vacuum”,“value vacuum” and so on,the community ethic and order of “master type according to family tree” should be constructed through autonomous institutional ethic to sublate rural acquaintance social ethic.In practice,“local resources” of community ethic and morality need to be prudently dealt with,the fundamental “kindness” and the basic “kindness” formulated by autonomous institution entities should be clarified,and procedural “kindness” should be emphasized,which are the easily neglected perspectives in reality.
Keywords:rural community; autonomy; institutional ethic; human ethic and order; morality
doi:10.3969/j.issn.1672-0598.2019.04.011
*[收稿日期]2018-11-29
[基金项目]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19JD71001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实现路径研究”;四川省新农村乡风文明建设研究中心项目(SCXF201510)“村民自治制度伦理与新型农村社区道德文化建设常态化研究”
[作者简介]
钱国君(1972—),男,河北张家口人;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基层社会治理与伦理道德发展研究。
吴燕霞(1981—),女,四川雅安人;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文化商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德育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19)04-0098-08
(责任编校:杨 睿)
标签:伦理论文; 制度论文; 道德论文; 社区论文; 关系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论文; 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19JD71001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实现路径研究"; 四川省新农村乡风文明建设研究中心项目(SCXF201510)"; 村民自治制度伦理与新型农村社区道德文化建设常态化研究"; 论文;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文化商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