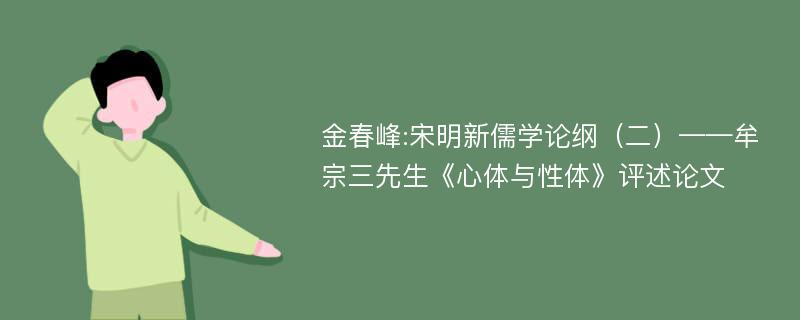
名家专稿
摘要:程颐心性论承孟子两种“性”之分而来,其“性即理”指“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於心”,属实践理性;冯友兰、牟宗三先生解为柏拉图式的“理型”“共相”,泛指人与万物之自然生理之性,故对程颐“性之有形者谓之心”,“涵养用敬”,“进学致知”,有一系列的误解。故有必要对之加以分析和说明。
关键词:性;理;心;涵养
本篇论述程颐的心性及涵养与格物致知思想,并就牟宗三先生关于这些方面的阐释作一评述。
富水软弱地层中交叉、重叠隧道盾构区间施工关键技术……………………………………………………… 杨义(10-213)
苏秋琴虽然是苏石的姐姐,但这个女人柳红也说不太清楚,她跟她不一样;苏秋琴很少下地干活的,尤其生了儿子之后。她高兴时带儿子玩玩,不高兴就去村口的小店那儿,跟一群老头儿搓麻将,一块两块,消磨消磨时光;或者跑去镇上玩。具体,柳红也说不上来。对了,有一次男人婆去小店吵过架,说是她的金耳环被烂眼阿根偷了,不知送给了哪个小婊子;男人婆认定是给了苏秋琴,还掀了他们的麻将桌,和苏秋琴扭打起来,一个揪头发,一个抓脸,闹得沸沸扬扬,但柳红从未见到苏秋琴有什么金耳环……
一、程颐论性
程颐论“性”,其根本或基础性的命题是“性即理”。字面上,“性”泛指天地万物之性(全称判断);“理”泛指规律、原理、本质属性。冯友兰、牟宗三先生解之为柏拉图式的“理型”“共相”。实际上,这是一特殊性命题(特称判断),所指是孟子所谓“君子所性”之善性。“理”指道德,内涵为仁、义、礼、智、信。按康德的划分,这属实践理性领域,因而它有心性关系与道德实践及修养的问题。程颐在“性论”中论述了这些问题。
程颐论“性”的言论很多,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涉及心性情关系;一类涉及性与气或气禀的关系。程颐论“性”的一条纲领性语录是: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商品房的价格始终保持加速增长的势头,这不仅对我国百姓的安居乐业产生影响,也给国家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因此探索房价的影响因素这个问题是学者聚焦的核心。
称性之善谓之道,道与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谓之善性。性之本,谓之命,性之自然者谓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谓之心,自性之有动者谓之情。凡此数者皆一也。(《遗书》卷二十五,伊川先生语十一)
聚光灯追逐的,不过是人们心中的焦虑,以及对不公的警惕。过去的一周里,一场金融圈的饭局异常扎眼,席间男男女女举止不雅,甚是辣眼睛。事后相关人士受到了行业处罚,可“贵圈”的各种潜规则传说也纷至沓来。这些事离普通人很遥远,但吃瓜群众们还是能感受到成吨的伤害。如果游戏规则是长袖善舞者通吃、心术可疑者恒赢,踏实做事的人就很难获得公平,很难不陷入焦虑。
“性之有形者谓之心”,这肯定了“性”为“心之体”。孟子说“心之官则思”,“心之有形”即因“心”之为“官”是有形的。“性”作为“理”,无形无象,但“性”为“心”所秉受,内具于“心”,成为“心之体段”(见程颐《中庸》“中和”说),它也就有“形”了。以镜作比喻,“照之理”无形无象,但镜有形,从镜子之有形,可见照之性理。故二程、朱熹常以镜作比喻,说明性心关系。如程颐回答“‘不迁怒,不贰过’,何也?”的提问时说:“须是理会得因何不迁怒。如舜之诛四凶,怒在四凶,舜何与焉?盖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圣人之心本无怒也。譬如明镜,好物来时便见是好,恶物来时便见是恶,镜何尝有好恶也?……圣人心如止水。”②程颢《定性书》说,“性”如明镜,物来自应,善恶美丑无所遁其形。朱熹说,“心犹镜,仁犹镜之明”。此皆类似说法。推而广之,直(理)之有形者谓之松柏,坚之有形者谓之石,流之有形者谓之河等等亦如此。但牟先生认为程颐所讲“心”只是且只能是认知心,故不从“性”为“心之体段”立论,而谓在程颐,“心”无形,但其“觉识活动”有形,故“心之有形即以觉识活动定”③。但“觉识活动”来无影,去无踪,“出入无时,莫知其向”,以之定“心之有形”,是不通之词。
牟先生说:“盖性只是理,而理之具体表现一般言之,不能不有赖于心之觉识活动。如无心之觉识活动贯注于性理上,则性理之为理只是自存、潜存,而不是呈现地现实的具体的理。”④“一般言之”,即泛而言之,“性理”只是自存、潜存,而不能是“呈现地现实的具体”的“存”,这与牟先生常讲的性体、理体“即存有即活动”,自己呈现,“沛然莫之能御”,完全矛盾了。
“觉识活动”即是眼耳口鼻等感觉器官之见、闻、口说等感性活动及在此基础上的心之分析综合活动,有此能力的只能是“气之灵之心”,道德本心或性体是不可能有此能力的。“性”既然有赖于此才能呈现,则“性”应在“气之灵之心”中而不能在其外。程颐说“性之有形者谓之心”,正是有见于此;但牟先生却谓,在程颐,“心之形著而形象化性理是认知地形著而形象化之”,“是依动静之情之存在之然而推证其所以然而形著而形象化之”⑤,将道德性理完全解构成动静之理了。实际上,“性”本无动静可言,因“理”无动静。程颐讲“性动”,是省略的说法,意谓“性”内含于“心”,为“心之体段”,心有动静,即可谓性有动静。“心之静”即“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心感物而动,即“发而为情”,“性体(善性)”发挥节制的作用,使之皆为道德之情而谓之和。牟先生所讲“动静之然”,指形而下的现实、具体的动静,如牛马之动静,草木之动静,球体之动静,认知心之动静等;其所以然之理或是机械力学定律,或是生物之生理心理活动规律,或是柏拉图式的“共相”,都是与道德性理及道德情感无关的。以此解彼,可谓风马牛不相及。
牟先生进而说:“心之觉识活动是道德本心之实践的活动。”⑥这更是混淆概念、自相矛盾了。“觉识活动”与道德实践性质完全不同。看见一个孩子掉进井里,这是觉识活动;不计功利,奋不顾身去援救,这是“道德实践”。两者并无必然内在联系。有前面的觉识,却视而不见,见死不救,做出反乎道德之事的人,也是有的。“道德实践活动”只能指具有觉识活动的人依照道德本心之绝对命令而活动。“道德本心”即康德所谓“善的意志”,它仍是人之“理性”的一功能,而非在其外的另一种“心”之功能。
整体而言,程颐这段话从“道”与“性善”一路说下来,意谓道、性、心、情都是善的。“道”就天言,就客观普遍的意义言,就其自然存在、自己存在而言;“性”就人之禀受于天而具有之善性言;“心”就人之知觉、情欲及意志主宰言⑦;“情”就心之发为情感言。程颐用一个“善”字把天道心性直贯起来。牟先生喜言“直贯”,却对程颐这种真正的“直贯”完全错解,原因无他,只是以偏见成见代替了具体问题之科学分析。
程颐类似的语录还有很多,如:“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心本善,发于思虑,则有善有不善。”(《遗书》卷第十八)“自性而行,皆善也(性指义理之性的善性)。圣人因其善也,则为仁义礼智信以名之;以其施之不同也,故为五者以别之。合而言之皆道;别而言之亦皆道也。”(《遗书》卷第二十五)“自理言之谓之天,自禀受言之谓之性,自存诸人言之谓之心。”“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指道德性)是也。” (《遗书》卷第二十二上)⑧这些话和上面第一条语录是一样的思想,“理”指“天命之谓性”之性理(非泛指物之本性、生理),内涵是仁义礼智信;“心”指人心,其体为“道德本心”;“发于思虑”指人心所发之“意”、意念。意念有善有不善,心之体——道德本心皆可知之节之,使之“中节而和”而皆为善。贯穿其中的要点,是天命之善性为心所禀受而成为“心之体”。由此,心性是一而非二。在《中庸解》中,程颐说:“人心至灵,一萌于思,善与不善莫不知之。”“情之未发,乃其本心。本心元无过与不及,所谓‘物皆然,心为甚。’所取准则以为中者,本心而已。”又谓:“故君子之学将以求其本心。本心之微,非声色臭味之可得,此不可得而致力焉!”(《二程集·河南程氏经说》卷第八。)把人有道德本心的思想讲得十分明确。
关于性与气的关系,程颐的主要语录有:
气有善不善,性则无不善也。人之所以不知善者,气昏而塞之耳。孟子所以养气者,养之至则清明纯全,而昏塞之患去矣。或曰养心,或曰养气,何也?曰:养心则勿害而已,养气则在有所帅也。(《遗书》卷第二十一下,伊川先生语七下)
这六条语录是以《礼记》“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及《说卦》“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为背景的。“天理”与“理”指德性之理。“知者,我固有之也”,即德性之知乃我所固有。“致”是致力于,达致。“物”指物欲、外物,如声色货利等。“因物有迁,故迷而不知,则天理灭矣”,即《乐记》所讲:“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故“格物”是不使德性之知为物所迁,不使“天理”为物欲所灭。如何“格物”?方法是“穷理”,是“求放心”。“穷理”的“理”即“天理”,即“德性之知”的内容。“穷”是穷尽,全副体现。“格”训为“至”,又训为“穷”;也即在“物”——接物或物欲萌发处,使天理、良知不为其所迁,即所谓“穷理尽性至命,只是一事。才穷理便尽性,才尽性便至命”(《遗书》卷第十八,伊川先生语四)。因“理”所指即天理、德性之知,故“尽其心者自尽其心。尽心则自然知性知天矣。如言‘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以序言之不得不然,其实只能穷理,便尽性至命也”(《遗书》卷第二十二上,伊川先生语八上)。“尽心”亦是“心”不为物欲所迁、所蔽,使其所具天德能全副呈现,所谓“尽其心者自尽其心”,如此则可回复到“天命之所与”。综合这些论述,核心是通过道德修养功夫,达致德性之知和“天理”的朗现与存而不失。
问:“性之有喜怒,犹水之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静如镜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或地势不平,便有湍激;或风行其上,便有波涛汹涌。此岂水之性哉?人性中只有四端,又岂有许多不善底事?然无水安得波浪,无性安得情也?”(《遗书》卷第十八,伊川先生语四)
综合这些语录,其所讲“性”为“善性”,认为性善是性之本然。现实中,圣、愚、贤、不肖等等的差异是“气禀”使然。因“气”有清浊,得气之清可保持“性之本然”,为圣为贤;得气之浊则为愚、不肖。孔子讲“性相近”是指气禀不同之性。气禀(包括质料及其生理或形构之理)虽为命定,但人可通过学而改变气质。扬雄、韩愈所讲“性”皆为气禀之性,非本来之善性。故总结地说,“论性不论气,不备”——不完备,后天的差别未能说明;“论气不论性,不明”——不明白性之本然,而徒见后天性的种种差异。禽兽亦有善性,有如纸上的一小孔,阳光亦照射进来,但只有一小孔,故性善也只有一点点。以后朱子解析“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说:“气相近,如知寒暖,识饥饱,好生恶死,趋利避害,人与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蚁之君臣,只是他义上有一点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点子明;其他更推不去。恰似镜子,其他处都暗了,中间只有一两点子光。”(《朱子语类》卷第四)此即发挥程颐以上思想。
孟子讲性有两种:生理食色之性与“君子所性”的仁义礼智之性。程颐把生理之性基本忽略不讲(归入气禀),主要以善性为性,以气禀的不同讲现实的“性”的差别。程颢、张载及以后朱熹讲“性”也是如此。这是读者要特别注意的。如张载说:“气质之性,君子弗谓性也。”气质之性包括生理食色之性,孟子说这也是性,但张载说“君子弗谓性也”即本于此。张载又说:“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天地之性即仁义礼智之性。“气质之性”则包括善恶良莠不齐之现实之性。
孟子言:“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心也、性也、天也,非有异也。(《遗书》卷第二十五,伊川先生语十一)
目前来看,下决心给企业减轻负担,让企业能够回归正常的经营状态,面临的经济困难或可早一点过去。庙堂中人不要眼光太短,要放得长远。现在给企业减负,减少政府收入,必然会带来一些当前的困难。这或许一下子看不到效果,需要一个恢复期。为此,未来几年就得准备过紧日子,为长远发展创造条件。把不必要的支出减下来,那些短期的困难应当没有什么不可以承受。
程颢的性论和程颐基本是一致的,如谓:“告子云‘生之谓性’则可。凡天地所生之物,须是谓之性。皆谓之性则可,于中却须分别牛之性、马之性,是他便只道一般,如释氏说蠢动含灵,皆有佛性,如此则不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者,天降是于下,万物流形,各正性命者,是所谓性也;循其性而不失,是所谓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马则为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则为牛之性,又不为马底性。此所谓‘率性’也。人在天地之间,与万物同流,天几时分别出是人是物?‘修道之谓教’者,此则专在人事。以失其本性,故修而求复之,则入于学。若元不失,则何修之有?是由仁义行也。则是性已失,故修之。‘成性存存,道义之门’,亦是万物各有成性存存,亦是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为德。”(《遗书》卷第二上,二先生语二上。未注谁语。牟先生认为系明道语)
戴威的经历堪称天之骄子,曾是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创办ofo时就立志要改变世界。戴威以30亿元财富排名《2018胡润80后富豪榜》第32位,可以说是最著名的90后创业者和企业家。
程颢这里的讲法,理念或概念的使用不够严谨,但人性善这一基本点是明确的。牟先生说,在程颢,性善是“性体自己之本然而粹然者”,“性之本然与粹然”“即是那‘于穆不已之真几’也”⑨。而程颐所讲“性理”或“性体”乃动静之然与所以然之理⑩。两者完全不同。但考之实际,这种不同不过是牟先生主观虚构的,在“文本”上没有经得起推敲的根据。
二、程颐论心
按康德的讲法,理性是一个,但有认知的运用,有实践的运用。前者即理论理性,后者即实践理性。康德所讲“理性”即孟子和二程通常所讲的“心”。孟子说“心之官则思”,“思”有认知之思,成就知识;有道德之思,成就道德;有情感之思,所谓“思念”、“想念”,成就诗歌、文学,还包括情欲等。成就道德之思的“心”,《书·大禹谟》称之为“道心”,程颢、程颐、朱熹亦称之为“道心”或“心体”,陆象山称之为“本心”,王阳明称之为良知、明德。“道心”与“人心”相对(人心指生理认知情欲之心),但两者都是“心”的功能作用。程颐论“心”即包括上述两方面,如:
程颐说,“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这与“共相说”的说法不同。“共相说”中,“理”自本自根,没有“所自来”的问题。程颐讲“理”——人之善性有所自来。来于何处?来于天道、天命。天道、天命是最终本源。因其如此,禽兽也是有善性的。程颢讲“生之谓性”,人与物皆禀善性,更突显这点。程颐又谓“理之自然者谓之天”,就是说善性皆出于自然,非有神造。这实际是说孝弟慈爱等善性皆出于血缘亲情,是自然形成的。这与“共相论”思想亦是完全不同的。而牟先生用“共相论”套宋明理学和程颐的性论,其不相应和牵强附会是必然的。
正叔言:“不当以体会为非心。”以体会为非心,故有心小性大之说。圣人之神,与天为一,安得有二?至于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莫不在此。此心即与天地无异,不可小了他。不可将心滞在知识上,故反以心为小。(《遗书》卷第二上,二先生语二上)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心,道之所在;微,道之体也。心与道,浑然一也。对放其良心者言之,则谓之道心;放其良心则危矣。“惟精惟一”,所以行道也。(《遗书》卷第二十一下,伊川先生语七下)
“滞在知识上”即认知心;与“天地无异”之心即道德心。“心,道之所在”,“在”是本质地在,分析地在,本原地在;非后天经格物致知而“在”。故“道心”即人生而即具之“仁义良心”。程颢谓:“‘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执厥中’,所以行之。”(《遗书》卷第十一)这是与程颐一样的说法。牟先生却说程颐是“心与道为二、而非即道也。其‘浑然一也’虽加浑然,亦是关联的合一。……放其良心,则不顺理、不合道,即谓之‘人心’”,且此良心非孟子本意之良心⑪。这是据己意对程颐的曲解。
在《遗书》卷第十八《伊川先生语四》中,程颐谓:“心譬如谷种,生之性便是仁也。”用今天的话说,使稻发育为稻,麦发育为麦的“基因遗传信息”是“性”,“谷种”则是“心”。谷种因内具这种遗传信息而能发育为麦为稻,有如“仁”之性使人成为人一样。这“心”中的仁性或“生之性”,按康德的讲法就是“善的意志”,这“善的意志”使人成为享有道德尊严的人。遗传信息和谷种是融为一体的。非谷种(心),遗传信息(性理)无以存;非具遗传信息(性理),谷种亦无以遂其发育为稻为麦之功。牟先生以“共相论”套入,将两者解为阳气生发之情(自然生理)与其所以然之理的关系⑫,将“性善”解为自然生理,这显然是曲解程颐了。
程颐说:“心具天德,心有不尽处,便是天德处未能尽,何缘知性知天?尽己心,则能尽人尽物,与天地参,赞化育。赞则直养之而已。”(《遗书》卷第五,《宋元学案》列于《伊川学案》)“心具”是内在地生而即具,非后天学习而具。“天德”即道德性理。故又谓:“如四端固具于心。”“固具”者,生而即具也。程颢谓:“人心莫不有知,惟蔽于人欲,则亡天德也。”(《遗书》卷十一)“天德”即仁义礼智。“圣人致公,心尽天地万物之理,各当其分。佛氏总为一己之私,是安得同乎?圣人循理,故平直而易行。”(《遗书》卷第十四)显然,两人的思想是一致的。而牟先生认为程颐的上述“心”论思想都非程颐的“本质思想”。程颐的“本质思想”在那里呢?只在牟先生的主观断案里!
三、程颐论涵养
程颐既认为道德源自性体——道德本心,故提出“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遗书》卷十八),作为全部工夫论的概括。这两句话虽有联系,但却是两件事。涵养与心性相联系,《近思录》列为“存养”,与“格物穷理”是并列的。
牟先生说:“惟至伊川始正式言《大学》,正式言致知格物,格物穷理……由《论》、《孟》、《中庸》、《易传》之纵贯型转化而为静涵静摄之横列型。朱子极力完成之。”⑰实际上,言《大学》,程颢是首倡,《大学章句》就是程颢首先新编定的。程颢谓:“《大学》乃孔氏遗书,须从此学则不差。”(《遗书》卷第二上)关于“格物致知”思想,程颢有下述语录:
刚住校时,我们这些娃娃年纪太小,又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在学校非常不适应,当时如果不是汪老师给了我们母亲般的关怀,我都不知道自己该如何走过那段艰难的岁月。
(苏季明)或曰:“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发,思与喜怒哀乐一般。才发便谓之和,不可谓之中也。”又问:“吕学士言:‘当求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信斯言也,恐无著摸,如之何而可?”曰:“看此语如何地下。若言存养于喜怒哀乐未发之时,则可;若言求中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则不可。”又问:“学者于喜怒哀乐发时固当勉强裁抑,于未发之前当如何用功?”曰:“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养便是。涵养久,则喜怒哀乐发自中节。”……或曰:“先生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下动字,下静字?”曰:“谓之静则可,然静中须有物始得,这里便是难处。学者莫若且先理会得敬,能敬则自知此矣。”(《遗书》卷十八)
对这条语录,牟先生套用“共相”说,谓:此“性善”之“善”为“绝对的善,纯然的善,善之自己。外乎此,皆不得说为绝对的善,皆是因这绝对的善(善之标准) 而有善的意义”①。“共相”说认为,动、静、美、丑、圆、方等等“共相”,乃形而下之现实世界中动、静、美、丑、圆、方等等之绝对的标准。如冯友兰先生常讲的,现实中的“圆”总是不够“圆”,达不到“共相”的绝对的“圆”。这是摹本与原本的区别。牟先生即发挥这一说法。在此说法下,现实的“性善”就是相对的不够“善”的“性善”。显然,这于程颐是完全不相应的。在程颐语录中,“性”是主词,“善”是形容词。它源于“道”、与“道”同一。“道”并非柏拉图“共相”说的“彼岸世界”——“绝对的善”,以彼套此是错误的。
为什么“言存养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则可”?盖因“中,状性之体段”,心未发时含具有之性体——道德本心,故可言存养,而不可言求之。“求之”则以之为一物而在心外了。程颐讲“涵养”与孟子讲“存心养性以事天”是一致的。如果无道德本心而讲“存养”“涵养”,就真正是无本原的“涵养”了。比之孟子,程颐讲得更为细致。牟宗三先生说程颐所讲“心”只是且只能是实然的生理之“心”,其讲“涵养”,落实处只是后天工夫之“居敬穷理”而已。这是显然的曲解。
程颐说:“闲邪则诚自存,不是外面捉一个诚将来存著。今人外面役役于不善,于不善中寻个善来存著,如此则岂有入善之理?只是闲邪,则诚自存。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内出。只为诚便存。闲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动容貌、整思虑,则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则既不之东,又不之西,如是则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则只是内。存此,则自然天理明。学者须是将敬以直内,涵养此意,直内是本。”(《遗书》卷第十五,伊川先生语一,《入关语录》)牟先生说:“此言存诚存敬,其背景仍是就实然的心理学的心施以后天的振作、整肃、凝聚之工夫以贞定之。诚敬只是工夫字,即就振作、整肃、凝聚而说。振作、整肃、凝聚亦只是这实然的心之经验地表现。其实处即是‘动容貌、正思虑’。‘但唯是动容貌,正思虑,则自然生敬’……‘涵养’者涵泳优悠以滋长此敬心,使之习久如天成也。涵养久,则此心常贞定,即由实然的状态转至道德的状态,故自然能如理合度,而作为理与度的‘天理’亦于焉彰明矣。”⑬但理论上,一个实然的生理之心,不管如何专一,如何主一,如何诚敬,如何闲邪,都是不可能转生出一个道德之心的。天天专注骑马,整齐装束,严肃容貌,心无旁骛,那也只能提高骑术,绝不可能转出一个道德心,变成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是够主一、专一以从事钓鱼之事了,但能由此转出一个道德之心吗?当然是不可能的。钓者可以以此为乐,但这并非道德境界。牟先生说“由敬来经验地直此实然的心使之转成道德的”,只能是胡扯了。程颐当然绝不会有这种糊涂不通的思想,故他一再强调:“孟子言性善,皆由内出。只为诚,便存。”“便存”之所以可能即因本有性善之仁义良心在“内”也。“存此,则自然天理明”,盖天理即仁义性理也。“人只有个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遗书》卷第十八) “天理”是生而即有的道德性理。这都是极明确的本质性思想。再如:
“理义之养心”即孟子所讲“礼义之悦心”。“敬以直内”,因为有“内”,故可如此。“内”即内在之“道德性体”也。对“涵养”的理解,程颢亦与程颐一致。《遗书》卷第一至第十“二先生语”中,有许多关于“涵养”的论述,如:“‘思无邪’、‘无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遗书》卷第二上) “若不能存养,只是说话。”(《遗书》卷第一)所谓“只是说话”指只知而不行者。“学者全体此心,学虽未尽,若事物之来,不可不应,但随分限应之,虽不中,不远矣。”(《遗书》卷第二上)“学”是后天功夫,但亦以“全体此心”为基本。“学者须敬守此心,不可急迫,当栽培深厚,涵泳于其间,然后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终不足以达道。”(《遗书》卷第二上)“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欲人将已放之心,约之使反,复入身来,自能寻向上去,下学而上达也。”(《遗书》卷第一)这些都是两人共有的思想。而牟先生论程颢时,将程颢关于“涵养”的论述都删除了,因为不合他臆造的“程颢思想圆融一本论”与“逆觉体证”——遇事则内省、顿悟以“明心见性”而达致“无限”的工夫论。但这也暴露了他的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
吁问:“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无事时,如何存养得熟?”曰:“古之人,耳之于乐,目之于礼,左右起居,盘盂几杖,有铭有戒,动息皆有所养。今皆废此,独有理义之养心耳。但存此涵养意,久则自熟矣。敬以直内是涵养意。(《遗书》卷第一》)
四、程颐“格物致知”的“心学”论述
程颐关于“格物致知”的论述,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明确的“心学”论述;一部分讲如何格物及读书明理,通晓修齐治平的道理。前一部分见于牟先生所引程颐下列六条语录:
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遗书》卷第三,二先生语三。谢显道记忆平日语。标明为伊川语。)
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则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遗书》卷第二十五,伊川先生语十一)
“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迁,迷而不知,则天理灭矣。故圣人欲格之。(同上)
闻见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则知之,非内也,今之所谓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闻见。(同上)
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也。穷其理,然后足以致之,不穷则不能致也。格物者适道之始,欲思格物,则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同上)
随事观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然后可以至于圣人。君子之学,将以反躬而已矣。(同上)
水利工程的建设使空气和水域的接触面积增加,改善当地气候,空气湿度的增加能够给周围植被提供有利条件,促进植被生长增加植被覆盖率,起到净化空气的作用,同时还为两栖动物提供了有利的生存环境,也对当地的土壤有所改善,特别是对于干旱地区的土壤提供了充足的水分,更利于农作物的生长,有利于某些鱼类的繁殖。
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本此下云:“二之则不是。)(《遗书》卷第六,二先生语六。未定谁语。)
牟先生采取主观断案的方法,将程颐上面讲的“知”解为心之认知能力与活动。谓:“‘致’者,推致其‘知之能’(指认知能力——引者),使之步步有所成,有所得(指得外物之物理知识),而至于其极也。”“‘致’是送到的意思。有一个‘知之能’,并不能算是明理也。知之能在与物接上而具体的表现方可有明理之成果,此即是‘致’也。故曰:‘不致,则不能得之。’‘得’一在得明理之成果,一在使知成其为知(有具体的表现)。此两层皆在与物接上成就,此即‘致知在格物’也。”⑭这是将程颐思想解构为认识论所讲关于外物的认知问题,完全违背程颐思想的原意。程颐明白地指出有两种知:一是“闻见之知”,一是“德性之知”。前一种乃物交物之“知”,由外得来,“今之所谓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见闻”,是由内产生的“性理、天德”。程颐明确指出,他所讲的“知”与认识论所讲物理知识、博物多能之知,性质完全不同。白纸黑字,如此清楚确定,牟先生却明目张胆,硬将其定为“物理之知”。这只能说是自欺欺人,以诬诳别人为能事了。
牟先生解“知”为认知能力,逻辑上不通,也违反语言常识。人们不会说,“耳,我所固有;听力,吾所固有。眼,吾所固有;视力,吾所固有。……如果不‘致’,则得不到听力视力,就会听不到声音,看不到外物”。因听力视力是天生的,不存在“固有、不固有”的问题,讲“固有”是多余的。程颐之所以要特别提出“知,吾所固有”,因讲的是一种特别的“知”——良知或德性之知。有些人是否认有这种“知”的,如告子、荀子。此种“知”很容易丧失,为物欲所迁,故必须有“致”的工夫。如果“知”指认知能力,则根本不存在丧失的问题,也不存在“致”才能得到的问题。牟先生把“知”解成认知能力,又引申成知识的获得和积累。这种曲解是很荒谬的。
以此曲解,牟先生认为程颐所讲“德性之知”乃依据敬心之涵养而起⑮,“涵养此敬心使之常常能振作、整肃而凝聚,不滞于见闻与见闻之对象,而能提起来以其心知之明(指认知能力)去知那超越之理也”⑯。所谓“超越之理”即物的“共相”或“理型”。而“共相”或“理型”和“德性之知”是性质完全不同的。硬把这种东西称之为“德性之知”,就如同把竹子之为竹子的“共相”之知称为“德性之知”。这是真正混知识为道德了。
心理学上的认知之心是绝不可能发出德性之知的。这是常识。告子、荀子讲的“心”是这种认知心,故道德在他们的体系中都是由外灌输而成的。“化性起伪”之后,始有道德之知。这种道德之知实际仍是以功利为心的,与孟子及程颐所讲“我所固有”之德性之知,本质上完全不同。
道德的敬心实际上也不可能由认知心格物致知而起。见鬼神而敬畏,敬畏天命与大人之言,可以是功利的敬畏。“道德的敬心”如果是自发的、原于内心的,则是德性之敬,这与由认知心明理而成的“敬”,性质亦不同。
程颐关于“涵养”的论述,由讨论《中庸》而起,见于下面这段论述。
作者在娓娓道来中以修辞与典故带来的意象搭建一个关于“胡同”中无力而诚挚“爱情”悲剧。用“雨”“淋湿”的梦来映照着最后的悲剧结局此处映照的使用无疑是成功的,此处修辞的使用使章句沾染上更加愁苦的意绪:雨淋湿的是人,更是心中的梦。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或以格为止物,是二本也。(《遗书》第卷十一)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穷理而至于物,则物理尽。(《遗书》卷第二上,二先生语上,《宋元学案》列于明道学案,牟先生从之。)
人心(即气之灵之心)莫不有知,惟蔽于人欲,则灭天德也。(《遗书》卷第十一,明道先生语一)
“致知在格物”,物来则知起。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则意诚不动。意诚自定则心正。始学之事也。(《遗书》卷第六,二先生语六。未定谁语。牟先生认为此当是明道语,认为《宋元学案》列入《伊川学案》,非是。)
其中第3条即程颐“知,吾所固有”之思想。“天德”即程颐所讲“德性之知”、“天理”。第4条即《定性篇》思想。第1条,为什么训“格”为“止”是“两本”?程颢未加说明。以后王阳明训“格”为“正”。《定性书》讲以“理”照物、处物,能使物各付物,即因“物”乃“理”所应对之物。如果是“止物”,就不是“物各付物”了。要之,程颢“格物致知”的心学论述实际上和程颐是完全一致的。而牟先生采所谓“一本论”的解释大讲“穷究”,说:“如果照‘一本’义去想,则‘致知’之知不是无规定的泛说之‘知’,乃是致的‘天理遍在’之知(也即良知。引者注)……。依此一本义而言,则‘致知在格物’意即欲致其‘天理遍在’之知,必须能‘至于物’而知此天理之通澈,或致天理遍在之知即在乎‘至于物’而能明知此天理之通澈于物也。……故第4(本文为3。引者注)条云:‘格,至也。穷理而至于物,则物理尽。’意即穷究此遍在之天理而能至于物以知其通澈于物而不隔于物,则物之理亦尽。”⑱而“穷究”是属于认识论的范畴,如穷研竹子之理:何时种竹子合宜,竹子有何特性等等。说穷究天理良知,这是完全不通的。
五、程颐对“格物致知”的一般论述
孔子仁智并重,以仁智勇为三达德,三德各有独立的意义。仁属于道德;智属于理论理性,认识范畴;勇属于意志。德性好,不一定智能好。反之亦然。勇亦如此。但三者亦可相辅相成。德性好,尽忠报国,无所畏惧,可以急中生智;智识多而高可以辅益德性修养,不致无知冥行;勇于担当,可以更勇于“道德实践”。程颐许多语录讲研究或穷至事理、物理,即有以智辅仁之意。“理”的含义有道德的、知识的、外在的、己身的。因儒学的本质是“内圣外王一体两面”,故天下事事物物该当理会,不能如佛老一样,只讲“内圣”了事。
译者将“neat little”译为“瘦小”,省略了“neat”。汤姆是整部小说里出现的第一位阅读四色笔记的人。此处,莱辛借汤姆之口,将安娜的外在形象描述为“neat little”(整洁、瘦小)。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汤姆读完四色笔记后,感到忧郁,追问“你害怕混乱吗”。译文省略了“整洁”,没能突出安娜整洁的外在与混乱的内心之间的反差。
程颐格物致知的言论很多,如:
或问:“进修之术何先?”曰:“莫先于正心诚意。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格,至也,如‘祖考来格’之格。凡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穷理亦多端:或读书讲明义理;或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皆穷理也。”问:“格物须物物格之,还只格一物而万理皆知?”曰:“怎生便会该通?若只格一物便通众理,虽颜子亦不敢如此道。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遗书》卷第十八,伊川先生语四)
今人欲致知,须要格物。物不必谓事物然后谓之物也,自一身之中,至万物之理,但理会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觉处。(《遗书》卷第十七,伊川先生语三)
问:“观物察己,还因见物反求诸身否?”曰:“不必如此说。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晓此,合内外之道也。语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语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学者皆当理会。”又问:“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性情,固是切于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须是察。”(《遗书》卷第十八,伊川先生语四)
这些论述与“敬以直内”、“涵养本心”有相辅相成的关系。明理有助于提高道德觉悟和道德境界,这是常识。近现代,无数志士仁人献身革命,赴汤蹈火,前仆后继,往往都是先明理,懂得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真理,坚定了信仰而能如此的。常言“平生不作愧心事,半夜敲门鬼不惊”,道德好使人能如此,但懂得无鬼的道理,更能如此。
程颢讲“天理二字是自家体贴出来”,但亦强调读书与格物明理,如他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学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彻上彻下之道。”“佛氏不识阴阳昼夜死生古今,安得谓形而上者与圣人同乎?”(《遗书》卷第十四)“知之明,信之笃,行之果,知仁勇也!”(《遗书》卷第十三)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此理也;‘在止于至善’,反己守约是也。”(《遗书》卷第十二)“知至则便意诚,若有知而不诚者,皆知未至也。”(《遗书》卷第十一)等等。要之,在进学致知上,二程的思想亦基本是一致的。
宋明儒学以“四书”为新的“经学”。学生入学,首先是读“四书”,了解书所讲道理并身体力行,真能如此,确可以提高修齐治平的能力与境界。“不立文字,直悟本心。”这在禅宗,也只是为不知有“本心”而一味向语言、书本讨生活,一味向外求道的人而说的。对知道“道在本心”的人,则读书是有益于求道的。《孟子》讲“人皆有四端之心”,读《孟子》,懂得这道理,岂不有益于“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所以程颐讲“进学在致知”,“进学”内容首在读《论语》、《孟子》等“四书”。程颐说“学者识得仁体,实有诸己,只要义理栽培,如求经义,皆栽培之意。”(《遗书》卷第二)“根本须是先培壅,然后可立趋向也。趋向既正,所造有浅深,则由勉与不勉也。”(《遗书》卷第六。《遗书》以此为伊川语)强调以义理栽培本心仁体,实本于孟子“礼义之悦我心”。将这些思想斥之为“以知识为道德”,是完全错误的。
注释:
①③④⑤⑥⑨⑩⑪⑫⑬⑭⑮⑯ ⑰⑱ 牟 宗三 : 《心体与性体》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29、230、230、231、231、141、231、281、285、321、326、395、329、331、342—343 页。
②《宋元学案卷十五·伊川学案上》,《宋元学案》第1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18—619页。
综上所述,考虑到金融结构在影响技术进步生命周期中各阶段的不同作用机理,本文提出如下待检验假设:金融结构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显著影响,且影响效果不尽相同。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时,技术创新、技术转移和扩散是金融结构影响产业结构的重要传导途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适宜的金融结构仍可以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凸轮式基质填料装置的配套动力为90W的电子调速齿轮减速电机,传动方式为链传动;生产率为180~600盘/h,可调;料箱容量为40L;填料深度为36~40mm,可调;配套皮带输送机构使用电机为YCT-112型电磁调速电机,有效转速为125~1 250r/min。
⑦ “性”授受于“心”,为心之体。
⑧ 此条原文甚长,此处所录是依《宋元学案·伊川学案》只节录其末段,辞句与《遗书》原文少异。
长阳县水产局办公室主任万松彤,是华中农业大学水产专业的研究生,也是当地的水产专家。他告诉记者,长期以来,当人们提到清江保护时,关注最多的是水体、水质,沿岸排污,水面清漂等显性的指标。但实际上,清江的生物和生态系统的保护与恢复,往往被忽略。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982(2019)01-0005-08
作者简介:金春峰,人民出版社原编审,北京,100706。
(作者编辑 胡 静)
标签:遗书论文; 伊川论文; 道德论文; 孟子论文; 天理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现代哲学(1919年~)论文; 二十世纪哲学论文; 《社会科学动态》2019年第1期论文; 人民出版社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