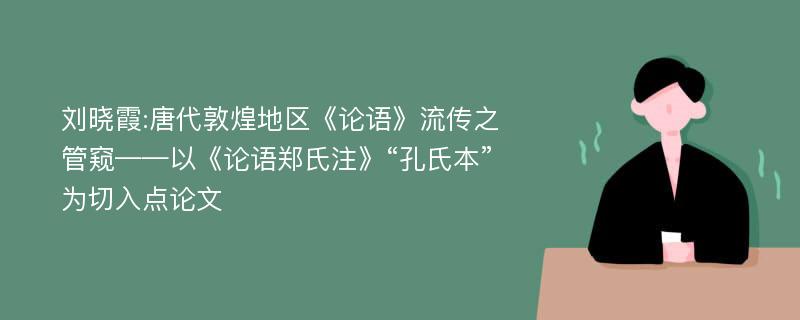
摘 要:今存郑玄《论语郑氏注》残卷,是20世纪初以来考古发现的郑玄经注的抄本遗物,原本至南宋时已全部亡佚。此《注》在《论语》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隋唐时期广为流传。《唐景龙四年卜天寿写本论语郑氏注》是吐鲁番文书中享有盛名的一个长卷,从此抄本中出现的“孔氏本 郑氏注”六字切入,可以借以探讨郑注本出现“孔氏本”的原因,进而揭示唐代《论语郑氏注》在敦煌地区的影响与流传。
关键词:孔氏本;郑氏注;世不传;后阅者
敦煌地区既是中原文化圈的西陲地带,又是与印度文化、希腊罗马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等古代世界四大文化体系交汇的一个重要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文化交流的要冲。历史上,丝绸之路是沟通亚、欧、非三大洲最为重要的交通路线,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而敦煌扼河西走廊的西端。敦煌的南面是属于祁连山脉的三危山,三危山的西南有鸣沙山,莫高窟就开凿在鸣沙山的断崖上。敦煌的北面是北山山脉,疏勒河由东向西横穿其北部,西边有玉门关和阳关。从以上地理位置分析可见,敦煌是东来西往诸色人等进出河西走廊的门户。隋人裴矩在其《西域图记》中曾说:
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钹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硃俱波、喝盘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忛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东女国、南婆罗门国等,并随其所往,诸处得达。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①魏征等:《隋书》卷67《裴矩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579-1580页。
正因为如此特殊而重要的地理位置,隋唐时期,敦煌地区已经形成了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原文化、外来佛教文化和敦煌本地文化等相互融汇、富于地方特色的敦煌文化。作为中西文化的交汇之地,敦煌地区虽然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但总体来说,以儒学的传播发展为基础、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传统文化在敦煌地区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在此背景下,敦煌流传的儒家文献数量颇多。在这些敦煌本儒家经典中,又以《论语》为多。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既有《论语》在科举考试中需要“兼通”,地位重要,还有在敦煌地区,《论语》作为儿童的启蒙书被广泛传抄。
正因为在隋唐时期《论语》在敦煌地区如此广泛的流传,才会有而今敦煌出土文献中诸多《论语》文献重见天日的盛况。关于敦煌地区《论语》出土文献的状况,此处暂不赘述,后文会略作交代。本文主要讨论的是1969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中出土的唐代《论语郑氏注》残卷。该残卷所署抄书人为“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厚风里义学生卜天寿”②国家文物局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7册),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551页。,该残卷即是著名的唐中宗景龙四年卜天寿抄《论语郑氏注》残卷。本文要探讨的“孔氏本”的问题也即出于此。“孔氏本”的问题,简单来说,是20世纪初,法国伯希和教授于敦煌千佛洞得《论语郑氏注》卷二残卷,存《述而》《泰伯》《子罕》《乡党》四篇,也被称为伯希和二五一零号写本。《述而篇》首阙,余篇首则题“《泰伯篇》第八”“《子罕篇》第九”“《乡党篇》第十”,篇下皆题“孔氏本 郑氏注”。而日本橘瑞超氏于吐鲁番吐峪沟得《论语》断片,存《子路篇》末及《宪问篇》首十行,《宪问篇》题下亦有“孔氏本”三字,其注亦郑注也。之后,在敦煌、吐鲁番陆续出土的唐写本《论语郑氏注》中,篇题下亦标有“孔氏本 郑氏注”,前面提到的著名的唐中宗景龙四年卜天寿抄《论语郑氏注》残卷也出现了“孔氏本 郑氏注”的字样。对于“郑氏注”,学者们将以上写本的注文和《论语集解》《经典释文》(以下简称为《集解》《释文》)及其他典籍援引郑玄注的文字相比较,得知确有删省增易者,然确为郑玄注解无疑。但为何明明是郑玄的注本,却会出现“孔氏本”三字?本文即是以“孔氏本”为切入点,在探讨郑注本出现“孔氏本”原因的基础上,试图考察唐代《论语郑氏注》在敦煌地区的流传与历史影响。
一、学界对“孔氏本”之探讨
学界对“孔氏本”的探讨由来已久,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
暴露源危险度的分级:(1)低传染性:病毒载量水平低、无症状或高CD4+T淋巴细胞水平;(2)高传染性:病毒载量水平高、艾滋病晚期、原发HIV感染、低CD4+T淋巴细胞水平;(3)暴露源情况不明:暴露源所处的病程阶段不明、暴露源是否为HIV感染,以及污染的器械或物品所带的病毒载量不明。
(一)写官漫题说
持此说者是罗振玉。他在其《〈论语〉郑注〈述而〉至〈乡党〉残卷跋》一文中,称:
今人黄彰健也持这个观点,在其著作《经今古文问题新论》中,称:
可见,罗振玉认为“孔氏本”三字是写官写此卷时随手题上的,可能只是无心之举。此说似乎太过随意,值得商榷。
王国维与罗振玉观点相似,他考之《集解》序、《释文》叙录与《隋书·经籍志》,称:
笔者认为,这是对“孔氏本”问题讨论的一大进步。首先,对《论语郑氏注》进行了有否“孔氏本”的区分,虽然没有从版本差异的角度对文本进行详尽比较,但在对“孔氏本”的探讨上有了极大深入,从写本源流的角度区分出北朝流行本和南朝流行本。其次,更是在文献基础上做出合理推断,否定了郑玄自己加“孔氏本”的可能性。这一推断更符合常理,也更切合《论语郑氏注》的文本。
M2和M3是运用分层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关于H2的检验结果。M2中,引入现金冗余FS、股票期权激励OPT和控制变量,发现FS与RD显著正相关(β=0.0014,p<0.01),与H1保持一致。M3在M2的基础上引入OPT×FS,发现交互项与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β=0.0022,p<0.1),且FS与RD始终保持显著正相关关系,表明实施股票期权激励会增强现金冗余与研发投入的关系,H2得到支持。通过对高管实施股票期权激励,将其收益与未来股价紧密挂钩,可抑制其操纵现金冗余寻求收益补偿的行为,增加其研发动力。
由此可知,王国维并未明确指出“孔氏本”三字是写官漫题,但他也认为郑注《论语》是以张侯《鲁论》为底本,以孔氏《古论》为校本。且篇章同张侯《鲁论》,字句全从孔氏《古论》。《论语郑氏注》底本、校本问题有待讨论,以底本、校本推论出“孔氏本”为写官漫题,似在逻辑上多有不通,论据不足。
上海理工大学测控专业工程认证教学改革总体思路如图1所示。在以学生为中心的基础上,通过制定培养目标、培养标准、课程计划、教学计划以及保障体系,并通过持续改进,最终实现以输出为导向(Outcome-Based Education,OBE)。改革的具体实施主要分为四个阶段。
(二)郑玄自题说
文物出版社在其集体撰写的论文《唐写本〈论语郑氏注〉说明》中认为“孔氏本”三字是郑玄自己题上去的,称:
据许建平先生的统计,纯敦煌藏经洞出土的《论语》写卷共有92个卷号,其中“伯希和编号47号、斯坦因编号22号、俄敦编号16号、北敦编号2号、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编号1号、日本藏本及散见4号”①许建平:《敦煌经籍叙录》,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91页。。而实际数字应该比这还要多。如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藏有四件《论语》残片,编号分别为4403《论语集解·子罕》、5788《论语·子路第十三》、8088(里)《论语·子路第十三》及《宪问》②据许建平考证,此写卷非敦煌写本。见于《敦煌经籍叙录》,第291页。、8110(里)《唐钞〈论语〉孔子本郑玄注〈子路〉断片》;日本静嘉堂文库亦有一件《论语》残片③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5、188页。。再加上北图临时编号L.0083号郑氏注《论语·述而》残片及其他一些散藏没有公布的,敦煌本《论语》写卷的数量已超过100个卷号。
对于郑玄在自己注本题上“孔氏本”的原因,他们提出是因为郑玄认为孔氏《古论》最标准,他以孔氏《古论》校,字句依从孔氏《古论》的缘故。
《释文》所举郑氏校正诸字,则皆改《鲁》从《古》,无一从《齐》者,始悟此卷所谓“孔氏本”者,乃据孔氏《古论》改正张侯《鲁论》;而何、皇诸家谓考校《齐》、《鲁》者,盖张禹本受《鲁论》,兼讲《齐》说,善者从之。郑君既注张《论》,则不异兼《齐论》,其实固仅据《古》以正《鲁》也,此卷写官漫题孔本,虽不免小疏,然因此而得知其实,亦可喜矣。
郑玄虽用《鲁论》篇次,而字句全从《古》文,故篇题下注“孔氏本”三字。
敦煌本P.3573号皇侃《论语疏》,是现在最古的一种《论语疏》。王重民先生以知不足斋本《论语疏》校之,认为“经文之下仅录注文句首,而以‘云云’二字概括之。然后以‘此明’二字总释全章大义,次疏经文,或解注语。疏经文者,则录经文之句,而以‘者’字终之,如《九(五)经正义》例。解注语者,或冠‘注’字终之或否,然每一事均隔一字写,以明断限。皇氏原书当如是”,因而断定其为“梁皇侃论语单疏”①许建平:《敦煌经籍叙录》,第70、71页。,而且认为知不足斋本《论语疏》是“日本所传义疏,先出何晏集解,次割裂皇疏,散于各条之下,或增或减,殊失本来面目矣”②许建平:《敦煌经籍叙录》,第70、71页。。经过日本人的删削篡改,已非皇侃《论语疏》原帙。李方《唐写本论语皇疏的性质及其相关问题》一文,认为该卷不是皇侃《论语疏》的原形。她通过写本与刻本的比勘,认为此卷“每章经、注之后,均有一段总括文。总括文以‘此明’二字开头,总括全章经注大意”,认为该卷很可能是一件皇侃《论语疏》的“讲经提纲”。③李方:《唐写本论语皇疏的性质及其相关问题》,《文物》1988年第2期。而日本的高桥均通过对比研究,也认为此卷“是被特定的编者改编过的东西,并不是皇侃《论语疏》的原貌”④转引自许建平:《敦煌经籍叙录》,第381页。。
这一论点,在笔者看来,颇有自说自话之嫌。只论一点,为何“孔氏本”三字只出现在了敦煌唐写本《论语郑氏注》上,而在其他版本的《论语郑氏注》上从未出现?且考郑注未曾全从《古论》,何来“郑玄认为孔氏所传的《古论》最标准”之说?
(三)后人所加说
持此说者为日本的金谷治教授。他在其论文《郑玄与〈论语〉》中,称:
虽然自己的校订本根据张侯《论语》对照过《古论语》,但是因此而称之为“孔氏本”,仍然有点不合道理。张侯《论语》是以《鲁论语》为底本,校对《齐论语》而成,因而新名张侯《论语》。郑玄是以张侯《论语》还是以包、周本作底本虽然还有问题,但属《鲁论语》系统而不属《古论语》系统,却似乎可以认定。据“《鲁》读某为某,今从《古》”的郑注,郑玄自称“孔氏本”,越发显得奇怪。笔者以为“孔氏本”这一名称,可能是知道“郑玄本”与“孔氏本”相类似的后人,在纯粹的《古论》失传之后加上去的。
在此基础上,王素在《唐写本论语郑氏注校读劄记》一文中,对“孔氏本”的源流进行了探讨,得出唐写本《论语》的篇题有三种类型,一为标“孔氏本 郑氏注”,二为不标“孔氏本 郑氏注”,三为无篇题。他认为:
不标“孔氏本”的写本,原是北朝流行的本子,标“孔氏本”的写本,原是南朝流行的本子。北朝流行的不标“孔氏本”的本子,即《隋志》著录的“《论语》十卷 郑玄注”,南朝流行的标“孔氏本”的本子,即《隋志》注中披露的“梁有《古文论语》十卷 郑玄注”。①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246页。
而对于标“孔氏本”的写本,他在其专著《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中提出:
郑玄决不会把自己的注本称作《古文论语》和“孔氏本”,《古文论语》和“孔氏本”只可能是后人加上去的。
余谓何、陆所说与此本所题皆是也。郑氏所据本固为《鲁论》出之张侯《论》,及以《古论》校之,则篇章虽仍《鲁》旧,而字句全从《古》文。《释文》虽云郑以《齐》、《古》读正凡五十事,然其所引二十四事及此本所存三事,皆以《古》正《鲁》,无以《齐》正《鲁》者,知郑但以《古》校《鲁》,未以《齐》校《鲁》也……故郑注《论语》,以其篇章言,则为《鲁论》;以其字句言,实同孔本。①王国维:《书论语郑氏注残卷后》,载于《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版。
(四)“孔氏本”之我见
笔者在《唐写本论语郑氏注相关问题探析》一文中详细考校了《论语郑氏注》与《论语》其他版本的文本差异,此不赘述。从比较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郑氏注》与孔氏《古论》有着许多不同之处,且多为实词方面的差异,并非如王国维、黄彰健等学者所说的“字句全从《古》文”。它与《简本》的差异也较大。相比来说,与《汉石经》的差异则主要表现为虚词上的差异。众所周知,《汉石经》属于三《论》中的《鲁论》系统。在比较中,《郑氏注》经文也多与今本《论语》同。再从《论语》的流传状况来看,郑玄所见的《论语》至少有《鲁论》《古论》两种,依据郑玄注经广罗异本、择善而从、博综众说的特点,郑玄撰著《论语郑氏注》时不会只采用一两种《论语》本子,应有多种。通过对诸版本的考证,笔者认为,郑玄所撰著的《论语郑氏注》是在张侯《鲁论》的基础上考之《齐》《古》形成的合校本,是继张侯《鲁论》之后出现的新的合校本,是今本《论语》的基础。
既然郑玄的《论语郑氏注》是一个新的合校本,不是全部依从孔氏《古论》,更不是以孔氏《古论》为底本,那么郑玄认为孔氏《古论》最标准而自题“孔氏本”的说法显然于理不通,无法自圆其说。因并非完全依从孔氏《古论》,写官因为相似而无意中漫题的观点明显也无法立足。于是,问题便向着更深层次的探讨发展:为何在中原地区流传的《论语郑氏注》未有“孔氏本”三字(否则在后世史书中应有著录),而在唐西北边境流行的《论语郑氏注》,据目前的出土文献看,几乎都在篇首标有“孔氏本”三字?日本金谷治教授和王素先生认为的“后人所加说”,是何“后人”?与《论语郑氏注》在敦煌地区流传的不同版本之间有何关联?这也正是本文探讨“孔氏本”问题的意义所在,以“孔氏本”为切入点,在追寻探讨为何题“孔氏本”的过程中,考察唐代敦煌地区《论语》的流传。
感知技术、识别技术和智能移动采集技术的发展,使得现代农业在全产业链中源源不断产生海量数据,农业大数据的重要意义不在于获得庞大的数据信息,而主要在于对这些数据进行挖掘和应用。
互联网高速发展和线上消费的普及,使得大学生越来越倾向于订购外卖.研究发现,大学生订购外卖的价格因他们的消费水平而异,低消费水平的学生青睐于低价格外卖,高消费水平倾向于中等价格外卖,高价格外卖消费率不高[7].
二、由现存敦煌本《论语》看唐代《论语》流传
班固《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论语》。”②班固:《汉书》卷30《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17页。
这些《论语》残卷,形式多样,有《论语》白文6个卷号、郑玄的《论语注》11个卷号、何晏的《论语集解》82个卷号、皇侃的《论语疏》1个卷号,也有佚名的《论语音》3个卷号、《论语摘抄》1个卷号等。其中何晏的《集解》残卷最多,并且内容相对完整,不仅与传本《论语》20篇的篇目都吻合,而且还有何晏、郑冲、孙邕、曹义、荀5人共写的《论语集解序》,对整理研究以及校勘传本有较高价值。郑玄《论语注》及白文《论语》数量居其次。
(一)敦煌本《论语》现存基本状况
郑玄校本为什么题称“孔氏本”?不难理解,由于郑玄认为孔氏所传的《古论》最标准,所以他的校本上许多字是改从的《古论》,据记载有五十处……他这个校本虽然并不是纯粹的《古论》原样,但字句依从《古论》,譬如一个校宋刻本校过的新刻本书籍,从字句内容说它是“宋本”并无不可,郑玄在他的注本中题上“孔氏本”,应该即是这样的缘故。
《论语》在西汉时期三个版本并传。景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论语》21篇,皆古字,这就是所谓的《古论语》。《古论语》发现以后,孔安国曾经“为之训解”,但流传的范围有限。除此之外,还有《鲁论语》和《齐论语》,是当时分别流行于鲁、齐一带的本子,属于今文《论语》。《论语》虽有今、古文之分,但并不互相对峙,而是相互融合、参考、借鉴。在这种情况下,东汉“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这才有后世《论语》定本的出现。魏晋时期,何晏抛弃了两汉经学繁琐的章句训诂,以玄学义理来解经,“集诸家之善”,作《论语集解》,晋以前诸家注,赖何氏《论语集解》才得以流传下来。南朝著名经学家皇侃作《论语疏》,保存了大量汉晋关于名物制度的章句训诂和玄学思想,在经学思想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而宋以后,郑玄注、何晏集解、皇侃疏皆亡佚。近代以来,敦煌石室中发现了大量宋以前的《论语》写本,使《论语》成为敦煌本儒家文献中保存数量最多的一部经典,总数超过百件,其中以郑玄《论语注》、何晏《论语集解》和皇侃的《论语疏》价值最大。
在11个郑玄《论语注》残卷中,除S.3339号的内容为《论语·八佾》残篇外,其他残卷的内容主要集中在《雍也》篇第六至《子路》篇第十三,即从卷三到卷七。而《论语》白文6个写卷的内容也全部集中在《论语》第三章至第七章这5章之中。
皇侃《论语疏》在敦煌儒家经典中仅存一件,即P.3573号。其内容残存《学而》至《里仁》篇,经文、注、疏总计共649行④陈铁凡著《敦煌论语异文汇考》谓有380余行,应将双行小字疏文按经文大字计为一行。见《孔孟学报》第1期。许建平计有647行,见《敦煌经籍叙录》,第377页。,16000余字。写本经文作单行大字,注、疏作双行小字。小字录何晏《论语集解》文首句后以“云云”二字概括,然后以“此明”二字开头,总括全章经、注大意。“此”字作单行大字,“明”以下在本行者用双行小字。由于疏文较长,写到后来字越写越大,双行疏文小字实际变成了两个单行。因卷内文字避唐讳,如“民”字作“人”或缺笔,因此可知其应为唐写本。
敦煌本《论语音义》共3个残片,法藏1件,编号为P.3474P2V,北图藏2件,并能拼接,编号分别为L0739和殷字42号。许建平为这3件音义作了叙录,对北图殷字42号进行了比勘,认定其为《论语郑注音义》,并考定P.3474P2V号为《论语集解音义》。
推动绿色食品品牌发展,应建成一批专业化的批发市场,开展国内外贸易促销项目,搭建平台、拓展渠道、推进贸易、促进交流、展示成果。
敦煌本《论语》中,有题记者为数不少,如P.3783《论语》(《述而》《乡党》)残卷末有题记一行:“文德元年正月十三日,墩煌郡学士张圆通书”。另 外 ,P.2510、P.2618、P.2681、P.2716、P.3193、P.3271、P.3441、P.3745等残卷,均有纪年题记。P.2604《论语》(《学而》《为政》)残卷末有题记:“大中七年正月十八日伯明书记”。大中七年是公元853年,这是迄今发现的敦煌本《论语》中纪年最早的一件。最晚的纪年题记为P.2510《论语郑氏注》(《述而》《乡党》),残卷末题记:“维龙纪二年二月墩煌县”,此年为公元890年⑤按:龙纪仅有一年,此“二年”应为大顺元年。许建平认为此题记“字体与正文不类,当是后阅者所加”,见《敦煌经籍叙录》,第302页。。由此看来,敦煌本《论语》的抄写时间大约集中在宣宗至僖宗在位的847—888年间的40年左右。
(二)敦煌本《论语》的研究及作用
我国最早介绍敦煌本《论语》并对其作初步研究的是罗振玉先生。1913年,他在《鸣沙石室佚书》中,对P.2510号《论语郑氏注》(《雍也》《乡党》)残卷进行了介绍并作序跋,首次判定此卷为唐代抄本《论语郑氏注》。此后有不少学者开始对敦煌本《论语》进行研究,其中中国以王国维、王重民、陈铁凡、郑静若、李方、王素、陈金木、荣新江、许建平等学者的研究为主;日本以石滨纯太郎、内野熊一郎、月洞让、尾崎雄二郎、新美保秀、金谷治等学者的研究为主。学界对敦煌本郑玄《论语注》研究较多、较深,成果也比较丰富;对何晏《集解》的研究,李方的《敦煌论语集解校证》一书堪称集大成之作;对《皇疏》的研究,除陈金木、李方及日本的高桥均发表了部分论文外,其他几无涉及者;对敦煌本《论语》白文的研究更是寥若晨星。
下面分别对幂零群、内幂零群以及内交换群的幂图或真幂图进行讨论.一般地给出了有限群的幂图为某图之线图的充要条件,研究了相应幂图独立数的临界取值与可平面化的充要条件以及相应真幂图的连通性.
他据《释文》,考得郑玄以《古论》校《鲁论》周氏章句,从《古论》读正,而为《集解》所依从者,计二十事。其不为何晏所依从者,计四事;而《释文》所举郑玄本与何晏本经文异者有二十六事。考得郑注即用《古论》,《释文》所举郑本、何本异文,郑本系《古论》,而何本异文,则或为《鲁论》,或为《齐论》。再从伯希和二五一零号写本的篇次,证得郑玄用《鲁论》篇次。
11月11日,由广州科通展览有限公司举办的第21届中国(广州)国际名酒展在广州·广交会琶洲展馆B区圆满闭幕。盛会规模空前,来自全球51个葡萄酒产国103个产区的1000多家葡萄酒庄和3000多家国内酒类优秀进口商与5万家经销商齐聚一堂。首日参观人数突破2万人次。3天内60多场不同主题活动,包括大师班、品鉴会、行业渠道与发展等不同主题的活动,国际化程度再创新高。
敦煌本郑玄《论语注》的发现,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重视,辑佚和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经过学者们的努力,现在唐写本《论语郑注》已经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恢复。据日本著名郑玄《论语注》研究专家月洞让在《辑佚论语郑氏注》中,综合清辑本、敦煌写本和他自己所辑,认为郑注大约有870条,现在通过敦煌及吐鲁番出土的唐写本郑玄《论语注》文献,已得佚文513条,也就是说郑玄《论语注》原貌已有60%为我们所知。台湾研究郑玄《论语注》的学者郑静若,在其《论语郑氏注辑述》一书中,综合清辑本和唐写本,加上他自己所辑,共得佚文863条。如果月洞让所说郑注仅有870条是正确的话,那辑佚工作就基本上完成了。但王素却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仅就现知唐写本,也只有“半部郑注”⑤王素:《敦煌本〈论语〉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梁尉英主编:《2000年敦煌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甘肃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474页。。
敦煌本《论语集解》为唐写单行本,“以之与皇本、邢本对校,不仅可以订正传本的许多错误,解决清人研究中的许多纠纷,还可以提供传本中没有的许多佚文,披露清人研究中未曾涉及的新的问题”⑥李方:《敦煌论语集解校证》,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但是,至今学术界只有很少一部分学者对这批写本进行了研究,其中李方《敦煌〈论语集解〉校证》对这批写本从释录、定名、断代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校证;许建平在《敦煌经籍叙录》一书中,对敦煌本《论语集解》在写卷形态介绍、缀合及定名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叙录。
此前召开的2018世界钾盐钾肥大会暨格尔木论坛是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一次盐湖资源综合性国际行业大会,也给盐湖股份公司发展提出了新要求。王兴富说,此次大会展示了中国形象,凝聚了行业信心,更为行业开启了新征程。他认为,此次大会通过论坛、展览会、高层访谈等模式,吸引国内外钾盐钾肥企业、技术设备提供商及行业权威专家,汇集中央部委、地方政府、两院院士、高校、科研院所、骨干企业、投融资机构、行业协会、国际组织等多方声音,从国家政策、行业发展、技术创新、农业应用等全方位探讨钾盐钾肥和盐湖资源的产业态势,为国内外钾盐钾肥的发展与盐湖资源的综合利用提供广泛交流平台。
由以上对现存敦煌本《论语》的统计可知,唐代敦煌地区既有郑玄的《论语注》、何晏的《论语集解》、皇侃的《论语疏》,还有形式多样的《论语》残卷,既有《论语》白文,又有《论语音》《论语摘抄》等。在这些敦煌本《论语》中,有很多都有题记。比如上文已经提到的“文德元年正月十三日,墩煌郡学士张圆通书”“大中七年正月十八日伯明书记”等。因为这些题记有不少与正文不类,所以应为后阅者所加。通过对这些敦煌本《论语》的整理统计,发现大部分抄写的时间大约集中在宣宗至僖宗在位的847—888年间的40年左右。
三、结论:“孔氏本”——集众家之长
如上所述,在敦煌儒家经典中,发现的《论语》残卷数量最多,占1/3左右。但其中书法、款式精美的写卷非常少。李正宇先生在其《敦煌学郎题记》一文中指出,有不少带有题记的写卷确为学童所抄。如P.2681号《论语》卷第一并序题记云:“维大唐乾符二年二月廿四日沙州敦煌县归义军学士张喜进书记之也”;P.2716号《论语》卷第七末题:“大中九年三月廿二日学生令狐再晟写记”;P.3441号《论语》卷第六尾题:“大中七年十一月廿六日学生判官高英建写记”;P.3745号《论语》卷第八尾题:“咸通三年二十五日学生张文营书”;P.3783号《论语》卷第五末题:“文德元年正月十三日墩煌郡学士张圆通书”;散0665《论语集解》卷第一末题:“大中五年五月一日,学生阴惠达受持诵读,书记”⑦李正宇:《敦煌学郎题记》,《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1期。等。陈铁凡先生也认为这些大部分书法拙劣的“恶札”与“伪俗之字”“触目而是”,这或是学童抄写时,胡乱应付,草草了事,或默书时忘记了本字,乃以同音字代之。⑧陈铁凡:《三近堂读经劄记》,《敦煌学》(第1辑),1974年版,第110页。由此可以推知,敦煌地区《论语》的流传应与唐代教育制度、科举制度有一定的关系。张弓主编的《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一书中,系统地研究了敦煌本儒家经典与唐五代的教育与科举的关系,认为“其种类的有无,数量的多少,均与唐五代的科举有密切的关系”,“其写本的来源,文字的善恶,均与唐五代的学校有密切的关系。……其中,有的是学校的教材,字体工整,书法精美;有的是学郎的作业,差讹百出,难称良善”。①张弓:《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7、96页。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敦煌《论语》写卷中不少题记可以证明诸多为学童应付学校功课所抄,这类写卷往往“差讹百出”。但还有一些写卷是学校教材,字体工整,书法精美。唐写本《论语郑氏注》中出现的“孔氏本 郑氏注”有题记:“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厚风里义学生卜天寿,年十二”,说明此为第一种情况,是学生卜天寿应付学校功课所抄,难免会有差讹。“孔氏本 郑氏注”这几个字,从常理推断,应非卜天寿这名12岁孩童所加,更为可能的是从教材中抄得。但教材中何以会出现此六字?单从这一本抄本中无从得出结论,我们可以结合同一时期敦煌地区流传的《论语》其他版本来看。
哀莫大于心死,孟导现在眼里全然没有了桌上那堆‘乾隆通宝’,就像是看到不成器的大儿子一样视而不见。他一边用手把‘乾隆通宝’们拨到桌子的另一侧,一边把目光集中到“次子”——数量更多的一堆古钱币。
李方对敦煌本P.3271号何晏《论语集解》校证时发现,此卷“并非纯粹的《论语集解》,它实际是在《论语集解》的基础上,根据《皇疏》补入了他家注的具有混合性质的论语集注写本”②李方:《伯希和3271号写本〈论语集解〉的性质及意义》,《敦煌研究》1995年第4期。。因为历代治《论语》学者,均不满足于一个人或一种形式的解释,必然要集众家之长,吸收更多的注文来理解经文,以满足对《论语》的学习和理解。“P.3271号写本作者,为省两读,便于诵习,率先在何晏《集解》中合并皇疏他注,可以说正是这种合并注疏的先声。”③李方:《伯希和3271号写本〈论语集解〉的性质及意义》,《敦煌研究》1995年第4期。这一解释给了笔者极大的启发。“孔氏本”三字的出现,正说明了《论语》在唐西北边境流传的过程中,《集解》《皇疏》《郑氏注》在出于教学或者治学的基础上,发生了人为的混合。《论语集解·叙》中有“《古论》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对于“世不传”这三字,历来颇有争论,有的学者认为是没有师传弟子,有的学者认为是没有流传开来,更有观点认为是表示其已亡佚。据近年来的出土文献和发掘资料,孔氏《古论》一直在西北边境流传,而《集解》中所谓“世不传”,当指孔安国为《古论》所作的训解,当然也包括孔氏《古论》可能在中原地区未受重视。唐代西北边境在当时文化较为落后,从中原地区流传过去的《论语郑氏注》,因其本身重训诂和名物制度的解释的特点,在当地广为流行。当孔氏《古论》与《郑氏注》二者并为当时当地人接受,为了教学或者治学的方便,被人为地进行了混合,并以“孔氏本 郑氏注”标明以便于区别,似乎就在情理之中了。
如表1所示,总体上来说,庐山市温泉镇主要温泉企业的旅游接待功能,都是十分相似的。基本上是集温泉、餐饮、客房、会议、娱乐于一体。少量的温泉企业伴有康养保健中心,跟体育休闲与培训功能。
雨水箱涵施工技术准备工作的另一个关键是采取自拌混凝土作为主要的施工材料,即垫层施工。施工正式开始前需要将所有材料在检查工作做好,确保施工材料的规格及质量与施工标准相符合,尤其是水泥质量需要特别留意。接下来自办混凝土的比例配置规定进行配置工作,为保障优质的混凝土质量,注意水泥和砂石用量的科学配比并进行合理控制。认真检查垫层平整度,之后的捣筑施工作业使用平板振动器进行。
当然,这也只是基于对现存敦煌《论语》本考察的基础上作出的推论,仍需更多的文本资料作为佐证。随着更多出土文献的出现,原本亡佚的版本而今得以重见天日。比如2016年海昏侯墓《论语》的出土,因其中的《知道》篇(按:竹简作“智道”),现今被学界推定为《齐论语》,更多的研究还要等待考古资料的公布。如果真的是《齐论语》,对于《论语郑氏注》的研究无疑会有巨大的帮助。且存论于此,供方家商榷。
Research on the Circulation ofAnalects in Dunhuang Area in Tang Dynasty in the Light of Zheng Xuan′s Analects of Zheng′s Note
LIU Xiao-xia
(Chinese Confucius Research Institute,Qufu Shandong 273100,China)
Abstract:Today′s Zheng Xuan′s Analects of Zheng′s Note is a relic of Zheng Xuanjing′s manuscripts discovered since the early 20th century.It was originally believed to be all destroyed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Therefore this book has a pivotal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It was widely circulated during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Analects Zheng′s Note is a long scroll that is well-known in the Turpanic documents.From the perspectives of"Confucius′s Note",and"Zheng′s Note"appeared in this transcript,this article try to analyze the reasons why"Confucius′s Note"appears in the"Zheng′s Note",thus investigating the historical influence of the spread of the Analects of Zheng′s Note in the Tang Dynasty.
Key words:Analects of Kong′s Note;Analects of Zheng′s Note;non-circular;later readers
中图分类号:B22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210(2019)02-0068-06
收稿日期:2018-11-13
作者简介:刘晓霞(1982—),女,山东曲阜人,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儒学史。
标签:论语论文; 敦煌论文; 写本论文; 郑氏论文; 郑玄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先秦哲学论文; 儒家论文; 《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论文; 孔子研究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