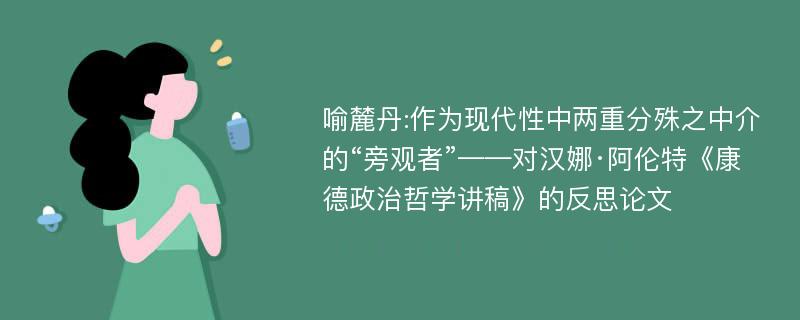
摘要: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区别与统一是现代性中最为本质的两重分殊关系,也是对“人们为什么要存在”问题的回答。整体(民族、国家、历史)对个体是否具有优先性以及个体意义向整体价值的过渡是否合理在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的争论中仍然成问题。作为一种对该问题的切入方式,阿伦特认为重新考察康德“旁观者”概念可使得特殊物与普遍物关系中内含的四个层次得以澄清,但她在强调“复数的人”的境况时却打断了与康德的道德主体的直接关联,重建这种关联或可使得拥有理性自由的现代个体与共同体得以各自扬弃其现代局限性,最终完成历史的统一。
关键词:阿伦特;康德;私人;旁观者;复数的人;《康德政治哲学讲稿》
个人与世界的关系的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古今哲人对它的回答从未中断过,虽然时代给予他们的难题并不一样,但思考的方式与深度却是可以互为比较的。然而问题在于我们今天对这些答案是否还保持着清醒的感受力?现代思想对传统思想是否有完整的继承或许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前者是否能使我们“获得一种沉思的动力”[1]523。在沉思古今差别的问题上,康德、海德格尔与阿伦特可被视为现代哲人中最具代表性的三位哲学家。康德哲学体系重在为世界中的独立个体及道德主体的联合找到先验根据,海德格尔旨在对存在者的形而上学基础形成批判,阿伦特则从传统与现代思想中继承并创新地发展了自己的政治哲学观,重新深入地讨论了个人、民族、种族、国家等问题。本文所能容纳的仅仅是他们思想中的片段,但是当这些片段被加以串联之后,其共通的思想高度也许即刻得以呈现。
一、康德:作为进步的普遍立场与作为自由的理性个体
康德曾经以开玩笑的方式提到:交战的国家就如同在一家瓷器店里挥舞大棒互相厮打的俩醉汉。[2]“世界(瓷器店)是不在考量之中的。”[3]81当个人凝聚成集体时拥有了厮打的力量和意志,而当个人只是作为个体存在时,他们自身的破碎被做成了醉汉打架应偿付的代价。对于战争,康德的态度是很复杂的,它一方面是“由人们无节制的激情而挑起的”,为我们内心的实践理性所明令禁止的一种赤裸裸的消耗殆尽,另一方面又是因自身的毫无意义而能够激发人们把所有用于文化的才能都发挥到极致,并为最终的世界性和平作准备的动机。我们在分析康德对战争的复杂态度时要明确以下两点:首先,他这些审美反思性的判断是基于一种“观者”立场:他的“无兴趣无利益、他的不参与、他的不卷入正是他的洞见之存在的基础”[3]82。与观者相对的是行动者,他们由于是演出的一部分而本质上是偏狭的,并像演员一样根据旁观者的意见来引导自己。其次,“观者”所面对的应是“世界性的整体”,也即一个“由所有国家——这些国家都面临着相互行不义的危险——所构成的体制”,与此类似的还有“种族”“民族”等概念。这是一条斯宾诺莎式的思路——只有在这些普遍物中,特殊物才是有意义的,即进步是种族的进步,对个体几乎毫无助益。即便是1933年的海德格尔也承认民族对国家、对个人有优先性。他把国家作为民族的外在表达和工具,并在1933年12月的演讲里说道:“个体,无论身处何地,都是毫无价值的。而我们这些身处国家中的人民(people-in-its-state)的命运却是充满价值的。”但这个共同体不能像当时的英国一样是由原子个人组成的竞争的社会,而应该是有机的、民族性整体(德国人的气质是“内在化的”和精神性的,德意志民族在其灵魂深处是文化的),个人在其中承担责任才能找到真正意义,而整个民族才能担任世界精神领袖。
康德把主体性交给人类种族时走得足够远,以至于康德对自己提出的“人们为什么存在?”这个问题时给出的答案也是“无法回答”。他把人类种族“理解为持续地向着无限性(换言之,不确定性[indeterminable])而进展的世世代代的总体。……[这条]世代的线,无休无止地向与其并存的归宿(destination)靠近。……[这条世代的线,]其各部分都是那条命数之线(this line of destiny)的渐近线,而其整体,则与命数之线重合。换言之,人类族群中的世世代代,没有哪个单独的成员能够完全抵达其归宿,惟有人类‘族群’才能够完全抵达其归宿。……哲学家会说,一般地来看,人类族群的归宿就是永久的进步。[4]57-58
到这里为止,我们赫然发现康德为普遍立场所叠加的“进步”概念——与他进行判断力批判所要奠定的自然和历史的“合目的性”相一致——仿佛成为了一种无可撼动的客观力量反过来支配着族群本身,而这种客观力量的必然性同时体现在它对个体主体的真理性上:
作为整个物种的人(man),其目的,……天意(providence)[有时他也说“自然”(nature)]将会促成其成功实现,即使作为个体的人们(men)目的南辕北辙。因为,个体倾向之间的冲突,虽是万恶之源,却正好让理性得以自由掌控它们;由此,不同的个体倾向之间的冲突,不是让“恶”占上风——恶是自我毁灭的,而恰恰是让“善”(good)占上风——“善”,一旦确立,始终会自我维持。[4]208
对康德来说,把历史视为一个整体,没有进步的假设所造成的是与“善”相对的“倒退”和“雷同”的景象,而倒退带来绝望,雷同将令我们烦死。但是作为道德个体,人心却可以被设想为“恶”的。康德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里把恶劣之心定义为从自然倾向中产生的任性和不把道德法则接纳入自己的准则的无能,即把出自道德法则的动机置于其他(非道德的)动机之后的败坏的思维方式——由于它从自然倾向中来,因而是由拥有不同立场和诉求的人们“自己招致”的,必然要随着人们立场的对立而对立,随着人们诉求的冲突而冲突。而这些可能发生相互排斥的本能倾向所要达到的目的如果仅仅是“保存它,使它生活舒适,一句话,就是幸福”,康德认为诉诸人的理性就太过奢侈。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康德在这里的“善”如果还不能直接理解为“进步”,至少不能理解为“获得幸福”,而个体根据本能倾向行动所造成的冲突尽管是一种“不幸福”却与理性“掌控”并无矛盾——理性设定了更崇高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自然及人类社会本身的合目的。换句话说,康德这两段话至少可以包含四个层次的意义:首先,作为个体的拥有南辕北辙的自然倾向的人,他们是感性自然界的一部分;其次,人类行动者进入共享的外观空间,开始了公共政治事务的生活,演员/行动者在这个事业中被赋予意义;再次,因为反思性判断也意味着关照特殊物的独特品性,因此个体要将自己本身作为自身的目的来关照,即作为道德主体;最后,人类自身的客观的理性目的会将历史带到人类的自由王国和道德世界。这四个层次相互间或许并不是截然分离的,但也并不适合被看作是能够混淆的。如果为了对抗“主体化的威胁”,力图确保一个由种种共享的外观和主体间判断所组成的、可能的公共领域而降低或忽略道德个体与目的王国的先验意义——或许就像阿伦特想根据第三批判来重建康德的政治哲学那样——或是将个体从共同体中剥离出来而赋予其极高的先天道德根据和自律性,倒是总会顾此失彼。
康德把“旁观者”做成了特殊物向普遍物过渡的中介,换言之,他同时代表的是存在于非客观感觉中的非主观因素。旁观者首先是“有距离的”,他跳出具体行动者平面,着眼于所有的行动者的景观,同时发挥着类似于想象力为心智之眼提供图示的功能,为具体行动者提供了对行动本身的反思。因此他或他们,是超越了特殊个人与纯粹共同体之单纯对立的现实存在。除此之外,康德为旁观者所叠加的“进步”概念意味着历史的进步是永远的,历史没有什么终结,历史的意义就在于历史对其主体来说包含着为未来世代的希望。上文说过“人类种族/族群”作为整体才能够达到与命数之线重合而抵达归宿,康德用“人类种族”表达的恰恰就是抱持一种整体理念的旁观者,正是旁观者的在场,一场历史事件才称得上是“世界历史性”的。法国大革命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由此可以说,康德设定“想象力”“共同感觉”“被扩展的心智”其真理在于得到“旁观者”的概念,因为后者才是“公开化”与“普遍性”之成道德法则之根本特性的基础。这个推理简单来说可以这样铺开:历史面向各个特殊阶段或视角的个人是不完整的,因此它只有在面向一般立场者(旁观者)时才有(进步)意义,这些是基于旁观者能够与行动者拉开距离并用一般图示表达特殊行动(正如想象力所做的那样,即呈现其表象或给出说明,都必是可公开的),进而形成对行动自身的普遍反思,即普遍判断;由于这种判断的对象是独立个体的内在感觉,因此它依据以自身为普遍规律为目标的准则进行,同时为普遍“主体间有效性”规定了条件——恰恰是康德的先验道德主体保证了旁观者能够发动全人类共同拥有的普遍官能,既投身于由一个判断者伙伴组成的共同体,以对“共同体感觉”的想象为自身判断的依据,又从中分离出以坚持自身为目的的先验的理性立法原则——我认为这是康德为旁观者独立性的证成所提供的基础,也是康德提出旁观者概念的最终所指,阿伦特虽然也主张反对任何群体本位的政治意识形态——“平庸的恶”,却似乎将个人判断的基础更多地放在“旁观者”概念本身而缺少对康德先验主体一环的完整批判。
二、阿伦特:并不由“单数的人”所叠加的“复数的人”的境况
Tassorelli C, Grazzi L, de Tommaso M, et al. Noninvasive Vagus Nerve Stimulation as Acute Therapy for Migraine. The Randomized PRESTO Study. Neurol, 2018, 91(4): e364-e373.
纳入标准:(1)所有患者均符合临床关于白内障的诊断标准,经眼压检查、房角检查或B超检查确诊;(2)年龄>60岁;(3)患者意识清晰、交流能力正常;(4)知晓实验目的,签署《知情同意书》。
但她没有反驳这一点:康德设定“旁观者”在其理论体系中是有必要的。否则他用来联结“复数的人”主体间肌理的概念如“共通感”“扩大的心智”并不能成为阿伦特式“复数的人”在与他人共处的经验中自行产生行动准则的充分条件。行动者,就他扮演整部剧目中的某个角色且必然要面对无数观众而言,不是自律的,“他不是依据与生俱来的理性之声而是依据旁观者对他的期待来引导自己。旁观者是他的基准,而这个基准是自律的”[3]84。康德在自己的政治哲学中所坚持的原则就体现在这里,由于他对群体的共同经验并不完全信任,因而他的目的仍然是要寻找使得判断成为可能的先天根据,因而对摆脱了具体行动者经验性立场,即他律性桎梏的“旁观者”的设定不失为一条好出路。
睡眠是人类正常的生理需求,是恢复神经系统的重要过程,具有促进人体生长发育的功能,其在维持人体注意力、警觉性、记忆力、学习能力、执行功能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一旦人体出现失眠现象,将可能引发多种躯体疾病、心理疾病及精神疾病等。因此,在临床治疗过程中需对失眠的发病机制及诱发因素进行全面了解,同时,还需对失眠与焦虑抑郁情绪的关系、失眠与认知功能的关系、焦虑抑郁情绪与认知功能的关系等进行详细了解,以制订最佳的治疗方案。
罗纳德·贝纳尔在《康德政治哲学讲稿》的中文版前言中提到阿伦特拒斥康德所代表的自由主义所用的理由是,她认为这种自由主义“处心积虑地把公共领域构想得很狭窄”是为了“赋予不容侵犯的私人领域以崇高而首要的道德地位”。因此为了抵制自由主义严重的主体化倾向,她宁愿转向《判断力批判》并用康德自己的概念,如“共同感觉”“被扩展的心智”“想象力”“无兴趣/利益”等将个体间相互打通,为公共空间让出地盘。
因此,从私人领域过渡到公共领域有一个曲折过程。基于个人对自己的反思:在苏格拉底那里,他将与自己的无声对话公共化,在集市上表演;在康德那里,他寻求的是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的自由;在阿伦特那里,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相反,它的旨趣在于还给人们“被他人看到和听到的中产生的实在性”,也即一种为自己“给出说明”的能力,而人们需要公开说明的不仅包括私人财产、处事准则,甚至包括个人较为隐私的品味水平,而这种说明反过来才使得主体自身将自己的私人领域从公共领域中真正区分开来,譬如,当人们私心希望自己成为唯一不遵守道德理性原则的特例并因此获得“不义之财”时,他才将自己与他人完全区分开来。然而这种区分是暂时的,它会被必要的“公开说明”所瓦解,人们在相互说明的过程中不得不逐渐丢弃一些狭隘的立场——进行说明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表演的过程,演员最重要便是迎合观众的胃口,而这除了需要将自己的内心情绪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也需要预料到观众可能的反应。首先,观众的视角必定是相互各异的,其次,每个人都担当着演员及观众的双重角色。从前者产生的是“一般化”立场,即“不偏不倚”的可能性,后者是每个人通过反思判断力融入公共生活的方式。多重观众视角的意义在于,“只有事物被许多人从不同角度观看而不改变它们的同一性,以至于聚集在它周围的人知道他们从纯粹的多样性中看到的是同一个东西,只有在这样的地方,世界的实在性才能真实可靠地出现。”[5]38不同角度强调的是特殊性本身的意义,至于如何由特殊性过渡到普遍性,康德是用“想象力”帮助人们形成认知图示和判断范例从而从私人境况中解放出来,用“心智的扩展”帮助人们从偏见中解放出来,用“共通感”保障主观审美感觉与客观普遍性一致等办法来解决的。在此基础上,逃离了狭隘立场而获得“一般化”立场、无兴趣/利益的个人作为“旁观者”才有可能出现。
旁观者是相对于“行动的人”的概念,他面对的是作为“整体”的人的领域,因而这个“整体”必定是“复数的人”。阿伦特在《康德政治哲学讲稿》中为“复数的人”下的定义是:“依附于地球的被造物;生活于各个共同体之中;被赋予了常识/共同感觉(common sense)、sensuscommunis,即一种共同体感觉(a community sense);不是自律的;需要彼此陪伴,哪怕对于思索(‘书写的自由’[freedom of pen])来说,亦复如是。”[3]43在她看来“复数的人”一方面被赋予了共同感觉,另一方面却不是自律的,这意味着人们用以达成相互理解的方式虽有客观普遍性,现实中的行动却是“不可预测”的。
在海德格尔看来,人的本质基于他的绽出之生存中——它“始终区别于形而上学所思考的existentia[实存]……康德在经验之客观意义上把existentia表象为现实性”[1]382——而如果用阿伦特的话说,人却是“被处境规定的存在者”。所有被带入人的积极生活的任何东西都变成人之境况的组成部分。由于“世界现实对人类存在的影响,被人类感触和接受为一种限制人的力量”[5]3,从而对个体本质的探究不可避免地要进入其生活方式中。由个体享有的私人生活似乎从一开始就仅仅作为“社会”的对立面,使人区别于奴隶和野蛮人的生活方式而出现的。因此阿伦特在这本书中首先阐释了公共生活,而私人生活是作为公共生活的对立面被提出来的,因此以“被剥夺性”为主要特性的私人生活,相对于公共生活来说带有更多的消极意味,如果沿用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对自由的定义——自由的前提是摆脱所有主要目的在于维生的生活方式,因此三种自由人的生活是享乐生活、政治生活和思辨生活——那么私人生活从古希腊始就已被视为最不自由的生活,但它却是所有自由生活的基础。及至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个人,仍然无法摆脱现代生产性命令将个人禁锢在私人领域中以维持物质性生存的魔咒。因此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一书中论辩的要旨之一就是通过重新凸显一个共享的公共领域从而将逐渐消失在人类经验主体化的现代性过程中的个人拯救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阿伦特所说的“被处境规定的存在者”相当于海德格尔所说的“在世界之内的存在in-the-world-being / Inderweltsein”,但是德语的“in”是一个意义非常强的介词,更贴近于英语的“within”,有一种拘束于内部、不得越雷池一步的意味。因此,“绽出之生存ecstatic existence / ekstatischeExistenz”顾名思义决不单纯处在世界“之内”或“被处境规定”——这当然不是否认世界的必要性——而是关系到世界的生产与变化、建立与消亡。换言之,“绽出之生存”意味着对现有的公共领域的某种形式的否定或突破;这当然不是反对公共性,而是公共领域的必然的自身运动。进一步地说,任何世界都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绽出之生存”的结果,或者说“绽出之生存”的遗迹。世界=创始行动所留下的遗迹。海德格尔说:“人强力行事地打扰了生长发育之平静,打扰了无劳无虑者[按:即自在的自然,所谓的土地/大地/ earth / Erde]之营养与结果。制胜者在此不是在把自己本身都吞没了的粗野中起作用,而是作为能从一个伟大的宝藏之平静的优越性中毫不费劲毫不疲倦地导致并给出超越一切烦忙之上的不可枯竭者的这样一个东西来起作用的。在此起作用中,强力行事者出场,年年岁岁运犁翻地并把无劳无虑者驱入其劳累不安中。”[7]可见,“绽出之生存”对于世界而言是一种原始而伟大的力量。
这一思索方式,由于是一般化的,就证明人类族群总体上共享着某一特性;由于其是无兴趣无利益的,就证明了这种特性是人类的一种道德特性,至少人类在其倾向或素质上有这样的特性,这一特性,不仅让人们可以对向着更好的进步怀有希望,而且,就其能量在当下业已足够充盈而言,这种特性本身是一种进步了。[4]152
历史中的真实个人受制于他的生活境况,是感性世界的一部分,康德为人区分了三种原初禀赋,[6]除了要为人们采取任性倾向提供可能性根据,更要为了以此说明出自自由的道德行为的崇高性。三种原初禀赋并不必然导致恶,但前两种却可以嫁接各种恶习,因此康德对人“天生是恶的”一句的解释是“人意识到了道德法则,但又把偶尔对这一原则的背离纳入自己的准则。”换言之,康德并不把人的本性自在地等同于天然形成善的或恶的道德次序本身,而是把它理解为自由地选取准则、为自己制定规则的主观根据。
三、旁观者:两种立场过渡之中介
康德与阿伦特对公共领域内在运动结构的理解都提示了旁观者的重要性,但二者对旁观者之于判断、之于公共领域自身内在的自我超越所具有的意义看法是不同的。旁观者正是要从人类事务中撤离出来,他既被景象吸引,又在景象之外,他放弃了决定他实际存在的立足点,也放弃了立足点上所有随机的、偶然的状况。[3]84因此旁观者所持的是一般立场,这并不是说旁观者为了实现完全的抽离而对各个特殊立场漠不关心,相反,他的“抽离”,即与具体立场之间拉开距离只是为了看到整体。这段距离不能太远——他要保证能够看清所有值得重视的细节从而将所有特殊立场紧密相连,也不能太近——他要保证不被一叶障目,要做到“不偏不倚”。由于旁观区别于行动,因此旁观者是要从这个有距离的视角来审视、形成判断,或者如康德所说,来反思人类事务。反思判断力,有别于纯粹认知能力,是指判断对错、将特殊包括在普遍之下的能力,也就是为多样性寻找其一般规律的能力,对康德来说,这样的能力是以私人感觉为基础的。而由于我们的私人感觉如嗅觉、品味原本是不可表达的东西,它们需要经过想象力转化为某种“被感觉到了”的对象,即转化为某种表象/再现从而引起人们在对之下判断的行为中感觉到快乐或不快乐。这就是康德所说的“反思的运作过程”,它的对象不再是直接的外部感觉,而是已转化为内在感觉的自己。我们可以看到,康德突出“想象力”“共同感觉”等概念的良苦用心就在于为人们借助反思判断力从感觉与认知对象的直接呈现中逃离出来准备好条件,这种逃离同时就是人们对具体立场、具体利益牵绊的逃离,也是人们对自身完全依赖“复数的人”本身的逃离。阿伦特对康德的“品味判断”是赞成的,因为品味判断打通了个体间原本被视为不可交流的私人感觉,促使人们总是把自己作为共同体的一员来反思他人以及他人的品味,把他者可能的种种判断纳入考虑,进而使共同体自身成为道德法则的来源,使人们在“复数的人”共同经验中发现行动自身内部的“解决之道”。在这一点上她所直接反对的就是康德所构想的道德主体——这种主体是从社会生活的更广阔的基体中剥离出来的纯然的道德主体,他在自身内就可以找到所有道德原则而具有独立性。这种纯粹主体看起来确实太过狭隘。然而康德从品味判断中推出的并不直接是纯粹的道德主体,而首先是拥有一般立场的“旁观者”,这个“一般立场”区别于他者立场,最终走向的是内在立场。关于这个“一般立场”的意义,康德作了如下阐释:
与此对应的是,阿伦特用复数的人的行动的“不可预测性”来反对西方思想传统中“自由把人们引向必然性”。柏拉图以来的政治哲学家们试图用一种制作艺术品的政治模式取代行动从而克服行动的偶然性,包括乌托邦设计的社会方案及“目的——手段”的理性框架,都以全然放弃人的创新性与独立性的方式来守护理性原则的强迫力。阿伦特反对这种用简单粗暴的命令方式来约束不同立场的人们去执行从理论推理出来的统一的行动标准,她认为唯一能够产生预测这种“不可预测性”的可能性地方就在复数的人希望在一起生活的言说和行动本身。这种预测不同于回到贯彻必然性,它是对指导行动的计算理性的强制力的打破,而计算理性区别于实践理性的地方恰恰就在于它没有给予行动者自由选择行动准则的机会——几乎是主体凭借自然本能并且是为了自然本能而被“理性”奴役的状态——因此它可以被人们的“宽恕”和“承诺”所终结。“报复”同所有依照逻辑推理可以预测到的人的行动本能一样,一方面延续着人类社会对自身应对伤害所采取的后续行动呈现必然性的绝望情绪,另一方面却同时加固着特定行动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的不可预测性,与基于自由的善行不同,这种不可预测性只是纯粹的无意义的任意性。因此,由“复数的人”所组成的政治社会既要摆脱由行动的必然性带来的对未来公共生活的绝望,又要避免堕入单纯的任意性而令整个历史丧失意义,正如“倒退令我们绝望,而雷同将令我们烦死”,必然的乃至拥有某种理性形式的行动序列与毫无根据的任性选择都同等地令我们绝望,又令我们烦死。相对的,阿伦特认为从宽恕和承诺的能力中引出的道德法则只能建立在依赖于他人在场的经验上,孤独状态中的个人甚至无力领会内在于行动的力量和复原力。因此,阿伦特的政治关怀可以用海德格尔的术语界定为“诸多‘绽出之生存’能否构成同一个世界,并同时使这个世界与‘绽出之生存’相适应,而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同时,如果“绽出之生存”对于世界而言是创始性的,那么“旁观者”至多具有黄昏的猫头鹰的地位(因为它对世界的旁观=对遗迹的旁观),因而不具有实践的地位。
2.2 药物敏感试验 GBS菌株对9种常见抗生素药物敏感试验见表2。红霉素耐药率从2014年的58.8%升至2016年的59.8%;克林霉素耐药率从64.6%升至71.0%;四环素耐药率从86.1%升至90.2%;左氧氟沙星耐药率有所下降,由32.1%降至21.0%。
在民宿的经营与建设中最重要的是体现当地的文化,通过具体的生活场景来展现宜兴特色的紫砂文化。宜兴是我国著名的陶都,将当地的紫砂文化融入到民宿中一定会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湖父镇民宿还可以利用当地的天然氧吧纯天然、原生态的特点,来体现一种安闲、自在、怡然自得、慵懒却又不失精致的田园生活。而且政府还要指导民宿经营者继续深入地去挖掘宜兴当地的文化内涵,引领他们在民宿的设计与开发上面融入当地的地方特色。不仅要为游客提供纯天然舒适的居住环境和富有本地特色的食物,还应该开发富有纪念价值的特色手工艺品,供游客欣赏和购买。
调查发现,大部分医护工作者认为医护职业风险大、责任重,在日常诊治、护理中经常会面临一些突发状况。因此,应关注医护工作者生存状态,制定相关政策法规,维护医护工作者的合法权益。同时,借助大众传媒在公众心目中树立良好的医护工作者职业形象,突出其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无私奉献精神,提高公众对医护工作者的尊重和信任,以增强医护工作者的职业认同程度。
四、结语
旁观者是否总是单数的?换句话说,鉴于道德主体的理性原则是旁观者下判断的先验根据,那么先验主体是否可以是彼此封闭的?
上文已提到过,旁观者是依据对“共同体感觉”的想象来摈除自己的私人化倾向的:
在sensuscommunis之中,我们必须把有关“一种为所有人所共有的感觉”——也就是一种判断官能——的理念包括进去,这种判断是能在自己的反思之中,(先天地)把其他所有人思想中的表象方式纳入考虑,为的就好像是要把自己的判断与人类的集体理性相比较。[8]
这是旁观者从具体立场中剥离出来、进入一般立场必须经历的环节。首先,反思必然包含着把自身对象化、转化为他者的过程,因而它是“非常自然的”;相反,人们脱离共同体、希望普遍规则能够在人们心中先天地完全呈现才是不自然的过程。其次,理性自身包含着这样的原则:“每个有理性的东西都必须服从这样的规律,无论是谁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把自己和他人仅仅当作工具,而应该永远看作自身就是目的。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有普遍客观规律约束起来的有理性东西的体系,产生了一个王国。”[9]每个道德主体作为这个目的王国中的立法者和首脑,通过普遍立法准则来与彼此相连接,倘若康德省略了这一点而让道德主体停留在独立个人阶段,其作为先验根据的理性法则是无法自我连贯的,其旁观者的一般立场设定亦会向特殊物倒退,进而失去其在自然与历史中的普遍意义和价值:随着人类种族的“进步”概念的消失,一同失去的更是特殊物与普遍物的本质联系,于是个体始终只是个体,他们的聚合甚至无法被称为“共同体”——他们的相互沟通实际上是失效的,即使达到某种经验的一致也是偶然和任意的,至此公共领域真正消失。
反过来我们要考察一下共同体与“进步”概念的关系,对于“自由”来说,“进步”所能表达的是否过于贫乏,或过于丰富。关于“进步”,海德格尔说道:“现今的‘哲学’满足于跟在科学后面亦步亦趋,这种哲学误解了这个时代的两重独特现实:经济发展与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简言之,海德格尔批判的是一种“私人”性质的进步,反过来,康德试图主张的是一种“公共”性质的进步。再看亚里士多德对三种自由人的生活的定义是享乐生活、政治生活和思辨生活,弗洛伊德证明了几乎所有的“享乐”都是生殖本能的曲折反映。最极端的例子是禁欲主义:通过严格的禁欲,僧侣达到了雄性动物相互竞争的一种极限——竞争的手段不是暴力、财富、“学问”等(虽然这些竞争项目显然构成了另一些享乐形式,并曲折地满足了生殖本能),而是对生殖本能本身的抑制,亦即对最终目的的抑制。之所以对目的的抑制反倒可以成为满足目的的一种手段,是因为这个目的本身(对雄性而言)就要求为人所不为、能人所不能,要求凌驾于同类的竞争者之上。于是,在(曲折地)追求这个目的的众人当中,禁欲主义恰好是人所不能的,从而反倒符合生殖本能的要求。只有在这里才可以看到马克思与弗洛伊德在人类思想的宏大历史中的地位。马克思证明了几乎所有的“政治”问题都是政治经济的综合问题,都不可避免地关系到生存、繁衍、舒适等,不论当事人是否意识到。例如,古希腊人的“纯粹的”政治生活突出地表现为一种殖民主义,而殖民的必要性源自本土人口的过剩。这不是政治“理念”的问题,而是本土存亡的问题。最终,无产阶级的政治运动不仅同样是政治经济的综合,而且很可能是历史上唯一公开承认这种综合的政治运动。因此,无产阶级的政治运动表现为最“私人化的”、最“平庸的”政治运动。然而显而易见,康德的“进步”概念只在针对理性共同体时才成立,享乐生活和政治生活都在他的视野之外,这也是他的庞大体系所不能面对和解决的世界一面。
参考文献:
[1] 海德格尔.路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2] Immanuel Kant.Kant’s Political writing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190 .
[3] 汉娜·阿伦特.康德政治哲学讲稿[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
[4]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5] 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
[6] 康德.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20-21.
[7]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55-156.
[8] 康德.判断力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36.
[9]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40.
Being“Bystander”betweenModernDoubleDifference——Reflection of “Kant’sPoliticalPhilosophyLecture” by Hannah Arendt
YU Lu-dan
(SchoolofPhilosophy,FudanUniversity,Shanghai200433,China)
Abstract:The Difference and unity between individual and society are the most essential modern double difference relationship and th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y people want to exist. Whether the entirety (nation, country, history) is superior to the individual and whether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individual meaning to the whole value is reasonable are still questions in the discussion of liberalism and conservatism. As a method cutting into the question, Arendt thought that reexamining the “bystander” concept of Kant may clarify the four levels included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pecial objects with the universal objects. However, when she emphasized situation of “plural person”, she broke the direct connection with Kant’s moral subject. So reconstructing the connection may make the modern individual and common body with rational freedom throw away their modern limitation and complete historical unity at last.
Keywords:Hannah Arendt; Kant; privacy; spectator; plural person; Kant’sPoliticalPhilosophyLecture
中图分类号:B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1901(2019)03-0019-07
收稿日期:2018-10-19
作者简介:喻麓丹,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哲学现代性,E-mail:13110160006@dudan.edu.cn。
[责任编辑:姚晓黎]
标签:康德论文; 阿伦论文; 旁观者论文; 的人论文; 目的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欧洲哲学论文; 欧洲各国哲学论文; 德国哲学论文; 《太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论文;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