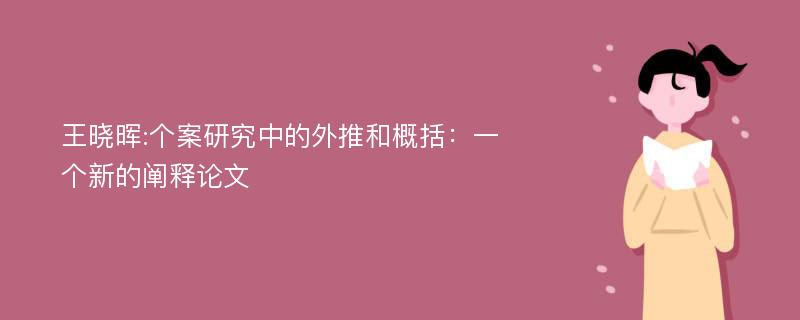
摘 要:根据哲学立场的不同,个案研究中的结论推广有三种具体含义:第一,研究结论在读者那里引起的共鸣、对话、认知图式的调整;第二,研究结论在其他情境中依然成立;第三,研究结论在其他情境中可用。哲学立场与人们对个案研究结论推广的理解密切相关。“拓展个案法”“迈向社会全体的个案研究”都不是外推之法,而是系统内的概括之法。所谓的个案研究中的外推和概括其实是一个阐释过程,是知识的积累,需要研究者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保持自觉性。
关键词:自然外推;理论承载的外推;适度外推;拓展个案法;迈向社会全体的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方法
一、引 言
从20世纪20年代起,个案研究结论可否外推以及如何外推就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议题。经过近百年,学界达成两点基本共识:第一,个案研究的结论可以外推甚至必须外推。虽然丹仁(Denzin)、林肯(Lincoln)、古巴(Guba)、斯塔克(Stake)等常被视为反对外推的学者,但其实他们反对的只是建立在实证主义之上的外推。约翰·吉尔林直接将个案研究定义为为了理解一类更大规模的相似个案而对一个或几个少数个案进行的深入研究[1],以表明特定个案研究的结论必须推广到一系列个案的立场。第二,个案研究应发展适合于自身的外推方式。学者们摒弃了基于代表性的概率样本的推论方式,(1)这类推论方式被称为统计性外推(statistical ge-neralization)、统计推论(statistical inference)、正式外推(formal generalization)、数字外推(numerical generalization)。提出了可迁移性(transferability)、自然外推(naturalistic generalization)[2]、分析性外推[3]51、适度外推(moderatum generalization)[4]、顺应与同化[5]420等替代方案。
争论深化了我们对个案研究结论外推的认识,但同时又衍生出一些需继续探讨的问题。第一,何为外推?大多数关于个案研究的文献都讨论外推问题,但并没有关于外推的系统化意义。第二,“拓展个案法”“迈向社会全体的个案研究”是不是外推之法?有些国内学者将其视为“走出个案”、超越个案之法,或明确视之为外推之法。诚然,“拓展个案法”和“迈向社会全体的个案研究”都有在个案中揭示宏观力量、宏观社会结构的企图。但是,它们是将研究微观个案所获结论外推到宏观社会,还是在蕴藏着宏观社会特征的典型个案中直接揭示宏观结构?第三,学者们开列出的各种个案研究外推法可否归类、整合以及如何归类、整合?学者们的争论展现了外推法复杂多样的一面,若要深化认识则需进一步揭示各种方法之异同,将其归类、整合。本文的任务即是回答上述问题,系统性地思考个案研究结论外推的方法论基础。
二、外推概念的复杂性
与定量研究关于外推概念的共识(2)定量研究公认的外推有统计推论和外在效度。相比,个案研究中的外推概念较为复杂。外推概念的复杂性至少有四个表现:两个多样性和两个值得商榷的问题。首先,术语多样性。据不完全统计,中文文献中的常用术语有“走出个案”“超越性”“一般化”“扩大化”“类推”“外推”“推论”,英文文献中的常用术语有generalization、extrapolation、transferability、portability、exportability、inference。其次,定义多样性。斯坦伯格(Steinberg)给出了一个最为宽泛的定义,即作为一种研究实践的外推是一种逻辑论证,它将观点拓展到经验资料之外,在被研究的事件与未研究的事件之间建立联系[6]。而依据如何建立两者之间的联系的观点,外推定义可分为三类。第一,外推是指研究结果和结论在其他情境中是否成立[7],外推意味着研究结论需经受从新情境中收集的经验资料的检验,若未被新的经验资料证伪,则结论具有普遍意义。第二,外推是指研究结果和结论在其他情境中是否可应用(applicable)。这种观点更强调结论对新的现象的解释力、预测力或实用层面的政策意义。第三,外推意指研究结果和结论在其他情境中是否引起共鸣,即读者阅读研究报告时,研究结果在读者心中是否产生了共鸣、共振、对话,是否自然而然地引起了读者认知图式的调整[5]421。
外推概念的复杂性还表现在两个值得高榷的问题上。首先,表现在关于外推基础的认识。个案研究结论外推需以代表性个案为基础吗?代表性是个案研究结论难以外推的原罪之源。定量研究学者质疑个案研究结论外推的主要原因,就是它只研究少量个案且个案不是随机抽取的。对个案研究进行反思的国内学者也往往基于个案的代表性来讨论结论的外推。例如,王宁认为,探索性研究和以资料积累为目的的描述性个案研究没有代表性要求,有代表性要求的结论性个案研究涉及的也不是“总体代表性”,而是“类型代表性”[8]。但在苟波(Gobo)看来,基于代表性来探讨结论外推,仍然没有逃脱统计推论的窠臼;不依靠概率原则同样能选择出有代表性的样本[9]。同样,弗里夫伯格(Flyvbjerg)也指出,异常个案、最大变异个案、关键个案、范例个案均可支撑外推[10]。本森(Bengtsson)和赫廷(Hertting)[11]、佩恩(Payne)和威廉斯(Williams)[4]、斯坦伯格(Steinberg)[6]、梅林(Mayring)[12]、伯格(Berg)[13]等学者则强调,被研究的情境与作为推论对象的情境之间的相似性、同质性是结论推广的学理基础。殷(Yin)则对外推条件不加限制,他特别强调,某个案研究的结论或经验可适用于多种情形,而不仅仅局限在被研究的个案所代表的类型个案(like-cases)范围之内[3]52。其次,表现在关于外推对象的认识。外推的对象是同类事物,还是总体或社会整体?英文文献有两种倾向:第一种含糊地认为外推就是将特定个案研究的结论推广到更广泛的情境中去,至于更广泛的情境是什么,则未加以明确界定;第二种则是明确地指出,外推是指个案研究结论在同类个案间的推广。中文文献中,陈向明、王宁的观点与英文文献中的第二种观点相同。陈向明将“外部推广”(3)Internal generalization与external generalization的区分是由Maxwell提出来的,参见Joseph A. Maxwell: 《质性研究设计》,陈浪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年版第146-147页。陈向明将它们分别译为内部推论和外部推论。定义为研究结果可以应用于样本范围之外的同类事物[5]410。王宁认为,个案研究样本代表的不是总体,其代表性是“类型代表性”,个案研究结论可以向“同质化类型”外推[14]。另有一些国内研究者在行文中交替使用“总体”“整体”这两个概念,并将“总体”“整体”视为个案研究结论外推的对象[15][16][17]。
三、什么是外推?
要理清外推概念的内涵,我们需要从generalize的基本含义入手。讨论外推时,generalize或其名词形式generalization是最常用的词,而使用extrapolation等其他语词,往往是要强调generalize的某种含义或强调某种特殊的推论法。根据朗文词典,generalize有两层基本含义:第一,在少量事实、例子的基础上形成一般原则、意见或对整个群体、事物作一般性陈述;第二,一个想法、结果等与一个更大的群体有关联。有少量方法论学者明确地区别使用generalize的两层含义。例如,斯坦伯格将个案研究中的推论法区分成两种:within-system generalization和cross-system generalization[6]。前者指研究结果准确揭示研究对象的程度,后者指研究结果可否推广至样本之外的同类事物。斯坦伯格举例说明了两种推论的含义:前者回答的问题是研究发现是否准确地反映了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后者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实证研究所得的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巴西。总体而言,英文世界的学者们通常在generalize第二层含义上讨论个案研究的方法论困境,即研究结果推广到其他情境的可能性。而从个案中提炼一般原则、普遍性陈述则是将它们推广到其他情境的前提,因为一般性原则、普遍性陈述比较抽象,从具体情境中“脱嵌”出来,从而具有了推广的可能性,因而学者们认为从个案研究提炼出的抽象概念、命题[18]、理想类型[11][19]、模型[20]都是有力的推广工具。结合generalize的含义和英文世界的学者的通常用法,本文将generalize的第一层含义译为“概括”,第二层含义译为“外推”或“推广”。
基于generalize两层含义的区分,我们便能很好地理清术语多样性以及有关外推基础、外推对象的争论。首先,Inference指从事实或前提中获得结论,与generalize的第一层含义大致相同;extrapolation、transferability、portability、exportability均表示将观点拓展到经验资料之外,即在被研究的事件与未研究的事件之间建立联系,其含义与generalize的第二层含义相同。中文文献中的“一般化”“扩大化”“类推”“外推”“推论”是generalize的不同译法,但研究者们均未注意到generalize有两层不同的含义。其次,苟波、弗里夫伯格等学者关于拟选取的个案特征的讨论,是关于具备什么样属性的个案能支撑“概括”;本森、殷等学者所分析的是在什么条件下可将特定个案研究的结论进行“外推”。再次,在外推对象上,英文文献的作者和陈向明、王宁两位学者认为,外推对象是同类个案。至此,我们可以总结出学术界对外推的基本共识:所谓个案研究结论的“外推”,是指将从特定个案研究所获的结论推广至其他的同类个案。
根据《文化的解释》第一章,可将格尔茨的理论立场概括为六个方面。第一,文化理论离不开它的基础即深描,所以它们不像实验科学的理论那么抽象;同时,至少在严格意义上,它不具有预测性,它有的是诊断功能,即它具有确认象征性行动的文化意义之功能;另外,文化理论也应接受明确的评价标准的评判。第二,理论建构的任务,不是编纂(codify)抽象的规律,而是要让“深描”成为可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从事文化阐释的“深描”需要理论的支撑,同时,脱离于运用的理论陈述要么是平淡无奇的要么是空洞的。第三,“个案中的概括”是以理论来阐释象征性行动的文化意义。格尔茨指出,个案中的概括通常称为“临床推理”。在临床推理中,医生首先确认症状,然后用理论来阐释症状。人类学家也从象征性行动(类似于症状)着手,企图把它们置于某种可理解的框架之下,此框架即理论,然后用理论去揭示行动中的意义。第四,每项研究用来阐释象征性行动的理论观点都不是全新的,它们是从其他相关的研究中借来的,它们会在研究过程中得到进一步的精炼。新的阐释理论要超越既有理论,它要比既有的更深刻(incisive);它要挑战既有的理论阐释,也会被后续的阐释所挑战。第五,理论不能只是与过去的现实相符,它还需在未来的现实中存活下来:随着新的社会现象的涌现,理论必须能够产生可为之辩护的阐释。因此,理论要在新的实际运用中接受检验。第六,理论进步的评判标准是阐释效果:如果理论不能胜任新的社会现象的阐释,它们可能会被遗弃;如果它们仍然能提出新的解释,则会得到进一步的精炼,研究者也会继续使用它们[28]。
将“拓展个案法”“迈向社会全体的个案研究”定位为“系统内的概括”之法,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关注结论外推。那么,它们如何处理结论的外推呢?《迈向社会全体的个案研究》没有讨论外推问题,只留下了“作为一种个体的总体,其自身的完整呈现即具有外推的属性”这样一句含糊的话。为“拓展个案法”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布若威(Burawoy)则认真对待了外推问题。他的外推方案是理论的拓展。“拓展个案法”不从经验资料中建构扎根理论,而是用经验资料来重构理论。具体重构法是:带着现有的理论进入田野,开展参与观察,目的不是要寻找经验资料来支撑该理论,而是要反驳该理论;在不触动现有理论的核心假定(硬核)的条件下,谨慎地吸收、消化反常,以重建理论(提高理论的普遍性程度、增加其经验内容)。布若威所谓的“反常”,大致就是异常个案(deviant case)、反面个案(negative case)。在布若威那里,用来衡量理论进步或退化的便是拉卡托斯的新经验预见标准[25]36-37,42-43,53-56,有更强预见能力的理论便有更强的外推性。除异常个案、反常个案外,在布若威那里,“反常”还有一种表现:重访(ethnographic revisit)同一田野再次进行参与观察时所发现的变迁(即以前的研究发现、结论与新的经验现象之间的差异)。研究者同样要带着既有的某种理论进行重访,在重访的过程中消化、吸收差异而重构理论[25]94-95。
针对情况最危急的迪庆、丽江供电局,云南电网公司要求根据预测的溃坝高程、洪峰流量,充分考虑应急处置范围、规模,针对性地制定应对高、中、低风险的应急预案,按洪峰入境前、过境时、过境后3个阶段启动响应予以应对。
图 外推的路径①
① 本图是对Philipp Mayring绘制的“外推过程”图的丰富和完善。关于原图,参见Philipp Mayring, “On Generalization in Qualitatively Oriented Research”, Forum, Vol.4, No.3. 2007.
四、概括还是外推?
“拓展个案法”和“迈向社会全体的个案研究”不是将个案研究论外推至整体的方法,而是“个案之中的个案归纳研究”“系统内的概括”之法。“拓展个案法”“迈向社会全体的个案研究”的学理基础相同,即典型个案中包含了宏观结构的基本法则。在拓展个案法中,典型个案称为“拓展个案”(extended case),它是蕴藏、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复杂性的社会情境(social situation)。人类学曼彻斯特学派认为,社会情境是特定社会制度和文化中的特定人和群体之间持续的社会互动的舞台,宏观社会过程形塑特定社会情境,而现实社会反过来也是普通人在日常世俗生活中建构的,因而相关的人和群体在其中行动的社会情境是社会结构复杂性的反映[24]。“拓展个案法”的目的之一,便是要从微观社会情境中揭示宏观社会整体的结构特征。其具体方法有“情境分析”(situational analysis )和“综合或纵向方法”(integrative or vertical approach)[25]。情境分析是将情境知识编织成各种行动者之间的持续互动及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综合或纵向方法”则是要探讨微观过程与外部社会力量之间的相互决定关系。同样,渠敬东认为,典型个案最大限度地、集中地体现了某类社会现象的重要属性,它在时空上具有与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关联,有外部结构性介入因素渗透进来的烙印,所以,典型个案“小细胞装载着大世界”,它是“考察社会整体构型和变迁的显微切片”[26]。“迈向社会全体的个案研究”的目的就是从典型个案中揭示出宏观的共变关系、社会机制、社会结构。其具体方法是“-graphy”和事件化。“-graphy”方法将“个案所蕴涵和关涉的社会全体不断加以呈现”,事件化则是藉由事件发生、发展的动态过程,发问、揭示其中的共变关系、社会机制、社会结构。总之,“拓展个案法”“迈向社会全体的个案研究”均要从典型个案出发去揭示整体属性。这两种以典型个案为直接分析对象而以整体为最终关怀对象的个案研究,是对社会整体自身可能性的释放,是在典型个案中概括整体属性,而不是将个案研究的结论外推至社会整体。
2017年4月20日3:00~6:00在某油田注水系统下游用户反映纳滤系统调试过程中入口保安滤器5 μm、压差高1 MPa,拆检发现滤芯有较大藻类味道,没发现什么明显的堵塞物,疑似有点像藻类和生物堵塞。说明上游水质可能变差。当天V30测试为9 L。
如前所述,有些国内学者将“总体”“整体”视为个案研究结论外推的对象。但是,个案研究的结论可否推论至“总体”“整体”呢?“拓展个案法”是不是由个案推论“整体”之法?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应该弄清楚相关概念的内涵。目前的争论中有混用“总体”“类型”“整体”这些概念的现象。在研究方法语境中,“总体”指所有个案构成的集合。它与“类型”概念一样,都是一个无情境(context-free)意涵的概念,也就是说它们缺乏个案之间相互作用、互为情境的内涵。它们就像一筐薯,每个薯就是一个个案,除了放在同一个筐内互有挤压之外,它们不发生联系,筐中的所有薯构成了“总体”,其中所有土豆就构成了土豆类型,所有红薯就构成了红薯类型。“整体”是指相互关联的部分构成的系统。它是一个关系概念、富有情境意涵的概念。整体中各部分之间相互作用、部分与整体之间相互依存,这意味着对于构成整体的某一部分而言,其他部分以及整体都是它的情境。因此,“总体”“类型”与“整体”是内涵各异的概念。从推论的角度来看,只要总体中的个案是同质的,随意抽选一个个案,根据对该个案的观察即可知悉总体的情况,因为构成类型的个案是同质的,根据其中一个个案所获的结论,即可推论至类型;整体则不然,相对于部分,它有更复杂的“突生”性质,凭借随意抽选的个案是不可能完整地认识整体的。“整体”与“类型”的差异,便是卢晖临、李雪质疑类型比较法能否认识“整体”的原因。类型是无情境意涵的概念,而“整体”是一个关系概念,即使总结出各种农村、小城镇类型,仍然不能揭示“那些在更大范围内才呈现的力量或关系”[15]。但这并不是说,不能从个案认识整体。只是我们还需弄清楚从个案认识整体的路径。根据“个案本身的研究”“个案之中的个案归纳研究”“收敛性的个案研究”[23]这种关于个案研究进路的分类,从“个案”认识“整体”,是“个案之中的个案归纳研究”,它以个案为直接分析对象,以整体为最终关怀对象、结论对象。依据斯坦伯格关于个案研究中推论法的分类,从个案认识整体采用的是“系统内的概括”,而不是“跨系统的外推”。从前述关于被研究的对象与被推论的对象需相似、同质的观点来看,研究个案所获的结论是不能推论整体的。
五、“拓展个案法”的外推
三种外推均以被研究的个案与作为外推对象的个案之间的相似性、同质性为推论基础,这是英文文献的作者及陈向明、王宁两位国内学者的共识。第二、第三种外推,均为分析性外推。由于它们均通过适当的理论实现外推,理论是外推的载体,故有学者认为理论承载的外推(theory-carried generalization)是一个更恰当的概念[22]。另外,这两类外推不追求在长时间内、在多种文化范围内都成立的社会学陈述,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也是“适度外推”。自然外推与理论承载的外推的路径不同。前者的路径是:研究者做深描,然后由读者对被研究个案与作为推论对象的个案之间的相似性、匹配度作出判断,并决定可否将结论运用于自身所处情境。后者的路径是:研究者先在经验观察基础上抽象、归纳出概念、理想类型、命题、理论,然后将其推广至新的情境(见下页图)。
自1932年但采尔回德国至蔡元培病逝的8年间,两人虽未曾再谋面,但一直保持着频繁的书信交流,但采尔也成为蔡元培交往时间最长、感情最深的一名外国学者。
3.法治保障社区居民合法权益。社区秩序法治,才能保障居民的合理诉求和合法权益。通过制定小区居民公约、楼规民约、议事规则、财务管理、停车管理办法和“三事分流”清单等,引导建立小区规范;加大普法宣传,发挥了社区民警和法律服务者的作用,增强居民法治观念;建立网格民警为主、网格长和志愿者为辅的帮扶帮控小组,对重点对象进行动态监管,确保小区和谐稳定;采取小区“红袖标”白天巡、网格民警夜间巡“两巡”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小区治安防控。
但是,对外推的具体含义的理解或明或暗地与哲学立场密切相关。借助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思潮的分野,结合前述关于如何在被研究的事件与未研究的事件之间建立联系的观点,我们可以区分出三种含义的外推。第一,倾向于人文主义立场的学者更赞同自然外推或迁移(transfer)。外推表现为研究结果在读者那里引起的共鸣、共振、对话、认知图式的调整。在这种外推形式中,研究者的任务是对被研究的现象、研究对象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研究过程、研究者自己等关键信息进行深描,而不是提炼抽象的结论。实际的外推过程是由读者接力完成的,即读者在阅读研究报告时,若产生某种程度的共鸣、对话,出现认知图式的调整,便实现了外推[8]421。第二,倾向于科学主义立场的学者更赞同外推是指研究结果和结论在其他情境中是否成立(hold true)。照此观点,研究者的任务是从经验资料中提炼命题、理论,这些命题、理论需用新的个案研究资料来检验。若重复研究(repeated study)获得相同的结论,则意味着成功实现外推。第三,倾向于建构主义的结构主义等综合立场的学者更赞同外推是指研究结果和结论在其他情境中是否可用。照此观点,研究者的外推任务是提炼概念、理想类型、命题、理论。而衡量外推效果的标准有实用主义“效果”论或拉卡托斯关于“发现迄今不为人们所知的新颖事实”的新经验的预见论[21]。
国内学者往往将“拓展个案法”与格尔茨(Geertz)所谓的“个案中的概括”(generalize with cases)联系起来进行讨论,并且有人错误地认为“个案中的概括”是外推之法[27],(4)作者用的是“类推”一词,但文章的一条注释写道:“‘类推’一词在不同学科或者研究者那里,有着不同的表述。‘概推’‘外推’‘外部效度’以及‘代表性’等都可以视为相同的含义......社会学则更倾向于使用‘类推’或‘外推’等词。通常而言,‘个案’与类推”联用,而‘案例’与‘概推’联用。鉴于本文在研究中使用了‘个案’一词,因而也采用了‘类推’的称谓”。从注释可见,作者用的“类推”与本文的“外推"同义。故而至少在国内,“个案中的概括”是讨论个案研究结论外推时绕不开的问题。我们需要回答“个案中的概括”是不是外推之法?格尔茨如何看待个案研究结论的外推?格尔茨是在分析文化理论的特征及其阐释功能的语境下提及“个案中的概括”的,为回答上述两个问题,我们首先需简述格尔茨的理论立场。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格尔茨所谓的“个案中的概括”不是个案研究结论的外推之法,而是文化阐释之法,其目的是揭示象征性行动体现的文化意义。第二,格尔茨认为,文化阐释的结果可以且必须推广。他强调在实际运用中批驳和推广理论。格尔茨和布若威一样,认为既有的经验事实、概念、命题能够启迪后来的研究,能帮助后续研究深化对社会现象的认识。但他们的外推之法有明显差别:布若威强调通过吸收、消化反常来重建理论,评价新理论的标准是新经验的预见力;格尔茨提倡在实际运用中精炼理论,衡量理论发展的标准是理论阐释新的社会现象之文化意义的效果,这是实用主义的效果论。
六、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个案研究结论的外推就是指将结论推广至其他同类个案,对个案研究结论推广具体含义的理解与人们的哲学立场密切相关,各种含义的外推亦对应着相应的质量评价标准。“拓展个案法”“迈向社会全体的个案研究”均非外推方法,而是系统内的概括之法;格尔茨之“个案中的概括”也不是外推之法,而是阐释象征性行动的文化意义的方法。
个案研究结论外推涉及对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认识。任何事物都是一般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一般寓于特殊、共性包含于个性,无特殊即无一般、无个性则无共性[29]。个性与共性的对立统一,意味着我们可从个案研究中提炼具有普遍性的结论,也可将普遍性结论外推至同类个案之中。而且,个案研究相对于社会调查的深耕之能,更能帮助我们深入认识个性,更能帮助我们创造出深厚、饱满的研究成果。胡塞尔说,“你必须亲身投入特殊性中,以从中发现恒定性”[30]。我们越是深入地认识个性,越能够在个性中揭示深层共性[8]412。
个案研究结论的跨系统外推,是知识积累的集结过程[10]。高质量的个案研究成果的积累,一方面可帮助我们深化对社会普遍机制的理解,另一方面可在对话、交锋、共鸣之中优化我们的认知图式。然而,外推不是自然、自动产生的,从研究设计起、直到研究结果呈现和结论提炼的整个过程中,研究者应保持外推的自觉性。同时,为保证研究质量,所有研究者均应做到方法上的严谨性,并在报告中呈现出令人信服的概括和外推逻辑。
本论文是从“城市艺术”以及“城市设计”的视角研究天津市的特色城市品牌。通过艺术与设计的手法将天津城市品牌的内涵外显化,将天津市的城市品牌转化为直观的视觉符号,将城市魅力艺术性的表达出来。通过“城市艺术”的思路塑造天津滨海新区的城市品牌,具有很好的应用价值和实施可行性。从城市艺术与设计的角度研究天津滨海新区的城市品牌的塑造问题,探索天津滨海新区的城市品牌及内涵建设方法与技术路径,最终为天津滨海新区特色城市品牌塑造提供思路。
参考文献:
[1]约翰·吉尔林:《案例研究:原理与实践》,黄海涛、刘丰、孙芳露译,张睿壮、黄海涛审校,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9页。
[2]Tomas Hellström, “Transferability and Naturalistic generalization: New Generalizability Concepts for Social Science or Old Wine in New Bottle?”,Quality&Quantity, No.42, 2008, pp.321-337.
[3]罗伯特·K.殷:《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周海涛、史少杰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4]Geoff Payne & Malcolm Williams, “Generalization in Qualitative Research”,Sociology, Vol.39, No. 2, 2005, pp.295-314.
[5]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0页。
[6]Paul F. Steinberg, “Can We Generalize from Case Studies?”,GlobalEnvironmentalPolitics, Vol.15, No.3, 2015, PP.152-175.
[7]Geoff Payne & Malcolm Williams, “Generalization in Qualitative Research”,Sociology, Vol.39, No. 2, 2005, pp.295-314; William A. Firestone, “Alternative Arguments for Generalization from Data as Applied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EducationalResearch, No. 22, 1993,pp.16-23.
[8]王宁:《个案研究的代表性问题与抽样逻辑》.《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第3页。
[9]Giampietro Gobo, “Re- conceptualizing Generalization:Old Issues in a New Frame”, in PerttiAlasuutari,Leonard Bickman,Julia Brannen, eds.,TheSageHandbookofSocialResearchMethods, Los Angeles, London, New Delhi, Singapore: Sage Publications, 2008, pp.193-213.
[10]Bent Flyvbjerg, “Five Misunderstandings About Case-Study”,QualitativeInquiry, Vol.19, No. 2, 2006, pp.219-245.
[11]Bo Bengtsson & Nils Hertting, “Generalization by Mechanism: Thin Rationality and Ideal-type Analysis in Case Study Research”,PhilosophyoftheSocialScience, Vol.44, No.6, 2014, pp.707-732.
[12]Philipp Mayring, “On Generalization in Qualitatively Oriented Research”,Forum, Vol.4, No.3,2007.
[13]Bruce L. Berg ,QualitativeResearchMethodsfortheSocialSciences, Boston: Allyn & Bacon,2009, p.330.
[14]王宁:《个案研究的代表性问题与抽样逻辑》,《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第2页。
[15]卢晖临、李雪:《如何走出个案——从个案研究到拓展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16]王富伟:《个案研究的意义和限度——基于知识的增长》,《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17]董海军:《个案研究结论的一般化:悦纳困境与检验推广》,《社会科学辑刊》2017年第3期。
[18]Keith F. Punch, IntroductiontoSocialResearch:QuantitativeandQualitativeApproaches, Los Angeles, London, New Delhi, Singapore, Washington D.C.: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14, p.123.
[19]Bente Halkier, “Methodological Practicalitiesin Analytical Generalization”, Qualitative Inquiry, Vol.17, No.9, 2011,pp.787-797.
[20]Ingrid de Saint-Georges, “Generalizing from Case Studies: A Commentary”,Integrative Psychological & Behavioral Science,DOI:10.1007/s12124-017-9402-x.
[21]伊姆雷·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22]AdriSmaling, “Inductive, Analogical, and Communicative Generaliz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Methods, Vol.2, No.1, 2003, pp.52-67.
[23]黄志辉:《理解费孝通的研究单位:中国作为“个案”》,《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第16页。
[24]Marian Kempny, “History of the Manchester ‘School’ and the Extended-Case Method”,SocialAnalysis, Vol.49, No.3, 2005, pp.144-165.
[25]Michael Burawoy, TheExtendedCaseMethod:FourCountries,FourDecades,FourGreatTransformations,andOneTheoreticalTradition,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26]渠敬东:《迈向社会全体的个案研究》,《社会》2019年第1期,第11页。
[27]王刚:《个案研究类推的方法与逻辑反思》,《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70-71页。
[28]Clifford Geertz,TheInterpretationof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p.13-15.
[29]《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8-320页。
[30]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邓正来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页。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9)09-0058-07
作者简介:王晓晖,1973年生,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朱 磊,张斐男]
标签:个案论文; 结论论文; 理论论文; 社会论文; 情境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学习与探索》2019年第9期论文; 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