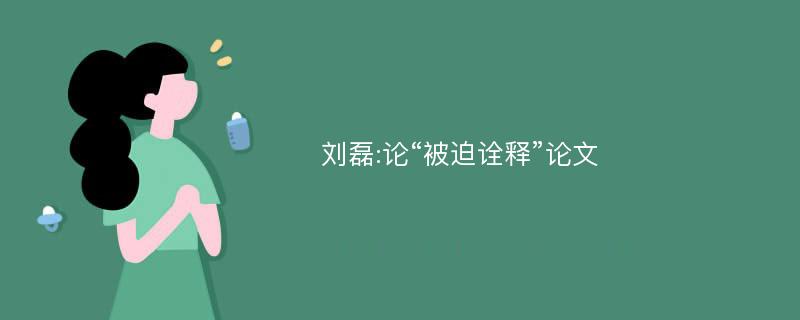
摘 要:方法论诠释学以追求文本意义与作者原意为主要特征,即诠释者要与作者一样准确甚至更加准确地理解文本。在具体诠释过程中,诠释者往往由于不能脱离自身的主观意识而对作者和文本造成误读,这一现象如从作者的角度来看,即造成诠释者对作者的“被迫诠释”关系,具体说来,又可分为“不解”“误解”“正解”“曲解”和“创解”等五个层次。“被迫诠释”本身并不存在“好”或“坏”的价值判断,但从诠释者应更好地理解作者和文本这一诠释目的出发,在文本诠释过程中,诠释者应采取“各释其释”的诠释路向。
关 键 词:诠释学;施莱尔马赫;被迫诠释
一、“被迫诠释”的提出及若干基本问题
德国著名诠释学家施莱尔马赫曾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文本的读者即文本诠释者应该如何更好地理解、解释文本,并在理解和解释的过程中尽量避免产生歧义。这一问题实际上是关于作者与诠释者之间相互诠释关系的问题,也是方法论诠释学当中有关诠释者对文本应采取何种理解方式的问题,同时还是关于诠释者在从事诠释实践的过程中如何实现真正的“好”的理解的重大问题。在施莱尔马赫看来,真正的“好”的理解是诠释者要通过对文本及作者本人生活经历的了解,在对文本诠释的过程中与作者实现某种意义上的“对话”,并且要“与讲话的作者一样好甚至比他还更好地理解他的话语”[1]61。任何文本皆具有鲜明的作者个性与时代特征,诠释者假如仅从字面上孤立地理解(或诠释)文本,那么该文本中所具有(或隐含)的作者个性和时代特征就会在有意无意间被诠释者所忽略,同时又有一些本不是文本原意的意义在有意无意间被诠释者解读出来,并“强加”给了文本的原作者。于是诠释者对于文本意义的诠释实际上在有意无意间放大了或缩小了作者的原意,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并不代表作者原有之意。
一般说来,因文本的作者已逝或其他客观原因不能对文本原意加以进一步说明时,诠释者对于文本的解释往往被大众当作作者原意来接受,而这时诠释者对文本的诠释又不是作者的原有之意,这样诠释者实际上在对文本的诠释过程中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作者和文本,这便是所谓“被迫诠释”。“被迫诠释”不仅仅是一个方法论诠释学的理论概念,同时也是每一个诠释者在具体诠释实践中必须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因为好的诠释首先应是对作者原意和文本自有之意的把握,而不应该把“自说自话”置于文本诠释的首位,所以对“被迫诠释”的研究,就必须对作者、文本及诠释者三者之诠释关系进行重新审视和分析,并在文本诠释的过程中为作者原意和文本原意寻找其自有应有之地。
“被迫诠释”的提出,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一部作品,它本身是否存在意义?这一意义又是否完全地通过作品展现于诠释者面前?(二)“被迫诠释”之所以被迫,在于诠释者将自己的某种观点融入对作品的解读,那么无论是overinterpretation(可译为“过度诠释”)或是underinterpretation(可译为“适当诠释”),皆是诠释者“强行”带给作品的意义,如果说它与作品的本意不甚相合甚至相左,那么评判诠释结果的标准又是什么?应该说,文本的意义,应指向的是事实,只要存在着一部作品,哪怕只是一个语词,那么它就一定正在描述某个事实,那么这个作品就一定是有意义的。如“吃饭”一词,它必然地指向吃饭这个事实,而不能把作者使用“吃饭”一词过分地理解为其他与吃饭这一事实无关的意义。既然某部作品指向或描述某个事实,那么它就一定存在其文本的意义,而且诠释者不能在诠释过程中忽视文本这种自有之意。文本这种指向事实的自有之意便是判断诠释者是否对作者和文本进行“被迫诠释”的基本标准。至于作品是否可以将意义通过诠释完全展示出来,则要依托于两个条件:(一)事实要可以用最简洁的语言来描述;(二)作者要可以完全驾驭他所使用的文字。同时,为了确保诠释者对作品达到完全的了解,诠释者还需要具备足够的理解力。
进而,造成“被迫诠释”的主要原因是:(一)作者创作作品的历史背景与心态不为诠释者所知,故而造成“被迫诠释”。作者,特别是作者的文本,必定存在于一定的时空条件之下,而且往往诠释者所处的时空条件与作者又是不同的,所以作者完成作品时的心态及语义是不能完全被文字所承载的。如陆九渊所说:“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2]432面对同样一部作品,由于作者和诠释者(这两个诠释主体)处于不同的时空背景之下,所以往往无法达到“同心之意”,不可避免地产生“不理解”。而从作者的角度来看,这即造成“被迫诠释”。(二)诠释者出于一定的诠释目的,故意对作者及其作品曲解或误解而造成“被迫诠释”。诠释者往往出于某种诠释目的而对作品有意曲解,以达到其个人的诠释目的,并体现所谓的现实意义或时代精神,这样的现实意义或时代精神往往并非作者的“原来之意”,或并非完全的“原来之意”。“我们可能太多或太少理解内容和细微差别”[1]36,所以出于某种需要和目的,我们就有一种“愿望”:作者可以站在自己的一面,为我们的行为或言语或诠释提供某种有力的证据,以证明我们的行为或言语或诠释的合法性。然而这样的“愿望”又往往超越作者或文本的原意,由诠释者“强行地”赋予作者或文本;或者,作者或文本所传达出的原始意义在诠释者那边没有完全得到表达,而是根据诠释者的需要和目的进行部分诠释甚至曲解。
艾柯在《诠释与过度诠释》一书中明确指出,现代文学研究中“诠释者的权利被强调得有点过了火”[3]28,诠释并非如某些人所说可以对本文(即文本)意义进行没有限制的肆意衍义,而必须回到作品本身,并受到作品本身意义的制约。这即他所谓的过度诠释理论。当然,这一理论力图解决的是关于作者、文本(或本文)、诠释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希望在“作者意图”与“诠释者意图”之间寻找第三种可能性——“本文的意图”[3]29-30。在他看来,作者意图难以被诠释者发现,而诠释者的意图则是要将文本按照诠释者自己的需要和目的进行诠释,所以最为可靠与可行的方法即把握本文的意图。在“被迫诠释”中,诠释者与作者的关系总是微妙的:一方面诠释者根据作者的语词及文本进行诠释,另一方面诠释者的诠释又是根据自身需要和目的对作者及文本进行的有选择的诠释,甚至为了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和需要,不惜牺牲作者的原意,这同样也是一种过度诠释。此二者的区别只是在于,过度诠释从诠释者的角度出发认为诠释者的过度诠释是对于作者本意的无限衍义,“被迫诠释”站在作者的角度认为诠释者的诠释对作者造成了某种“被迫”。严春友则认为,“解释本是一种‘居中’的行为,但中国哲学的解释却偏向了文本一方,把自己的理解和解释归于作者和文本”[4]。这里姑且不论解释是否如严氏所说是一种“‘居中’的行为”,当哲学家(或思想家)“把自己的理解和解释归于作者和文本”,无疑已经对作者和文本造成了某种不可避免的“强迫”,特别是对于重要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如果诠释者(这里特指那些有一定社会名望和地位的权威专家和学者)不从客观的历史事实出发,而是将自己的好恶、道德标准、价值观念杂糅进对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解释当中,那么这种理解和解释必不能称为一种好的(准确的)的诠释,也势必在客观上对诠释对象(这里特指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造成某种“被迫”。所以,所谓的强诠释只是说出“被迫诠释”的第二个特征而已。可见,过度诠释与强诠释依然按照一般意义上的方法论诠释学的思路,即从诠释者的角度出发,来看待作者与诠释者的诠释关系;而“被迫诠释”所关注的,正是此一诠释关系的“反向”,即从作者的角度出发,来看待诠释者与作者的诠释关系。
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备受关注,鲁迅在《〈绛洞花主〉小引》一文中说:“《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注]另据《鲁迅全集》编者的注释,清代张新之认为《红楼梦》“全书无非《易》道也”;清代梁恭辰认为 “《红楼梦》一书,诲淫之甚者也”;清代花月痴人说“《红楼梦》何书也?余答曰:情书也”;蔡元培认为《红楼梦》之意旨所在是“吊明之亡,揭清之失”;王梦阮、沈瓶庵则说《红楼梦》是写“清世祖与董小宛事”。详见鲁迅:《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180页。从“被迫诠释”的角度来说,无论是“经学家”“道学家”,还是“才子”“革命家”“流言家”,他们的理解都只能说是《红楼梦》作者思想的一个侧面,而且都是从“自己”的角度(或特定用意)出发来解读《红楼梦》,而《红楼梦》作者的本意似乎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当然,鲁迅先生所提到的这几种诠释结果,同样也是他们对《红楼梦》的“曲解”。
认定某种诠释是否为“被迫诠释”,主要需要考察这样三个问题:(一)诠释是否依托于作者和作品,并解释出与作者和作品本意不同的新意;(二)诠释者是否根据个人需要或社会需要对作品进行诠释;(三)诠释者对作者的“被迫诠释”是否在一定范围内得到认同,并对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造成影响。
lncRNA在肺癌、神经系统肿瘤、消化系统肿瘤及其他肿瘤中调节自噬可以增强化疗药物敏感性、减少耐药性;在心肌细胞及脑细胞缺血再灌注中,lncRNA通过调节自噬减少细胞凋亡;lncRNA的改变影响了神经细胞的自噬过程,找到了治疗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新方法;在细菌的感染中,lncRNA调节自噬的过程可能成为根除病原体、抵抗炎症反应的重要途径。另外,不仅局限在以上疾病中,还有研究提示,lncRNA通过调节细胞自噬影响治疗药物的敏感性,如胰岛素[31]。因此,在更多领域中进一步研究lncRNA调控自噬过程仍有许多挑战。
二、“被迫诠释”的五个层次
“曲解”是诠释者在理解作者和文本原意的基础上,出于某种现实需要或特定诠释目的,“故意强加”给作者和文本的解释。兹举数例。
受傅伟勋创造的诠释学的启发,“被迫诠释”如从理解程度上来划分,可依次分为“不解”“误解”“正解”“曲解”和“创解”等五个层次。“不解”,即诠释者因对作者及文本缺乏起码的认知而造成的不理解。“误解”,即因诠释者的认知水平所限而对作者和文本造成的错误理解。“正解”,即诠释者在深入了解作者生存背景和思想层次的基础上对作者和文本产生的正确理解。“曲解”,即诠释者在对作者与文本具有正解的前提下,出于自身思想当中的某些特殊诠释目的,“特意地”对作者和文本做出错误的解释。“创解”,即诠释者依据作者和文本原意并结合自身时代背景创造出新的解释。这五个层次虽是依次之序,但并非不能跨越,特别是在“正解”的基础上可以直接达到“创解”,不必通过“曲解”而达到“创解”。或者说,在“正解”的基础上,可产生两种诠释路向,一为“曲解”,一为“创解”,而在傅伟勋创造的诠释学当中,由“实谓”到“必谓”的这五个层次,是“不得随意越等跳级”[5]240的。其中“不解”“误解”“正解”的含义,相对于“曲解”和“创解”,比较好把握,因为存在着直接的、客观的标准(即作者和文本原意),可用以判断诠释者是否出现“不解”“误解”和“正解”的情况。而“曲解”和“创解”都是在诠释者对作者和文本产生“正解”的前提下进行的创造性诠释活动,所以评判诠释者所做的诠释结果为“曲解”或为“创解”,就需要对诠释者的诠释动机和诠释目标做深层次的考察:
傅伟勋所谓创造的诠释学认为,作为一般方法论的创造的诠释学可分为五个层次,即“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其中前三者均以原思想家为中心,讨论原思想家实际上说了什么、要表达什么和可能要说什么;后二者则以创造的诠释学者为中心,讨论他们应当为原思想家说出什么和为了解决原思想家未能完成的思想课题必须践行什么[5]240。从创造的诠释学的角度出发,“实谓”“意谓”“蕴谓”就是希望诠释者通过对文本的诠释实现对作者原意及文本自有之意的理解,“当谓”“必谓”则是希望诠释者通过对文本的诠释实现对作者原意和文本自有之意的再创造和发挥。如果说方法论诠释学关注到的是“一元”(诠释者),那么“被迫诠释”则关注到了另外“一元”(作者)。从诠释关系上来看,傅伟勋的创造的诠释学可称为诠释二元论,即同时注重作者原意和诠释者新解的诠释学思想。
一般而言,在诠释者阅读作品(文本)时,总会产生一种自我对作品(文本)的理解。一方面,这种理解多会被认为是作者在作品(文本)中所表达的思想;另一方面,当众多的诠释者对同一作品(文本)进行理解和解释时,又往往会产生多种理解和解释。所以在整个诠释过程中,几乎不可能真正实现如施莱尔马赫所说的“与讲话的作者一样好甚至比他还更好地理解他的话语”[1]61。作者生活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他的作品反映的是影响他的那段历史;对于诠释者来讲,假如对这段历史不甚了解,那么诠释者在诠释作者的文本时所遇到的困难将不再仅仅是来自文本的或语法的或语词的或片断的困难,而是由作者所处时代所带给诠释者的整个的困难。如果不能首先解决这个困难,那么诠释者对于作者及文本的定位势必将出现偏差,出现误解也就在所难免了。
再如现收藏于巴黎罗丹美术馆的著名雕塑作品《思想者》(原名《诗人》)。该作品本是罗丹为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的大门所做的雕刻,其原型为《神曲》的作者但丁。可是今天,《思想者》的意义已被放大,有人曾就《思想者》的复制品入驻上海发论说:“对于一个崇拜罗丹雕塑《思想者》的人来说,这无异于闻到了一股玫瑰的馨香,心里不知多么舒坦快意。然而,快意之余又不免为另一个问题而惆怅。什么问题?就是我们的‘思想者’太少的问题。”[8]从但丁对世界、对人的特定思考,到上述作者对中国社会、对中华民族复兴的广义思考,其意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那些不了解《思想者》本意的人们,或许会因论者的解释而曲解了《思想者》的本意。
五行学说最早出现在《尚书·洪范》中。《洪范》对于五行最基本的定义为:“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6]后经邹衍、董仲舒等人的加工改造,五行逐渐成为一种解释国家政权交替的理论基础。在秦汉之际,《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均以土为五行的中心,到了东汉,随着统治者认定自己承继火德,道教经典《太平经》利用五行学说为统治者的愿望做出了以火为“五行之君”的论证:“火能化四行自与五,故得称君象也。本(木)性和而专,得火而散成灰。金性坚刚,得火而柔。土性大柔,得火而坚成瓦。水性寒,得火而温。火自与五行同,又能变化无常,其性动而上行。阴顺于阳,臣顺于君,又得照察明彻,分别是非,故得称君,其余不能也。”[7]《太平经》的这一论断,虽然存在着对自然科学和社会实践的总结和把握,但是这种以火为“君”的思想,其政治思想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其目的就在于为统治者承继火德的说法做出理论上的证明,借此引起统治者的注意,并取得他们的信任和支持。实际上,以火为“君”的思想不仅是《尚书·洪范》当中所没有的,而且在五行家、汉代经学家的著作和思想中也是难以见到的,这既可以说是《太平经》的作者对于五行理论的新发展,也可谓五行理论在《太平经》这里遭遇“被迫诠释”。这一“被迫诠释”,不能仅看作如同五行家或董仲舒对于五行学说的那种诠释(尽管在他们那里也存在着对五行学说的“被迫诠释”),而应该看到《太平经》的作者更加直接与现实地将五行学说发展成了人间帝王承继上天意旨的有力证据。总之,从“被迫诠释”的角度来讲,《太平经》以火为“君”的理论过分强调了火的属性而忽略了其他四行的属性,基本脱离了《尚书·洪范》对五行的基本定义。
房子里很暖和,还响着均匀的熟睡的呼吸声。次卧里睡着妈,主卧里睡着弟弟和李倩倩,易非只想站在门口,站在主卧的门口,看看这间本该属于她的卧室,从这个窗口可以看到永南河大河奔涌,从这个窗口可以看到永南大桥横跨东西,可以看到永南大桥上灯光闪烁,车流如织,如一幅流动着的《清明上河图》,从这个窗口可以看到对面狮子山上的永南亭,可以看到永南亭上祥云永驻……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对联虽小,仍为表情达意!对学生晒出来的对联,除适时肯定,竖起拇指大力表扬外,更重要的是进行修改、点评,指引孩子前进。通常来说,孩子初写对联总会存在问题,可运用以下五法,一一规范。
“创解”是诠释者在对作者和文本原意的理解基础上,结合新的时代问题或理论问题,对于作者和文本原意所做出的创造性的诠释和发挥。兹举数例。
“被迫诠释”又有下列三个特征:(一)“被迫诠释”往往在形式上依托于作者和作品,但诠释的实际内容和结果却与作者和作品的本意大相径庭[注]这一部分将在下文详述,此处不再赘言。;(二)“被迫诠释”中,作者一般与诠释者处于不同的时空背景下,而诠释者却因其个人需要或社会需要,对作者和作品的本意进行更为广义的衍义;(三)作为比较高级的“被迫诠释”,诠释者一般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力,他对作者和作品的诠释会在一定范围内达成“共识”,得到同行的认可,以及对社会一般民众造成影响。
近5年,不少病人常常问我一个问题:我不抽烟、不喝酒、注意饮食,为什么也会得肝癌、胃癌或者肠癌?我家很干净,为什么孩子会得白血病?这使我越来越感觉到,假如我们生活在一个空气污浊、饮水有害、食物有毒、家具有味的环境里,再好的生活习惯也会得病。
宋明理学区别于先秦诸子学、汉唐经学、魏晋玄学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它将讲学的依据——经典——从六经转变为四书。四书地位的提高,特别是《大学》《中庸》地位的提高,直接为宋明理学家们的“为学次第”“道德性命”等问题找到了强有力的经典依据。此中,对于《大学》的整理又成了几代理学家共同努力的方向,北宋的程颢、程颐到南宋的朱熹直至明朝的王守仁,均有其各自不同的《大学》版本。按照朱熹的说法,“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9]1,所以他自觉地以《大学》作为从学者由训诂名物的“小学”转向探讨道德性命的“大人之学”之起点。朱熹的《大学》,其特点之一是将《大学》分为经和传两部分,他认为经的部分为孔子所作,传的部分是曾子及其门弟子所作,传是对经的解释和说明。在朱氏看来,《大学》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人们可以通过它看到古人的“为学次第”,学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9]3。其特点之二,在于朱熹按照以传释经的结构作《补格物致知传》,极大地丰富了《大学》的内容。在朱熹看来,《大学》中“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一句,“上别有阙文”,“而今亡矣”[9]6,所以他依据程子(当指程颐)之说补之,遂成《补格物致知传》。而在《礼记·大学》及二程那里,均不具备上述特点。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哲学家和训诂家不同,他所追求的不是经典的本义(意),而是极力使自己的理解臻于上乘,凭借这种理解来发挥自己的哲学思想”[10]109。但“为了使这种哲学思想站稳脚跟,必须找到解释学上的依据,能够证明自己的大破大立不仅符合时代的需要,也是对传统经典的最正确的理解”[10]110。朱熹所注《大学章句》从体例(以传解经的体例)上讲,较之《礼记·大学》更为系统,更加突出地体现出《大学》“三纲八目”的中心思想,并“依程子意”(实际上是朱熹自己之意)补写《格物致知传》。他对《礼记·大学》的作者和文本也造成了“被迫”,而且这样的“被迫”随着《四书章句集注》成为科举考试的官方标准,被后世儒家知识分子普遍接受。可见,处于“被迫诠释”关系下的作者和诠释者,会实现某种“和谐”:《大学》的作者在创作《大学》时,或许并没有在体例上采用以传解经的方式,但通过朱熹对《大学》的再创作,“更好地”使《大学》为朱熹的理学思想做出论证。
佛教传入中国的时代,正是神仙方术、谶纬之学盛行的时期。佛教初入东土时,人们曾用看待神仙的眼光来审视佛,认为佛“能小能大,能圆能方;……欲行则飞,坐则扬光”[11],这无异于把本意为“觉者”的佛“打扮”成了一个中国式得道神仙的模样。当时佛教学者解释佛教经典和基本概念,多采用“格义”[注]《高僧传·法雅传》:“时依门徒,并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与康法朗等,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详见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52页。的方式,其目的就是力图使中国人特别是社会上层阶级能够理解并接受佛教思想。僧人们借用“无”解释“空”、借用“言意之辩”解释“二谛义”,这一方面推进了佛教的初步中国化,进一步提升了魏晋玄学的理论程度和思想深度,另一方面正是在魏晋玄学的话语平台上才产生佛学“六家七宗”的繁荣。例如僧人们常在解释佛教经典时借用《老》《庄》的思想,据《高僧传·慧远传》记载,释慧远曾为人讲法,听者根本无法理解,于是慧远便借助于《庄子》的义理来解释佛经思想,终于使听者明白佛教的义理所在,起到了极好的诠释效果[12]212。这无疑是印度佛教思想在中国思想背景下所造成的“被迫”。又,东晋法显、觉贤曾译六卷《泥洹经》,倡“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除一阐提”[13];北凉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即《北本涅槃经》),倡“一阐提等悉有佛性。何以故?一阐提等定当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14]。僧人竺道生在未见《北本涅槃经》的情况下,仅据所见六卷《泥洹经》,经过自己的研究和思考,断言“阿(一)阐提人皆得成佛”[12]256。这说明竺道生对于佛理的了解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到了隋唐以后,佛教中国化终于“结出了果实”,形成了以天台宗、华严宗、禅宗为代表的具有中国特色并区别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思想,进而为宋明理学的产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佛教不断被中国化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中国人不断理解、接受外来佛教思想的过程,而对于佛教自身而言,中国人根据自己的理解对佛教思想进行解释,从客观上对印度佛教思想形成了“被迫诠释”的情况。当然,也正是在这一“被迫”中,逐渐形成了中国佛学思想。可见,现实的需要与目的是诠释者进行“被迫诠释”的最初动因,而作者原意经过“被迫诠释”,以一种更利于诠释者理解和需要的形态出现,在客观上也能够使作者原意得到进一步发展与提升。
三、“各释其释”:避免“被迫诠释”的有效方法
在诠释者对作者的“被迫诠释”过程中,存在这样三种情况:(一)诠释者根据自己的需要过多地解释了作者或文本的原意,造成对作者的“被迫”。(二)诠释者根据自己的需要过少地解释了作者或文本的原意,造成对作者的“被迫”。(三)诠释者限于认知水平和知识背景而造成“被迫”,即诠释者出于对作者和作品的认知水平的限制,也会对作者和作品造成“被迫诠释”。在具体的诠释实践中,结合施莱尔马赫要诠释者“与讲话的作者一样好甚至比他还更好地理解他的话语”[1]61的这一论断,方法论诠释学应该更加强调的是诠释者对于作者的把握(或者称之为由诠释者到作者的趋向性),这是站在诠释者的角度来看待作者及作者的原始意识。出现“被迫诠释”时,我们又应采取何种方式方法来对待它呢?我们知道,“被迫诠释”的出现是诠释者根据自身的喜好和需要对作者与文本进行加工,并“强制性地”赋予作者与文本的,所以要避免“被迫诠释”,就需要诠释者反求诸己,改善进而转变旧的诠释思维模式。这一新的诠释模式,就是“各释其释”。
社区大学教师来源多元,通常有各领域实务工作者、专业技术人员、社区工作者、传统工艺匠人、一般大学退休教师等。各类型的教师所需的专业成长也有所差异,关注的方向也有所不同,如:专业领域如何前进?如何与学员互动?新进教师如何让课程开得好?如何走入社区?如何与社区合作?社区大学教师专业发展是什么?如何透过参与的专业发展内容,补足教师的不足,是社区大学开设培训课程的一大考验。近年来,许多社区大学教师也从原来的兼任模式,逐渐转型为专职的社区大学教师,虽然在不同社区大学教学,但工作场所全为社区大学。因而社区大学教师的专业发展问题是当前社区教育中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
所谓“各释其释”,就是诠释者从诠释对象(包括作者和文本)的角度出发来研究诠释对象,使诠释结果成为诠释者对诠释对象的“合适”解释。例如,中国历代学者对孔子的定位就有着不同的说法:孔子自己以周公礼乐制度的继承者自居;其弟子和再传弟子认为他是一位老师(“夫子”)、一位与时代相适应的“圣人”(“时圣”);而在楚狂看来,孔子则是一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到了汉代,孔子又被看成为刘汉政权确立统治地位的圣人,是没有即位的王(“素王”)。魏晋时期,孔子被那些清谈人士视为名教的教主。到了宋明时期,孔子又成为所有儒家知识分子的道德楷模和精神支柱。时至晚清,康有为又认为孔子不仅仅是儒教的教主,更是一种政治改革家。如此林林总总,孔子却还是他自己。孔子已逝,层层“光环”只是历代学者赋予(“强制性地”赋予)孔子的,而假使孔子复生,他又会如何看待这层层“光环”呢?由此可见,研究孔子时,应当采取孔子的思维方式、用孔子的语言,而不能采用朱熹、王阳明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更不能使用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来研究;同样,研究苏格拉底的学者们,更应当采取苏格拉底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而不是用康德或黑格尔的思维方式,更不可以使用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来研究,这样才能做到“各释其释”,才是“事称其能,各当其分”[15]。
纵观全市土地流转工作的实践,总体上是健康的,但在少数地方也存在着因政策宣传不到位、部分农户恋土情结较重、农民对土地流转价格预期过高等而导致土地流转不畅,以及违背农民意愿、采取行政手段搞土地流转、“非粮化”、“非农化”倾向严重等方面的突出问题。有些问题从表面上看并不突出,但其实是矛盾被暂时掩盖,尚未充分暴露;有些问题虽然是个别现象,或者目前在其他地区比较突出,但也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和重视。为此,针对以上问题,我们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引起关注。
在中国历史上,最善于运用“各释其释”这种诠释方式的思想家,非陆九渊莫属。在中国历代文人当中,陆九渊具备一般哲学家所少有的大气魄,他幼年时即体认到“宇宙即是我心,我心即是宇宙”,成年以后又倡“心即理”“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道外无事,事外无道”等论,影响甚大。虽然陆九渊一生主张“六经注我”,其实他又非常强调阅读经典的重要性[注]如他说:“某读书只看古注,圣人之言自明白。”“后生看《经》书,须着看《注》《疏》及先儒解释,不然,执己见议论,恐入自是之域,便轻视古人。”详见陆九渊:《陆九渊集》卷35《语录下》,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41、431页。,即一方面要在阅读经典、诠释经典的过程中突出读书者(诠释者)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又非常强调古注[注]陆氏所述古注,是相对于其所谓新注(宋人经注)而言。具体指汉代学者的经注。的重要性,其目的就是准确地理解经典原意。而陆九渊讲“六经注我”的立意处,正是“我”已经“非分解式地”将所有“义”全部设置于六经之中[16],那么“我”与六经的一体便成就了“我”对六经的理解和生命价值追求,同样六经与“我”的一体也成就了六经对“我”的自我意义的体现。陆九渊注解《论语》“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一章时,直言“然则以其道而得焉,君子处之矣,曷尝断弃之哉”[2]157。这就可以看出,陆九渊在理解经典时不仅仅看重文字本身的义理,同时还根据文字的义理,在不违反原文义理的基础上对文字进行义理上的发挥和解释。甚至当我们把孔子的原话和陆九渊的解释放在一起阅读时,也丝毫感觉不出有什么突兀的地方:“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然则以其道而得焉,君子处之矣,曷尝断弃之哉?”这就是陆九渊在解释经典时的高明之处,他能够使解释与原文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所以读起来常常让人更容易理解原文,而且时有所省。由此可见,要在具体的诠释过程中实现“各释其释”(一如以孔子的方式研究孔子,一如以苏格拉底的方式研究苏格拉底),就要求诠释者必须放弃所有个人主观臆想,本着研究和探索的目的来研究、探索诠释对象,方能使“我”与诠释对象融合为一,进而对诠释对象的本意做出准确的理解,从而避免“被迫诠释”的出现。
余敦康认为:“所谓解释,也就是理解,而理解是存在着层次上的差别的。有人停留于字面上的理解;有人能发掘出隐藏在字里行间的深层的含义;有人更能结合时代的需要,引申发挥,推出新解;有人不仅在某些个别的论点上推出新解,而且融会贯通,创建出一种既依据经典而又不同于经典的崭新的哲学体系。”[10]109我们今天研究中国诠释学的目的,“不在于清理或发展出一套与西方阐释学不同的阐释理论,而在于从阐释学角度把握和思考中国学术本身所面临和亟待解决的根本问题”[17]。中国学者真正需要做的,是在学习和理解诠释学的过程中,将诠释学应用于中国本土学术研究中,帮助我们来解释中国学术本身所面临并需要解决的问题。“被迫诠释”一说正是在此意义上提出的,而且它关注具体诠释实践活动中作者、文本及诠释者三者之间的诠释关系。当诠释者面对作者及文本时,如果没有放弃自我主观的意识及客观的现实需要,进而由此对作者和文本进行诠释,那么相对于作者和文本的“被迫诠释”便产生了。当然在某些特定意义上,由于语词的局限,文本并不能完全展现(或承载)作者的意图,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作者的意图可以大致地或较精确地通过他对语词的使用表达出来。作为诠释者,如果希望自己能够更好地理解作者和文本,就会在基本把握作者语词意义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准确理解作者和文本的原意,以“各释其释”的诠释方法,避免“被迫诠释”的出现。“被迫诠释”本身也并不具备善恶好坏的价值标准,至于出现“好”的诠释或“不好”的诠释,还是要从诠释者与作者和文本的交流程度来考察。因为在整个的诠释过程中,只有诠释主体的自主选择才是造成或避免“被迫诠释”的关键因素。
参考文献:
[1]洪汉鼎.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2]陆九渊.陆九渊集[M].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
[3]艾柯.诠释与过度诠释[M].柯里尼,编.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4]严春友.中国哲学的强解释学特征[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103.
[5]傅伟勋.创造的诠释学及其应用[J].时代与思潮,1990(2).
[6]孔安国,孔颖达.尚书正义[M].廖名春,陈明,整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01.
[7]王明.太平经合校[M].北京:中华书局,1960:20.
[8]侯百索.引进雕塑《思想者》所引发的思考[M]//党建在线.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191.
[9]朱熹.大学章句[M]//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10]余敦康.魏晋玄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1]僧佑.牟子理惑论[M]//弘明集校笺.李小荣,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14.
[12]慧皎.高僧传[M].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
[13]大般泥洹经[M]//乾隆大藏经:第31册.法显,觉贤,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477.
[14]大般涅槃经[M]//乾隆大藏经:第29册.昙无谶,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461.
[15]郭象,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M].曹础基,黄兰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1.
[16]刘磊.“孟子之后,至是而始一明”——牟宗三对陆九渊的解读[J].平顶山学院学报,2008(4):77.
[17]李清良.自序[M]//熊十力陈寅恪钱锺书阐释思想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1.
中图分类号:B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670(2019)03-0090-07
收稿日期:2018-04-26
作者简介:刘磊(1983— ),男,河南省郑州市人,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思想与绘画、古代文本与图像诠释研究。
(责任编辑:李智萍)
标签:作者论文; 文本论文; 孔子论文; 自己的论文; 原意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哲学理论论文; 哲学流派及其研究论文; 其他哲学流派论文; 《平顶山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论文; 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论文;
